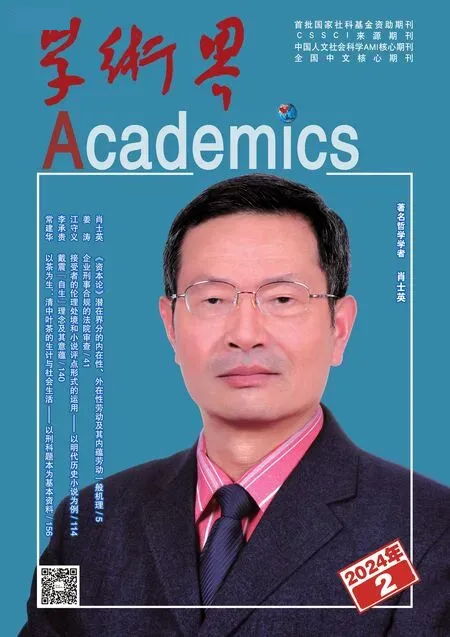《保训》写作年代考〔*〕
陈桐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40)
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以舜、上甲微“求中”事迹勉励太子姬发。〔1〕如果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那绝对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因为它坐实了所谓上古圣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将孔子创立的“中庸”思想提前了一千多年。舜、微时代真的已经出现“执中”思想了吗?“中”真的是出于神谕吗?《保训》所说的“求中”就是《论语》《中庸》的“执中”“用中”吗?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搞清楚《保训》的写作年代。本文拟以文献为依据,梳理先秦时期“执中”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而考证“求中”与“执中”“用中”的联系和区别,最后来看《保训》究竟写于什么时代。
一、《保训》不会作于周文王时代
舜、上甲微、周文王分别生活在虞、夏、商时期,此时会不会出现具有思想方法意义的“执中”思想呢?虞、夏时代文献不足,殷商传世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和《尚书·商书》《诗经·商颂》,这些文献里虽然不乏“中”字,但这些“中”远远没有达到思想方法的水平。
现存的五篇《尚书·商书》中两次出现“中”字。一是《盘庚中》载盘庚告其臣民“各设中于乃心”。孔安国传:“各设中正于汝心。”孔颖达疏:“各设中正于汝心,勿为残害之事。”〔8〕刘起釪将此句译为“要把你们的心合于中正”。〔9〕盘庚要求群臣处心中正,不要对迁都之事起歪心眼。另一条材料出于《高宗肜日》:“民中绝命。”孔颖达疏:“民自不修义,使中道绝其性命。”〔10〕这个“中”意为“中途”,“民中绝命”是说“活到一半就死了”。《高宗肜日》这个“中”字与本文讨论的“执中”主题关系不大。
《诗经·商颂》里没有“中”字,但《长发》有几句诗包含了“执中”思想:“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孔颖达疏曰:“汤之性行,不争竞,不急躁,不大刚猛,不大柔弱,举事具得其中,敷陈政教则优优而和美,以此之故,百众之禄于是聚而归之。”〔11〕这四句诗是说,商汤品性中正,既不刚强也不柔缓,他以这种中正品格施政,其政宽裕和美,各种福禄聚于一身。这几句诗表明,中正是殷商人赞美的品性。
文献表明,殷商处于“执中”思想的早期萌发阶段,“中”的意义从“氏族社会之徽帜”,逐步引申为中央、中心,进而引申为中正。殷商人从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经验认识:办事以适中为准,性格以中正为好。需要强调的是,殷商人所说的“中”,大都是就事论事,远没有抽象为一般规律。《保训》载周文王在临终之际以一般规律“求中”嘱咐姬发,并且说早在虞舜、上甲微时代就有“求中”思想,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由此推测,《保训》不可能作于周文王生前。
二、《保训》不会作于西周春秋时期
西周春秋时期,“执中”思想沿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继续发展。
暗的线索是周礼的制定以及后人对它的履行情况。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周公做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事——制礼作乐。据文献记载,周公根据政治宗法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级,确定士以上的各个统治阶层成员所承担的政治伦理责任和所享受的权利,规定他们在祭祀、出师、朝聘、丧葬、宴射、相见、饮食、起居、婚姻、加冠、观乐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使整个上流社会用一种与自己政治宗法身份地位相称的适中方式来表达思想观点和情感态度,构建一个既严格区分上下尊卑又彼此相敬相亲的井然有序的社会。周公当年究竟是遵循怎样的指导思想去制礼作乐,由于缺少文献记载,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他通过周礼来规范上流社会的言行,在客观上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西周春秋上流社会就是根据周礼来评价王侯卿士大夫言行究竟是“中”还是“不中”。在周公制礼作乐以前,由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因此对何者为“中”,往往会因人而异。以商王盘庚迁殷为例,盘庚认为迁殷为“中”,但朝中很多大臣贵戚却认定迁都“不中”,最后是由商王意志来决定迁都。这种缺少“中”客观依据的情形,在周公制礼之后彻底改变了,因为周礼就是“中”的客观标准:符合周礼的就是“中”,违反周礼的就是“不中”。《左传》《国语》往往以“礼也”“非礼”来评价历史人物言行,换一个词语说,“礼也”就是“中”,“非礼”就是“不中”。从字面上看,周礼似乎与“执中”不沾边,为什么我们将周礼制作及其后世履行情况视为“执中”思想一条发展线索呢?这个谜底是由后来孔子揭开的: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从周礼中总结出来的。
明的线索是指西周春秋上流社会所发表的关于“执中”的思想言论。这些思想言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语句里出现“中”字。如《周书·酒诰》载周公告诫康叔“作稽中德”,戴钧衡将此句释为“使合中正之德”。〔12〕《周书·召诰》载周公语召公:“自服于土中。”“服”意为“接受天命”,“土中”是指“土地之中央”,指在地理上居于天下中心的洛阳。“自服于土中”意为“周成王在洛阳接受天命”。同篇又称“其自时中乂”,“自时”犹言“自是”,意为“从这里”,“乂”意为“治理”,“其自时中乂”意为“从洛阳这里治理天下”。〔13〕又如《周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日中”指的是“中午时分”,“自朝至于日中昃”是说从早上到中午再到日头偏西。《周书·立政》载周公称“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伪孔安国传:“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罚,不轻不重。”〔14〕《周书·吕刑》是法律文献,篇中十次出现“中”字:“罔中于信。”“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罔不中听狱之两辞。”“非天不中。”“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咸中有庆。”刘起釪指出:“就中字的通常意义立论,主要谓其中正、正道,意为在断狱中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不枉不纵,不僭不滥,赏罚平允,无有过忒,无过与不及,等等。”〔15〕第二类是采用格言化的句式,虽然语句中没有“中”字,但却表达了“执中”思想。如《周书·洪范》载箕子曰:“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6〕箕子认为,只有王道才是中道,其他一切偏颇、私好、结党、作恶等背离中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虞书·尧典》载帝舜谓夔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7〕帝舜要求乐官夔用音乐培养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宏而严肃、刚强而不苛虐、简略而不傲慢的中正品性。与帝舜语意相近的还有《尚书·皋陶谟》,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18〕皋陶认为,一个君王应该培养宽仁而严肃、柔和而自立、笃厚而谦恭、有为而敬慎、和顺而果毅、正直而温良、简率而廉正、刚劲而踏实、强直而合义等九种中正品质。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人士用“执中”思想评价音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中和之声,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19〕之语来评价《诗经》颂乐。庞朴将先秦这些表达“执中”思想的格言化语句归纳为四种形式:一是A而B,以B济A的不足;二是A而不A,以不A来补充A;三是不A不B;四是亦A亦B。〔20〕第三类言论,语句既不出现“中”字,也不采用格言句式,但却同样表达了“执中”思想。如《国语·周语下》载单穆公语曰:“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21〕民患轻则铸重币,民患重则铸轻币,钱币政策要在适中,子母相权,不轻不重。
西周春秋时期,“执中”思想在继承殷商基础上有两方面发展:一是周礼从制度上为“执中”思想提供了依据;二是政治文化界人士初步注意到,在品性、音乐、货币政策、刑罚处置等方面存在着宽与栗、乐与荒、轻与重等“两端”现象,他们主张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也就是执两用中。这些思想为孔子“叩其两端”的理论积累了思想资料。尽管如此,西周春秋时期“执中”思想发展仍然停留在经验层次。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自然不可能产生以“求中”为最高价值的《保训》。
三、孔子对“执中”思想的特殊贡献
为“执中”思想理论作出划时代贡献的是春秋末年的孔子。孔子使发轫于殷商甲骨文的“执中”由经验智慧上升到哲学层次,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其理论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孔子提出“礼所以制中”,用一个“中”字来概括周礼的精神。孔子这一认识来自于他毕生从事的克己复礼活动,是他捍卫周礼事业的重大思想成果。孔子对春秋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形痛心疾首,他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礼制,认为周礼在文采方面明显超越了夏礼和商礼,从而作出了“从周”的理性选择,为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2〕的周礼秩序而奔走呼号了一生。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23〕的时代僭礼大潮之下,孔子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周礼要求人们言行适中的精髓,由此而对周礼精神作出了精辟简要的理论概括。《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曰:“夫礼,所以制中也。”〔24〕前人对孔子这句画龙点睛的话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轻易地读过去了,甚至当年编辑《论语》的人也没有把孔子这句名言收录进去,实际上它的意义非同小可。从西周到春秋几百年间,上流社会人士不知道说了多少礼,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精确地归纳出周礼精神。直到春秋末年,周礼精神才被思想巨人孔子用一个“中”字深刻地概括出来,这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经过孔子的概括,由甲骨文发端的“中”的思想智慧,其间经由周公制礼及其后世对周礼的践履,再到孔子以“中”说周礼,至此,先秦时期一条完整的“执中”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第二,孔子提出“中庸”心性道德范畴。如果孔子对周礼的概括仅仅止步于“礼所以制中”,那么他对周礼的论述尚不能脱离具体礼仪。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揭示周礼制中精神之后,又对周礼精神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抽象提炼。《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5〕为什么说“中庸”是对周礼的进一步提炼呢?这就要看什么是“中庸”。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26〕据此,“中庸”的“中”,就是“礼所以制中”的“中”,就是孔子概括的周礼精神;“庸”是指平常生活(也有人把“庸”解释为“用”);“中庸”就是要将周礼的制中精神贯彻到人们平常生活之中。两千多年来,研究“中庸”的论文汗牛充栋,但是还没有人指出“中庸”哲学是孔子从周礼精神提炼而来的。将这一点揭示出来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发现。在孔子以前,人们用“中”来描述空间、时间、性格、刑罚、金融、音乐等各个方面的状态,现在孔子使“中庸”超越具体事物,抽象为一种最高水平的美德,这就使“中庸”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一言一行,人们怎样才能做到适中,避免过与不及呢?孔子给人们指明了一条路径,这就是培养“中庸”品德,一旦具备了“中庸”品德,就会无时、无处、无往而不“中”了。这样,“中庸”相对于孔子以前人们所说的“中”,就脱离了就事论事的经验认识,而具有了一般规律的意义。自从孔子从周礼中提炼出“中庸”哲学以后,“中庸”就作为一种最高的思想价值,积淀到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方法论。
第三,孔子还提出了实现“中庸”的“叩其两端”“执两用中”的具体实施方法。从培养“中庸”这种最高的美德,到运用这种美德来指导具体社会实践,这其间还有一段距离。孔子感叹人们长久缺少“中庸”美德,一再强调“中庸不可能”,就是因为智者和愚者都不懂得掌握“中庸”的方法。有鉴于此,孔子为人们实践“中庸”美德提出了具体修练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对此,下文还要详细讨论。
孔子之后,其嫡孙子思作《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中庸”学说。《中庸》的理论内涵非常丰富,这里只能讨论几个要点。第一,“中庸”源于天命所赋人性,说明“中庸”不仅是人性也是天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7〕子思所说的“性”是指以“中庸”为主要内容的心性,他将“中庸”心性追溯到终极源头——天之所命,将人性与天性打通,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提升了“中庸”品质修养的价值,使“中庸”成为一种天人共有的伦理品质。第二,“天性之谓性”说明“中庸”这种最高美德不是外力所加,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固有天性,它就内涵在人的心性之中。因此“中庸”修养不必外求,只要将自己本来具备的“中庸”天性加以培养就行。〔28〕第三,“天命之谓性”还说明,由于“中庸”心性是上天赋予,因此它是人力所无法改易的。从生命胚胎形成的那一刻起,“中庸”心性就伴随着一个人生命的始终。第四,子思指出,中庸之道“费而隐”,“费”是“用之广”,“隐”是“体之微”(朱熹语),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事不在,广泛地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中庸之道须臾不可离开。第五,子思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之下,都能在“中庸”品质修养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29〕“中庸”修养不是富贵者的专利,那些处于贫贱中的人,那些生于夷狄之邦的人,甚至那些困于患难的人,都有进行“中庸”修养的资格和权利。第六,子思借孔子之口,指出“中庸”虽然极普遍,但它又极难做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小人反中庸”、小人“无忌惮”、“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的因素,也因为人们饮食而不知味,不知道自己是在践行中庸之道,或者行道而不能尽道,这些原因导致“中庸不可能也”。〔30〕第七,子思以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圣人为例,并借助鲁哀公向孔子问政,阐述了“中庸”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说明政治成就的大小与心性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第八,《中庸》用了十三章篇幅重点阐述了“诚”的思想。什么是“诚”?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31〕据此,“诚”是一种不受后天污染的澄澈透明的人性原初状态。要想培养“中庸”品质,就要拂去遮蔽在人性之上种种后天的尘埃污垢,让人性清明澄澈的原初状态呈现出来,“中庸”品质就完满地保留在这种人性原初状态之中,做到了“诚”,“中庸”也就在其中了。《中庸》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宣告“中庸”哲学至此完全成熟。《中庸》也是中国礼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巨著,它标志着先秦礼学从行为礼向心中礼的转变——使习礼由进退俯仰、左右周旋的动作行为转变为一种内在的心性道德修炼功夫。
上文说《保训》不可能作于虞、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是因为“执中”思想在这一历史时期尚处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层次,《保训》写作的思想条件还不具备。在孔子以“中”概括周礼并提出“中庸”的哲学思想之后,特别是在子思作《中庸》之后,《保训》的写作条件完全具备了。《保训》会不会是孔子、子思之后儒家后学的作品呢?
四、《保训》不会作于先秦乃至中国古代
战国秦汉之际,儒家后学在传授礼学过程中,往往通过讲述一些历史上的礼学故事,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礼义,如《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等,都是这一类的文章。那么,《保训》的性质是不是像《文王世子》《武王践阼》一样,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讲述的礼学故事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奥秘在《保训》关键词“求中”之中。检阅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就可以发现,在表达“中”的思想时,先秦儒家用“执中”或“用中”,而从来不用“求中”。例如,《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32〕又如,《礼记·中庸》载孔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33〕为什么《论语》《中庸》用“执中”“用中”而不用“求中”呢?是不是在孔子时代,人们很少使用“求”字呢?不是的。“求”在孔子时代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字。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中“求”字出现37次。《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同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34〕等等,都是例证。这说明《论语》《中庸》使用“执中”“用中”而不用“求中”,不是因为孔子时代不用“求”字,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执中”“用中”与“求中”虽然都包含有“中”的思想,但彼此存在着三大区别:
第一,《论语》《中庸》所说的“执中”“用中”蕴含了一个“叩其两端”的辩证思维方法,而《保训》“求中”来自于神赐,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看不出其中包含有什么思维方法。冯友兰指出,中庸之道“有不少的辩证法因素”。〔35〕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分成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两个对立面。孔子所说的“两端”就包含有这样的思想。《论语·子罕》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36〕“叩其两端”与《中庸》所载帝舜“执其两端”意思完全相同。关于“两端”的涵义,邢昺释为“事之终始两端”,〔37〕刘宝楠解为“所疑之两端”,〔38〕杨伯峻译为“问题的首尾两头”。〔39〕“叩其两端”就是在遇到问题时,要抓住这个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先秦儒家文献中有不少通过“叩其两端”而达到“执中”的例子。《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40〕“过”与“不及”是事物的“两端”,因其失之片面而不可取。《论语·先进》又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41〕子路与冉有问了同一个问题,孔子却给予不同的回答。这是因为子路胆子太大而行为超过了礼的标准,而冉求性格退让而达不到礼的标准。子路和冉有分别处于“兼人”和“退”的两端,孔子通过一“退”一“进”,最终使子路和冉有都达到礼的适中水平,这就是“叩其两端”思想方法的典型体现。《礼记·中庸》载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42〕“知者过之,愚者不及”是为事物的“两端”,这是导致大道难行的根本原因。《礼记·杂记下》载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43〕“张”和“弛”是治理国家的两端,一味的“张”和一味的“弛”,都不符合适中的礼义,正确的做法是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做到有张有弛,张弛结合。《礼记·坊记》载孔子曰:“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44〕“富骄”与“贫约”是社会现象的两端,圣人通过制礼,将富贵者的骄气压下去,把穷人的志气提上来,这样就从社会心理层面上减少了祸乱的根源。《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孔子对子产施政的评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45〕“宽”与“猛”是为国家治理的两端,“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通过“叩其两端”而“执中”“用中”。孔子之后,儒家后学继续阐述“叩其两端”的“执中”思想。《礼记·丧服四制》说:“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46〕贤者会长期履行丧礼,不肖者则会尽量缩短丧礼,圣人通过考察贤者和不肖者对待丧亲情感的两端,而制定了三年之丧这一符合中庸之道的丧礼,以此避免贤者之“过”与不肖者的“不及”。《礼记·檀弓上》载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47〕制礼者确立一个适中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人要弯腰俯就一下,而够不着标准的人则要踮起脚来。可见“执两用中”是通过“叩其两端”即考察事物的两个对立面而实现的,“求中”则没有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
第二,“执中”“用中”包含了“时中”思想,而“求中”之“中”只是一个先验的神灵启示。“时中”的概念见于《中庸》所载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什么是“时中”?朱熹解释为“随时以处中”。〔48〕冯友兰进一步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个‘中’并不是两端间的一个等距离的地方……‘中’是随着空间、时间上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死的,所以它又和‘时’分不开。”〔49〕为什么“执中”不是简单地指两端间的一个等距离的地方而是“时中”?孟子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孟子·尽心上》载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50〕孟子评价了杨朱、墨子、子莫三位诸子学者,认为杨朱为我,墨子兼爱,两人各自“执一”,只有子莫能够做到“执中”,这近于“叩其两端而竭”的圣人之道。不过孟子强调指出,“执中”应该与“权”相结合。所谓“权”,就是指“中”随着空间、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执中而不知权变,但若执一介之人,不知时变者也。然而所以恶疾其执一者,是为其有以贼害其道也,是若知举一道而废其百道也。”〔51〕“执中”而不能“权”的人,他是把“中”看作是固定的、不变的一个点,这样的“执中”其实与杨子、墨子的“执一”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举一而废百”。既“执中”而又能做到“权”,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时中”。《保训》所说的先验的神秘的“求中”,近于孟子所说的“执一”,它与孔子所说的“执中”“用中”貌似而实异。
第三,“执中”“用中”是中华哲人千百年来辛勤求索的思想结晶,它发端于殷商甲骨文,其后经过西周春秋思想文化人士的继承发展,最后由孔子总结提炼而成,它发展的每一步踏踏实实、清清楚楚,都有文献可寻。“求中”则来自于神灵的恩赐:“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伏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52〕这就是说,上甲微是向河神求“中”,完成复仇大业后,微又把“中”归还给河伯。这样一个玄而又玄的神话,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保训》的“求中”与孔子“执中”的思想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从“执中”“用中”与“求中”三点区别来看,“求中”显然不能等同于“执中”或“用中”。孔子后学和中国封建后世的儒士经生熟读经典,他们谙熟孔夫子“执中”“用中”的特定思想文化语境和“叩其两端”的思想方法,在表达“中”的思想时,都采用“执中”“用中”而不用“求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东晋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其中有一篇《大禹谟》,文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几句。〔53〕《大禹谟》作者虽然是在作伪,但他却用“执中”而不用“求中”,这说明到魏晋时代,儒士经生仍然恪守“叩其两端”的“执中”本义。宋代大儒朱熹作《中庸章句》,其序言仍然使用“执中”,在注文中用“用中”“处中”“取中”,〔54〕而不用“求中”。进入现代以后,儒家经典失去了统治地位,“叩其两端”的历史文化语境不复存在,因此人们以“求中”取代“执中”或“用中”。以此推测,“求中”是现代人的用语,《保训》不可能作于中国古代,应是现代人的仿古之作。〔55〕
注释:
〔1〕〔5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2〕唐兰:《殷墟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3、54页。
〔3〕〔5〕〔6〕〔7〕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33、1487、1734、379页。
〔4〕〔周〕吕不韦撰、〔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11页。
〔8〕〔10〕〔14〕〔53〕〔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1、257、479、93页。
〔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16、917页。
〔11〕〔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7页。
〔12〕〔13〕〔1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98、1440、1163页。
〔1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8、2109页。
〔17〕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2页。古今对《尧典》写作年代争议甚多,顾颉刚认为《尧典》初写于春秋,写定在战国。
〔1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00页。刘起釪认为《皋陶谟》写定于春秋后期。
〔19〕〔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3页。
〔20〕庞朴:《“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1〕吴绍烈等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22〕〔23〕〔25〕〔32〕〔34〕〔36〕〔37〕〔40〕〔4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3,250,82,265,9、11、90,114、115,115,148,153页。
〔24〕〔42〕〔43〕〔44〕〔46〕〔4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3、1424、1223、1400、1676、200页。
〔26〕〔27〕〔29〕〔30〕〔31〕〔33〕〔48〕〔5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17,24,19、20、21,31,20,19,14、19、20页。
〔28〕后来孟子说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禅宗说佛性在人心中,都应该是受到了《中庸》的启示。
〔35〕〔4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138页。
〔38〕〔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79页。
〔39〕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21页。
〔50〕〔51〕〔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6、367,367页。
〔55〕《保训》留下了仿古痕迹:它模仿《尚书·顾命》周成王临终遗嘱的形式;它模仿《多士》《无逸》《多方》等篇历数夏商周三代事迹,排列帝舜、上甲微求中事迹而成篇;它甚至模仿《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之说,编造了上甲微“假中”“归中”于河的故事。《保训》在文字上也有过度模仿之处,如《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有“钦哉”,《吕刑》有“敬之哉”,《保训》则同时在一篇中用有“钦哉”“祗之哉”“敬哉”。“钦”,《尔雅·释诂》:“敬也。”“祗”,《尔雅·释诂》:“敬也。”可见“钦”“祗”“敬”本是同义词,何必重复使用?又如《尚书》在“钦哉”之后,不再使用他语,《保训》则有“钦哉,勿轻”“敬哉,毋轻”;似乎是反复叮咛,但一篇之中用“钦”“祗”“敬”,在“钦哉”等语之后又加上“勿轻”,却不合《尚书》用语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