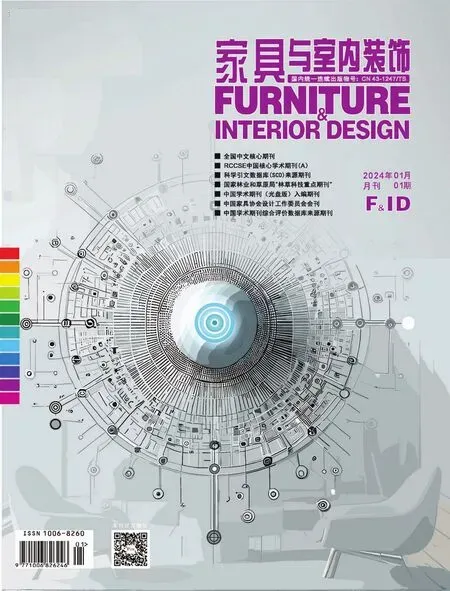八十年代家居装饰设计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
——以《家具与生活》杂志为对象的考察
■关晓辉,容泳珊,宋逸菲
(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广东广州 510642)
自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民众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在随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各大城市涌现一批提供生活服务和推介产品的生活类杂志,包括《文化与生活》《家用电器》《现代生活用品》《家具与生活》等,从设计史研究角度看,这些刊物构成我们考察当时的民众生活和民生设计的重要材料。“民生设计”通常是指与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谋生方式息息相关的的设计行为[1],本文讨论的家居装饰设计即是民生设计的重要部分。戴维斯(D.S.Davis)曾指出:“八十年代的中国孕育着民众对新生活、新环境和新产品的热切渴求。”[2]具体到家居装饰设计领域,“新”意味着民众的家庭装饰消费大幅上升,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余还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事实上,“生活方式”对家具风格流变[3]和对某类家具设计[4]的影响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本文选择区别上述研究的路径,以八十年代《家具与生活》杂志为切入点,从设计媒介的视角考察家居装饰设计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的联系,并进而发掘这种联系作为设计文化史的学术意义。
1 《家具与生活》杂志与八十年代民生状况
可以说,《家具与生活》杂志是八十年代民生状况的产物,其早期探索的为“家”服务的路线成为杂志办刊的最大特色。

■图1 床与折叠书桌组合家具效果图(原载于《家具与生活》杂志1986年第2期)
在1949年至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将工作重心倾斜于重工业建设上,而忽略轻工业发展。其结果是,人们发现难以买到保障生活质量的产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政策发生调整。国务院在1979年发布轻工业发展保障政策,执行“六个优先”原则,在能源、技术、制度、资金、运输、进出口方面对轻工业建设给予支持。到“七五”(1981年至1985年)计划时期,“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被列为核心工作任务之一。随着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民生产品产量扩大、价格下降,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意愿也有所提升。
设计史研究者沈榆说过,在改革开放初期“设计”概念在中国尚未成型,它们通常是一些与工艺技术相关且被某个领域内的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从五十到七十年代,国内已有一些与家庭装饰相关的活动,但官方认为它们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而不应被提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装饰的价值才得到认可。同时,“家具与室内设计”即家居装饰设计也得到正名,成为中国现代设计体系的一部分[5]。
《家具与生活》杂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在1981年由西安家具设计研究所创办,并得到西安轻工业局的支持。杂志第一任总编是赵士荷(1935年至1989年),建筑师,上海人。他在五十年代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后移居西安,在城市规划设计院和建筑设计院工作。直到1977年,他和几位同事一起调到新成立的西安家具研究所,在那里他们将建筑知识应用于新兴的“家居装饰设计”领域。其实,在1980年还出现一本由国家轻工业局和上海家具研究所主办的《家具》杂志。它主要刊登科研和技术类的文章并在全国发行。与之不同,《家具与生活》杂志开始只在西安发行,在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后才在1983年向全国各地发行季刊。
至少在七十年代末以前,各大城市居民购置大件家具(如衣柜和床等)还需要凭“购物券”。例如,七十年代北京市民会领取各种购物券,他们要等到券上的号码公布才能到国营商店消费。大件家具在北京城区通常供应不足,要等六个月以上才有货。即便等到购买的当天,也要很早去商店排队,并且有可能被告知缺货,需要第二天重新排队。其他大城市(上海、西安、济南等)和北京的情况也类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几点:首先,家具通常在当地的工厂手工生产,产量受限;其次,木材要由国家分配,工厂无法扩大产能;再次,城市间的产品运输并不顺畅。
除此之外,城市居民面临的另一状况是居室面积变小。八十年代中国的住房分配制度是国家建房、单位分房。年轻人,特别是新婚夫妇住房紧缺是很多城市存在的现象。年轻夫妻在单位需要等候数年才能分配住房,因此很多年轻人结婚后与父母同住。据资料显示,在1980年上海市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是5平方米,到1988年上升到8.7平方米,但是,有33%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6]。在1986年西安市民人均居住面积是5.82平方米,到1990年上升到8.62平方米[7]。西安的数据已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城市的情况比上海略好一点。能够想象,这种状况使空间优化设计成为趋势,即在小面积空间中满足睡觉、工作、用餐、社交的功能。而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家庭空间的舒适和美观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新时代中国民众对居住环境要求提高的背景下,《家具与生活》杂志选择了为大众家庭装饰提供服务的定位,设置了“问问工程师”“自由设计”“我的家”等生活化的栏目。这一路线得到一大批城市“新生代”读者的认可,他们包括年轻的专业人士、事业单位人员和工人等,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是最高的。杂志的发行量从最早的一期几千份增长到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万多份。

■图3 造船厂工人单间设计效果图(原载于《家具与生活》杂志1986年第2期)
2 板式组合家具:生活方式变迁下的理想产品类型
事实证明,在当时出版一本服务于民众的家居装饰设计杂志是明智的,因为越来越多人对家庭装饰感兴趣,但这类大众读物在市面上又很稀缺。戴维斯在考察八十年代上海城市消费现象后说道,人们愿意花更多钱使家庭环境变得更舒适和漂亮,他们需要这一方面的指引[8]。而在西安,从1984年到1988年平均每个家庭的家具消费接近翻倍[9]。不过,《家具与生活》杂志的办刊目标并不是刺激消费,而是解决民众的生活难题。因此,杂志很少单独讨论家具,而是将它们作为空间、家庭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从杂志的角度来看,八十年代的理想家具有何特征呢?1982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这个时代最好的家具应该是实用、经济和美观的,这类家具将促进人民家庭生活的和谐、健康发展。”[10]从杂志的主推方向来看,符合上述特征的正是“板式组合家具”。
2.1 充满时代感的产品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在家中摆放的是“成套家具”,包括床、衣柜、餐桌、抽屉柜和椅子等。不过,仅有少数城市家庭拥有一整套家具,农村家庭则更少。因为成套的实木家具需要纯手工生产,既耗时又耗材,而且造型厚重和占据较大空间。可见,成套家具并不适合城市居住环境。相反,组合家具是更好的选择。上海家具研究所的工程师曾在《家具》杂志中发表评论:“组合家具是满足未来民众生活需求和设计‘三个转变’(产品、技术、标准)的理想类型。”[11]事实上,早在五十、六十年代已有人提出“组合家具”概念。到了八十年代,家具研究所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希望将这个概念投入批量生产。为了探索适合中国的设计和生产方式,他们从国外产品中寻求灵感,如宜家的平板组装家具,还有德国Hülsta(优适德)和Deutsche Werkstätten Hellerau(海勒劳)公司的产品。
除有利于灵活利用空间之外,板式组合家具使用的板材区别于实木,具有自身特殊的结构美和技术美,得到工程师和设计师们的青睐。上海家具研究所最早研发以颗粒板为材料的组合家具样品,计划用于批量生产。板材可用于建造或连接墙身、床、桌子、架子等。这种材料的德语为Endlosbauweise(无穷尽的结构),意为千变万化构造的基本单元。板式组合家具最初由颗粒板制作,后来被密度更高的纤维板所代替。在“七五”计划期间,国家将大规模生产人造木材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之一,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很快市面上也出现各式各样的板式组合家具。在1984年《家具与生活》的一篇文章中,板式组合家具被形容为“充满时代感”,因为它象征着“生活用品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阶段,向国家的长期奋斗目标又迈进一步”[12]。而在1985年的《人民日报》中板式组合家具又被描述为“未来家具市场的第一大趋势”[13]。
2.2 优化小居室空间的产品
《家具与生活》杂志大力推介板式组合家具,是因为它们符合当前和未来城市的小面积居室空间发展趋势。以往人们多使用成套家具,并习惯于随意摆放,无需专门空间规划。相比之下,采用板式组合家具必须提前考虑整个房间的空间功能布局。因此,杂志必须令读者相信将架子、床、沙发、桌子进行不同的组合,可使空间得到最大利用。例如,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叶宝峰曾讨论如何最大效率利用10至13平方米小单间。他认为,根据门和窗的位置首先确定沙发的位置,一般摆成“L”形;架子可以与沙发或床或桌子组合,根据剩余的墙面面积进行灵活分隔和安装;利用储物架把不同墙面连接起来,形成整体感[14]。
杂志还会经常介绍适用于不同小面积居室的板式组合家具设计方案,它们富有创意,为读者带来很多灵感。在一期“问问设计师”栏目中,就介绍了一款适合祖孙合用的双层床。它的下床面积比上床大一倍,这样的话老人能坐在床上进行活动。板式组合家具的另一大优点是可折叠,或者安装在其它家具上,以腾出更多空间。例如,在图1中的书桌安装于床的一端(图1),在平时折叠,等到使用时再打开。图2是题为“聪明规划小空间”的漫画(图2),有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描绘一对男女在一个狭小但整洁的房间中欣赏墙上的画作;在第二个画面中男士放下隐藏在中间画作后面,一端安装在墙上的桌子,女士大为惊讶;第三个画面描绘男士已坐下,女士正打开隐藏在旁边小画后面的椅子准备坐下。这组漫画表明,别出心裁的板式组合家具可兼备艺术品和实用品的属性。
板式组合家具的最后一大优点是便于“自己设计”和“自己做”。国家已明确板式家具是未来发展趋势,但读者无需等到其大规模进入市场,购买板材便能自己制作。杂志也一直鼓励读者培养自主的生活态度,于是有了“问问工程师”这个栏目,专门为读者“自己设计”和“自己做”提供技术指导。例如,栏目会讲解在制作储物架时如何使板材排列整齐和安装牢固;还有在房间角落如何进行工作等。除提供指导之外,杂志还会偶尔展示读者“自己设计”和“自己做”的成果。例如,1985年某一期刊登了一位读者13平方米单间的设计构思和几张实景照片,当中全屋板式组合家具都是由他独立设计和制作的[15]。
3 家居装饰:形塑八十年代的家庭精神生活
在八十年代,政府部门普遍要求报刊承担读者思想教育的职责。对《家具与生活》杂志而言,这意味着引导读者在家中实践健康的精神生活。这一重要任务在1984年的周年特刊中被反复提及,当中有省市重要人物对杂志使命和发展方向的陈述。西安家具研究所所长田磊认为,“新中国的家具产品融合了科技与艺术,影响着人们的道德,美学判断和生活方式。设计、室内环境、美感、健康和精神生活是紧密联系的,杂志在家居美化方面有重要的指引作用。”[16]无疑,这一观点与国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有关。改革开放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在重要的社会转折时期,政府十分重视引导民众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媒体对于“精神污染”,即过度的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给予严厉批评。事实上,室内空间对居住者精神状态的影响已经被西方现代建筑师所强调[17]。在改革开始之初,人们通常认为家居装饰设计只是与物质生活相关,随着家庭装饰需求的提升,官方意识到这些活动对精神生活也有重要影响。西安副市长金易仁就阐述过家居产品和设计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物质文明并不是‘物质财富’,它反映着广大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文化习性’,他们的‘民族情感’。家居产品和设计应该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即简单、朴素和有品味,鼓励人民进行‘自我陶冶’”[18]。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居装饰设计被赋予前所未有的精神价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潜移默化的精神陶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3.1 营造“理想之家”
作为一本大众刊物,《家具与生活》必须将办刊指导思想和民众日常生活相结合。“自由设计”便是这样的栏目,它在创刊时就已设置,由室内设计师王易南团队主持。王易南在第一期前言中指出,这个栏目旨在“为读者提供设计方案,解决小户型空间装饰的问题。”[19]他们邀请读者来信说明房间面积、成本预算、生活需求和意向效果等,每期会挑选三到五个案例刊登出来。栏目主要解答选择什么家具和如何布置房间等,还会附带设计师的效果图。
从栏目刊登的案例来看,板式组合家具确实解决了各种小居室空间的利用难题。例如,一位上海造船厂的工人和单亲母亲与十几岁的女儿同住,房间不大,但母亲还是希望女儿有私人学习区域。栏目组为她们推荐一款双层床,白天用布帘遮挡;还建议在相对的墙面摆放两张小桌子(图3)。如何让人在房间中白天和晚上都活动自如是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一对安徽夫妇希望使工作室融合休息和娱乐的功能。栏目组提出很实用的方案:把工作桌和储物架设计成组合家具,与沙发和电视一起摆放在房间一边;另一边则摆放床和挂墙储物柜。有时,栏目组还会帮读者构思板式家具改装的方案。一位来自石家庄汽车厂的工人自己设计板式床和靠墙落地储物架,但后来发现空间不足,有些家具无法摆放。栏目组建议他把储物架改为半挂墙式,这样床便可靠墙摆放,还可增加一个小沙发(图4)。
在浏览读者来信过程中,杂志发现新婚人群对家居设计有诸多诉求。于是,“自由设计”栏目在1987年策划了一期“一室户新婚居室设计”专题。据编辑介绍,大量新婚读者给杂志来信,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购买新家具;如何在小空间中摆放家具;如何确定房间整体风格等。编辑还提示读者,理论上家中的休息、学习、会客、煮食、进餐区域都应分开,但就目前城市住房条件而言,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因此,他们建议选择优先解决基本生活需求,即选择双人床、小沙发、桌子、衣柜和储物架。经调研后,栏目组把设计户型限定为宽3.3至3.6米,长4.2至5.4米的房间。根据不同的隐私需求,读者可有三种类型选择:以储物架和布帘隔开床的“隐闭”式;以家具隔开床的“半开放”式;把床放在显眼位置的“开放”式。此外,读者还要考虑宽敞的工作区域是否必需,不然的话,桌子和椅子可放在边角位置,腾出更多活动空间。结合门、窗和阳台的不同位置,杂志刊登了12个功能和空间布局各异的室内设计方案,供读者自行选择(图5)。
3.2 布置“健康之家”
如果说“自由设计”栏目提供了设计和施工参考,那么“我的家”栏目展示的是现实中的家居布置案例。这个栏目意在传递“家的故事”,用图片呈现杂志推崇的理想家居生活。开始栏目主要刊登演员、演唱家、艺术家等名人的家居照片。到1987年,栏目将视野转向普通读者,邀请他们寄出关于自己家庭装饰的文字和照片。编辑会筛选出那些精心设计施工并带有背后故事的案例,将它们刊登出来。可以说,“我的家”栏目将读者转换为设计师的角色,为其他人在装修时提供参考。
“我的家”每期都能使读者了解不同家庭如何营造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家”。例如,在1987年第3期中刊登三对夫妇家居的照片。第一组照片来自广东佛山的年轻夫妇,分别是塑料厂和糖厂的工人。他们的两房间居室摆放这浅粉色的家具,配以各式鲜艳的装饰品,反映都市年轻人的审美趣味。还有一对五十多岁居住在河北唐山的夫妇寄来照片,他们原来的家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摧毁。但他们宣称,灾难无法剥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并以白色家具,橙红色的落地灯和大叶的龟背竹装饰新家。明亮的色调和强烈对比的装饰折射出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第三组照片来自一对重庆的夫妇,他们对于完全靠自己设计和施工完成12平方米单间的装修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照片呈现的是两人的日常生活场景——阅读杂志和织毛衣,一幅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上述的家庭都使用板式家具,证明这种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经济改革成功的物质证明。
整体而言,杂志竭力阐明家居装饰设计的精神价值,并引导读者在日常生活中予以实践。在1986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曾讨论设计与“过度装饰”的区别。文中指出,在家中对物质一味追求可能会造成“过度装饰”,导致“肤浅和杂乱”的效果。相反,好设计应该是“聪明的,物尽其用,保持对物质的节制”[20-21]。曾有一段时间“我的家”栏目收到不少把家堆满装饰品的照片,于是杂志编辑部发出倡议:不要贪心地把家装饰得像杂货铺,这不是杂志推崇的干净、简洁和现代的“家”[22-23]。另外,杂志还希望通过设计传播正面的价值观[24-25]。他们收集家居设计背后感人的故事,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依然乐观地布置令自己满意的家,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更激励读者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4 结语
通过梳理《家具与生活》杂志文本和图像可发现,八十年代家居装饰设计呈现几点时代特征。首先,由于其“轻、巧、省”的特点,板式组合家具成为适应民众生活方式的理想产品类型,被专业人士赋予时代价值感并得到杂志的大力推介。其次,居住空间变小是民众面临的普遍问题,由此优化小居室空间成为杂志主推的方向。再次,随着城市“新生代”的个性化需求增多,“自己设计”和“自己做”受到广泛欢迎。此外更重要的是,家居装饰设计被赋予其前所未有的精神价值,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引导人们实践朴素、务实、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本文所揭示,八十年代家居装饰设计与民众生活方式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透过这些联系审视设计的技术性、功能性、精神性等问题,使我们对“设计作为文化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具体言之,在八十年代被生活杂志广泛传播的板式组合家具、小居室空间优化和个性化需求的设计趋势反映了中国家居文化的变化,显示出一种日常生活文化的演进。也就是说,这些家居装饰设计折射了人们生活条件、生活空间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成为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设计史学者法兰曾梳理西方设计文化史转向的历程并论述其前景,他提出:“将日常用品设计融入更广泛的文化史领域,使其成为一种设计文化史……设计的文化史不仅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走在文化史领域的前沿”。这一思路对于扩宽中国家具与室内设计史的研究视野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