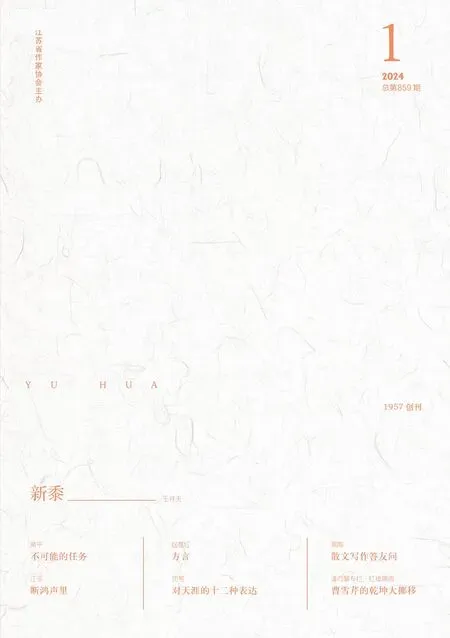枕山记
巴音博罗
枯坐
年愈五十,总喜一人独去我家邻近的一座名叫烈士山的小土山枯坐。
枯是一种味道,坐是一种境界。一个人活到年愈五旬,需要时常从时间的湍急河流中停驻匆忙的脚步,痴痴地躲到僻静处坐上那么一上午或一下午,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喘息声、风刮过花白鬓发的刮擦声。当然,你还可以数着心跳去望一望逝去的日子,还有屈指可数的未来的日子。
我猜那八大山人和弘一法师的日子亦不过如此罢。
其实那烈士山不过是我所蜗居的城市中心的一丘小矮山,因埋有诸多烈士遗骸而得名。从乍暖还寒的初春始,我就去闲坐了。初时尽拣阳面,用缓缓上升的朝阳那万亿金针炙自己;从额顶到面颊,再到胸口、肚腹、裆部、膝盖骨和趾尖……我微合双目,什么也不想,只等待太阳霍霍然的响亮一跃,我已和周遭肃然呆立的石头松树们一道,迎来了那引颈斩首的一刻了。
但这只是我一味的瞎想。如果四下里忽然一暗,一定是偶尔路过的一抹云朵遮挡住了金灿灿的阳光,而不是我违背了这堂皇太阳的旨意。我和太阳、以及我和我的影子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平衡,我们谁也没有惊动对方。
风徐徐地掠过荒草和去岁的焦叶,有几针嫩芽在一片枯黄中灼闪。有人在不远处唱歌吊嗓子,其声犹如哭坟;又有人沿半山腰的山路疾疾奔跑,后面跟着一条气喘吁吁的胖狗。而山脚下的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火柴盒似的小汽车和蝼蚁似的行人。
人过五十,渐渐有了“枯”的心境,从此眼中的风景也有了质的变化,从此山河是荒凉广袤的,风声是锋利的,鸟叫也是惊心的。而春天的绿,又有了叫人忍不住想痛哭的冲动。所谓人生的况味,其实就是一棵树,强忍住不开花的意念。
由此我推测八大画中的一只鸟,一块顽石,水墨不能言尽的落寞,是独享的落寞;而李叔同所说的清凉,必是看破红尘了然无憾的清凉。
我曾仔细玩味过日本人的“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庭院即指不使用池塘或人工溪流,转而采用石子和砂砾来表现山水风景的方式。例如在地上铺盖一层白色细沙借以表现波光粼粼的水面,用一块石头代表一座大山与岛屿,这和我的好友、诗人杨键所画的“苦山水”如出一辙。在这里,枯和苦,都不是枯萎和贫苦的意思,而是一种自我修为的禅意,是生命中至高层次的哲学。
我想,苦瓜和尚的苦,是不是老而弥坚的甘冽呢?
而我的枯思和坐忘,也终于有了可以类似一棵树一株草的心境。在今春,也可以咬定青山,做到不开花不言说的自在了。
和一只花喜鹊谈论爱情
和一只花喜鹊谈论爱情,自然不怕说出彼此的隐秘。
这是早晨,花喜鹊在树上一直“叽叽喳喳”大声喧哗,我知道她还是去年的那只,我知道她在抱怨天气,继尔又呼吁环保。但是她的同伴似乎对此不感兴趣,他跳上忙下一直围着花姐姐打转,他要谈论诗歌,而花姐姐此刻需要谈及爱情与早餐。
我闭着眼,听见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般,她会先说出三个单词,“喳喳喳”。然后她还会接上一到两句,依然只是“喳喳喳”“喳喳喳”。这时阳光稍稍有些晃动,正好遮住了她的一只好看的翅膀,像是我老婆年轻时的裙摆。这时她会倾斜小巧的头部,停顿那么一小会儿,似乎在等待远处的某种回应。但是显然,她没有听见,所以性急如火的花喜鹊忽地一跳脚,突兀响亮地又来这么一长串的叫嚷:“喳喳喳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叽喳喳”……
她鼓腮振翅,挺胸扭颈,像是数落她爱伴的种种愚蠢和错误,我想恋爱中的人大都如此,急赤白脸的怒气能否换来那只小冤家小郎君的表白或回心转意?哦,你黑白花相间的灵羽上有光在闪烁,你纤细灵巧的脚趾有一颗露珠的破碎,还有你略带沙哑的嗓音里有三弦和二胡的幽怨。唔,我也许说的不是你——一对美丽异常的花喜鹊,我所有朴素邻居中最令人头疼的家伙,除了另外一只灰麻雀和黑松鼠,我不能一一指出你们的天真和诙谐。我只是一个落寞的诗人,一个满手油彩的画家,今晨和傍晚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落日与清风达成谅解协议。我保证不会在日渐哀老的妻子和日益长大的儿子们的生活中不爱他们!
松鼠的跳跃姿态很美
松鼠的跳跃姿态很优雅也很美,我不敢保证我看到的就是真相。比如,一只蚂蚁从蚁穴爬到一根金色草茎的时间是一小时零三分还是五小时零七分?但我每隔一个时辰要打一次嗝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还有,我无意中对一棵粗壮的青冈柳撒出的尿液能否使它在一整天蒙羞和愤怒中得到解脱呢?
日本散文家德富芦花也写过杂木林,我猜树种与烈士山的差不多,也大都是一些榛、松、槐、榆、枫和柞树。我独喜野樱树和山楂树,我曾挖掘过一些小幼苗栽到花盆里,养过几年后就蓬蓬松松自成风景了。而墨绿色的黑松则高高而立,宛如一威严肃穆的勇士,令人敬畏。
我独自在松畔的岩石上小坐,巨大松冠的翠盖遮掩住碧空,使我和一地阴凉拢成一团。我听见松鼠在虬曲的松枝间唰唰掠跳,这儿是它们的乐园,当然也是我的。我是松鼠的另一个玩伴。
这儿的松鼠一律是黑灰色的,它们并不惧怕人,有时就在我头顶不盈数尺的地方出现,我能清晰地看见它们顽皮小巧的头从苍劲嶙峋的松干后露出。
它们就那么肆无忌惮地望着我,仿佛望着一截木头,一块蹲在那儿不挪窝的岩石。
去年的叶子还挂在树上
清晨去烈士山,我总是避开晨练的人群选择一条野狗的路径。即,从侧门踅进,绕英泽湖畔的木质栈道环行到湖的厕所位置,然后跳上矮矮的石墙,穿过老槐树与厕所后窗的间隙,再沿一条荒草蔓生的碎石小径蛇行至一破败的石阶上。那儿的野山里红树和野樱桃树此刻正鼓着红豆粒似的叶苞,它们纷纷伸出手拉扯我的裤角和衣襟,它们知道拉我不住,而一只俗名驴粪蛋子的山雀正惊恐地一蹿而起,像被某个野孩子甩出的泥巴块儿呼啸着直冲云天。
正是三四月的交汇季节,北方的旱晨仍然有些寒冽,但我家阳台盆景里的枫树已然冒出婴儿手掌般的嫩叶。春天真的是不可阻挡地来了。人的心也因这重活的讯息痒痒起来,像挂在对面楼顶的暖阳。
万物安宁,像母亲甘愿受苦的脸,像石径上踩不烂的苔藓。我站在烈士山侧光的地方,仔细观摩一些光秃秃树干上挂着的叶子——去年枯萎的叶片,是时间榨干水分之后为我们保留下的诚实,是贯穿了一条叶脉的去岁的浩瀚,仿若一条灌满绿色汁液的大河,艰忍地诉说着尘世……
哦,古代沉睡的智慧从那里返还,故去多年的亲人将从那里回来。所以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日子!所以一个年愈五十的老男人眼里的枯叶,是最美最忧伤的春光!
寂
寂是我最喜欢的汉字之一。这就如同日本艺术家井上有一所书的翰墨淋漓的巨幅“贫”字,现藏京都国立现代美术馆的贫龛中,曾参加了1972年的“第六届现代书展”。据说前首相三木武夫站在贫龛前谛视良久,末了说出一句:非这样不可吗?而写此字的书法家井上听到这一段子时,倒吸一口凉气,“他是这么说的?”他问,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也只好沉默了。我承认我喜欢研习这个被西方艺术界视为抽象画家的日本书家写下的“痕”“花”“刎”和“素直”等汉字,由于长时间凝视,这些汉字会从素白的宣纸上个个挺立起来,像一排玄衣飘拂的壮士屹立在我面前,让我敛气屏息,汗然自卑。
我承认,我一米八〇身高的躯体和骨架,与这些墨气充沛的大字相比,简直丑陋不堪。
而“寂”,是“寂灭”的“寂”吗?当然不是!之后的好些日子里,我浮想联翩,也许“寂”是我能想到的安放在烈士山上的最好的汉字了。它让我想起烈士山的晚霞和月光,这时它是“沉寂”的“寂”。春天,有野樱花、野桃花开在坟畔,寂是寂寞的寂。而漫山遍野的老槐花开时,满山素白仿佛冬日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寂又随之有了生命壮烈。畅怀古今的宽阔——饮刀成一快,白了少年头。我总觉得空气中浓郁的槐花香气,暗含些许清苦的乡土中国的味道。
到了晚秋,湖中芦花点点,簇簇如佛掸。空中的行行雁叫声惊心动魂,寂又有了空旷寂寥的因素。因此此刻的寂是无言而又无声的,是念及双亲不禁泪湿衣襟的,是空怅空惆有了人生迟暮的苍凉的,寂是寂然的模样。
而冬天降临时,烈士山清静许多,也瘦下许多。雪后的环山路少有人迹。唯有兽痕和鸟爪的美妙印章,像极了金石闲章留在古宣上的款儿。我有些伤感,却不悲哀。当那棵日日坐忘的黑松针也褪了些许浓重,寂该是枯寂的寂否?抑或此寂为禅寂。释家以寂灭为宗旨,所谓“一心禅寂,摄诸乱意”是矣。寂这时为悟寂,了悟寂灭,入于不生不灭之门,该是多么形而上的事情!
至若侘寂,乃日本美学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泛指朴素安静的事物,源出小乘佛教的三法印之说,岛国之人喜欢幻灭之空寂,喜欢质朴而无常的寂静。犹如生出苔藓的石头,要的是石头内部的力量和自然无华的重生。
而此时坐在烈士山上无端避想的我,不禁又想起弘一大师病重时手书的一偈文: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也许,寂有七层境界,而我只说对三层,剩下的都交与风、花、雪、月了。而风说过的话儿,是最算不得数的,我想。
风没说过的,方好。
论一条小径的消失
在烈士山半山腰上,我拐进一条荒芜的小径,竟一下呆住了。这是往年我时常光顾的地方,但现在却被恣肆厚实的荒草掩盖住了,仿佛之前从没有过人迹,仿佛根本就没有这条路。
我的脚印被荒草吃掉了!
我的记忆,我过往的生活,一瞬间也被什么轻柔地抹去了,不留一丝痕迹。所谓长日留痕,在此刻不过是一句空话。我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了,祖宗的戒律,动荡的人生,寺庙里的经籍和香火……唉,一粒尘土似的人到底该不该留下这清苦的印痕呢?
风儿轻轻从杂木林的缝隙里吹过去,风儿也像锋利的刀刃一般吹过了我的骨缝。我感受到了这万物彼此消融的寒冽、清澈,是梦幻般的人世的苦痛和快乐,是我回到自然母亲怀抱里的磅礴力量。
我听见一只山雀子欢快地叫着,哭泣一样地叫着。我嗅着一棵虬曲刚劲的老松的浩然之气,像一位从古至今一直在死着的哲人。
当往事从心底浮起,当一阵战栗回到刚刚冒绿的草尖,一条经岁的小径像蛇一样溜走了,消失了,它消失在自己的消逝里,它成了精,通了神,仅仅保留了一点点对这尘世的留恋和爱……
等待一棵老松的倾倒
我在烈士山阴坡闲逛时,遇见一棵歪斜在另一棵枫树上的老松。
老松的主干足有成人的腰粗,估计至少也有百余岁了,它那苍然浊重的躯体此刻正完全压在那棵腕口粗的野山枫上,有一些枝丫还压折了那年青枫树的枝杈。
我走近去,轻轻触碰一下老松的虬曲朽枝,顿时它们便灰烬一般跌落下来,撞到岩石上后,又瞬间化为烟尘……
老松是北方山林里最常见的黑松,我了解它们的习性,我在我家阳台上养了至少五盆黑松桩的盆景,我喜欢它们伟岸、苍劲的身姿和顽强果敢的性格。一般情况下,一棵黑松活上两百年也不为老。而眼前这棵,不知什么原因,竟凄凄然成为一棵朽木了。
望着它痛楚地跌伏于一棵小小山枫上的惨状,我倒期待于它轰然的仆倒。
“不要等到烧成灰烬的时候,我们才是灰烬。”(杨键语)这之后的几天我日日都来,却始终没见到它的仆倒。就这样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连憋了一冬的杏树、李树、山梨树都争先恐后地开花了。老松也仍没轰然倾塌。
最后连我都失去了耐性。我猜此刻只需有人轻轻地用最小最小的指尖推它那么一小下。
甚至风稍稍加把劲儿,风稍微狠下心。
抑或,某人路过这儿时猛然吼叫一嗓子“驴腔”。
但是几乎全朽的老黑松至今仍然斜挂在那棵年轻的枫树上,像是一件破絮遍体的厚棉袄披在一个瘦弱小孩的身上。
就这样又是三个月过去了。李树、杏树和梨树们说尽了繁华,现在到了盛夏时分。乌云和雷电开始了新一轮的演说,暴雨用透明的鞭子抽打大地,我成为风雨的帮凶,山也不能再次让我感动和痛苦,像是旧日里愚钝,又像是人生中饱含卑怯的不断衰老的容颜。我看见环山的柏油路上,一个老者用自制的扫帚大小的毛笔蘸清水写古诗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在清晨的朝阳映照下,一首古诗往往还未写完,字迹就干涸不见了。
而老者却视而不见,仍然忘情地写着。
我想我有这老者一半安详就好了。
而安详来自一颗无法倾述的心。
有时无端地又想起那倾斜不倒的老松,想起弘一法师李叔同圆寂时的情景,欣欣而来,漠漠而去,成为世间万物的化身。
鸟影是锋利的
我想这样的年代,坐在树荫下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数着被松鼠登踏滚落下来的松果也是好的,看一颗熟透的落日被山下的楼群一口吞掉,像病人吞下中药丸也是好的。我们是有着先天心脏疾患的病人,我们一激动就会休克,像那些对黑夜过敏的灯光。
黑夜是山下这座漠漠大城褪下的古典汉装,枯涸的大河是它的一只被风扬起的袍袖,另一只是我。我是因大声吟诵从此传颂千年的碑文。
而碑也被时光的刀子刻得遍体鳞伤。
就这样好多时候,我时睡时醒。我在我自己的躯体里进进出出,躯体像个被废弃的古堡。我是一缕清风,我可以轻松翻遍这古堡的每一个角落,像一个穷汉总是饿急眼时翻自己空空落落的口袋。有时我会听见一声拉长的喊叫声从耳畔划过:“唉,人生啊,我到底要靠什么过活哟?”有时我又清醒异常,一整天保持沉默。我听见金灿灿的阳光像野蜂群轰鸣着,笼罩住透明的天穹。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遐想是否也是我的权利?
而更多时候,我斜卧于烈士山的草丛里,感受不断划过我凛烈额际的鸟影。锋利如刀刃的鸟影挟着唰唰的风声凉凉掠过。我缩缩头,充分感受到了光的力度、影的重量。“这一切也许都是我的过失。”就像某个囚徒,即便他被从那高墙铁网的监狱释放出来,未来他的生活里也处处留有罪责的痕迹。
“如果我们能在最后一刻钟毁掉自己,能否毁掉今日的善行?”
而鸟儿竦竦飞行时在空中弯折出的弧度,恰巧是语言之诗的韵脚,是月亮的触须留在夜晚的温情,是一个人替代故人说出的挽辞。他说:你不该仇恨任何人。他说,我在衰老之前就亡故了。我离开故乡,离开祖先的灵牌和香火,我的灵魂得不到宽恕。
我不是被鸟影杀死的第一人。
如果一棵野樱桃树真的能照亮自己
四月里,野樱桃蓦然开花了,就像在黑黝黝的旷野里突然撞见一位少女,那圣洁的光芒会一下子刺瞎你浑浊的双眼。
我忘情地走在草软泥酥的山坡上,温暖的阳光轻托着我的额顶,像我的亲妈。我封冻一冬的心扉瞬间就融化了,像河堤上因新绿而悲啼的杨柳。
连家燕的新衣裳也像借来的,像是一个唢呐练习者吹出的不连贯的音符,那亮亢的、总是跑调的旋律,使我尽情体味着爱的痛苦。我在自己干枯的心底里重建起来的幸福,是否就是这一棵野樱桃树开出的妩媚的壮烈?
是啊,多少年来我们需要借助古今圣贤来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而春天好像另一个圣贤,另一个母亲,她吹亮了一盏杏灯,又吹亮一盏李树灯,她吹亮的灯盏仿佛神的教诲,让熬煎一冬的人借助大地掩埋恒久的疼痛。我还能在这古灯边看见死去的先人的面容吗?
我眼含热泪,自言自语,像是一只因巨大的幸福而眩晕在花瓣上的蜜蜂。
也许一棵悄然盛开的野樱花真的能照亮自己,它看见俗世的幸福,碑的不朽,人的愚直和兽的快乐,这在今天仍然是难能可贵的,像朝霞映红的圣典,也像人之本性中遗留的一粒小小尘沙。那根源的丧失呵,那奉献的热忱啊,以及山河依旧的道路上回荡着的求索的足音,如今都化为一树繁花,等待它的自我拯救。
我比一块石头更有耐心
石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石头一站就是万载千年。石头不像水,哪处低就向哪儿去。石头的一生就是在默然无声的伫立中度过的。
我离开故乡几十年,回去时看到儿时坐过的石头还立在原地,只是上面多几块苔藓。我家院子通往河边的一条陡而窄的泥路上,当年曾狠狠撞过我脚踝的那块尖角青石,至今仍突兀地等在那里,只是我已年过五十,再不会像小时候那般顽皮疯跑,因而也再不必硬生生磕上去痛得龇牙裂嘴。
石头很少吐露心事。大多数时光,我们人类总也弄不懂石头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即便偶尔有一两块所谓的灵石被我们拣回来,佩上几座摆上案头,每日欣赏把玩,但石头眨着灰色的眼眸,只是向我们投来呆懵的一瞥。
好多时候我在烈士山闲坐,枯寂地望着某一块熟悉的岩石,我看到满是皱褶的石头的脸上平静如初。从初夏到深秋,风不会把石头吹得像草一样摇摆起伏,雨也不会把一块岩石的腰肢洗成白色,当雷电的刀锋斜劈下时,静默不语的岩石不会躲避。
有几次我听见岩石在嘀咕,为一个死去不再到来的老者,为一棵倒卧的黑松或被虫蛀而死的老槐,但是灰色脸膛的岩石也只是低低嘀咕而已,即便我努力睁大眼睛耸起耳廓,我也没听清一句。
后来有一次我听见岩石的惊叫,我疑心我听错了,出现了幻觉。因为即便大风吹彻了我的心扉,也不会吹动一块岩石——哪怕一块小小的、拳头一样紧握的岩石!而岩石内部的结构,内部的秘密,是最难以破解的自然万物的隐秘,是岩石之所以活着、伫立、千载万年坚守不动的隐秘。
但我确实听过一声悠长的、叹嘘般的呼喊。我开始怀疑岩石的耐性、岩石的忠贞以及岩石那冥顽不化的固执笃定,它被武装过的头脑真的能坚守到地老天荒吗?抑或,一块巨硕岩石的爱情也能比一只蝴蝶的飞翔要轻?
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只胡蜂在向它俯冲,轰炸机般盘旋并俯冲,它们没投下炸弹,而是留下了族群的颂歌!我看见那个高高悬挂的蜂巢似乎是一只轰鸣的马达,而坚忍不语的岩石承担了这一切!
我和岩石久久对望,我们有了某种默契。时间滴答作响,我的手背渐渐生出凉意,并且长出黛色青苔……
被取消的落日
现在我写作此文的时间是2022年4 月1 日的下午四时零五分,本来这个时辰我是要到附近的烈士山上去走走的。在那儿,向南偏西的一处山岩坡地上,我会静静伫立在那里,等待落日稳稳沉落时的苍然壮景。
但是现在,我只能闷在书房里,用意念想象那往日的柔美风光。因为落日——那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一刻,被冥冥中的一只巨手,像橡皮擦涂掉错别字一般轻轻抹去了。
是的,这情形也如同一个正在晒日光浴的人,被突如其来的某某遮挡住了阳光——野蛮的、粗陋的阻挡,是后工业时代对自然风物最直接的侵害。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像我日日享受的烈士山美景。在我和烈士山西南面的铁西区之间,是一大片开阔的后工业化时期典型的厂房、车间、道路、民居以及低矮的丘陵。如果赶上个晴朗的好天气,就会在傍晚暮霞满天的微岚之中,看见一生中不曾际遇的苍凉幻景。之后是一颗硕大的,淹制熟透的鸭蛋黄般的落日缓缓降落,我能听见地平线上英雄挽歌般的合唱队的合演。
而现在,这一切竟被山脚下一大片刚刚建起的水泥楼房完完全全挡住了,水泥森林——足足有三十几层楼高的冷冰冰的混凝土墙体,像是一个警示,一个卡夫卡式的预兆,我是这蛮横无理的强盗行径的第一个受害者,然后是烈士山,烈士山上的野草及树木。
我知道一只松鼠再也不会向那落日的喟叹声投去幽怨的一瞥了。
就这样有好多日子,我取消了与落日的约会,尽管长久以来我与落日早已达成某种默契,但那又能怎样?在我和落日之间猛然插进一只脚的,是这种钢铁般冷漠的庞然大物,也是此刻我在纸上疾速流淌的文字的唯一障碍。
从此我亦不必再有落日映照下的黯然神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