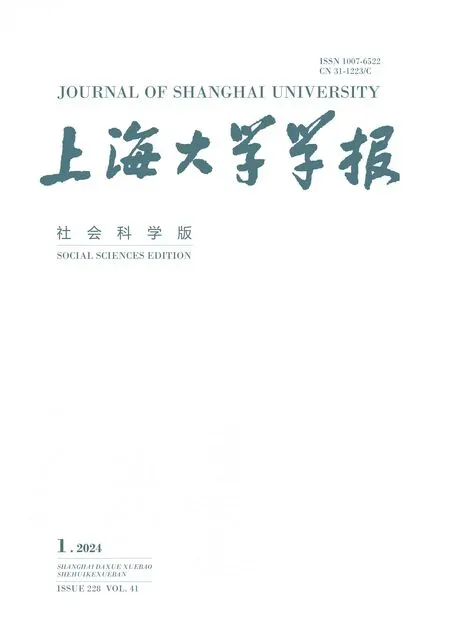澄怀味象: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的电影表演美学
冯 果,韩 鸿 滨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青年形象是电影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书写对象,中国电影中青年形象的表演塑造离不开传统美学的浸淫。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中,家国同构的儒家思想充斥于各时期的青年形象中,通过符合礼仪规范的行为举止塑造典范。如《三八线上》(1960)中小战士面对敌人的物质诱惑,以铿锵有力的台词、挺拔的身姿完成了威仪式的人物塑造;《生活的颤音》(1979)中郑长河以乐器道具修身明志、感化人心;《天山行》(1982)中郑志桐在滂沱大雨里张开双臂,激昂慷慨的朗诵中尽显浩然之气。这些富有外在感染力的言行与人物达济天下的精神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中华文化虽历来以儒家诗教为主体,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同时,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对银幕中的青年形象表达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电影《体育皇后》(1934)、《大路》(1935)中黎莉莉与工人们纯真放达的身体展示,杨耐梅与黎灼灼以前卫的生活方式塑形角色的表演,《孩子王》(1987)、《棋王》(1988)中向内观照的王一生和老杆,以及20 世纪80 年代末自嘲调侃、疏懒异行的“顽主”们,都以超脱世俗束缚的言行强调人物内在的自由放达。
不同青年形象展现出的是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与审美趣味,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与审美经验的历史视野中,每当身处社会巨变之时,人们常常会感到迷茫与无助,向外追求困惑不得,便会转而向内,这时关照个体心灵自由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便成为养料与资源。道家美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深刻而全面,要求主体以一种虚静空明的心斋境界摆脱世俗束缚,使自身与外在世界相互照应、合二为一。作为心斋境界在绘画创作中的转化,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曾提出澄怀味象的重要美学命题,旨在突破比德美学框架。具体而言,从静赏万物的蓬勃生机出发,经由山水之形捕捉其内在之核,最终体悟“大道”自然之境界。在这种审美体验中,“澄怀”是前提,是宗炳对老庄“涤除”“心斋”观念的审美回响,是内心清除杂念后,对外物的直接应接,在此基础上方能体味自然之象。而“味”的方式则以“应目会心为理”,[1]155先“目”应,后“心”会,先对“形”作观照,再对“神”加以把握,此时对山水之形是不受道德比附、不受实用功利目的干扰的欣赏,唯有在不受外物宰制的状态下,才能达到心灵快适的畅神,获得精神生命的自由。
转型时期是价值观驳杂多变的时期,亦是除旧布新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不同思想的涌入与交织,青年一代原有的价值体系被逐渐消解,内心困顿的他们将目光转向自己,向内探索,寻求新的确定性。相比于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的思想指南,道家澄怀味象的审美实践为身心交困的青年开出了救治药方,成为他们游离于儒家思想之外的精神依托。整体来看,20 世纪90 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中国电影中的演员表演,在传统文化根脉与时代变革相碰撞后,呈现出澄怀味象的美学风格。人物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相互照应,塑造角色时,演员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以去纹饰的表演塑造实现人物生活状态与情感状态的自然流出,在与角色的精神同构中,达到去成见、不凌驾的表演境界。
一、精神同构:剔除主观成见之“澄怀”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不同文化相互交汇,价值观驳杂而多元,为了寻求新的确定性,人们开始向内关注自己,关注社会中不同个体的生存及生命意义,由此,银幕中的形象开始丰富起来。既有为祖国荣誉而日夜奋战的建筑工(《情洒浦江》),又有受到传统伦理道德与外来文明双重影响后充满矛盾的农家女(《香魂女》),也有在商品经济浪潮下艰难坚守的知识分子(《站直啰别趴下》)。与此同时,行为艺术家、都市灰色人群、底层弱势群体等,这些传统影像中被遮蔽的一些边缘人物形象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并且这些边缘的青年形象及其生活状态得到了不加评判、不做修饰的真实自然的展现,具体到表演中,这需要演员剔除外在干扰,不断走向内心,借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内心体验去重塑角色。
首先,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塑造人物是演员自身经历走向银幕审美的过程,影片中角色的故事就是演员自己或朋友的经历遭遇,[2]204这样一来,演员的表演便可以一种自然直觉的方式来减少世俗成见的干扰,原生态的呈现就能达到自然真实的效果。《东宫西宫》(1996)中胡军饰演的派出所民警小史,将同性恋者阿兰抓到值班室后,言行中不乏对阿兰的歧视与侮辱,但随着阿兰的讲述,小史也渐渐发现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胡军刚上大学时曾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一个追求者,在争斗之后虽摆脱了纠缠,但“心里其实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那个人”,[2]123正是这种情绪与态度成为胡军参演《东宫西宫》(1996)的契机。秦燕本是《妈妈》(1990)的编剧,但因其是残疾孩子的母亲,遂又在片中饰演了妈妈这一角色,影片中无论是其举止行为还是采访,都“不是演员能扮演,不是剧情能完成的”。[3]《冬春的日子》(1994)中画家夫妇由新生代画家刘晓东和喻红夫妻本色出演,不仅能在镜头前更完整地呈现作画过程,更能从这一过程中延展出人物创作时的情绪状态与精神困境。《站台》(2000)中崔明亮的表弟由导演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饰演,崔明亮的表弟追赶着远去的拖拉机,将五块钱交给明亮让他带给妹妹后,转身而去,沉稳又坚定地走回到了残酷的生存世界,此时演员的“节奏,还有他的尊严与自信”[4]与角色是一样的。与角色相同的经历使演员们在创作时可以摆脱胸中尘浊,抛开成见顾虑,“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5]最终显现出“忘乎物,忘乎天”(《庄子·天地》)的最自然表达状态。
其次,演员塑造形象时,援用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创作之法,所选演员的气质与角色气质高度接近,甚至骨子里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贾宏声自称“生活在旋涡里……和电影里的人一样,我就那样”,[6]1他的皮肤并不光滑白皙,痘印坑坑洼洼,眼睛不甚明亮却带着从容感,在最自然的状态下也会呈现出仿佛溺水般陷入自己精神世界的神色。拍摄《苏州河》(2000)时,贾宏声虽已戒毒,但眼袋与略显病态的肤色尽显忧郁颓废,当正值年轻、本应充满力量的身体与略显倦态的容貌重合,再加上他自己也不愿剪去的一头长发,直观地呈现出一种反叛与多元的生趣。也正是这种魅力“不在表演”而在“他个人骨子里的状态”,[6]1使其成为都市边缘人的代言人。贾宏声在创作中以自身作为表达样式的呈现无疑是《田子方》中“真画者”的现代转写。“真画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则解衣般礴,臝”。[7]202他在众人作揖恭让时神闲而气定,这种任情恣性的状态不仅主宰着“真画者”率性自然的行为,更是其画作得以真情表达的重要来源。“以气论文”,“书为心画”,这一时期的表演创作中,演员的自身气质、内在状态代替了种种外部技巧,直接作用于角色的塑造。《苏州河》(2000)中,娄烨对女主演的要求是“又得成熟、又得是小女孩”,[8]136第一次见到周迅时,“她穿一身黑衣服,完全就是十六岁的长相,再一装小,差不多十二岁。但是一说话,声音极低,特成熟,有点分裂,完全是想要的美美和牡丹的结合体”。[8]137
最后,演员还会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以抛弃成见、“虚而待物”的心境作为基础,“不是我到角色那儿去,是角色到我这儿来”。[8]126《苏州河》(2000)结尾处,美美看到马达与牡丹双双自杀后陷入思索,此时演员的面容情态不断释出细微而摄人的能量。这源于周迅在表演时将自身这个“‘杯子’洗净,让自己保持天真和干净,不要去想那么多”,[9]在此基础上,以空明虚静的精神状态进入角色,呈现最真实的感受与反应。每当评价周迅的表演时,总绕不开灵气和少女感两个特质,其实这靠的正是演员心虚而待物的塑造方式。灵气作为一种对直觉的依赖,是将自己抛到生活中,在经历不同的工作、生活之后,不被社会规训的结果。少女感不单单指向面容的年轻靓丽,更是一种从人物身上散发出的纯净、明朗之感,是人物对所处世界的新鲜感,一种即便受到挫折和磨难,也会对明天抱有期待的孩子气。“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气,因为我觉得能用一种孩子的眼光看世界是一个礼物”,[10]虚而待物,方能实现对不同角色更有效的认识与接纳。
由于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原在感受出发去塑造角色,这一时期演员的表演去除了程式技巧,以澄明虚静的内心呈现最日常的言语、最闲放的体态和最纯粹的生活状态,显现出亲切有味又自然的真。
二、应目会心:自然野趣的外在状态
“澄怀”方能“味象”,而“味象”以“应目会心为理”,[1]155先“目”应,后“心”会。以目应物是基础,是眼观形与色的把握,应目也就是“观物”。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事物的形象及审美属性不是来自人对对象的主观性赋予,而是来自事物本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强调与生俱来、不假人工矫饰的自然审美成为道家审美思想的核心。转型时期价值观驳杂多变,原有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被逐渐消解,人们将目光投注到自身,意图在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价值意义,20世纪90年代保留生活毛边的表演塑造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不加修饰、没有附加意义的日常生活图景看似杂乱,实则直指生活的本质,本身就是意义的直接呈现。因此,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会最大限度地保留角色与周遭环境的真实关联,无关美丑,只自然而然显现其生动具体的外在状态。
首先,表演塑造呈现出野趣的美感,在原生态的生活图景展示中,生命自有其魅力与意义,不仅演员的面容不再局限于浓眉大眼、国字脸,角色所处的空间也多是不加修饰、充满野趣的真实生活空间。
“野”,郊外也,本为质朴荒凉之地,进入文化语境后有自然质朴、未经雕琢之意,在道家的美学思想中,是不加修饰、充满生趣的自然之美。就20 世纪90 年代演员外形面容的选择而言,呈现出以自然生动代替典雅俊秀的审美变化。大气正派的国字脸、浓眉大眼不再是主角脸的选择标准,伟岸健硕、英俊潇洒也不再是主角身姿体态的衡量尺度,这种承载着儒家修身、修心规范的社会理想范型,渐渐让位于更显自然生动的平凡形象。梁天眯着的小眼睛、葛优光亮的脑门、刘子枫清瘦的样貌,这些朴素的面容不再是端庄雅正的陪衬,曾经的“配角脸”开始成为主角。道家审美观中,真实自然、不为物役才是美,“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11]葛优与梁天“天成”的喜剧脸既具大众化特色,又有特殊性,可以达到“别人演也许就出不来的效果”。[12]在表演课上,王宏伟是表演系老师眼中“最不会演戏的学生”,[13]单从外在条件看,其外形、五官和身高绝对达不到传统影像中主角的标准,但生活状态下自然流出的甩袖子、推眼镜架、眯眼看天、双手抱胸等丰富的身体动作,成就了贾樟柯镜头下从小镇走来的朴素青年。
空间作为角色生活的载体,它需要与角色协调一致,才能营造出人物完整的生活状态。影片中的角色自由穿梭于肮脏凌乱的小巷、破败无序的街道、狭长逼仄的胡同,这些真实的场景正是人物生活的根基。《北京杂种》(1993)中卡子寻找毛毛,穿越的小巷路面脏乱、房屋破败,一旁是正在盖房子的一户人家,在抛砖与接砖的动作间,砖屑时不时掉落在乱糟糟的街道。这种原生态的展现是“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的顺物之性,荆浩在《笔法记》中就曾提出,如果松之物性是“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那么作画时便应即目直寻,呈现其本然,而不是将其表现为“如飞龙蟠虬,狂生枝叶”,[14]不能因一己之好恶遮蔽了“松之气韵”。《巫山云雨》(1996)中的青年穿梭于生硬杂乱的不和谐建筑,《任逍遥》(2002)中的斌斌和小济整天闲逛于郊外的废弃矿区,《十七岁的单车》(2001)中的小坚骑着自行车在昏暗狭窄的胡同里练习,《周末情人》(1995)中的青年男女在下水道、垃圾站旁随音乐摆动。“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15]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些充满“野趣”的毛糙感真实自然地展示着角色及其所处环境。
“目亦同应,心亦俱会”,[1]155在对“形”进行观照的基础上,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从外到内,由目到心,心与目共同参与,在对琐碎生活的直接展示中,借助无目的、无功利性的举止言行,慢慢展现出人物的内在状态。《站台》(2000)结尾处,赵涛饰演的尹瑞娟重新找到崔明亮时,赵涛身着制服,敞着外套,跷着二郎腿,眼神与言语中有试探也有迟疑,最终垂首低眉,把玩着手中的香烟。此时赵涛的表演没有完全做实,神色、言语及手部动作因为缺少明确的指向性而显得模糊暧昧。中国主流的山水画透视观深受“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观念影响,逼真地刻画物象只能停留在纯粹的“应目”,自然少了生趣,只有心存目想,将视觉所观内化,才能在方寸间展现无限的心理空间,才能实现“溪谷间事……屋舍……中庭及后巷中事”皆可“重重悉见”。[16]以此来反观影片中赵涛的表演,没有做实的表演是演员将眼睛看到之物象与内心之情感相结合后,体悟角色内在精神本质的表达。从当初为什么没有离开、为什么从跳舞的文工团女孩变为了身着制服的税务官,到为什么多年后仍独身一人,尹瑞娟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是何时何地因何而变,可能是出于父亲患病无人照顾的实际考虑,也可能是认为漂泊不定的走穴演出终究还是会回到县城,但她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梦想,不然不会有前一场戏中独自一人跟随音乐翩翩起舞的表达。
同样,《苏州河》(2000)中贾宏声饰演的马达总会整夜地看盗版VCD,贾宏声无目的的“看”亦是道家“观物”美学向表演创作的落实。他所呈现出的“看”不是完全做实的表达,不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碟片故事的专注,而是长时间、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正是在任由思绪游离地“看”之下,角色孤独、痛苦等各种复杂情绪才得以慢慢释出。一般而言,孤独是一种缺乏陪伴、无从倾诉、不知方向的感觉,并且这种不知方向会渐渐演化为无能为力的痛苦感。在规定情境中,贾宏声的表演没有停留于纯粹的眼观,而是借助无目的地“看”,在呈现角色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余,达成“应目会心”的呈现。作为曾经幻想着“骑摩托车到很远的地方,做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城市青年,他的痛苦不仅源于孤独,还有深陷于自我的情感寄托。从曾经的远大抱负到现在运送不知名货物,绑架信任自己的女孩并用其换取赎金,贾宏声盯着电视屏幕的冷漠容止可以延展出若干富有深刻内涵的意味,有对于目前处境的无奈,有对于未来的茫然,亦有对于精神世界因消费时代来临而变质的悲哀,在单调的日常生活中,唯有通过看碟片获得存在的感知。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17]这一时期的表演创作在对角色生活作直观的基础上,由目到心,呈现出不加修饰的生活图景与自然真实的内在状态,以此最大限度地保留生活的毛边杂色。
三、畅神:游心于物之初的内在精神
“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1]156澄怀味象的审美实践是为了畅神的达成,畅神即庄子说的“游心”,“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7]261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累、抛除功利目的之后内心自得适性的自由状态。就审美而言,意指摆脱比德观念束缚,悬置实用功利欣赏,达到“畅于己也无穷”的精神自由。这是一种内向化与心性化的审美追求,每当人们身处社会巨变,困惑迷茫于外界之时,以往寄托于世俗名教的价值观念便会发生内转,人们向内关注心灵的真实感受,在心灵上为个体生命自由寻找出路。《北京杂种》(1993)中演员们曾对着镜头讲道“我们都是由着性子活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之初,身处转型时期的青年一代挣脱了世俗之德、荣誉价值的束缚,转而向内关注自身的喜怒哀乐,关照心灵自由。这一时期的电影表演亦呈现出审美变化,从强调社会生活规范,内转到超越道德教化比附,走向内心。演员借助纯然自然的外部动作与言行模式,呈现出剥离了道德实践、名教规范后,角色自由的内在精神状态。
首先,演员在表演塑造时悬置了道德观念的束缚,不为角色的行为本身赋予道德评判,而是更注重角色内心状态的呈现。“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荀子·修身》),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身体是伦理、政治、社会的承载,相较而言,道家文化则强调自然的身体,赤身露体不会显得庸俗粗野,更不会为君子所不齿,反而是近于自由的精神象征。《小武》(1998)中,平日羞于表达情感的小武会在空荡荡的浴室唱歌,此时裸体姿态成为其情绪的出口,角色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在此时显现。《男男女女》(1999)中无论是小博洗澡,还是冲冲夜起,两位演员都自然地将赤裸的全身展现在镜头前,小博在学会使用热水器后,整段侧身洗浴的过程被细致地展露。借助裸露身体的表演塑造,人物的身体从社会性的生存中解放,呈现出了最真实的内心情感。这些将道德悬置,进而充分显现内在情绪的表达是郭象以“适性”达庄子“游心”的现代转写。“夫大鹏之上九万,尺 鸟安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7]35一物与一物各有不同的情态,合乎其自然本性,能够做到“性分自足”,便可达“游”之境地。同样,还有不少被传统观念视作“丑陋”、在以往银幕中罕见的行为也被大大方方地展现于镜头前。《北京杂种》(1993)中的先锋艺术家们满嘴的脏话,《男男女女》(1999)中同性间亲密的肢体接触,《苏州河》(2000)中的牡丹、《安阳婴儿》(2001)中的跟班小弟在公共场合解手,《哭泣的女人》(2002)中的王桂香毫无顾忌地与情人幽会。在这些以自然状态呈现而非文明包裹的言行中,表演塑造超越了单纯的放纵形骸,以悬置道德的方式,将角色内在精神状态的自足自由升华为具有审美品格的生存状态。
在道德层面小偷无疑是丑恶的,《咱们的牛百岁》(1983)中新良外号“三只手”,由于生活贫困,他成为贪小便宜的小偷。影片中新良的戏份较少,在他偷东西的一场戏中,月黑风高,新良蹑手蹑脚从窗户跳入,边小心观察四周,边狼狈地用袖口擦汗,演员的表演配合着带有戏谑的打击乐,俨然一副丑角的样貌。不难看出,此时的演员表演塑造,正是道德劝谕的流露。《小武》(1998)与《少女与小偷》(1985)中,与新良相似的处于主流价值观念之外的人物成为主角,梁小武是扒手,青工小王也一度失足偷窃,在塑造角色时两位演员都合理挖掘了角色人性中的闪光点,最终引发了观众的同情,影片中两位演员的表演塑造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但是表演处理的方式及侧重不同。
以梁小武、小王与各自爱慕的异性相处的段落为例,《小武》(1998)中梁小武与梅梅漫步在歌厅一条街,听到梅梅说“我今天不应该穿高跟鞋”时,小武便走上了台阶,随着梅梅“你咋不往楼上爬,那不更高”的继续调侃,小武则又略显优雅地爬上了二楼。在长镜头的配合下,演员连贯的表演将角色更为细致和丰富的信息一并呈现,在演员王宏伟的塑造中,我们看到了小武作为真实的人的复杂性,小武几乎不言,情感内向,但观众却能在一瞬间感受到小武的自尊、冲动以及内心深藏的教养和温柔,这也是日常生活交往中,我们最为熟悉的隐衷。同样是与爱慕的异性一同在马路漫步的戏份,《少女与小偷》(1985)中,演员袁苑的表演则与短镜头相配合,多以懊悔的神情、支支吾吾的言语以及略显颓废的体态呈现角色意欲改过自新、去恶向善的内心世界。相较于《小武》(1998)悬置了对“小偷”的道德批判,意在呈现个体多面性及内心隐衷的表演而言,《少女与小偷》(1985)中的演员表演是在道德评判的规约之下,通过对“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的现代化转写,力求呈现出角色通过人为努力而归于善的一面。
其次,表演挣脱了习俗名教的牵累。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思想提倡以内在精神的本有状态替代被习俗名教约束的“伤性”。当抛弃名缰利锁对人的束缚,当超脱于外力牵连的“有所待”,当民警形象的塑造变得没有什么事业心,与嫌犯的关系从对抗变化为柔和,人物自由的内在精神便得到了显现。
张明在访谈中谈到《巫山云雨》演员表演时说:“身份并不重要……他们这种生命的状态才是强调的。”[18]演员通过准备戒指、选购建材、与人讨价还价等言行,展现警察忙于筹备婚礼而对工作不上心的情绪状态,角色还脱去警服与嫌犯一同吸烟,甚至为嫌犯理发。在这一规定情境中,警察和作为工人、服务员的嫌犯们,共享着小城即将搬迁而带来的情感变化。这种对名教牵累的挣脱并非是为了反叛而反叛的纵恣,而是任从内在精神的放达,其精神内核继承于庄子的“自得自洽”,是具有“游”之审美属性的内在状态。《任逍遥》(2002)中斌斌“抢银行”反被抓到派出所的一场戏中,警察并未让斌斌蹲墙角、铐手铐,而是与其并肩坐在沙发上,以轻松对话的互动代替严肃的审问。寥寥几句对话,警察最终让斌斌唱歌的举动并非是刻意为之,作为独自值守的警察,照常看完电视后,看着让人生气却又好笑的少年,唯有通过让其唱歌的“调戏”[19]方式解闷,方能排解自己生活的无聊。
同样,《东宫西宫》(1996)中民警小史的塑造亦是借助悬置习俗名教,慢慢释出不假修饰的人性状态。起初的交锋中,胡军饰演的民警小史尚未抛下“警察”这一符号对他的影响,在听到对手台词后,仅就字面意思做出反馈,因此多是阿兰(司汗饰演)主动讲话。此时两人距离较远,坐在各自的位子上,民警针对这些“证词”,也是多以“然后呢”“怎么回事”的追问作为回应。随着两人交谈的深入,胡军的表演塑造发生了转变,通过对阿兰言语间深层意义的挖掘,继而再给到对手反应。阿兰在“坦白”的过程中总会不自觉地陷入自言自语,用大段非口语化的文学性语言抒发内心隐秘的情绪,胡军饰演的民警则会通过打断或呵斥的方式,既终止阿兰的讲述,也提醒自己不要受阿兰影响。此时两位演员的走位已发生变化,两人同处于一个镜头,阿兰从蹲姿改为坐姿,甚至和民警的空间位置也发生了对调,民警坐在了被审问者的座位上。
之后两人的表演塑造到了第三个阶段,即便台词还没被对方说出口,但无论是情绪的铺垫,还是对方的表情举止,都可以揣摩出未说出口的潜台词,并以此给予反馈。规定情境中,阿兰总是会将民警小史混入自己的回忆,由小史假扮自己的男性爱人。作为观众,我们可以通过画面看到阿兰的臆想,但是对小史而言,阿兰暧昧的神情、模糊的言语,已经透露出对自己的试探。面对这种尚未宣之于口的潜台词,民警小史也渐渐融入了阿兰的情感体验,直至升起理解和共鸣。不同于孔融“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20]以公然反抗为目的的“失礼”,亦不同于王武子、石崇之流形而下的肉身放纵,胡军对民警小史情感变化的表演塑造皆从自然真情出发,如同面对“居丧追婢”的阮咸,阮籍认为这是一种不合名教但合乎自然的真情性流露一般,此时民警摆脱名教束缚的情态塑造,亦是违礼而不违道,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种解除道德名教顾虑、注重内在的自由快适,正是“畅神”的精华所在。
自先秦儒家学派起,艺术与政治教化、审美与道德观念就紧密相连,起着规范自我、家庭乃至国家的作用。“十七年”时期与新时期初期,银幕中的青年形象塑造强调“尽善尽美”,《李双双》(1962)中帮助丈夫提高思想觉悟的李双双,《天云山传奇》(1980)中轻物质重精神的罗群、冯晴岚,《都市里的村庄》(1982)中兢兢业业的丁小亚,这些人物的种种言行具有垂范性质,在表现理想人格之美的基础上,达到作用于精神的功用性。到了20 世纪90 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社会的转折巨变促使人们向内关照心灵,这一时期的表演塑造从内心出发,呈现出任其自然、依其本性的表演范式与美学风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大分支,道家文化中关照心灵、返璞归真的思想与儒家文化互为补充,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中,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形象表达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例如,早期电影《野玫瑰》(1932)、《小玩意》(1933)中女性健美野趣的身体展示,近年《芒种》(2005)中热心善良但心中亦有执念的王警官,《路边野餐》(2016)中陈升以内心流转为依托追寻自我。在老庄美学的影响下,银幕中的表演塑造突破了道德比附观念,表现为各有其自成、各有其自用,不仅为银幕中的角色塑造带去新的审美观照方式,也成为透视人物心灵、反思社会变革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