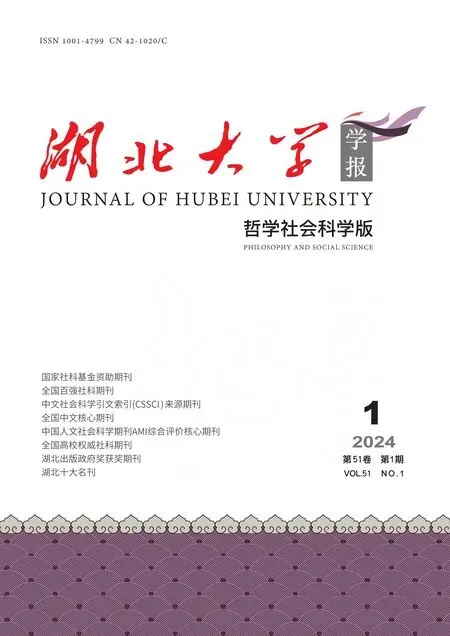自尊与同情:霍耐特对法国和英国承认观念的思想史重构
洪 楼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自《为承认而斗争》(1992)问世以来,承认理论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批判理论的基石,并在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对这一概念的辩护和发展也延续至今。对承认观念欧洲传统的系统性梳理,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2017年霍耐特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承认:欧洲思想史的一个篇章”(“Recognition:A Chapter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的系列讲座(1)“The J.R. Seeley Lectures 2017”,https://www.polthought.cam.ac.uk/seeley-lectures/seeley-2017,2023-02-23.“剑桥学派”(以昆廷·斯金纳等人为代表)有着“思想史熔炉”的盛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语境出发解释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些重要观念。这次讲座促使霍耐特从思想史角度系统性地思考承认观念自近代以来在欧洲的历史源流。,2018年他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承认:一部欧洲观念史》(Anerkennung.EineeuropäischeIdeengeschichte,以下简称《承认》)一书。在这一著作中,霍耐特从思想史角度系统性地梳理了承认观念自近代以来在欧洲的历史源流。这一观念史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呈现了一种从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视角出发的、独特的欧洲思想史,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传统对于承认主题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也能为承认理论添加更多的“历史元素”,自《自由的权利》(2011)出版以来,霍耐特更加侧重于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史语境出发探究承认规范的形成机制。
尽管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深受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的启发,但他在《承认》中对承认观念的法国和英国思想传统的梳理,则清晰地呈现出对承认观念的一些新的理解,并由此进一步深化了其承认理论。对霍耐特而言,一方面,在法国,从道德主义者、卢梭、萨特直至后结构主义者对承认的认知性理解,主要强调了承认观念的否定性维度,即对社会承认的依赖会导致个体无法把握自身的真正个性;另一方面,在英国,从休谟、斯密到密尔的道德哲学,在经验层面上展现了承认规范所蕴含的道德心理学机制。因此,本文将聚焦于霍耐特如何梳理承认观念在法国和英国思想传统中的起源与发展,探究他如何从法国和英国思想家那里的“自尊”、“同情”等观念中发掘出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意蕴。
一、承认观念思想史重构的方法论
在霍耐特看来,承认观念思想史重构的主要困难在于,承认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呈现的“语义特殊性”或“语义差别”:我们对他者承认的依赖,要么被理解为现代道德平等的来源,要么被理解为促进社会有益行为的手段,要么被理解为对真正个体性的威胁(2)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Joseph Ganahl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p.xii.。他认为,区分这些不同语义用法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承认是指某人的社会名誉,还是指某种更深层次的、独立于公众对其评价的东西;其二,承认是一项道德行动,还是一项认知事件。霍耐特根据这两条区分标准进一步阐述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承认理论的基本含义。法国思想传统将承认理解为个人对社会名誉的追求,这一追求使个体无法认知真正的自我。英国思想传统尽管也将承认理解为对社会名誉的追求,但它却使我们能够设想一位内在的中立观察者,进而产生对他人的道德同情。而只有到了德国思想传统中,承认才被设想为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
霍耐特在《承认》一书中言明,对承认观念的历史考察不能仅仅着眼于单个术语的历史用法。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对“承认”这一术语在德语、法语和英语中的对应语词(即“Anerkennung”、“reconnaissance”和“recognition”)作词源学的考察,因为假如只是梳理单个语词的历史沿革,那么我们就会忽略许多的思想资源,而正是这些思想资源从不同的维度呈现出我们以某种相互承认的方式彼此关联。因此,只要诸思想传统中的核心观念(如“自尊”、“同情”、“敬重”等)包含了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意蕴,那么它们就处于霍耐特的探究范围之内。霍耐特对承认观念的思想史重构的另一个方法论要点是,他并非严格地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或“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学科的角度去考察承认观念的历史起源(3)“history of ideas”的另一种常见英文表达是“intellectual history”。在历史学界,剑桥学派的思想史(观念史)有时被等同于德国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因为,除了一些方法论的差异之外,二者都强调社会史研究应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典型观念(如“国家”、“改革”、“民主”等)入手,由此反对实证主义者完全抛开观念来研究所谓的客观历史事实,忽视观念的构成性作用。二者也都反对观念的永恒论(如某些传统观念史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哲学家们总是讨论同样的基本问题)。从霍耐特在《承认》中对德国概念史研究代表人物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反复提及和援引可以看出,他基本认可这一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但他使用“Ideengeschichte”(观念史)这一措辞,以区别于“Begriffsgeschichte”,并非要反对概念史的基本研究方法,而仅仅是想表明由于自己缺乏专门的历史学训练,不得不满足于一种非严格学科意义的、朴素的思想史研究。另外,美国学者Melvin Richter最先尝试将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和德国的概念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一做法引起了争议。受此影响,关于是否存在“剑桥概念史学派”,汉语学界也产生了相关的学术争议,赞成者将上述两种传统归为一类,而反对者认为所谓“剑桥概念史学派”与德国概念史学派之间存在根本的方法论差异,因而二者不能等同。参见M.Richter,“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8,No.2,1987;李宏图:《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方维规:《臆断生造的“剑桥学派概念史”》,《读书》2018年第3期;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因为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观念史或概念史研究,需要证明某一观念的各种版本之间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或者需要通过比对出版信息、私人日记或信件乃至专业的目录学研究,以证明某位思想家的确影响了另一位思想家。因此,霍耐特刻意使用了“Ideengeschichte”(观念史)这一术语以区别于“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4)Axel Honneth,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Berlin:Suhrkamp,2018,S.13.,后者更接近于通常理解的学科意义上的“观念史”。这一做法正是为了强调,他关于承认的思想史重构是一种更为温和的、弱化的观念史研究。也就是说,他的观念史研究不是要呈现一个作者如何影响另一个作者的因果序列,而是依据我们已经熟悉的文献资料来呈现承认思想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这些不同的承认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他尤为注重的问题是,“某一既定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是否给予承认观念以某种特殊的色彩”(5)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4.。因此,他的考察预设了承认思想的“民族特殊性”。但这并非要对民族思维方式或集体态度进行总体考察,而是要探究某个特定国家的社会文化条件如何使那一国家的人就承认观念产生相似的联想。这种相似的联想并非一种历史巧合,而是源自承认观念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传统。
霍耐特的观念史重构选择聚焦于法国、英国和德国思想传统的理由在于:其一,这三个国家的政治思想传统已经分别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为我们所熟悉,因而便于进一步的系统性比较;其二,这三个国家在观念史中事实上处于核心位置,这些国家的作者几乎排他性地创造了欧洲政治思想史的“经典”(霍耐特提到斯宾诺莎和苏亚雷斯作为少数例外),并且占据着当前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其三,除了上述两个实用的理由之外,霍耐特还援引柯塞勒克和美国历史学家西格尔(Jerrold Seigel)的共同看法,即英、法、德的历史发展代表了17世纪以来欧洲市民社会发展或资产阶级现代化的三种典型模式,并且这三种模式分别体现在英、法、德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之中。柯塞勒克论证说,在法国,启蒙运动带来的普遍平等观念让“citoyen”(公民)概念深入人心,这使得它与因占有财富的多寡而区分社会地位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概念(如grand bourgeois和petit bourgeois的区分)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都是这一张力的反映。德语的“Bürger”(市民)由于混杂了太多的传统和现代的不同含义,以致无法表达一种一致的革命目标,因而只具有很弱的政治影响力。这导致1848年的德国革命没有一个地理中心,同时也没有明确的新市民的诉求。在英国,“公民”概念只起到了非常边缘化的作用,相反,直到19世纪,具有中世纪传统的合法性概念和颇具现代社会经验色彩的词汇之间依然相互竞争,这使得“middle class”(中间阶级)被迫妥协,以便温和地解决矛盾和进行改革(6)Reinhart Koselleck,“Three bürgerliche Worlds?Preliminary Theoretical-Historical Remarks on the Comparative Semantics of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England,and France”,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8-217;Jerrold Seigel,Modernity and Bourgeois Life:Society,Politics,and Culture in England,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31-32.。因此,“citoyen”、“Bürger”和“middle class”的语义差别指明了欧洲新社会秩序的三种基本选项。霍耐特受此启发而断言,如果说英、法、德三国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能够反映资产阶级现代化所经历的这三种典型发展模式,那么,选择对这三个国家的承认观念进行历史分析,也并非随机和实用的,因为“‘承认’观念在这三个国家所呈现的语义色彩和腔调,将反映欧洲意识视域已经证明的、能够呈现的仅有变化”(7)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8.,并且这一历史分析将大体上能够穷尽这一术语在近现代欧洲思想史中的含义。此外,霍耐特认为,尽管在欧洲其他地区也可以找到有启发性的承认表述,但它们都没有确立起关于承认的持久含义和影响。
根据上述的方法论理由,霍耐特着手在特定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梳理承认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并且,只要这些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核心观念明显地带有相互承认的意蕴,那么它们对于各自语境中的承认观念就具有构成性意义。由此,霍耐特将论证的重点放在了“自尊”、“同情”等观念上面。
二、从卢梭到萨特:承认的认知性理解
霍耐特从法语思想传统开始其承认的观念史重构,因为他将欧洲近现代承认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了17世纪的法国,并反对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洪特(István Hont)将这一源头追溯至霍布斯。洪特在《商业社会的政治学》中论证,霍布斯第一个强调了承认对于人类共存的至上重要性,即人们首先是出于“心理上的”对荣誉和卓越的欲求(社会的承认),而非出于“身体的”需要,与他人进行社会性的联合。因此,寻求社会承认的心理需求才是理解政治的第一要素(8)Istvn Hont,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11.。但霍耐特认为,这并非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论断是,自然状态中的有理性个体出于身体安全而臣服于一位主权者的统治。反过来,以这一策略性计算为基础而掌权的君主,首先要确保其臣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不是满足社会承认的欲求(9)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0页。。所以,即便霍布斯那里有一些关于承认的心理学—人类学的洞见,但它们与其核心的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着裂隙,因而不能直接将霍布斯视为承认观念的理论先驱。
在霍耐特看来,在17、18世纪的法国现代化进程中,旧的封建秩序所固有的社会联结和阶级附属逐步瓦解,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行为要求不再是固定的,因而个体必须追问自己所占据或想要占据的社会地位,并力图获得相较于他人的优势地位。这种由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承认问题走向了前台,成为哲学和文学的主题之一。与此同时,承认观念还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法国式的否定含义,并且承载这种否定含义的法国式概念是“自尊”(amour propre)。霍耐特注意到,卢梭之前的法国道德主义者如蒙田、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等人在其格言式著作中已经从世俗而非神学角度谈到了人性中的“自尊”。他总结了拉罗什富科《箴言集》的主旨,即个体出于“自尊”这一自然激情而强烈地期望获得由名誉、声望等体现的社会敬重或承认,甚至为此不惜伪造他们并非真正拥有的品质。在这种自尊激情的驱使下,个体不仅无法确定互动伙伴的真正品质,而且在自我关系方面,陷入一种自我欺骗,从而无法辨识自己的真正品质。这些富有辛辣警句的文学作品,尽管有其深刻洞见,但并未从概念上精确且自觉地思考人的主体间性,也未试图理解社会互动的动态机制和冲突本质。不过,这些作品依然昭示着法国承认理论的诞生,揭示了个体总是试图通过表现自己并非真正拥有的品质而获得他人的敬重。霍耐特简要回顾了《箴言集》产生的历史背景,即17世纪中叶福隆德运动(1648—1653)失败后,失势的法国封建贵族为保留其旧有的特权,争相向专制君主及其亲信展现所谓的卓越品质,以获得国王的青睐(10)参见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71-73页。。他特别关注的是,在这种出于“自尊”而伪造道德品质所赢得的承认中,包含着一种否定性的认知色彩。就是说,当个体刻意伪造出某些卓越品质以赢得社会承认时,他将无法认识自己和他人的真正品质。在霍耐特看来,道德主义者作品中所包含的关于承认的否定性认知含义对整个法国承认思想传统具有深远影响。
然而,真正系统地论述“自尊”概念,并呈现其承认的否定性意蕴的法国思想家,当数卢梭。在卢梭所处的18世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此时,争取宫廷支持的主要力量是处于上升势头的资产阶级。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希望进一步获得政治影响、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财政特权等,当时的唯一实现途径就是争取专制君主的支持。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资产阶级不再如贵族那样把展现传统的美德当作争取支持的手段,而是把时尚与奢侈视为展现荣誉的更好手段。
尽管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以下简称《论不平等》)的主要议题是社会不平等问题,但其理论核心是“自尊”概念,主要探讨“自尊”的危害如何在社会不平等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卢梭首先论证说,人类历史的“原始时代”是值得赞美的,而人为的文明(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却腐败了,但这一进程已无法逆转(11)卢梭在《爱弥儿》中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塑造新人、新风尚、新秩序,进而保障社会幸福。参见李平沤:《译者前言》,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74-375页。。他通过自爱(amour de soi)与自尊的区分来论证不平等的起因。前者是一种与维持自我生存相关的、自然的情感或冲动,后者则是在文化习俗中新生的需求,即想要比他人显得更有价值并赢得众人的尊敬,但在卢梭看来,“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开头第一步,就是从这里踏出的……最终给人类的幸福和宁静带来了巨大的危害”(12)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第276页。。自然状态是没有自尊心概念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观察其自身的唯一观察者”,当作自己才能的“唯一裁判者”,没有攀比的情感,也不存在彼此故意的冒犯、傲慢或轻视(13)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第343页。。然而,一旦个体依据同类所期待的评价而行动时,他就努力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尊敬,并将这种获得成功的能力确立为一种社会性的标准。采纳这样一种社会性视角将会迫使个体进入一种竞争状态,参照既定的社会标准与同辈进行比较,以此证明自身的能力、卓越或优越性,但是却丧失了对于自身真正个性的辨识。“野蛮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终日惶惶不安的文明人的生活价值,是看别人的评论而定,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是以别人的看法作自己看法的依据的”(14)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第305页。。由此,霍耐特认为,卢梭赋予承认的否定性含义就在于,个体主体“将‘自尊’中所寻求的那种承认,排他性地视为对于那些使某个主体脱颖而出的品质的承认”(15)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26.。
当然,霍耐特考虑到了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的“卢梭难题”(Rousseau problem)对这一否定性论断可能造成的挑战。这一难题是指卢梭《论不平等》的悲观诊断与《社会契约论》的乐观态度之间的裂隙,二者似乎难以调和。在前一著作中,卢梭强调对公众意见的依赖导致了自我的丧失;而在后一著作中,他似乎又相信这同样的一些人能够决定自身的意志。对于这一难题,霍耐特提到了卢梭研究专家登特(N. J. H. Dent)的解释方案。登特试图通过区分“自尊”的两种形式来化解这一难题,他认为卢梭区分了自尊的过度或“发烧”形式与“健康”形式。进一步而言,“自尊”概念所包含的承认的需要,在不利的社会条件下会呈现出有害的形式,而在平等共和政体的条件下则呈现为相互尊重这一健康的形式。霍耐特认为这一解释实际上是赋予了“自尊”完全不同的含义,使它具有了心理上的可塑性,就是说,它能够依据社会条件来改变其呈现形式。但他并不赞同登特等人的这一解释,而认为卢梭终其一生都对“自尊”持保留意见。这种否定性的理解在卢梭那里从未发生根本变化,只不过相比于《论不平等》,其后期著作中所给出的理由复杂且微妙。
首先,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区分了公意和众意,前者只考虑共同利益,是“让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而后者考虑的则是个人利益,是个别意志的叠加(16)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第45-46页。。公意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是“由全体个人联合起来形成的公共人格”或者“共同的‘我’”,是每个“个人同他自己订约”(17)参见卢梭:《卢梭全集》第4卷,第32-33页。另可参见邓晓芒:《从黑格尔的一个误解看卢梭的“公意”》,《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根据这一公意概念,个体既是主权者又是主权者的成员,这一说法预示了后来康德的一个论断,即每一个有理性者都是目的王国的首脑及成员,后者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白式的理性构想。霍耐特在卢梭的论述中所看到的是,个体意志的形成不依赖于他人,这里面带有对“自尊”所包含的社会性态度的怀疑。
其次,霍耐特从卢梭身后问世的两部著作——《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以及《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得出了如下基本论断:对承认的追求通常会导致一种虚假的自我理解,从而无法区分伪造的自我和真正的自我。在前一著作中,卢梭认为,社会文化总是要求我们从他人视角来评价自身,并且由于这一视角恒常地充当一种内在评价标准,因而我们无法将其搁置一旁来自我评判。他还进一步诘问:“一个自感配受尊重和荣誉而公众又任意歪曲贬损他的形象的人……应该用他当之无愧而又总是受到否认的赞美之辞谈他自己吗?”(18)让-雅克、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袁树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霍耐特由此认为卢梭想表达的是,对社会承认的依赖会导致我们无法把握自身的真正个体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卢梭描述了圣皮埃尔岛上的宁静生活所带来的满足和乐趣。这种满足和乐趣不在任何身外之物上面,而在我们自身,在于“排除一切其他欲念而只感到自身的存在”,在这里我们不会因追求社会名誉而失去自我(19)卢梭:《卢梭全集》第3卷,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0-91页。。
总之,根据霍耐特的解读,卢梭通过一种关于人的需求之本性的哲学人类学,来探究“自尊”概念包含的否定性的承认含义。所谓“自尊”其实是为了追求他人的尊重,或者说是用同辈人的视角来评价自己。那么,承认在卢梭那里是指认知性的肯定或认可,还是指道德尊重呢?霍耐特认为首先是认知性肯定。也就是说,通过竞争性的努力让他人相信自己的确具有某些品质,然而这一强烈兴趣常常会让我们倾向于伪造自身的品质从而无法真正地认识自身。
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自尊”在从18世纪末开始的100多年里已不再是法语文化生活的主要范畴,社会政治(Gesellschaftspolitik)的议题走到了前台。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萨特、梅洛-庞蒂、马塞尔等思想家的阐述,承认关系才再次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霍耐特重点关注了萨特的主体间性分析的承认意蕴。如果说对卢梭而言,承认的否定性含义在于导致主体对于自身品质的不确定性,那么对萨特而言,承认的否定含义则在于导致主体失去了“自为存在”和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区分了“自在存在”(being-in-itself /être-en-soi)和“自为存在”(being-for-itself/être-pour-soi)这两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存在样态。前者是指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世界(20)“自在存在”既非意识,亦不等同于客观物质的存在,是一种超现象的存在。由此,萨特试图避免实在论和唯心论。参见杜小真:《萨特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2页。,后者则是意识的意向活动所指向的存在。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自为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自在的纯粹虚无化”,但同时,人的自为存在总是努力实现并设定新的可能性,因而揭示了自为的意义是一种“命定”的自由(21)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45、174页。。霍耐特在此聚焦于萨特如何通过“注视”(the look)来分析主体间的关系。我与他人同样作为“自为的存在”共存于一个世界之中,他人的世界与我的世界相混交错,他人的出现引起了世界的混乱、分裂和冲突(22)杜小真:《萨特引论》,第116-117页。。因为在别人的注视下,我变成了自在的存在,或者说被物化了。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逃脱不了他人的目光时,“他人就是地狱”,自为存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自为的存在与他的‘为他的存在’是不能够同时发生的”(23)杜小真:《萨特引论》,第138页。。霍耐特认为,尽管我们大概了解了萨特关于主体间相遇的上述结果,但在这一结果发生之前还是存在着承认的环节。在一个主体感到自身被另一个主体观察的那一刻,他就突然获得了一种“与他人共在”(being-with-others)的完全确定性,而且双方都在这种确定性中感受到自身作为一个“自为存在”的个体而得到承认(24)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43.。不过,这种承认是短暂的,一旦某个主体在既定活动中感到被另一主体观察,他就感到自身被剥夺了完整的“自为存在”,即上文所说的物化。霍耐特在这里还补充了一个论断,即他者的承认将赋予我们某些固定的品质,使我们无法认识真正的自己。因此,在他看来,萨特揭示了,感受到被他人“注视”这一经验同时包含着承认和物化:一方面是对我们的“自为存在”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未能如此这般地承认这种“自为存在”或自由。
萨特并不像卢梭那样从关于人性(或类本质)的人类学出发,而是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因为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类本质,存在的过程乃是人的不断自由选择的过程。但霍耐特认为,萨特在关于承认的否定性理解上面与卢梭相似,即都不把承认理解为一项道德规范性的行动,而是理解为认知行为。此外,霍耐特试图依据阿尔都塞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进一步支撑这一带有法国特色的“文化偏见”,即对承认的否定性强调(25)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52.。尽管后结构主义者是要消解主体的传统理论地位,将主体性的获得,要么视为意识形态的显现,要么视为无意识的作用结果(“大他者”操控下的无意识表演),但是,承认作为系统组织的实践后果,比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造成其社会成员的甘愿服从,有助于维持现存秩序中的宰制关系。至此,霍耐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足够多的证据来断言法国思想中对承认的否定性强调。
三、从休谟到密尔:承认的道德规范性
与17、18世纪的法国关注社会等级及其相应冲突不同,同时期的英国哲学所回应的主要时代背景是,商业化社会的来临逐渐侵入传统道德习俗所规约的社会公共生活。这一时代变迁反映在英国文学和哲学中关于自利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广泛讨论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种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学观点,即对同胞利益的关切这一自然倾向是一切道德原则的基础。在这里,“道德感”(moral sense)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从自利出发推己及人的“同情”(sympathy)概念又是理解道德感的关键。霍耐特将此称作主体间承认观念的英国版本,与法国的“自尊”的否定性承认含义不同,“同情”有着完全正面的含义。霍耐特重点分析了休谟、斯密和密尔的相关论点。
受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哈奇森的影响,休谟试图在经验层面上考察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反应和评价,并认为这种反应首先源于自然情感而非理性认识。“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理性的结论”,“理性只是情感依据某种辽远的观点或考虑所作的一般的冷静的决定”,甚至“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26)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7、626、453页。。休谟进一步将借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自然情感追溯到快乐或痛苦的情感,根据快乐或不快,我们相信某些品格是可以赞美或可以责备的(27)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经验主义者,休谟将必然性归结为较大的概然性(probability),因而在通则(general rule)之外,总是存在着可能的例外情况。因此,无论是在“论知性”还是在“论情感”中,他总是在论述某种通则或一般的自然倾向之后,分析一些例外情况。。而苦乐情感和对他人行为的道德判断之间的重要关联机制则是“同情”。只有借助“同情”这一人性的自然倾向或“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原则”(28)休谟:《人性论》,第620、661页。,我们才能彼此传导快乐或不快的情感。霍耐特将此解释为,与他人共有的情感经验作为“看不见的纽带”,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感受他人的幸福或痛苦,并对相应的行为和品格作出评价。但我们还不能因此就把这种“情感的共振”(affektive Einschwing)等同于“承认”,因为“对他人的规范性依赖”才是承认的题中之义(29)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61.。因此,“同情”只是承认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休谟还提到关于同情原则的潜在反驳意见,即同情容易发生变化,比如受距离远近的影响,我们对本国人比对外国人较为同情,然而,我们对有些道德品质却给予了同样的赞许,虽然同情虽有增减,但我们的道德尊重却没有改变,因此“我们的尊重并不是由同情发生的”(30)休谟:《人性论》,第623页。。对此,休谟的回应之一是,“我们各人如果只是根据各自的特殊观点来考察人们的性格和人格,那么我们便不可能在任何合理的基础上互相交谈。因此,为了防止那些不断的矛盾,并达到对于事物的一种较稳定的判断起见,我们就确立了某种稳固的、一般的观点,并且在我们的思想中永远把自己置于那个观点之下,不论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如何”(31)休谟:《人性论》,第624页。。因此,休谟认为我们有时的确会根据这种一般判断来改正自己的情绪。但同时他又指出,我们的情感并不愿意随时接受一般判断的决定。但无论如何,霍耐特认为,这里还是隐含着一种“理想的”中立旁观者的观念,它对我们可能产生的道德偏见起到矫正作用。并且,在休谟《道德原则研究》中,这一中立旁观者的观念更为明显,在那里,旁观者有时是指现实的人,有时则是指我们内心的虚构人物。不过,休谟对“旁观者”的论述似乎导致了其道德理论的内在张力:一方面,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旁观者,都指涉了某个外部主体,它有着某种道德的规范性权威;但另一方面,休谟又认为只有内在欲求才能驱使我们进行道德行动。但在霍耐特看来,如果暂时将这一张力搁置一旁,仅考虑外部主体的规范性权威,那么人际承认的迹象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无论是在《人性论》还是《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都论述了我们对于社会名誉的追求。在前一著作中,休谟认为由于同情的作用,我们能够从他人的赞美中获得快乐,因而我们追求自己的社会名誉,努力符合他人对我们的行动的期待(32)参见休谟:《人性论》,第352-360页。;在后一著作中,休谟也同样认为,“通过热切而不懈地追求世俗的声望、名声、荣誉,我们经常省察我们自己的举止和行为,考虑它们在那些亲近和尊重我们的人们眼中形象怎样”(33)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8-129页。。简言之,休谟认为我们之所以从不偏不倚旁观者视角来检视自身的行动,乃是出于对自身名誉的关切。因此,霍耐特最终还是将休谟的道德理论归结为“内部主义”(internalism),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一动机,即“从不偏不倚的外部主体视角来检视自己”,是来自最内在的欲求,而非来自外部强加的规则(34)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66.。
与卢梭的“自尊”所蕴含的对承认的怀疑态度不同,休谟继承了由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所发展的乐观的人类学。进一步说,对他者之承认的依赖,意味着我们赋予自身以规范性权威来共同决定我们的行为取向,从而有益于普遍的社会福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休谟对人际承认的初步的和谨慎的探索。同时,休谟认为,我们的同情心是变化着的,依据同情原则进行道德评价时可能产生谬误和偏见,因此矫正可能的谬误或偏见,需要采取不偏不倚旁观者的视角,以便作出尽可能客观的判断。霍耐特从中看到了人际承认的初步构想,即我们赋予另一主体以规范性权威,从而通过赞成或批评来展现我们自身的行动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但是,休谟没有在经验层面上说明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评价如何具有道德权威性。因此,霍耐特评论说,就从主体间性出发反驳个体主义这一意图而言,休谟只完成了一半,而只有斯密才清楚地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学会让道德行为依赖于更为完备的社会承认形式”(35)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72.。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斯密那里,我们才能完整地了解18世纪英国社会关于人际承认的正面含义。
要阐释斯密思想中的承认观念,霍耐特首先碰到的疑难就是“斯密难题”,即《道德情操论》所论述的“同情”与《国富论》预设的“自利”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张力。这一难题意味着我们不确定斯密思想中有没有一贯的道德理论。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学术界发生的这一争论,最终以大多数学者否认存在所谓“斯密难题”,并认可上述两部著作之间的一贯性而收场。其中,以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对二者一贯性的辩护最为知名,他认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其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并且限制市场中的私人利己主义乃是其一贯的立场(36)Keith Tribe,“‘Das Adam Smith Problem’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mith Scholarship”,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34,No.4,2008.。霍耐特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斯密思想中的承认理论。
与哈奇森和休谟一样,斯密也肯定了我们可以在经验层面上找到一种同情的自然情感。但他界定我们的同情能力的方式,与休谟有所不同。休谟把“同情”看作是受他人情绪感染的一种被动能力,而斯密则认为“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37)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页。,因此,我们是依据想象力“投射性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38)与这种“投射论”(projection account)相反,休谟的“同情”被解释为一种“感染论”(contagion account)。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73.。由此,霍耐特着重论述了《道德情操论》中与人际承认观念相关的核心要素。他认为,斯密从上述“同情”观念出发,论证了道德态度和德行如何是普遍有效的,或者说如何被一切主体认为是值得欲求的。并且他把斯密的论证总结为三个步骤。第一,从经验观察中归纳出我们同情他者的自然倾向,并进一步断言,与他人情感和谐的需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情感经验中的相互期待,并没有揭示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原则。第二,我们运用想象来评判他人的情绪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标准是,这一情绪对于引发这一情绪的场景而言是否“合宜”(propriety)(39)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4页。。但此时,该标准的起源仍然不清楚。第三,规范性标准来自中立的旁观者视角。起初,我们设想自己处于旁观者位置上,学习如何以某种情绪上适当的方式对某种行为作出反应。进一步,我们设想他人在受某件事情影响时,也是从旁观者角度思考合适的情绪反应。因此就产生了一种相互的且共同的欲求,即希望不仅得到互动伙伴的赞许,而且得到外部观察者的赞许。
然而,在霍耐特看来,斯密还在上述“情绪相互性”(emotional reciprocity)模型之上补充了两个要素,以便能够“在其自然主义伦理学中推导出他认为能够普遍地得到辩护的伦理德行”(40)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77.。其一,进一步澄清不偏不倚旁观者的本性。在互动双方达成一致的过程中,随着“同情的圆圈”的逐步扩大,规范性地评价情绪行为的旁观者只会越来越抽象,这样才能具有普遍性。其二,将这一普遍化的旁观者想象为我们的内在良心,而非纯粹的外部评价者。这样一来,对情绪行为的自我检视所参照的规范性标准,就来自逐渐普遍化的他者的内化。到此,就可以清晰地得出,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何以具有道德权威。同时,斯密对我们遵从道德评价的动机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即我们规范性地检视自身的行为首先不是为了获得赞扬或喜爱,而是为了证明我们实际上配得赞扬或喜爱(41)参见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58-159页。。霍耐特指出,斯密的论证存在着张力,因为一方面,经验主义是斯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因此他肯定我们对社会赞扬的自然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对不偏不倚旁观者的论述有时走得似乎太远,以至于提出了一种与我们的“经验”本性不同的“理智”本性,这种“理智”本性类似于康德对人作为理智世界存在者的表述(42)参见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60-163页。,这与其经验主义立场相悖。不过,霍耐特关注的是斯密理论中的承认观念,并认为这一观念在斯密那里包含两种形式。第一种承认形式是一种自然的承认形式,每一个体希望通过直接的情感纽带而与他人联结起来,但这还不足以保证我们会自动地以恰当方式同情他人,由此需要进展到承认的第二个阶段。这第二种承认形式依赖于普遍化的他者,因而个体之间的交往是“间接的和以他者为目标的”,此时,“承认首要地在于一个由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理想化共同体,我们使这一共同体内化并配以道德权威,以评判我们情绪的适当性并由此形成我们个体自我的性格”(43)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81.。
基于上述解释,霍耐特反驳了关于“斯密难题”的一种流行看法,即斯密的首要目标是为了不受限制的市场进行辩护,这一看法源自《国富论》中关于个体自利的社会效用的相关论述。但如果斯密的经济理论不是对自由市场的直接辩护,而是必须从其道德哲学出发来理解的话,那么对《国富论》的另一种更为准确的理解则是,斯密试图阻止市场中经济自利的进展,并且试图凭借一些限制手段和制度,将道德考虑糅合到新兴的市场经济之中。因此,霍耐特认为,斯密一贯的哲学目标是“通过阐述总是把我们彼此关联起来的承认关系,来反对资本主义信念的传播”;而斯密思想的主体间承认的观念则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这一自然意愿,即“通过由所有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普遍化他者的赞许或批评来教育我们以一种促进公共善的方式而行动”(44)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84.。
为了找到更多带有英国特征的承认观念,霍耐特还分析了更为晚近的密尔社会政治理论中的承认意蕴。在他看来,密尔也相信赞扬或责备的道德力量,并将这一力量追溯到人的社会承认的需要。但密尔是以其对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的辩护而知名的,“普遍化他者”一开始在其理论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因此,似乎很难把他与主体间承认的议题关联起来。霍耐特首先认可这一基本论断,即密尔最为关注的是个体权利,并认为自由社会就是要创造一种社会条件以尽可能少地限制个体,同时实现个体的独特性。但霍耐特认为不能把这一基本论断作狭隘理解,从而排除密尔思想中其他的理解可能性。因此,他作出了两点提示,以反驳这种狭隘理解。第一,除了论述基本自由权和相关社会制度外,密尔身后问世的《论社会主义》中讨论了对于工人更为有利的、新的经济形式的可能性。第二,以赛亚·伯林最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密尔社会理论的论证方式到底是如一般所认为的功利主义的,还是完善主义的。假如前者成立,那么从个体利益出发的功利主义预设就似乎与主体间承认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的张力;但假如后者成立,那么密尔关于美好生活的构想,就是一种制度原型而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标(45)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87.。但霍耐特将这一元伦理学问题搁置起来,而聚焦于密尔如何解决不同个体之间的自我实现的冲突问题,即社会控制的手段问题。他认为,在《论自由》和《功利主义》这两部著作的一些关键段落中,密尔找到的防止或仲裁个体冲突的手段是,“通过道德赞扬或责备激发主体去尊重其同辈人的利益”,并且“这要比法律惩罚的威胁更为有效”(46)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88.。尽管密尔提出了对“社会工具”的担忧,如“多数人的暴政”或“道德警察的宰制”,但对他而言,谨慎的、自由主义的公共赞许仍然是最好的解决冲突的手段。因此,霍耐特评论道,尽管与休谟和斯密不同,密尔克制使用旁观者或内在评价者的观念,但他仍然相信得到共同体的敬重构成了我们行动意图的内在权威,从而将我们在道德上与他人关联起来。因此,在霍耐特看来,哪怕这三位思想家都没有使用“承认”这一术语,但他们的确都持有对于人际承认的肯定的看法。
四、结语
根据霍耐特的重构,在法国思想传统中,每个主体对同胞的承认的依赖被视为对本真的自我关系的威胁。而在英国,对他人承认的依赖被视为道德自我控制的一个机会。在霍耐特看来,法国和英国哲学文化中的承认理解,都没有把承认设想为“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具有同时相互性的事件”(47)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94.,而只有在德语语境中,才有了这一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承认”术语的理论起源及其完整意义(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只有到了近代早期的德国哲学中才初现端倪。在德国,对他人承认的依赖才被视为个体自我决定的可能性条件。尽管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语境中已经事实性地形成了关于承认观念的理解差异,但我们在理论上依然可以思考是否能够出于某种充分的理由将它们整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完备的”范式(48)Axel Honneth,Recogni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p.145.。由此,霍耐特在《承认》中进一步探讨了对这三种承认理解进行整合的可能性。然而,从目前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霍耐特这一思想史研究工作——对法国和英国承认观念的思想传统进行重构,使我们能够在主体间相互承认这一基本含义之上,进一步理解承认观念的丰富内涵:我们不仅可以把握承认的否定性含义所蕴含的社会危害,也可以澄清承认的肯定含义对于道德自我控制的心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思想史重构工作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一次深化。
近年来,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性思想家,不约而同地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论证各自规范性思想的内涵,只不过前者所要辩护的对象是交往理性,后者则致力于承认理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二者都认为应当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出发来思考规范性原则的起源,这种从“是”中寻求“应当”的做法,必然要求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思想史研究。同时,这种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做法,也彰显了批判理论的思想史厚度。霍耐特的重构工作展现了其深厚的思想史功底和视野,细致且巧妙地涉及了卢梭难题、斯密难题等经典问题,并从中发掘出对承认的新的理解。但这种“六经注我”的研讨风格,在其批评者看来,可能有对思想史任意裁剪和拼接的嫌疑。有评论者质疑说,霍耐特对于英法思想传统的重构所涉及的文本和思想家是高度选择性的,因为似乎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反驳霍耐特关于英法承认观念的一般结论,比如,法国的涂尔干认为主体间的相互依赖会导致社会团结,而英国的埃德蒙德·伯克却认为他人的赞誉和肯定会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和心理影响(49)Jean-Philippe Deranty,“Recognition in a Historical Key:Axel Honneth on the History of Recognition and Social Freedom”,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Vol.1,No.2,2022;David Kretz,“Recognition for Good Europeans:On Axel Honneth’s Recogni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History,Culture and Modernity,No.9,2021.。这些反驳也是霍耐特需要进一步回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