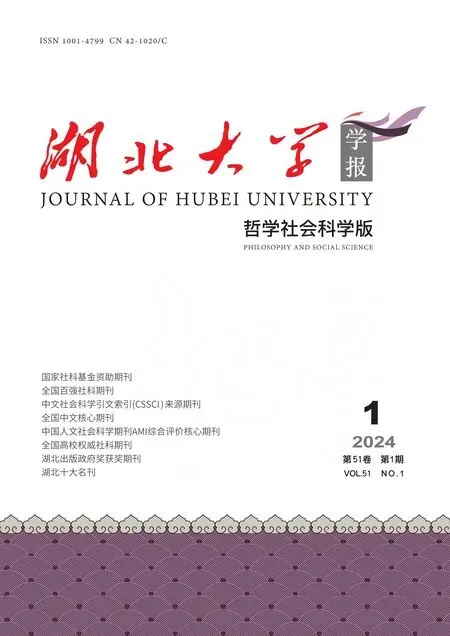同安悟道: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
乐爱国
(上饶师范学院 朱子学研究所, 江西 上饶 334001)
引言
朱熹(1130—1200)于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泉州府同安县(今属福建厦门市)主簿;绍兴二十三年赴任,途中始见李侗;至绍兴二十六年任职期满(1)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223页。。在任同安县主簿期间,除了勤勉于职守,朱熹在学术上正处于由佛归儒的重要时期,其中最关键的是他对二程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因而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的觉悟和融会贯通,简称“同安悟道”。
今人考察朱熹同安悟道,缘起于《朱文公文集》所收录的朱熹的诗《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衾听子规?”(2)朱熹:《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钱穆根据诗中所言“一官今是五年期”,推断该诗大致写于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期间绍兴二十六年(3)钱穆:《朱子新学案》第3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又根据《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中其他材料,认为该诗写的是当时朱熹“以事至漳”,“宿德化剧头铺”所发生的事。关于“剧头铺”,清康熙《永春县志》注曰:“朱文公夫子常至,止一宿,有诗云:‘一官今是五年期,鞅掌贤劳只自嗤,如何独宿荒山夜,雨拥寒衾听子规。’”(4)郑功勋修、宋祖墀纂:《永春县志》第二卷《规制志》之四《铺舍》“剧头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此诗虽与《朱文公文集》中所载的诗略有差异,但应属于同一首,只是传抄有所差误,由此可以证明朱熹所宿剧头铺当在永春县。雍正十二年(1734),永春县升为永春州,下辖德化、大田二县。乾隆五十一年(1786),时任永春知州郑一崧将朱熹该诗刻碑立于永春的剧头铺(5)永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春县志》,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年,第859页。。因此,朱熹所谓“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应当理解为朱熹前往德化,宿永春剧头铺,夜闻杜鹃叫声;钱穆以为该诗写的是朱熹“以事至漳”,“宿德化剧头铺”,恐有误。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载,朱熹于绍兴二十六年三月“至德化,宿剧头铺,寒夜苦读《论语》,顿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6)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第204页。,并且还说:“朱熹荒山寒夜听杜鹃啼叫苦读《论语》而顿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其所悟‘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实即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事有小大’为‘分殊’,‘理无小大’为‘理一’,故胡泳记此朱熹闻子规啼而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语录下又云:‘泳续检寻《集注》此章,乃是程子诸说,多是明精粗本末,分虽殊而理则一……此是一大统会,当时必大有所省……’”(7)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第205页。在这里,束景南不仅对朱熹同安悟道作了记述,而且强调朱熹同安悟道“其所悟‘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实即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在论及朱熹早年思想变化时指出,绍兴二十六年春,朱熹因公事出差到德化,寓居在剧头铺寺院,寒夜一边听着杜鹃的啼叫,一边苦读《论语》,通宵不眠地思索;正是经过不断思索,他忽然从对程颢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困惑中顿悟,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谈起这一不同寻常的“杜鹃夜悟”。束景南还说:“朱熹觉悟到的儒家‘真谛’,就是‘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这实际上就是李侗对他说的理一分殊,‘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8)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1-142页。
不可否认,朱熹后来撰写的《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对二程的解读作了概括,并运用“理一分殊”概念进行阐释,提出“其分虽殊,而理则一”(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1页。;直到晚年讨论二程的解读时,他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明确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1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8页。。但是,这并不等于朱熹早年同安悟道已经觉悟到“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并且有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事实上,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以及“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的提出都是同安悟道之后的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论语集注》运用“理一分殊”概念阐释二程的解读,还是晚年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朱熹都特别重视二程所言“君子教人有序”。据此可以推断,朱熹同安悟道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对二程所言“君子教人有序”的觉悟,并由此而展开。所以,束景南以为朱熹同安悟道“其所悟‘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实即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尚需要作出更多的论证。
与束景南不同,韩国学者刘承相在《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中通过深入分析《朱子语类》中诸多相关文献资料,同时参考《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所引的二程解读,作出推断,认为:“朱子当时对该章参究的主要疑案,不是对原文大意的领会问题,而是对二程所言‘理无大小’与‘君子教人有序’,‘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的关系上感到互相矛盾的问题。……及至夜间觉悟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它事也。’此则为同安觉悟之语。”(11)刘承相:《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朱子语类》载朱熹说:“因在同安时,一日差入山中检视,夜间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7页)其中“其曰‘理无小大’”可能是指二程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因此,“‘理无小大’……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或许是朱熹同安所悟,但刘承相将该段直接称为“同安觉悟之语”,恐证据不足。在刘承相看来,朱熹同安所悟并不是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之大意的领会,而是感到二程的解读既讲“理无大小”又讲“君子教人有序”,既强调“洒扫应对”又重视“精义入神”的互相矛盾,朱熹同安悟道则是对这一困惑的觉悟,从而意识到二程讲“理无大小”正是要“教人有序”,而重视“洒扫应对”并不是只讲“洒扫应对”,不用做其他事,是要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简而言之,是对二程既讲“理无大小”又讲“君子教人有序”的觉悟。显然,刘承相对朱熹同安悟道的理解,与束景南所讲朱熹同安悟道在于“顿悟‘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其所悟‘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实即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多有不同。
刘承相认为朱熹同安所悟是对二程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既讲“理无大小”又讲“君子教人有序”的觉悟,固然有一定依据。但无论是二程的解读,还是朱熹对二程解读的觉悟,实际上都是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并非如刘承相所言“不是对原文大意的领会问题”。因此,朱熹同安所悟之道,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需要围绕《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深入分析二程的解读以及朱熹对二程解读的困惑与觉悟。更重要的是,同安悟道既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也是朱熹后来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起点。而且,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对二程的解读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超越了前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天的《论语》解读也仍具有参考价值。
一、同安悟道对二程解读的觉悟
朱熹同安悟道,缘起于二程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解读。《论语·子张》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1页。
子游说子夏门人“洒扫应对”只是末而无本;子夏反对子游所言,认为君子教人,有先后之序,并且“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对此,汉儒包咸、马融和孔安国分别作了注释。包咸强调对于门人要“先教以小事,后将教以大道”。马融讲“大道与小道殊异”,强调“学当以次”,还认为“君子之道,焉可使诬言我门人但能洒扫而已”。孔安国注曰:“终始如一,唯圣人耳。”(1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02页。应当说,汉儒的解读区分“小事”与“大道”的不同,强调“学当以次”,以回应将“洒扫应对”视为“人之末事”、“本之则无”的责难,既是对学道要从小做起、循序渐进之肯定,但又有将“洒扫应对”视为“小事”、“小道”而予以轻视之嫌。
至于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孔安国解为“终始如一,唯圣人耳”,后世多有争议。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解为“唯圣人有始有终,学能不倦,故可先学大道耳”,而其他人则必须先从小事做起。皇侃还引东晋张凭所言“唯圣人始终如一,可谓永无先后之异也”(14)皇侃:《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4、505页。,认为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始终如一,可以不分先后。与此大致相同,宋初邢昺《论语注疏》解为“人之学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终始如一不厌倦者,其唯圣人耳”(1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册,第5502页。,认为只有圣人能够做到“终始如一不厌倦”。
与汉儒解子夏所言强调“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因而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不同,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强调“理无大小”,因而非常重视“洒扫应对”。二程解读的有关论述,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所言时概括为五条:
其一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其二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其三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其四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其五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1页。
根据朱熹《论孟精义》可知,其中第一、二条为程颢所言,第三、四、五条为程颐所言(17)朱熹:《论孟精义》,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19页。但是根据《二程集》,第一条为“二先生语”,第二条为“明道先生语”,第三、四条为“伊川先生语”,第五条为“二先生语”。可分别参见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2、139、152、148、78页。。从朱熹对二程解读的概括以及先后排序可以看出,第一条讲“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最为重要;其后四条既讲“理无大小”、“圣人之道,更无精粗”、“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又讲“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对于“洒扫应对”之重要给予了同样的肯定。
然而,从字面上看,二程的解读很容易引起困惑。与汉儒将子夏所言解读为“先教以小事,后将教以大道”、“大道与小道殊异”,因而强调“学当以次”一样,二程的解读明确讲“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既然是“学当以次”、“教人有序”,就必须区分出大小、远近,所以,汉儒既讲“学当以次”,又讲大小之不同,因而可能会造成对“洒扫应对”的轻视。但二程既讲“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圣人之道,更无精粗”、“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并且强调“洒扫应对”之重要,甚至讲“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问题是,似乎只要“洒扫应对”便能够成为圣人,而若是这样,又如何“教人有序”?显然,对二程的解读需要作出进一步阐释和完善,而这项工作后来由朱熹同安悟道以及《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来完成。
《朱子语类》中有许多关于朱熹同安悟道的文献资料。对此,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作了细致的梳理(18)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第204页。。以下三条对于分析朱熹同安所悟之道尤为重要:
问:“子夏之门人小子洒扫应对进退”章。曰:“某少时都看不出,将谓无本末,无大小。虽如此看,又自疑文义不是如此。后来在同安作簿时,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说‘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无缘看得出。圣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终,乃是合下便始终皆备。‘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便都在这里了。若学者便须从始做去方得,圣人则不待如此做也。”(1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7页。
在这段答问中,朱熹讲述了自己早年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时对本末、大小的思考以及在同安任官期间对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强调“洒扫应对”的困惑和觉悟,并且意识到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并非“无本末,无大小”,二程的解读讲“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只是对圣人而言,而学者则必须讲“教人有序”,从“洒扫应对”做起,才能达到“精义入神”,才能成为圣人。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解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认为圣人“不是自始做到终,乃是合下便始终皆备”,“若学者便须从始做去方得,圣人则不待如此做也”,与孔安国解为“终始如一,唯圣人耳”、皇侃《论语义疏》引张凭言“唯圣人始终如一,可谓永无先后之异也”以及邢昺《论语注疏》言“能终始如一不厌倦者,其唯圣人耳”,就字面上看,颇为相似。
亚夫问:“伊川云:‘“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又曰:‘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虽“洒扫应对”,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来费无限思量,理会此段不得。如伊川门人,都说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说;解来解去,只见与子夏之说相反,常以为疑。子夏正说有本有末,如何诸公都说成末即是本?后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验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当时说与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话起,颇同所疑。”(2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8页。
在这段答问中,朱熹讲述了自己早年对二程解读的困惑、程颐门人对二程解读的误解以及同安任官期间的觉悟,尤其是讲述了对子夏所言“正说有本有末”而二程的解读却看似讲“末即是本”的困惑和觉悟。子夏讲“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显然是有本末之分;既然如此,二程的解读为什么又讲“理无大小”、“圣人之道,更无精粗”,还讲“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显然,这是朱熹同安悟道的重要内容。
问“洒扫应对”章程子四条。曰:“此最难看。少年只管不理会得‘理无大小’是如何。此句与上条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问之前辈,亦只似谢氏说得高妙,更无捉摸处。因在同安时,一日差入山中检视,夜间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7页。
在这段答问中,朱熹特别强调自己早年对二程解读五条中后四条讲“洒扫应对”之重要的困惑,并指出当时以为后四条中“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与第一条讲“君子教人有序”是相互矛盾的;继而又讲同安任官期间由困惑而悟道,特别强调二程解读讲“理无大小”、“圣人之道,更无精粗”,是为了要“从头做去”,讲“教人有序”,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由此可见,朱熹同安悟道实际上是对二程的解读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因而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的觉悟。如前所述,刘承相《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直接将“‘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视为朱熹“同安觉悟之语”。这一说法,虽然证据不足,但总体而言,较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所言“其所悟‘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实即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更为准确。
朱熹同安悟道是否包含对李侗所说之“理一分殊”的觉悟?据《朱子语类》载,朱熹在赴任同安县主簿途中见李侗,李侗批评朱熹“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并且指出,“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2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68页。。又据赵师夏《延平答问跋》所述,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李侗所言“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23)赵师夏:《延平答问跋》,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进行了反复思考。但是,由此并不能断言朱熹同安悟道就是对李侗所教“理一分殊”的觉悟。台湾学者吴展良《实践与知识:朱熹的早期学术取向析论》说:“二十七岁那年朱熹的思想体系开始有根本性的变化。他于公务旅途中苦究《论语》‘子夏之门人小子’一章,理会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亦即理一而分殊,道理无处不在,不可因事物大小而生拣择之心。这显示他对于李侗早先的教诲,有了更亲切的认识。”(24)吴展良:《实践与知识:朱熹的早期学术取向析论》,田浩:《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92-93页。显然这里采纳的是束景南的观点,也认为朱熹同安悟道是对李侗所教“理一分殊”的觉悟。然而从相关的文献资料看,朱熹在论及同安悟道时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对“理一分殊”的觉悟。因此,笔者更愿意主张朱熹在同安任官期间对李侗所教“理一分殊”有过反复的思考,尤其在悟道中又有了“更亲切的认识”。
二、同安悟道对朱熹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朱熹同安悟道,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论述。
第一,同安悟道是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朱熹由佛归儒的时间,后人多有争议。清王懋竑说:“所谓‘出入老释者十余年’,则自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时赵师夏《跋延平答问》言‘同安官余,反复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归在丁丑朱子二十八岁,自此以前所谓出入老释者也。”(25)王懋竑:《白田杂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6页。他认为朱熹于绍兴二十七年(朱熹28岁)任同安县主簿结束时而由佛归儒。后来,夏炘《朱子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考》说:“‘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此朱子《答江元适》书乃其铁凭。辅汉卿所录,十五、六岁‘在病翁所会一僧’云云,则出入释老自十五岁始矣,二十四岁始见延平。又‘年岁间始觉其非’,则二十四、五矣,所谓‘十余年’者是也。”(26)夏炘:《述朱质疑》,《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这里认为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朱熹24岁)赴任同安县主簿途中始见李侗而由佛归儒。夏炘的观点被民国时期唐文治称为“深得事实”(27)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钱穆《朱子新学案》说:“甲戌朱子已注意县学事,据《同安县谕学者》又《谕诸生》两文可见。乙亥又留心储庋经史书籍,《年谱》记是年春建经史阁,《文集》卷八十六有《经史阁上梁告先圣文》。《年谱》又记是年定释奠礼,申请严婚礼,《文集》有《申严婚礼状》。又记立故丞相苏公祠于学宫,《文集》有《苏丞相祠记》,又有《奉安苏丞相祠告先圣文》、《奉安苏丞相祠文》、《奉安苏丞相画像文》,又有《屏弟子员告先圣文》,均在同年。故知乙亥一年,乃是朱子一意归向儒学更为确定之年。”(28)钱穆:《朱子新学案》第3册,第20页。钱穆认为朱熹于乙亥年,即绍兴二十五年(朱熹26岁)由佛归儒,较为强调朱熹任官期间勤勉于职守对其由佛归儒的作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认为钱穆的考辨,与朱熹自言“后年岁间渐见其非”基本相合(29)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则明确将绍兴二十六年(朱熹27岁)春的同安悟道看作是朱熹由佛归儒的“最初的觉醒”(30)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第141页。,更为强调同安悟道对朱熹由佛归儒的作用。应当说,朱熹由佛归儒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赴同安任职途中始见李侗,还是在任官期间勤勉于职守,或是对李侗所教“理一分殊”的思考,或是同安悟道,都对朱熹由佛归儒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的学者有所侧重并据此对朱熹由佛归儒的关键节点作出判断,虽各有不同,但都不可能否定同安悟道在朱熹由佛归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使按照夏炘、唐文治以及钱穆等人的分析,朱熹先是由佛归儒,然后同安悟道,也不可能否定同安悟道与朱熹由佛归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采纳束景南的观点,将同安悟道看作是朱熹由佛归儒的“最初的觉醒”,是关键节点,更多的是要强调同安悟道在朱熹由佛归儒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和象征意义,并非否定朱熹始见李侗、同安任官期间勤勉于职守以及对“理一分殊”的思考所起的作用。
第二,同安悟道是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起点。“理一分殊”概念为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最早提出(3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二程集》上册,第609页。。李侗讲“理一分殊”,较为强调“分殊”,不仅如上所述,说过“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而且据朱熹《延平答问》,他还说过“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32)朱熹:《延平答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324页。。李侗的这一思想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体系的建立影响很大。朱熹在赴任同安县主簿途中始见李侗,在同安任官期间对李侗所教“理一分殊”进行了反复思考。朱熹晚年论及“理一分殊”概念时认为,“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3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页。,并赞同所谓“佛氏自谓理一而不知分殊”(34)朱熹:《答郑子上》,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89页。的说法,即佛学也能接受“理一分殊”的道理,但只是讲“理一”而不知“分殊”。因此,朱熹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3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册,第677、678页。,儒佛的分界不在于讲“理一”,而在于讲“分殊”。朱熹同安悟道对二程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因而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的觉悟,实际上就是在“分殊”上下功夫,也就是在建构“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同时也正是在由佛而归儒。
第三,同安悟道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最初萌芽。朱熹十五六岁时读《大学》,但不知“格物”之意。同安悟道后不久,朱熹于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为柯国材的居室“一经之堂”作《一经堂记》,明确提出“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36)朱熹:《一经堂记》,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96页。,对《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有了认识,强调由“格物”而“致知”,由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然后则“诚意”、“正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当说,朱熹《一经堂记》提出由“格物”而“致知”、重视循序渐进是同安悟道对二程解读觉悟的推广。由此出发,朱熹于淳熙初年(1174年前后)形成了关于格物致知的基本思想(37)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68页。,并于淳熙十六年完成《大学章句》,形成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其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总目》说:“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38)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页。钱穆甚至认为,“朱子全部学术,即是其格物穷理之学”(39)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然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乃至全部学术思想,起始于他同安悟道后所撰《一经堂记》对《大学》“格物致知”的阐发,是来源于同安悟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同安悟道包含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乃至全部学术思想的最初萌芽。
第四,同安悟道为朱熹形成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洒扫应对”为“小学”工夫,而“格物致知”为“大学”工夫。对此,朱熹《大学章句序》有详细的论述:“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4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朱熹《大学或问》则认为,“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41)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27页。。也就是说,“小学”工夫是要“习于诚敬”,“大学”工夫则是要“即物而穷其理”,显然朱熹非常重视“小学”工夫,尤为强调“小学”工夫对于培养人的心性的重要性。他甚至还说:“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42)朱熹:《答胡广仲(1)》,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94-1895页。在朱熹看来,只有“小学”的心性培养成功,“持守坚定,涵养纯熟”,才能进于“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始。朱熹不仅撰《大学章句》,而且撰《小学》,既讲“格物致知”,又重视“洒扫应对”。《小学》中引述二程所言“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是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43)朱熹:《小学》,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456页。,此句正是二程解读的第一条,也是朱熹同安所悟之道最为重要的内容。而且,朱熹晚年在讨论二程解读第三条所言“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时,说:“‘洒扫应对’是小学事,‘精义入神’是大学事。精究其义以入神,正大学用功以至于极致处也。”(4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9页。因此,朱熹强调由“小学”而“大学”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来自他同安悟道对二程解读的觉悟。
三、从同安悟道到《论语集注》的阐释
自绍兴二十六年同安悟道尤其是由佛归儒之后,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草成《论语集解》(45)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篇》上卷,第248页。,最终于淳熙四年完成《论语集注》以及《论语或问》,其中对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对于子游说子夏门人“洒扫应对”只是末而无本,子夏说“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朱熹《论语集注》说:“君子之道,非以其末为先而传之,非以其本为后而倦教。但学者所至,自有浅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类固有别矣。若不量其浅深,不问其生熟,而概以高且远者强而语之,则是诬之而已。君子之道,岂可如此?若夫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则惟圣人为然,岂可责之门人小子乎?”(4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1页。这里是认为,君子教人不是因为教的是末而先教,也不是因为教的是本而后教,也就是说,不是依据所教内容之本末来确定教学的先后次序,而是要根据学生能力水平的高低层次循序渐进,不是一概讲高深的道理,“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如前所述,朱熹《论语集注》的注释还引述了二程的解读五条,除第一条讲“君子教人有序”,其后四条特别强调“洒扫应对”之重要。对此,朱熹特别加了按语:“程子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其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盖与第一条之意,实相表里,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4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1页。在朱熹看来,二程所言第一条讲“君子教人有序”,说得“最为详尽”;其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盖与第一条之意,实相表里”,而且“其分虽殊,而理则一”,所以,既不可“厌末而求本”,也不可“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认为教学应当循序渐进,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始终本末一以贯之”,就字面上看,与汉儒讲“学当以次”、“终始如一,唯圣人耳”颇为相似,而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汉儒是依据所教的内容之本末而讲“学当以次”,讲“大道与小道殊异”,把“洒扫应对”看作“小事”、“小道”,看作末,因而难免有轻视“洒扫应对”之嫌。二程虽然讲“物有本末”,但强调“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朱熹也讲“‘洒扫应对’,末也;‘精义入神’,本也”,但又认为“不可说这个是末,不足理会,只理会那本,这便不得。又不可说这末便是本,但学其末,则本便在此也”(4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9页。。因此,既要反对“厌末而求本”,轻视“洒扫应对”,同时又不可本末不分,不可说“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朱熹《论语或问》对二程所言“理无大小”及其与“君子教人有序”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对于二程的“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朱熹认为,“洒扫应对,所以习夫形而下之事;精义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则未尝有大小之间而无不在也。程子之言,意盖如此”(49)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05页。。朱熹同安悟道把“君子教人有序”与“理无大小”结合起来;《论语集注》强调“君子教人有序”,认为“理无大小”与“君子教人有序”,“实相表里”;而《论语或问》则认为“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其事之大小,固不同”,而“以理言,则未尝有大小之间”。《论语或问》还说:“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则洒扫应对之与精义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语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则初未尝以其事之不同,而有余于此不足于彼也。”(50)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06页。这里既讲“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其事之不同,又不赞同对二者有所偏颇。由此,朱熹晚年进一步明确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并且还说:“‘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无大小,故随所处而皆不可不尽。”(5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9页。显然,朱熹晚年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并用以分析“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的关系,既讲二者“理无大小”,又讲二者“事有大小”,实际上就是要既反对轻视“洒扫应对”,即《论语集注》所言“不可厌末而求本”,又反对将“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混为一谈而只是停留于“洒扫应对”,即《论语集注》所言“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这较二程只是讲“理无大小”更为周全,也是朱熹自同安悟道之后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进步。
尤为重要的是,朱熹《论语或问》对二程“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说,“方举洒扫应对之一端,未及乎精义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无大小结之,故其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难明耳”,因而认为二程此言之意“正谓理无大小,故君子之学,不可不由其序,以尽大小者近者,而后可以进夫远者大者耳”(52)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05页。,就是要从“理无大小”进而强调“君子教人有序”。《论语或问》还说,“无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无大小,而无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遗也”(53)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第906页。,认为二程讲“理无大小”就是为了讲“君子教人有序”。由此可见,朱熹晚年由二程讲“理无大小”而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既要求“不问大事小事,精粗巨细,尽用照管,尽用理会”,又认为“从粗底小底理会起,方渐而至于精者大者”,最终还是为了要讲明二程的“君子教人有序”(5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4册,第1208页。。
相较于朱熹在论及同安悟道时而言“其曰‘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非是谓‘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朱熹《论语集注》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更为强调二程所言第一条“君子教人有序”,并与汉儒讲“学当以次”区别开来,同时又明确运用“理一分殊”概念解释二程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以及对于“洒扫应对”的重视,既认为“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又反对“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显然较同安悟道又进了一步。与此同时,朱熹《论语或问》对“理无大小”作了进一步解释,不仅由此而在晚年明确提出“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而且又将“理无大小”归于“君子教人有序”,并视之为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最为根本的内容。由此亦可看出,朱熹《论语集注》以及《论语或问》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实际上是对朱熹同安悟道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或者说,朱熹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阐释经历了从同安悟道到《论语集注》和《论语或问》的解读乃至晚年的发挥这一不断深入的过程。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同安悟道对二程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因而既重视“洒扫应对”又强调由此而“精义入神”的觉悟,不仅在朱熹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同安悟道发展而来,朱熹《论语集注》以及《论语或问》解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的解读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尤其是对二程既讲“君子教人有序”又讲“理无大小”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无论在经典解读还是在义理发挥上都有所创新。
然而,程朱的解读在传播并影响后世的过程中,也多有被误解而备受质疑。清代毛奇龄《四书改错》认为程朱的阐释“皆多事矣”,“在《六经》与圣贤口中,并无此言”,并且还说:“朱氏尚云洒扫应对须用涵养,须用持守,而程氏则直云洒扫应对即是形上,即是精义入神,即是圣人之事。无精粗,无本末,无大小,圣学、圣道从此大乱,大乱矣!”(55)毛奇龄:《四书改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2-443页。应当说,毛奇龄对程朱重视“洒扫应对”的指责,以及认为二程所言是“无精粗,无本末,无大小”,不仅是对二程的误解,而且也忽视了朱熹解二程所言,既讲“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有大小、精粗、本末之别又认为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思想。后来,戴大昌《驳四书改错》说:“毛氏引程子四条,讥其以末即是本,是‘无精粗,无本末,无大小,圣学、圣道从此大乱’,不知此章圈外注首载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然后载此四条。朱子复加以愚按曰:‘程氏第一条,说此章文意,最为详尽。后四条,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虽殊,而理则一……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即便在此也。’则朱子已有辨正,固无烦毛氏之哓哓也。”(56)戴大昌:《驳四书改错》,《续修四库全书》第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在戴大昌看来,朱熹重视“洒扫应对”,但更为强调“君子教人有序”,是围绕着“君子教人有序”讲“洒扫应对”,而毛奇龄的指责实际上忽视了朱熹运用“理一分殊”概念对二程所言的解读。
毛奇龄《四书改错》不仅对程朱的阐释多有误解,而且还说:“洒扫不是物,固非形下之器,然亦安所为形上?安所为道?然且直进之为精义入神,吾不知执箕泛帚有何神义。即洒而扫之,其得进于义之精而神之入,端是何故?……今事在洒扫,则其理不过粪地而已;事在应对进退,则其理不过侍宾长、执役使而已,而谓有精义,得圣人之事,实未之闻。”(57)毛奇龄:《四书改错》,第442-443页。显然,他在指责程朱对“洒扫应对”重视的同时,表现出对“洒扫应对”的轻视。
今人对《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的解读,尤其是对子夏所言的解读,大多只是停留于汉儒所谓“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学当以次”。杨伯峻《论语译注》解曰:“君子的学术,哪一项先传授呢?哪一项最后讲述呢?学术犹如草木,是要区别为各种各类的。君子的学术,如何可以歪曲?[依照一定的次序去传授而]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罢!”(58)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9页。钱穆《论语新解》解曰:“君子之道,哪些是先来传给人?哪些是放在后,厌倦不教了?就拿田圃中草木作譬,也是一区区地分别着。君子之道,哪可用欺妄来对人呀!至于有始有卒,浅深大小都学通了的,哪怕只有圣人吧?”(59)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57-458页。李泽厚《论语今读》解曰:“君子的学问,哪一种先教,哪一种后教,好像树木花草,各有种类区别。君子的学问,又怎能这么曲解呢?能从头到尾合在一起的,只有圣人吧。”他还认为,对于子夏所言“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大多解作教学需循序渐进,先小节、后大事,先实践、后理论,先末务、后本体(60)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55页。。应当说,今人的解读,大都承袭汉儒,通过讲“大道与小道殊异”,而讲“学当以次”,并不了解这种将“洒扫应对”视为“小道”的解读,实际上很可能包含或是导致像毛奇龄那样对“洒扫应对”的轻视。
无论是汉儒还是程朱,或是像毛奇龄那样对程朱持批评态度的清儒,乃至今天的学者,都肯定《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意在“学当以次”,或“教人有序”,讲教学需循序而渐进。然而,在二程的解读以及朱熹通过同安悟道乃至《论语集注》对二程解读的进一步阐释中所强调的“教人有序”,不是根据所教内容的本末之别的“学当以次”,而是要根据学生能力水平高低层次的循序渐进,因此又讲“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既讲“学者当循序而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又反对讲“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便在此”,正是要在讲明“教人有序”的同时,强调“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在形上层面的相互贯通以及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给予“洒扫应对”足够的重视,以克服汉儒讲“大道与小道殊异”而可能包含的对“洒扫应对”的轻视。也就是说,朱熹解《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应对”章讲“教人有序”,包括了对于“洒扫应对”的重视;但又不是把“洒扫应对”完全等同于“精义入神”,而是强调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这既是朱熹同安所悟之道,也是朱熹《论语集注》进一步加之以“理一分殊”的解释和发挥而超越前人的创新之处。显然,这样的阐释对于今天的《论语》解读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它对根据学生能力水平高低层次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的“教人有序”的强调,也能给予当下的道德教育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