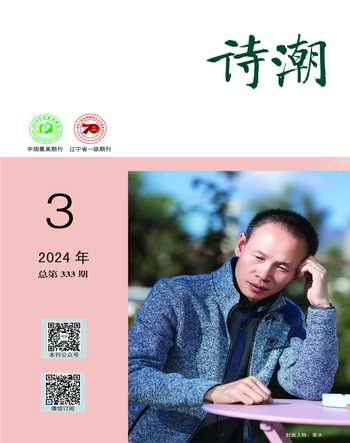屠龙术(节选)
胡亮
落叶有两种扫法:僧人式扫法,清洁工式扫法。诗人懂得两者的差异性。
总会找到足够的词或容器:珠穆朗玛峰,甚至还填不满马里亚纳海沟。
元好问教我一个词组:“万古新”。
理想与面条擦出了诗之电火。
阿赫玛托娃教我一个词组:“隐形墨水”。
阿赫玛托娃——也许还有茨维塔耶娃——宁愿承认自己是欧洲诗人。俄罗斯部分土地在欧洲,部分土地在亚洲。亚洲怎么就招惹了她们呢?
他们批判大象不会上树,批判松鼠没有翅膀,批判秃鹫不会钻地洞,批判穿山甲没有漂亮的尾翎,批判锦鸡没有獠牙,批判老虎没有蒲扇般的耳朵和一米多长的鼻子……如是而已。
词法,句法,均有奇技淫巧。
既有高级的口语,就有低级的口语;既有高级的书面语,就有低级的书面语。那么,口语与书面语之争就存有四种情形:高级与高级之争,高级与低级之争,低级与低级之争,低级与高级之争。除了两者之争,还有两者之交:高级或不高级之交。高级的口语与高级的书面语之交,就是一切写作的至境。但是,非要说得这么清楚吗?
每一眼都是第一眼之必要。每一眼都是最后一眼之必要。
天啦,老是这样,我更愿意谈到“字”而不是“词”。
克罗齐教我一个词组:“小的大诗人”。经我与杨碧薇博士讨论,小的大诗人或有两种:局部的大诗人,片面的大诗人。前者比如陈子昂,后者比如黄庭坚。
只要羞愧没有失传,诗就不会失传。
颓废和官能主义,有时候,甚至就是最低限度的坚持和反抗。谈论后期柏桦,尤当注意及此。
我们可否借助拖鞋、钉子或红烧肉这样的事物来阐述诗学或哲学呢?
我们爱上了字和词,同时呢,不免怀恨在心。
余光中教我一个词组:“兑了水的浪漫主义”。他用以指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诗,这让我着实有点儿猜不透。
这次我与艾略特说的不一样:我们既是语言的奴隶,也是语言的奴隶主。
诗人总是侦破着——并设计着——字与词的萍踪。
“巧克力”和“奇书”,对狄兰·托马斯来说,两者皆有助于忘忧。
“兴于喜悦,终于彻悟。”当过皮匠的弗罗斯特如是说。
“蒹葭”二字,比蒹葭更美。这会不会导致我们对蒹葭的虚美呢?
耳朵可以失明,眼睛可以失聪,心可以瞎,花儿可以哑,天地万物可以聋。
诗之二分法:客厅之诗,卧室之诗。
诗之二分法:诗大于人,人大于诗。
诗之二分法:作为变形记之诗,作为还魂记之诗。
“一个平庸的时代,”陈先发说,“平庸就是它最大的资源。”
诗与盘山公路的相似处在于:向左,向右,都是为了某个峰顶。
走出困境的诗人太少了,以至于,这些诗人像是走进了困境。
庞然大物或会造成滑稽感(幽默感)在诗中的缺席。
诗是这样一种未知数:它让巧舌变得支支吾吾,让爱变得笨拙,让堕落得了光辉,让严肃与荒诞互为掩体。
“清空如话。”俞陛云谈及李商隐《夜雨寄北》时如是说。此外,我完全同意后者举出贾岛《渡桑干》与此诗并读。附带说一句:德清俞氏,自曲园,而陛云,而平伯,真可谓诗心不绝。
“它哀伤得几乎可以收进教科书。”毕晓普谈及童年时如是说。
诗人共有的幸与不幸:总是能从字的夹缝里找出一缕躲闪不及的不完美。
李贺、凡·高、顾城和海子:他们都被抵押给了自身的天才。
泰山有花期,海棠就有百丈崖。
除了谈论诗之无用,还有机会谈论爱之无用:妈妈,爱与诗,都挡不住您的牙齿掉落。
真理也有阴影;而且呢,很多人只乐意(选择性地)看到真理的阴影。
以诗为文者众,以文为诗者寡。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张岱《湖心亭看雪》,都是以文为诗的极品。
绝大多数诗人没有终生写作的资格,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大量制造次品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或应更信任这样的诗人:在某个短期内灵光乍现,然后再也不写作,并拒绝自认为诗人。
不小心说漏了嘴之必要。
见垂丝海棠如见故人之必要。
“红色”“黑色”和“白色”,其政治学语义均已剧增。“黄色”,其政治学语义在骤减,生理学语义却在剧增。“蓝色”,其宗教学语义渐滋,而物理学语义未泯。“绿色”,物理学和诗学语义均已剧增。
蜜蜂喜欢油菜花,不喜欢黄金。我们说“黄金般的油菜花”,是否构成了对蜜蜂的冒犯呢?
与一只灰斑鸠交换心脏之必要。
才者,累也;情者,累也;臭皮囊者,亦累也。
诗中达利之必要。
诗人要不断成为他的诗的陌生访客。
“即便不停改变主意,”夏宇说,“诱引之物恒以万物之名显现。”
诗是字的如意算盘,也是字的极限运动。
“其小無内”,诗之现代主义也;“其大无外”,诗之后现代主义也。
溪声和山色都是偈子。
“语未了便转。”陈衍谈及杨万里时如是说。
随便摘一枚竹叶,都会扯痛山神的耳朵。
孤独地赞美!——难道还能有其他的赞美方式吗?
汉人所作乐府《枯鱼过河泣》,展示了独步而骇人的想象力。王夫之只用两个字作评:“无限!”陆忆敏《沙堡》、钟鸣《枯鱼》,两诗均用其典。
名词暂借作动词,或暂借作形容词,形容词暂借作动词,此物属性暂借给彼物,凡此种种,往往可收得奇效。
我们允许一个人有多重面孔:个人的,单位的,或社会的面孔;欲望的,道德的,或无懈可击的政治的面孔。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选择用哪张面孔盖住其他面孔呢?
何者饱含更多的真理?一座图书馆,还是一只柑橘?
“月毕竟是何物,”金圣叹假装不解,“乃能令人情思满巷如此?”
司马迁爱游侠,甚于贵胄。杜甫爱宋玉,甚于屈原。金圣叹爱李逵,爱鲁达,爱武松,不爱宋江。吾爱孙二娘,不爱扈三娘。
袁中郎谈乃弟之诗,极喜其疵处,以其疵处亦多本色,而其佳处未脱气习故也。这番见解发表于1596年,彼时,袁小修仅二十七岁,袁中郎仅二十九岁。
诗里没有乐观主义,只有乐观主义猜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以为证也。
为了一眼看到白骨,诗人忽略了临时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