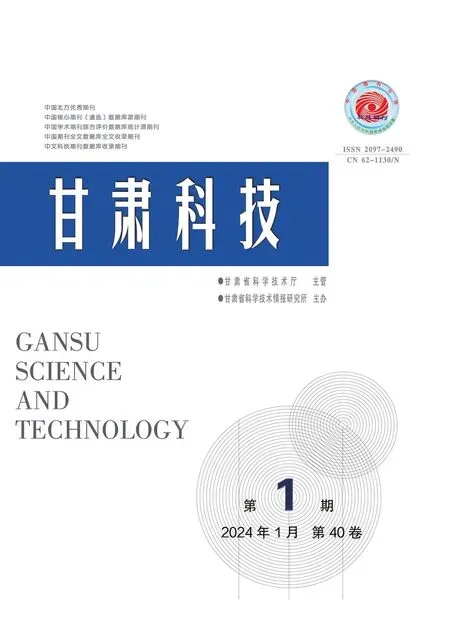产权制度背景下甘南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路径探析
何旭明
(1.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9;2.甘南州委党校,甘肃 合作 747000)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南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黄河流经西南部,洮河、白龙江流贯境内,州域平均海拔3 000~4 000 m,光照充裕,降水较多,热量不足,年平均气温在1~13 ℃之间。统计数据显示,全州草地面积272.27万hm2,湿地面积38.4万hm2,属全国“六大牧区”之一,是黄河、长江上游地区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黄河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和黄河、长江上游的河源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州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实施退牧还草、鼠害综合防治、沙化草原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重点工程项目,有效治理中度以上退化草原103.8 万hm2,累计治理沙化土地0.41 万hm2、潜在沙化草原1.79 万hm2,草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1]。截至“十三五”末,草原平均草群盖度、高度、产草量三项指标明显增加,沙化、鼠害、虫害、毒害草等分布面积逐渐减少,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所增加,黄河首曲草原涵养水源、蓄水保水和补给能力趋于平稳,草原生态系统逐步恢复,但全州局部区域草原退化和沿黄沙化问题仍在不同程度持续,针对草原退化的问题,许多学者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富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1 草原退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文献,草原退化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制度因素3个方面。
首先是自然因素。部分学者认为草地退化是在全球变暖和降水减少的背景下发生的,戚登臣等[2]对甘南玛曲县气候变化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县的气候特点开始从干冷大风向干暖型转化,降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沼泽地大面积干枯,诱发草原退化。张继承等[3]通过对青藏高原气温和降水变化特征的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平均气温伴随全球持续升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而且藏北地区降水量的逐年减少加剧了河源地区的干暖化趋势。史激光等[4]、赵晓英[5]利用锡林郭勒盟近50年气象观测数据的统计分析,证实了气温升高、降水减少与草原退化的高度相关性。气候变化降低了草地保水蓄水机能,影响了草本植物群落结构,甚至区域植被退化影响到气候,形成双向推动的恶性循环。另外,草原鼠虫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草原退化强化了草原鼠、虫对草根的生存性依赖,加之毒害草的蔓延生长进一步加剧了草原退化。
其次是人为因素。部分学者认为草原有自身生长修复的周期,而超载过牧导致植被严重啃食,叶量减少,光合能力降低,多年生牧草营养物质消耗增加,牧草再生能力和种子繁殖能力降低,打乱了草原修复的时间周期。过度放牧致使土壤夯实、间隙变小,通气蓄水和保肥能力减弱,导致土壤质量恶化[6]。而且超载过牧和乱采滥挖破坏了草原生物链,引发大面积鼠虫繁殖,破坏了草原表层植被。同时,牧区人口数量增长也对草原退化施加了一定压力,人口增长加大了对畜产品的需求,刺激牧民增加了畜群数量,进而引发草地退化,而草地的退化、沙化又加剧了对更多草地资源竞争性开发,二者互为联系,相互促进[7]。据统计数据,1965年甘南州牧业人口24.9 万人,截至2022 年,全州农牧业人口达到55 万人,而牧业人口就占54%,约29.7 万人,牧民人口的增加以及相对单一的生计方式加大了对天然牧草的生产性依赖,使天然草原的载畜量持续增加,加剧了超载过牧和草原退化。
最后是制度因素。部分学者对气候变化或超载过牧引起的草地退化持不同看法,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较为缓慢,而且超载过牧也会随着生产条件改善和非牧区牲畜产能的提升而得以缓解,很多地区在载畜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依然存在草地退化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土地利用方式决定着土地附着植被的种类、土壤的性质和物种多样性,草地作为土地资源种类之一同样面临着此类问题。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区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区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实践也促成了在牧区实施相同制度的草原治理逻辑。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至今,先后经历了“草原共有、牲畜承包”“草原承包到组、牲畜私有”到“草原承包到户、牲畜私有”的变革历程,形成了现今草原资源“三权分置”,鼓励草地流转经营提升经济效益和草原生态补奖保障生态效益的草原管理政策体系。随着草地使用权的落实,牧户通过草地围栏建立了排他性边界,减少了外来牲畜对草场的过度利用,提高了牧民保护承包草场的积极性,保障了牧民产业发展的基本权益,避免了“公地的悲剧”。然而,草地承包到户改变了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草原承包前逐水草而牧的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划区轮牧的草地经营方式,从而缩小了牧民和牲畜的空间移动范围,阻碍了牲畜的时空采食,又使草地践踏频繁,进而引起草原退化。
2 草原围栏困境的表现与化解
在草原承包制前,草场集体所有的经营方式始终伴随着诸如草场纠纷、超载过牧等社会经济问题,困扰着草原畜牧业发展和牧区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后,草原承包制的实施提高了草原管理和利用绩效,然而草原围栏引起的对草原生态系统的条块化分割,打破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以及草原牧民原有的生活方式。
2.1 围栏困境的表现
草原围栏引发的问题,学界也给予了深入研究。阿不满等[8]通过对甘南玛曲的调研分析指出,草原承包到户后,新的经营体制与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曾贤刚等[9]认为“围栏效应”的主要表现是,阻碍了牧区野生种群的取水、觅食、迁徙和繁殖,影响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同时草原牧区生态质量的空间差异性与流动性不足的矛盾影响牧民的生计方式。李继刚[10]通过对牧民生产生活的微观分析,指出草场分割与生态系统不可分性的矛盾造成草场价值下降,也阻断了牧民之间的互助,降低了风险抵御能力,草场继承与家庭人口增加的积累性效应加重了贫富差距。韦惠兰和祁应军[11]认为,牧区实行的草原家庭承包制增加了牧民的生产成本,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围栏陷阱”等生态外部性问题。另外,从理性经济人视角分析,草原承包制实施后,随着游牧文化规制的弱化和强势市场资本的嵌入,牧民在维持草原生态平衡的长期收益和增加畜群数量获得市场短期收益的两难困境中往往选择后者,甚至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将承包草原流转而退出牧业生产,而草原承包户以其经济、信息等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收益,这不仅导致草原退化,更是拉开了贫富差距。但也有学者认为,草原“围栏困境”的形成不是草原家庭承包制的问题,而是因为承包制的实施不彻底、不科学、不合理[12]。还有其他诸如法律不健全、交易费用、技术限制等导致的产权模糊问题,造成为增加收益而增加畜群数量的“搭便车”行为,加剧了草原退化。
2.2 围栏困境的化解
基于国家层面的草原产权制度安排,牧区家庭根据自身实际和传统文化的路径依赖而采取联户经营模式进行牧业生产,由牧民自己选择灵活的组合方式发展牧业,以减少排他性成本并提高牧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曹建军等[13]认为玛曲草地联户经营既可避免集体产权制度下草地资源无人监管的弊端,又能对单一牧户的草地不合理利用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具有生态高效、生产监督成本低及社会资源丰富等诸多优点。韦惠兰等[14-15]从牧民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的享用权三方面对甘南州玛曲县草场单户和联户经营模式进行了界定,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认为联户经营作为草原承包到户基础上的自发合作方式,可以提高牧业劳动力配置效率,降低草场排他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实现牧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联户经营是对草原生态整体性和家庭承包权分散性的有机结合,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草场联合经营。联户经营扩大了牧业生产半径,降低了牧草供给压力,促进了劳动力迁移,有效提高了牧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和生产力水平,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的目标。同时在国家草原治理顶层设计框架下,草原社区拥有草原资源的所有权,而草原资源又具有天然的生态完整性,因此,草原“三权分置”框架下的牧业生产更需要政府与社区的协同共治才能促进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草原社区治理可以化解政府草原治理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巨大的难题,使牧民利用草原资源的传统方式和力量得以复归,同时减少围栏使用可以提高草原牧业生产的流动性,激发牧民保护草原的动力,丰富牧民经济收益的结构[16]。综上可见,草原生态治理与牧民生计改善的双重目标理应通过构建草原社区治理与牧民联户经营互动结合的长效机制得以实现。
3 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路径
保持草原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从国家治理而言,草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绿色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主体,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从自然生态角度来看,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维持生物多样性、优化土壤结构和养分循环、调节自然气候。从家庭生计来看,可以为牧民群众提供持续的牧草资源,增加牧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因此,基于甘南草原生态治理和围栏困境的共性特征,持续推进草原资源优化利用,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促进。
一是完善政策供给。建立完善草原社区综合治理和牧民联户经营互动结合机制,给予社区管理规则制定、权利义务划分、资源收益分配等自主权,在保障牧户经济收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草原社区对连片草原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同时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制定完善草原保护、草原调查、草原征用等法律法规,适时提高牧户社会保障补助和生态补奖标准,切实保障和促进集体经济组织和牧户利益。此外,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遥感、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草原生态检测与管理,明晰草原承包权,为草原补奖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承包权的合理流转提供产权依据,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
二是推进牧民群体主体性建构。牧民群体是草原生态保护和牧业产业发展的主体,在草原承包制度背景下,激发牧民群体草原保护和发展动力,提高草原资源存量和未来价值预期,可有效缓解政府信息不对称和财力不足的困境。首先是加强牧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政策宣传。针对牧业从业人口,通过网络课堂和基层组织平台定期开展培训,强化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宣传,提高牧民牧业生产技能和生态保护意识。其次是加强对牧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法律咨询等服务,提升家庭生计能力。同时提高牧民群体的教育、医疗、养老和救助支持力度,鼓励参与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工程建设,使牧民群体切实从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受益。
三是加大草原保护与修复资本投入。根据国家草原保护和建设规划,对草原生态重点县市提高专项投入,科学实施草原禁牧封育、病虫防治、草籽产业、防灾减灾、草原自然保护区建设、草原生态旅游等项目工程,促进草原生态恢复,提高牧草产能,改善牧区基础设施,实现牧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同时加大草原生态检测、价值评估的技术、人员投入,建立和完善草原监测管理体系,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加强草原生态数据库建设与运营,提高草原生态管理者的管理决策能力。
四是鼓励草原承包权流转经营,缓解牧业人口压力。草原畜牧业从业人口增加势必会增加对草原资源的需求,进而导致对草地的掠夺性利用,加速草原退化。鼓励草原承包户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养殖大户等中长期流转草原承包权,同时给予草原流转家庭转移就业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供给,使草原流转家庭获得稳定的流转收益,从而缓解牧业人口压力。就承包权流转受让方而言,草原连片经营既可实现牧业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草畜平衡,因为中长期流转合同期内增加畜群数量不仅会增加人员和监管成本,还会引起草原退化而得不偿失。
五是延伸产业价值链,缓解草原载畜压力。畜牧产业发展是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然而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畜牧初级产品的利润空间有限,牧民增收的动力机制便是增加畜群数量,这为草原生态恢复形成了压力,加之高昂的监督成本,影响了禁牧政策的有效落实。因此,应探索引进市场资本,以集体经济组织或合作社为主体发展畜牧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价值链,培育品牌价值,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相结合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生产经营机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创造就业和增收渠道,转变增加畜群数量创收的惯性行为。同时辅以草原补奖、转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稳定提升牧户生计能力,激发牧民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动力。
4 结语
草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资源,是牧民群众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牧民群体改善生计、提升福祉的有效保障,草原承包制作为处理人、草、畜相互矛盾的科学制度设计,还需在实践中随着知识增长和科技创新,以及制度、环境和文化的时域性融合不断完善,以使其更具生命力,在草原资源优化利用和牧民持续增收方面实现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