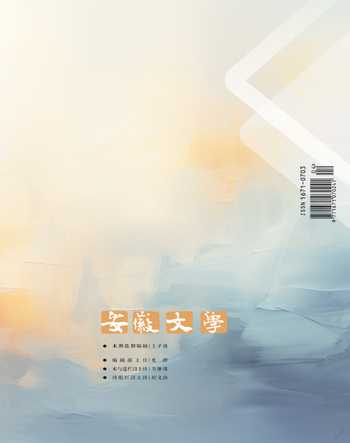花砖
蔡盛
花砖是安徽省泾县茂林镇的特色产品,也是省级非遗。
走进千年古镇茂林,花砖也似一张脸,给茂林贴了金,撑了脸面,成为一张厚重的名片。
到茂林看花砖,尚友堂是必去的。
清晨的一米阳光照进古巷,柔光下,八字形院门、花砖门墙、青石墙裙、白石门坊的尚友堂也红了脸,像个青涩婉约的少女。
站在古巷里,左看右看抬头看,满眼都是花砖。怎么形容它呢?初见像邂逅了皖南雨巷里撑着油纸伞的少女,那种美是带着呼吸的,也像带着露珠的荷叶,有雨滴一样的心跳,很想抓住,很想时光就此驻足……
尚友堂是有故事的,堂厅正中悬有钦赐的“四代五世同堂”匾额,是这座古民居的“金子招牌”。在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四代皇帝执政期间,从吴善政开始,居住在尚友堂的吴氏家族四代五世同堂,共13人受朝廷旌表。光绪十七年(1891),茂林吴氏绘制了《四代五世同堂图表》,状元吴鲁为其作序称:“一堂聚五世,得旌十三人,叶方传有四,乾嘉道咸间,历来入通志。”细细算来,从吴善政出生算起,到光绪年间的第九代,有170余年历史。第一代吴善政就有13个儿子,分为13房;第二代长房吴寿昌、二房吴寿麟各有8房子孙……一代代算下去,这个枝繁叶茂的吴氏大家族,人口的确不在少数。
除了钦赐匾额,花砖也为尚友堂增了色。乍一看去,尚友堂的单块花砖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像京剧脸谱,有的似行云流水,抑或像瓜果花卉、飞禽走兽、敦煌飞天、水纹罗裙、苍松翠树,似禽似兽,似花似草,似奔马,似关公,似长河……经能工巧匠之手,花砖与花砖组合更加巧夺天工。乾隆年间茂林花砖拼出来的《群英图》,有一百零八个人物脸谱,像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招摇皖南。茂林吴组缃故居“七房里”、吴波故居等处,也有“桃园三结义”“东海八仙图”等花砖杰作,意象如诗,画面如画,让人仰视。
通往茂林花砖厂窑址的小径开满了橘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像开在大地上的星星。踏花迎面而来的是一名村妇,拎着手编竹篮,笑靥如花,那种山里人的质朴純良写在她的脸上,久违而又亲切。她手指的方向成为我前行的路标,指尖碰触到了山顶的蓝天与白云。
来到窑厂,与老窑工攀谈,花砖那曲折的历程又平添了一份传奇。
相传,宋元时期当地人开窑烧制大块头的砖,用于阴宅(陵墓建设)。茂林人捡金(迁葬)时,潮湿的砖块与砖块碰撞、摩擦,砖的花纹便凸显了出来,仿佛是祖上显灵、庇护后人,让捡金者心安理得。
无独有偶,当地的一樵夫打柴时捡到一块阴宅出土的砖,拿到水沟边用来磨刀。随着“霍霍”的磨刀声,黑白相间的精美图案渐渐呈现,像一幅水墨画,让樵夫惊讶万分……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茂林窑工的耳朵里,大家开始琢磨,想烧制出这样的“画砖”用于建房。可是,砖烧制出来了还是没有画意。聪明的窑工想到了阴宅,就把刚出窑的砖放到潮湿阴凉处存放去火;又受樵夫磨刀启发,将存放一段时间的砖进行水磨。水磨之后水墨效果呈现,砖不仅细腻光洁,而且千姿百态,气象万千,水磨花砖就此诞生。
兴奋的窑工们从茂林东边的窑湾里、西边的西山脚取来了黄色的“油黄土”和黑釉色“冷水土”(俗称“观音土”),碾碎后混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加入清水,牵来水牯牛,人站在中间牵着牛绳,水牛一圈圈原地打转。随着“咕咚咕咚”的踩踏声,泥巴被踩得稀巴烂。炼熟的泥团,再经过制坯、晾干、装窑等程序,砖就缺一把火了。烧窑前,窑工们在窑洞口上方堆砌了一道防火砖,下方留有风口,用以控制温度、把握火候。火太“嫩”,烧出来的砖块是灰白的。闭窑后,下水是个关键环节,远比铁匠的淬火麻烦,必须慢滴慢渗。水少则会“回生”,像土块一样;水多则会“水酥”,让砖块脆化、断裂。冷却、出窑之后,经过一块块的水磨,花砖的水墨效果呈现,一块砖就是一方艺术品,形态千变万化、千姿百态。
老窑工上了七年学,是窑厂的“秀才”。他拿着一块花砖给我看:“这一块花砖像不像我们茂林的美女,羞答答的;这一块花砖像不像茂林的东溪河,清澈而悠长;这一块花砖像不像眼前的魁峰,巍峨而俊秀;这一块花砖像不像茂林的十里长堤,蜿蜒而曲折……”
茂林花砖始于宋代,兴于明清。明清时期,人文荟萃、科举兴盛的茂林出了进士20多个、举人 130多个。这些达官贵人在茂林大兴土木,白如玉、青如墨、不沾灰、不上苔的花砖成为紧俏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达官贵人的门庭,甚至“一砖难求”。
从此,花砖从茂林出发,开始了它的“万里长征”。因为有“洛阳纸贵”的新派头,花砖首当其冲进入荣耀门第、大户人家。
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扁官巷内的德公厅屋最先享受恩泽。德公厅屋是为纪念被元顺帝敕封“明羲官”的永德公而建,其门楼既是厅屋的大门,又是一座可以独立的“义官”坊。《查氏宗谱》《查氏支谱》记载,永德公四个儿子均为明朝洪武年间的封疆大吏(广西兵备使、湖北巡察使、两河漕运使、浙江按察使),为纪念其父,彰显孝道,又不违背朝纲,他们睿智地将元代所建牌坊改为门楼。门楼四柱四层,有三层翘角,上有皇帝御书的“圣旨”和“明羲官”。德公厅屋虽位于巷中,不那么显眼,但是屋内的16根楠木柱子、呼之欲出的“鲤鱼跳龙门”花砖砖雕以及花砖饰面,都是无可挑剔的。其布局之巧、营造之工、结构之奇、装饰之美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永远为查氏家族历代子孙所景仰。
花砖荣登大雅之堂,显贵们趋之若鹜。始建于明朝的查济村宝公祠、洪公祠、二甲祠以及泾县桃花潭镇翟氏宗祠、茂林镇吴氏大宗祠等祠堂都用花砖来打扮自己,让这些明朝的建筑锦上添花。
花砖成为古建筑的“流行款”之后,又款款走进了清朝。泾县云岭镇陈氏宗祠、榔桥镇黄田敦睦堂、茂林镇尚友堂等民居,无不在花砖的点缀下变得花枝招展。
黄田村的思慎堂是当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的故居,这里有最大面积的水磨花砖墙面,同一块砖上有青、白两种颜色,白色似纸,青色似墨,像京剧脸谱,有的像“包公戏”里的包拯,有的像“三国戏”里的曹操、张飞,有的像“水浒戏”里的李逵,有的像“杨家将”中的焦赞,有的像“打严嵩”中的严嵩与秦桧……整体看上去,气势恢宏的花砖墙面又有中国画的五色墨法,气韵生动,纹理清晰,是难以复制的一绝。
每一块花砖都有不同的脸谱,绝不雷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花砖可谓是砖中的凤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友人来到茂林镇尚友堂,当他们看到质地古朴、花纹独特、不结蜘蛛网、耐腐蚀的花砖时,一个个驻足惊叹。有人掏出放大镜查看,有人用手摸了又摸,有人试图取下一块带走,还有人想出高价收购一组花砖,却被房主婉言谢绝……最终,尚友堂花砖的照片登上了日本《住宅建设》杂志的封面,让世界叹而观之。
曾任北大教授、安徽省泾县茂林籍的文学家吴组缃说,小说中的人物不可千人一面,就像我的家乡茂林的花砖一样,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绝不雷同。
正如每一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块花砖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个性的,有风骨的,有筋骨的。吴组缃撰写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将笔墨集中于宋氏祠堂这一隅之地,他以人物对话为推动情节和表现性格的主要手段,用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了20多个人物不同的身份、举止和心理,揭露了宗法制社会里一批“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小说中,那些破落衰败、纷繁多面的地主就像一塊块花砖一样,各有各的脸谱,有的虚伪,有的贪婪,有的残暴,有的下作,构成了一幅人物众多的脸谱图。
正如《一千八百担》里描绘的时代背景一样,鸦片战争爆发后,社会动乱,经济萧条,茂林生产花砖的窑工们也食不果腹,难以维持生计,被迫关窑停产,茂林花砖制造工艺也一度失传。
光阴从宋朝走到了今朝,在阳光雨露的抚摸下,如今古民居的花砖纹理更加清晰,手感更加舒服,用洁白的卫生纸擦拭竟无一点灰尘。尤其是门口触手可及的地方,花砖上已有一层包浆,质地更加细腻。
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泾县茂林镇的纪建新、泾川镇的郭维清争着“吃螃蟹”,破译花砖密码成为他们不懈的追求。
花砖纹理有黑、白两色,因而得名。纪建新找到干湿度、收缩度、黏合度等高度吻合的油黄土、高岭土,两种泥土加水搅拌成泥……经过取土、踩土、制坯、晾干、装窑、烧窑、看窑、闭窑、下水、冷却、出窑、水磨等工序,在屡败屡战中凤凰涅槃,成为茂林花砖制作技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装窑预留火路、闭窑要密封、下水注意流速、烧砖窑口放拦火砖传导热量……烧窑时,温度低了,砖烧不熟;温度高了,砖上的花纹就没有了。”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纪建新终于取得真经,破译了花砖密码,生产出茂林花砖。
和纪建新一样,郭维清也一直在花砖领域深耕。他俩“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像花砖两色一样,撑起了泾县花砖南北新天空。
郭维清千寻老窑工,配比高铝土和黄土,反反复复陈化泥土、制坯、试烧,也复活了花砖生产工艺,拿到花砖抗风化、抗静电、不开裂、不沾灰的秘方。2012年,他终于拿到了泾川水磨花砖国家专利。
从此,似神似仙的花砖像一只山中凤凰,一飞冲天。
“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如今,一片片花砖乘着非遗的东风,开始了长足的旅行,黄山、宜兴、哈尔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河南、北京和广东等地都留下了它的芳容。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下,花砖漂洋过海走到了日本、走到了意大利,走向了世界。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