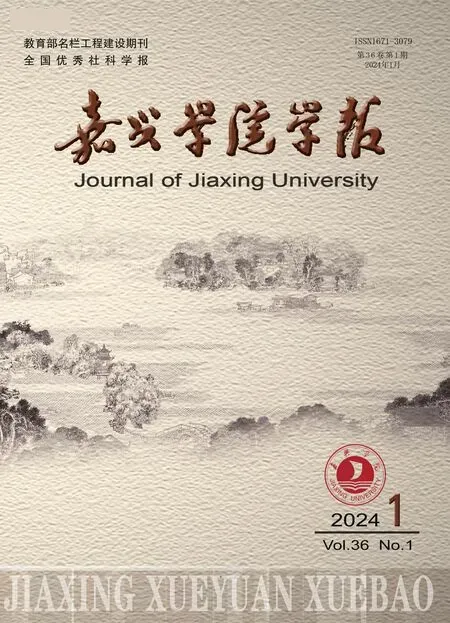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王金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8)
2001年,对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我国出台的法释〔2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在第4条中明确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规定,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虽然《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在立法层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依据,但在适用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践困境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尚存在一些解释不清、规定不明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规定,以促进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被正确地适用理。
(一)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不清
《民法典》中关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在《解释》第4条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完善,但未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作出明确界定。从学理层面看,我国学者主要采用类型化研究方式探究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之范围,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特定物以不同依据分为不同种类。由于各个学者分类化研究的依据各不相同,以理论指导实践的传统观点难以付诸于实践,百家争鸣的背景下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判断方式多样,难以统一。从司法层面看,经过长期实践的积累,各级法官逐渐形成一定的裁判经验,通常认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包括与结婚礼仪有关之物、近亲属死者相关之物和祖先遗留之物三类。[1]然而,上述规律也常有失灵的时候,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裁判以上三类特定物案件之时,仍有否定其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之裁判结果。此外,虚拟财产、宠物与体外胚胎等特定物是否具有“人身意义”引发学界激烈争论,关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还须从理论结合实践出发进行探讨。
(二)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体范围不清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仅规定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为“被侵权人”,其中“被侵权人”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无法明确具有人身利益但非所有权人的主体是否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侵权人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时,可能会导致两种性质不同的权益受损,即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虽然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时,物品所有权人肯定会遭受损失,但是其并非一定有资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因为在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畴内,存在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相分离的可能性。与特定物具有情感牵连但并非物的所有人,在该物受损后是否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尚不明确。在“钱钟书书信拍卖案”中,(1)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保字第 9727 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 1152 号民事判决书。“书信”同时承载着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且分属于不同权利主体。李国强(物品所有权人)将钱钟书书信拍卖,杨绛(钱钟书妻子)向法院提起侵害隐私权的诉讼,物品所有权人和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属于同一个人。虽然李国强拥有物的所有权,但该物并未承载其人身利益。当该书信作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被侵权人损坏,李国强仅能向法院主张财产权益的救济,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固然书信之上蕴含着杨绛的精神利益,但她并非书信所有权人,如果杨绛被认为属于第2款“被侵权人”的范围即可向李国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被侵权人”的范围的正确界定与否直接决定该项条文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三)主观构成要件立法取向过严
《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对侵权人的主观方面有严格的限制,仅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一般过失的行为不能造成该条的精神损害,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有误,立法者对适用的主观构成要件限制过于严格。
在主观要件上,《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过于考虑侵权人承担责任的适当性,而未着眼于受害人权利救济方面。[2]“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对其构成要件应当加以限制,若侵权人的过错形态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即使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也无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因为,侵权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侵害他人物权,但未必知道自己所侵害的特定物具有人身意义,除了遗体、骨灰盒等具有明显性质的物品外,法律不能期待性地要求社会公众对他人特定物上所存在的人身利益有明确的认知。如此,当侵害他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时,若侵权人没有明知该特定物所承载着人身利益,则其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3]从侵权人承担责任角度看,立法者对该条文解释似乎有道理,但对条文解释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侵权责任的规范目的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立法者应当着眼于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救济这一方面,过严的主观构成要件将成为被害人主张救济的障碍。虽然区分被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有立法者的相应考量,但在救济受害人方面可能并无价值。侵权责任的创设目的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观要件的规定似乎与其创设目的产生了偏差。
(四)对“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缺乏参考标准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关于“精神损害”严重性的认定缺乏参考标准,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长时间的局限和空缺。精神损害是自然人的精神遭受了痛苦,主观上的痛苦缺乏客观的评价标准,实践中无法利用客观证据予以充分的证明,或者说用客观证据来证明主观上的事实存在现实的困难。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易受其主观意志的影响,过于依赖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可避免地会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加入主观因素,以自己的经历和价值来判断当事人的精神损害是否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现。
二、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建议
着眼于社会公众的现实需要,为缓解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在适用中的困境,落实民法对人身权益的保护理念,可以对该条文作进一步解释。
(一)明确特定物中“人身意义”的判断标准
如前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界定不清,直接导致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条文适用困难,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范围界定的关键在于确定特定物之上是否存在“人身意义”。“人身意义”作为人与物之间亲密关系的表达,法官在判定时易受权利人的主观影响,要形成一个普适性的判断标准难度很大。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主客观因素去判定特定物之上是否存在“人身利益”以及“人身利益”的大小。
1.特定物是否为一般社会观念所认可。即以一般社会公众的角度思考,特定物上是否承载着公众所认可的人身利益。特定物上所蕴含的情感是一种社会公众认可而非特定主体仅凭个人喜好产生的情感。[4]在对情感的感知上,自然人由于社会认知、受教育程度、成长经历的不同,导致其对不同特定物所寄托情感的认知存在差异。同时,由于自然人寄托在特定物上的人身利益纯粹属于主观感受,以客观要素进行判断不免有些困难,为防止实践中被侵权人夸大其精神利益的受损程度,有必要建立“一般社会观念所认可”的标准以判断特定物上是否承载“人身意义”。一般社会观念作为一种共性观念,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民事主体与特定物之间的个性情感差异对案件的影响。
2.特定物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特定物上承载的人身利益能够被一般观念所认可,但能否满足《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中“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要求,还需要看其是否具有可替代性。通常情况下,同一类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可能具有可替代性,这就导致了精神损害是否达到严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以遗物为例,逝者生前所遗留的唯一首饰和一堆首饰,对于逝者后代而言,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不具有可替代性的遗物一旦毁损灭失,遗物中寄托的人身利益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进行恢复,使这种损害成为一种不可愈合的伤害。[5]因此,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应当作为特定物中“人身意义”的判断标准。
3.特定物是否存在特殊来源、特殊用途以及权利人对该物所持有时间的长短、爱惜程度等。与特定物是否为一般社会观念所认可以及是否具备可替代性等外部属性相比,权利人对特定物所持有时间长短、爱惜程度等内部属性更能彰显权利人与特定物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6]其一,特定物的获取方式多种多样,较为亲密的恋人、家人赠送的特定物往往寄托着某种特殊的情感,相较于市场上贩卖的同种商品,其与我们的人身利益联系更为密切。特定物因来源的差异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人类作为一种情感较为丰富的生物,善于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特定物内部,从而完成情感表达。其二,从人们使用特定物的方式也可以反映出特定物中是否存在情感寄托以及寄托情感的大小。若将特定物用于实际生活消耗,则特定物所蕴含的物质价值大于精神价值;若将特定物用于满足权利人的精神需要,则特定物中精神价值占比较大,往往能够满足特定物中“人身利益”的内涵。其三,权利人对特定物所持有时间的长短能直观地反映出特定物中有无“人身利益”。人作为富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日久生情的情感积累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也体现在人与物之间。一般认为,权利人对特定物保存时间越长,其情感倾注就越大,特定物上所蕴含的“人身利益”也相对更丰富。其四,权利人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能够判定该物在权利人心中的地位,可以作为特定物上所蕴含“人身利益”大小的考量方式。爱惜程度作为一种量的界定,能够判定特定物所涵盖精神利益的大小,却不能直接判定特定物中是否涵盖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因为物的金钱价值也能够直接决定权利人对物的爱惜程度,也即在明确特定物上所蕴含的“人身利益”后,以权利人对物的爱惜程度来考量特定物所蕴含精神利益的大小。
特定物的内部属性反映出权利人对特定物具备的紧密情感联系,该情感联系是判断特定物是否具备“人身意义”的重要特征。因此,判断特定物是否蕴含“人身利益”以及“人身利益”的大小要以物的特殊来源、特殊用途以及权利人对该物所持有时间长短、爱惜程度等内部属性对特定物进行综合考量。
(二)完善特定物中权利主体的界定
在可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上,我国学术界大致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狭义说”“广义说”和“最广义说”三种。“狭义说”认为,可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仅限于物品所有权人。[7]“广义说”认为,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仅限于物品的所有人和管理人。[8]“最广义说”认为,可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不仅限于物品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应当将请求权主体扩展到对特定物具有一定人身利益的权利人。[9]审视三种不同观点,“最广义说”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相一致,能够为具有人身利益但非特定物所有权人的主体提供完善的保护。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上存在人身和财产两种不同的利益,实践中存在人身、财产利益归属于同一权利主体与人身、财产利益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情形。主张“狭义说”和“广义说”的学者将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限制于一定的范围,无法解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上人身、财产利益相分离的情形,与《民法典》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相违背。从事实判断角度而言,三种观点的争议点在于可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范围不同。从“狭义说”到“最广义说”,可主张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范围依次扩大。从价值评价角度而言,当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上所蕴含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分属于不同主体时,物品所有权人和管理人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充分保护,由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上所存权利主体的复杂性,其权利主体不仅限于物品所有权人和管理人。以“狭义说”和“广义说”来界定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主体的范围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条文的困境,造成请求权主体的保护缺陷。人格权的本质是物权,但其本质意思是基于人格或生命、自由、尊严等产生对自由一切物的权利。[10]我们可以认为特定物之上所蕴含的自由、尊严、生命等人身利益应得到充分的释放,特定物上存在的人身利益不因其从属权利主体的不同而得到价值偏差式的保护,对于在特定物上具有人身利益但非所有权人、管理人的权利主体应当予以充分的保护,以满足“人格权向财产权夺回桂冠”的趋势。
单个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之上可能有不同的权利并存,且权利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主体,若是仅仅规定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之权利主体为物品所有权人,不免会遗漏保护那些具有人身利益但非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11]因此,为了维护具有人身利益但非所有权人的合法利益,需要对《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中的“被侵权人”进行进一步界定,将在特定物上具有人身利益但非所有权人、管理人的权利主体纳入“被侵权人”的范畴。同时,以理论指导实践,法官在判断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充分考虑特定物权利主体的外延,对寄托情感于特定物的非所有权人主体予以认可,维护案件的实质正义。
(三)将“一般过失”纳入行为人主观过错形态之中
从立法层面而言,将“一般过失”纳入行为人主观过错形态之中有利于保持法条一致性,维护实质正义。立法者设立《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和第2款的初衷是维护受害者的精神利益,两款条文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落脚于严重精神损害,不同之处在于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较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其主观要件更为严格,即前者主观要件只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后者除故意和重大过失外还包括一般过失,立法者如此规定似乎并不周延。依笔者之见,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并不必然大于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而造成的精神损害。当被侵权人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时,其是否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在于侵权人主观过错,而应当着眼于被侵权人是否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因此,将“一般过失”纳入《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保持其与第一款的一致性,更有利于维护实质正义。
从司法层面而言,将“一般过失”纳入行为人主观过错形态之中有利于保障受害人的诉权。《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对侵权人的主观要件规定较为严格,被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侵权人主观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意味着若侵权人因一般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被侵权人严重精神损害,则被侵权人没有向法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若被侵权人坚持向法院起诉,法院将会驳回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试想,张三故意毁坏李四生母生前唯一照片和张三一般过失毁坏李四生母生前唯一照片,都造成了李四严重的精神损害,此结果有何不同?在造成结果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得到法院截然不同的受理结果?法院在面对一般过失侵害特定物的案件时,采用驳回起诉的处理方式违反了该条文的立法初衷,偏离了民法保护受害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应当将“一般过失”纳入《民法典》第1183条第2款侵权人的主观要件中,保障法院对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方式不受侵害人主观过错的影响,从而维护受害者的诉权。
(四)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认定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的标准
对于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这一构成要件,关键是判断何为精神损害的“严重”。有观点认为,所谓严重精神损害,就是超越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2]这种观点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统一裁判。对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严重性”的认定,应当结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建立一套司法实践的普适性标准。
客观上,判断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性”,应当结合特定物的类型、特定物的毁损程度以及对被侵权人的生活影响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侵害坟墓、骨灰等带有伦理道德因素的特定物,无需致使其灭失即可造成被侵权人严重精神损害。原因在于该种特定物所承载的人身利益具有社会一般人认识的可能性。这种判断标准类似于英美法上的普通损害,即无需当事人举证,仅依靠法律认定的不可反证之损害,法官在审判此类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只须结合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即可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侵害婚礼录像、死者生前录像等特定物则须达到“永久性毁损或者灭失”的程度,因为记录特定场景的录像是不可恢复的,只有在其毁损或灭失时才会造成被侵权人严重的精神损害。同理,法官在认定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时还需考虑特定物之损害结果对被侵权人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同一个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行为对不同权利主体的精神生活影响不同,被侵权人生活质量的下降与否可以直观地表现精神损害是否“严重”,若被侵权人的生活未因特定物的损失而产生不利影响,我们通常认为精神损害未达到“严重”的程度,被侵权人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12]
主观上,判断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性”应当结合一般人的认知标准。在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领域,只要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且这种精神损害是社会一般人所认可的,侵权人就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于一般人的认知标准属于纯主观因素,侵权人在司法实践中举证较为困难,因此,法院在判决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当将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以主观因素作为参考。
综上,在认定特定物精神损害“严重性”的标准时,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采取统一的标准,用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分析具体案件中被侵权人的精神利益损害是否达到了“严重性”的程度。一方面,设置客观标准可以明确该案件中的侵权行为是否有造成被侵权人精神严重痛苦的可能性,规制案件处理过程中的认定标准,将法官对案件的主观看法的影响降到最低,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缓解“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另一方面,增强法官对案件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尊重法官的自由心证原则。在客观标准的条件下,允许法官结合一般人的观点对侵权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了被侵权人的严重精神痛苦作出判断,积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使其灵活对案件作出处理,有利于增加司法实践过程的顺畅,避免法官机械执行法律,造成司法实践的僵化。因此,采取主客观相一致的认定标准,有效发挥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官裁判的灵活性,尊重立法和保障司法,有利于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平稳实施,增强法律的教育功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