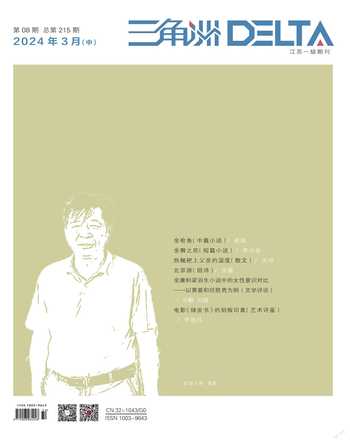“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与“作者之死”
向柯洁
古代文论中,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强调,文本的功能却被忽视,直到十八世纪“作者之死”之后,文本才获得了独立地位,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文本与作者本人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于文学活动。这段文本所蕴含的意义极为丰富。保障读者自由的同时,文本的独立性也为作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诠释方式。
知人论世
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了一种著名的文学批评方法,即“以知人论世”,这一方法被广泛引用,指出了解一个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是了解他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的关键。探究一个作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对其论世的必要认知。知人论世,就是要从历史角度研究作家及其作品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原因。孟子主张,文学作品与作家自身的生活思想及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只有对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创作生平等进行深入探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社会背景,从而对文学作品的构思和题材有一个客观而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知人论世”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知人论世”实质上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定时代的产物并与作者生平相结合加以研究,这是古代以来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更贴近并恢复了文学作品的真实面貌。放到阐释学中,文学作品的原义是有的,或者说相对贴近原义的状态是有的,但现在的文学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接受了美学风行以后,总觉得原义不重要,怎么读才重要,重点在于读者的阅读,但孟子告诉我们,不一定如此。“知人论世”还注重文本的历史价值与实用价值,把诗歌等当作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反映了中国古代悠久的史学研究传统,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学会研究、考证,而不是依靠空地用自己的思想表达对作品的认识,一切看法与认识都必须有据可依,这就强调了阐释学的语境意识,又体现了第三种观念,强调语境对文本意义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引发出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永远历史化。历史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同一时代的人们有其共通性,文化则有其时代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就成了知人论世的重要理论依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提示我们语境或背景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基底,而是始终参与到意义产生中来。
但不可否认,孟子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首先,这种以“人道”为中心的诠释往往忽视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解释,实则是运用一种审判和独立判断的方式,进行最终审判。这种结果往往会导致文本被肢解和消解,无法实现其意义。其次,这将引发一种倾向,即对“庸俗社会学”的追求。庸俗社会学把文学当作一个纯粹的纯学术领域来看待,它对文学创作中的许多现象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引导读者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简单的历史资料,忽视了作者个性和审美问题,从而导致作者或社会与文学作品之间单向、直接的因果关系。最后,会造成对文学自身价值的遮蔽性理解。审美的力量超越了社会和时代的限制,超越了功利性的范畴。
以意逆志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即“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孟子·万章上》。后来人们把这一句话用来比喻读诗时必须注意把握字面上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不可因字面意义影响到文章主旨和艺术特色。阅读诗歌时,不应受限于个别文字的华丽,损害对辞意的理解;也不应被个别词句所束缚,损害对作者思想和情感的理解。“意”所涵盖的是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志”则是作品所传递的情感和意图,或者说是作品的创作目的。先秦时期,“言不尽意”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它只是一种解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所以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在春秋时期,当解读诗歌时,出现了一种脱离语言环境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阐释方式,旨在满足孟子在春秋时期只满足自身需求的挪用阐释。
“以意逆志”也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它肯定了作者的主体地位。在作品的阐释过程中,作者被赋予了权威角色,成为作品意义阐释的权威。作者及其“志”具有的客观性、社会性因素已被确认,这为解读文本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出了作者在创作时应该有客观性,有一个“志”接下来在阐释的过程中,应该可能阐释出作者的本来之“志”。“以意逆志”还从解释的角度揭示出一种“文—辞—志”的理论结构系统,与孔子从创作角度揭示“志—言—文”的系统遥相呼应,相互阐释。
对于“以意逆志”这一理论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首先,该文旨在追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而非仅仅追求作者意图的恒定不变。其次,“以意逆志”并不能完全消除作品意义与接受者理解之间的矛盾关系,要想提高文学接受的效果,必须把文学作品置于具体情境之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读者对文学文本的解读能力,使阅读变成一种考证和考据,就像文本中蕴含着一个明确的意义,读者却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所以,阐释过程必须考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读者自身对作品理解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接受活动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創造。然而,所接受的结果并未呈现一种普遍的唯一性。在接受理论中,应以“作者之心”为唯一的阐释目的。
作者之死
类似“知人论世”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论,西方也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传记批评”。圣伯夫法国著名传记批评家提出了“传记批评”这一理论,其批评聚焦于作家的生活,通过对作家的分析来解读作品,被称为传记批评。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开始经历一次重大转型。传统的作者论逐渐走向现代读者中心主义。在此背景下,对于“传记批评”这一议题,人们重新探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罗兰·巴尔特并非首位反对传统作者理论的人,但在他于1967年发表的《作者之死》一文中,他以一种直接、全面、正式的方式宣告了作者的“逝世”,成为“谋杀”作者实践中的致命一击。作者之死的实质是读者对文本的参与,读者则被置于一种特殊位置上——作者死于读者之手。巴尔特主张,只有在作者被埋葬后,人们才能将注意力聚焦于文学本身,因为文本意义的生成受到作者在场的制约。
在《作者之死》一书中,罗兰·巴尔特主张,文本可以脱离作者的身份,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实体,从而呈现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文学进入浪漫主义时代之后,作家们的创作活动也越来越自由。罗兰·巴尔特主张,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作者已经“死去”,其旨在使读者不再依赖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而是以阅读文本为主要方式,借助自身的思想,以自由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在文本与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开放的对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当作者的生命结束后,读者才能获得新生。这意味着,只有读者与文本之间进行对话,相互沟通,共同建构起一个新的意义世界,从而实现文本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只有透过读者的视角,才能深入挖掘文本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从而实现文本的真正价值。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者之死”所带来的限制。首先,作者去世后,读者可以通过文本生成文本意义,从而使作者无需对文本的语言或意义承担任何责任。一般而言,我们所指的某一篇文本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能够传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而非仅为了让读者自行组合而随意解读;其次,读者在阅读某一文本时,所追求的并非自身生成文本的意义,而是深入挖掘作者在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以达到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世界里,读者并不能成为文本意义的真正创造者,而是被文本赋予一定意义的人,或者说文本的意义只能由读者自身来创造。若读者生成文本的内涵,则其对文本的诠释并不具有正确性或错误性,因为本质上不存在任何误解。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便完全丧失,其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将荡然无存,最终沦为无源之水、无水之木。
二者的联系
无论是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还是巴尔特的“作者之死”,都是对作者文学作品的权威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要强调的是“作者之死”并不代表作者完全死亡。尽管存在对立的观点,但它们都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孟子强调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和背景,以促进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确认作者的主体地位,巴爾特则注重否定作者的权威和重视读者阅读过程。
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导致我们脱离了西方理论话语,无法对文本进行有效阐释,甚至认为早期中国古代传统文论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反对“强制阐释论”,并挖掘自身已有的文论资源。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即作者是否应该“死”。
罗兰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并不是要让读者完全放弃作者,而只是希望读者能够不受作者思想与社会身份的束缚。他认为作者应该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而不是作品的全部,从而使读者不再受作者影响,摆脱对作者的控制。然而,作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分割的,读者需要摆脱作者的霸权,摆脱其创作意图的束缚,积极观察、思考、领悟和诠释,而不是被动接受。作者必须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对读者进行引导和控制。作者作为一位缺席的在场人,通过文本与读者建立了思想上的纽带,从而诠释了文本所蕴含的情感共鸣,这象征着文本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和升华。
尽管“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作者之死”看似相互对立,但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如同鸡生蛋、蛋生鸡的难题一样棘手。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作者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种相对的、多义的、单向的存在,它不会导致作者的消亡。在文学文本中,“作者之死”是一种必然现象。
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除了需要读者的想象力参与,作者的引导和暗示也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那些叙述描写最详尽细致的作品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往往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取向,即他对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或观念的阐释与接受。读者在解读文本之前,已经接受了自己以往的经验。尽管作者已经逝世,在解读文本时所获得的信息将逐渐减少,然而通用的审美平台和历史上积累的艺术经验却不会因此而消逝。所以,文学接受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期待视野,即“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这些经验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但如果脱离了这些经验,就会陷入过度的解读之中。要想让读者真正读懂作品,就必须在解读之前对文本作一番精心准备。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作者已死”,都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中发现其中的深层含义。对于文本的理解,我们可以运用单一理论,也可以运用多种理论,以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