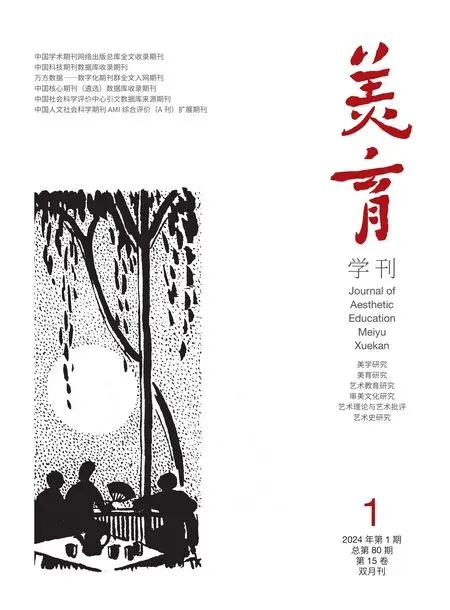当代艺术的审美危机与救赎方案
张泽鸿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一、引言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现代社会在不断“祛魅化”(Entzauberung)[1]的进程中加速与分化,人类的艺术生产也迈入了本雅明所谓的“后灵晕”(post-aura)的现代性阶段。按照波德莱尔的观点,现代性本身就暗含着“永恒”与“瞬间”的悖论,一方面对传统保持欲拒还迎的态度,另一方面追逐“新之时尚”。在灵晕日渐消散的现代艺术世界中,审美经验也从对古典艺术永恒之美的凝神观照蜕变为对先锋艺术的“震惊式体验”(本雅明语)。据此我们可以说,诸神的退隐、世界的祛魅、文化的媚俗化以及现代艺术的去审美化(anti-aesthetic),共同构成了审美现代性进程中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
自20世纪初达达主义开始,现代艺术逐渐演化到激进的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阶段(1)从时间上说,当代艺术被认为是现代艺术更为晚近的阶段,现代艺术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实验”艺术的兴起,而当代艺术一般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艺术;从精神特征说,当代艺术要具有“当代”精神,应是富有“先锋逻辑”的艺术,当代艺术是后现代艺术的同义词。参见河清:《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25页。,这一阶段被丹托命名为艺术终结之后的“后历史艺术”,即所谓“达达主义之后,艺术里头再无新事”[2]。在艺术哲学家看来,当代先锋派艺术是“过度历史化的产物”[3]30,其内部充满危机:从历史层面来说,它表现为“具象艺术”(figural art)向“抽象艺术”(abstract art)转向的范式危机(2)亚菲塔精辟指出,具象艺术在20世纪已是一个衰落的范式,而新的艺术范式尚未产生,现代主义不过是具象艺术的范式危机尚未化解所产生的副产品,今日的艺术危机不是现代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具象艺术的范式危机。参见齐安·亚菲塔:《艺术与非艺术》,王祖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0页。;从现实层面说,当代艺术本身存在审美危机、表征危机(表象危机)、意义危机以及合法性危机等。这足以表明,当代艺术是新旧范式转换中的历史过渡形态,它们本身就是传统的具象艺术出现范式危机的一种征兆。从意指逻辑上看,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3)按照霍尔的解释,表征(representation)就是使用语言、符号或形象等任一意指系统来有意义地表述世界,即“通过语言生产意义”。按照构成主义的表征理论,表征为了实现意义生产,它需要在三种不同序列的事物——经验的世界、概念的世界、可传递概念的符号(意指系统)之间建立联系来达到,即通过编码和解码过程来实现概念的传递和意义的滑动。语言符号作为意指系统,它首先指向概念世界,概念世界最终指向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事件和经验,完成表征的过程。所谓“表征危机”,就是在符号系统、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出现断裂,语言的意指系统进行自我指涉,无法与概念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当代艺术家往往通过拼贴、挪用、戏仿或观念化的手法来制作艺术品,传统艺术的符号、形式和形象等意指系统被彻底颠覆,艺术的形象性被摧毁,艺术失去了表征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功能,艺术的意义生产被消解,这就是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参见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1-62页。是以形象/幻象的危机(crisis of illusion)形式体现出来的,因为当代艺术拼贴、挪用和复制现成物或其他艺术品,不再具有传统艺术那般完整化的感性形式,某些艺术甚至透过传闻即可被欣赏:“如今不再有艺术品,有的只是艺术的境遇。”[4]50艺术生产比艺术对象更重要,追求“没有艺术品的艺术”。所以在形象/幻象迷失的后现代语境中,艺术的表征功能出现严重衰退,它不再指向现实世界或观念世界,而沦为空洞的自我指涉之物,在艺术符码的自我增殖中,所指与能指不再保持同一性,从而引发意指的危机。(4)意义的危机主要有两方面体现:一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缺乏明确易懂的意义,无法被一般受众所理解;二是艺术批评和阐释的多元性,带来作品意义的含混性、不确定性或矛盾性。艺术的形象危机必然导致审美经验的贫乏症,因为审美是基于感性形象的,而当代艺术早已突破生活的界限,追逐去定义化和反审美化的现成物,或者成为去物质化的观念性存在,其感性特征和审美自律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当代艺术危机本质上是“表征的危机”,并进而引发形象再现与审美经验的双重危机。
当代先锋艺术的表征危机和反审美化倾向滥觞于杜尚和达达主义,1917年杜尚的现成品(ready-made)艺术作品——《泉》的诞生,严峻挑战了艺术定义,也颠覆了传统美学的“趣味宰制”(tyranny of taste)。杜尚对现成品的挑选标准是建立在冷漠的视觉反应之上的,现成品艺术恰处在“好”与“坏”的品味同时缺席的状态中,是一种彻底的去审美化对象。自此,现代艺术跨越感性的界限与审美决裂,徘徊于更为复杂的生活化与去审美化的边缘境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达达主义引领之下,当代艺术批评提出了“艺术(史)终结”和“艺术理论终结”[5]的诸多主张:一方面,古典艺术的“神圣性”光晕全面消散,“艺术乌托邦”走向终结,艺术拒绝感性经验而走向观念思考;另一方面,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审美模式(“艺术是美的”)对当代艺术失语,一种总体性的艺术理论不再可能。从古典艺术到当代艺术不断激进化的范式变革,最具有颠覆性的主张之一就是“艺术与审美无关”,诚如阿多诺所说,真正的艺术总是向其自身的本质(美的定义)提出挑战,当代艺术便是如此,它不仅拒绝传统艺术的感性形式,还质疑和颠覆既有的本质规定性,这使“今日之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艺术的挽词”[6]3。当代艺术的表象危机或“功能表征的危机”[3]198,不能依靠自身的改变来解决,“慢慢地回归再现的作品”[4]52越来越不可能。换言之,我们无法通过重建形象体系来再现现实或表现真理,自动化解危机,而只能寻求外部的理论解释,或通过有效的美学阐释来予以赎救,“与其谈论艺术合法化的危机或艺术表征的危机,更应该谈论美学言论在试图把握当下创作时的危机”[7]193,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构直面当代艺术的新的美学话语。当代德国涌现了诸如“显现美学”“气氛美学”“突然美学”等新美学流派,这些新的理论话语都试图突破康德美学藩篱,注重吸收知觉现象学、实用主义、身体美学以及鲍姆加登美学资源,以重建审美感知经验为中心,对当代先锋艺术的审美危机作出合理阐释与感性救赎。
二、当代艺术的反审美与观念化
长期以来,西方生产现代艺术的土壤“经历着参照系的瓦解,忠于自然、美、和谐等观念的解体,以及古典标准的解体”[7]8,现代艺术宣告与(古典的)“美”(beauty)无关,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晚近艺术潮流和动向看,“美”不再是艺术最重要的目标[4]149。当代艺术进一步寻求接近日常生活,现成品成为最寻常的艺术实践,因此在趣味判断上,要么走向“非美”和“丑”,要么走向崇高(sublime),总之,审美无效说颇为流行。1917年,杜尚的《泉》(Fountain)横空出世,宣告了现代艺术“审美的终结”。杜尚、沃霍尔等前卫艺术家们在选择现成物时不带任何美学情感,如杜尚所说:“选择现成品也常常基于视觉的冷漠,同时,要避开好和坏的趣味。”[8]他的现成品艺术是对传统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的根本否定,杜尚之后,现代艺术拒绝“美”的定义成为一种惯例。可以说,当代先锋派艺术彻底祛除了古典艺术神圣的、美的光晕,因而无论是康德的美学理论,还是格林伯格的现代艺术理论,在分析、阐释先锋艺术以及赋予其合法性方面,都变成了相当拙劣的工具。当代艺术创作的异质性,即对全新材料、形式、物品和载体的应用,对自然、身体、技术等主要议题的探讨,必然导致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和美学都受到了深刻的质疑。[7]63当代艺术不断升级的对艺术体制、道德、审美甚至法律的僭越,以及面临的意义危机,驱使西方理论界——如英美分析哲学、法国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等——着手建立有关艺术定义、艺术制度和艺术合法性的阐释模式和分析框架,以回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艺术所面临的后现代困境。
在分析美学阵营中,“当代艺术无关审美”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自觉,如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所言,“当代艺术有一个特点让它区别于15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艺术,那就是它首要的目标不是审美”[9]183,“从杜尚的作品开始,大量后现代艺术根本就没有美感之维”[10]。杜尚以后的当代艺术在本质上都是概念性的存在,美学的关联性遭到了当代艺术的严峻挑战。现代艺术史企图证明美与艺术没有必然联系,甚至说“艺术减去美的污名,就成了世界前进的方向”[11]118。在丹托看来,当代艺术哲学要告别黑格尔时代的美学,旨在建构一个极端反审美化的话语体系,丹托认为今天的艺术哲学不同以前的美学,它的任务是要解答艺术是什么,何物能成为艺术,以及考察是什么将艺术从非艺术的世界中区分开来。显然,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无法合理解释什么是当代艺术,因为“艺术前卫的能量打开了艺术与美之间的裂痕”,在当代艺术中,“美”已被彻底废黜[11]25-30。丹托认为,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和沃霍尔的波普艺术,都是一种“意义的呈现”(embodied meanings)(5)丹托认为只有通过“艺术状态”(artness)才能理解艺术的本质,艺术本质无非是“意义的呈现”(embodied meanings)。参见Arthur C.Danto, What Art Is, 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3,p.37。,而不是“美”(beauty)的现身。
当代艺术极力去审美化,并对“美”进行污名化,这一现状也迫使当代美学界做出回应。吉梅内斯(Marc Jimenez)认为,当代艺术早已颠覆传统的审美体制和艺术体系,因此亟需建立一种当代语境下的美学新模式,重新对当代艺术作品进行有效的阐释和批评,以解决当代艺术的危机,这也意味着拒绝让艺术界本身成为评判“当代艺术是什么”等问题的唯一裁决者。[7]173当代艺术仍未超出美学范畴,因此需要引入一种全新的美学思考,去评判艺术与非艺术、挑战与骗局、审美与商业的边界问题。丹托认为,古典美学无法思考“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因为后现代的艺术嘲讽一切前现代的审美品质,因此,“作为理论的美学如果还想在面对艺术时有所助益的话,它就迫切需要被修正”[9]85-86。按照丹托的逻辑,必须从思辨的美学走向实际的艺术批评,在批评实践中建构崭新的美学话语。
由于当代艺术的日趋观念化以及观念艺术的流行,艺术理论界也逐渐以“观念”(concepts)代替“美感”(sense of beauty)来理解艺术,思想(理论)成为当代艺术研究的重心。自丹托宣告艺术终结之后,与之相关联的是审美判断的终结,值此语境下,“当代艺术还能是美的吗”似乎已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当代艺术的“反艺术/非艺术”倾向,进一步彰显了当代艺术的审美危机。“当代美学不能忽视艺术早已进入后先锋派阶段的事实,也同样不能忽视历史上的先锋主义运动给艺术领域带来的深刻变化。”[12]因此,与其谈论艺术的表征危机或形象危机,不如谈论美学话语在试图言说、批评当代艺术时的失效,也就是说美学阐释出现了危机。换言之,当代艺术表征危机的去除,有待于美学危机的先行解决。如果承认当代艺术危机是一种审美危机,那么此危机的最终解决,只有依靠新理论的出场,需要美学家们建构一种直面当代艺术的美学话语,实现美学对当代艺术的收编。戴夫·希基(Dave Hickey)曾预言,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艺术将会重新转向“美”,试图引领当代艺术批评的“审美回归”[13]。尽管从艺术实践看,当代艺术还很难说已重归“美”(beauty)的路途;但从美学理论界的新动向看,审美回归已有积极成果,譬如当代德国美学试图重新思考和回应当代艺术的审美属性问题,继续发挥美学理论对艺术的批评适用性,这成为当代德国新美学建构的主要目标。
三、显象的游戏:当代艺术的审美感知
针对当代艺术的阐释和批评,西方学界产生了反美学与新美学两套不同的阐释话语,前者以英美分析美学为主流,后者以新现象学影响下的德国新现象学美学为代表。关于当代艺术的反美学化阐释,笔者已有专论[14],而新现象学美学对当代艺术的审美阐释路径也值得借鉴。这其中,被保罗·盖耶(Paul Guyer)誉为当代德国最杰出美学家的马丁·瑟尔(Martin Seel)[15]在21世纪初所建立的“显现美学”(Aesthetics of Appearing),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崭新的美学理论话语,并对当代先锋艺术作出了深刻的感性重释。
按照马丁·瑟尔的看法,显现美学以分析审美感知经验为立足点,其研究重心集中于审美对象如何“显现”问题,审美感知所要把握的不是审美对象的实在性,而是审美对象此时此地的感性状态。瑟尔的显现美学认为,所谓“显象”(Erscheinung)就是指对象中“可以通过概念来区分的对象的感性特征”[16]41,它是对象在此时当下的感性状态、感性特征;而“显现”(Erschein)是指一个对象“诸显象间的游戏”。换言之,显象是一个对象的“出场方式”,而显象的出场与逗留(Verweilen)就是显现,也就是对象感性特征的多样性或“感性构造”的显现。譬如一个球(对象),它可能具有诸多显象:红色的、圆形的、潮湿的、躺在草地上、转动的等等,显象是复数的。我们可以借助一种或多种感官,从一个或多个立场去感受显象的差异性,对象的感性显象是诸多的,而不是单一的。在一次具体的审美感知中,某个对象的感性显象被主体的感知所把握和体验,就完成了一次审美的经验,对象的显象或显象间的游戏在审美经验中被呈现出来,“审美逗留让某物完满存在”[16]47,这就是美的显现与生成。显现美学主张一切审美对象都是诸显象的游戏,这具有三层非凡的意义:一是审美活动具有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能性,因为审美感知是对任一对象身上出现的“显象游戏”的关注;二是审美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经验领域,而是任何经验都可以随时随地转化为审美经验;三是任何对象都可以随时随地转化为审美对象。[17]这正是显现美学理论的独到之处。
在康德鉴赏判断理论的基础上,瑟尔强调审美对象与审美感知是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两个概念,他说:“审美对象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感知的对象,这种感知不是对某种孤立的显象的感知,而是对于其对象的显象过程的感知。”[16]3-4在审美活动中,审美对象是一种显现之中的对象(“显象”),审美感知经验是对这一显现的关注,“显象”是指对象朝向主体显现的感性状态,它是对象的一种独特的出场方式。(6)显象作为审美对象,在审美感知经验中的显现具有“此时此地性”,可借用王阳明的“南镇观花”典故来解释显象的出场方式:“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此时此地,花树的“颜”(容)、“色”(彩)、摇曳的姿态等都是显象,也就是花树对主体显现出来的感性状态,这些诸多显象之间构成了一种“游戏”关系,从而被主体(我心)所体验到,呈现为美的意象。由此可见,作为审美对象的“显象”是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东西,审美经验(显现)就是主客融合的“逗留经验”。就此而言,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艺术品,它们作为审美对象,就不再是客体(object)的实在性,而是客体的感性状态对主体共时的显现,此时的审美对象是一种过程性的复杂事态,不再是静止之物,审美对象是“暂时”的显现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瑟尔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时间的艺术”[16]5-6。按照显现美学的理路,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在我们的审美感知经验中生成、显现和逗留,它是同时和暂时的“显现者”,是诸显象在相互游戏,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作品就是“一种有意味的显象”。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是充满灵晕的(aura)古典绘画还是令人震惊的机械复制影像,都可以在感性经验中实现“诸显象的游戏”和幻象呈现。20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似乎反复地从自身中驱逐感性的“显现”,但在瑟尔看来,去物质化、非感性的装置艺术却是一种独特的“成全显现”的艺术。下面拟从三个案例来具体分析显现美学如何重现当代艺术作品的感性特征(显象),从而实现美学理论对当代艺术的有效批评并化解当代艺术的审美危机的。
首先,显现美学如何感知杜尚现成品(ready-made)的显象?瑟尔认为,杜尚的《泉》《晾瓶架》《断臂之前》等现成品都是介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一种颠覆性的艺术对象,它们看似寻常物,实则不然:它们被演出和展览,因此获得了与其他普通对象不同的显现。丹托认为现成品艺术与普通物品在外观上别无二致,因此需要寻求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知识来解释,只有在“艺术界”的语境下才能对其进行反审美、反感性的理论判断和认定。就《泉》而言,丹托认为杜尚创造了一个“没有美学的艺术”,是“用知性代替感性”,探讨“小便器美学”对于这件作品是毫无意义的[11]96。而瑟尔认为丹托对现成品艺术的去审美化解释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艺术对象在显现方式上是不同的,而“对于看待任一非艺术对象而言足够的感知,对于一个艺术对象来说是不够的。只要我们把某物看成造型艺术品,我们就能在它身上发现完全不同的视觉特征,有别于孩子们所描述的那些特征”[16]122。这就是一种更加特殊的艺术式显现。同一个主体,对于艺术对象与非审美对象的感知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艺术对象(审美对象)的感知方式有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某物被赋予造型艺术作品的身份,就要求我们能在它身上发现完全不同的视觉特征(显象)。
其次,观念艺术的感性显现如何可能?瑟尔着重分析了科苏斯(Joseph Kosuth)的观念艺术作品——《作为观念的观念艺术》(Artasideaasidea)中的审美难题。科苏斯将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定义为“哲学之后的艺术”,实现当代艺术从视觉形式向观念形式的转换。科苏斯的观念艺术滥觞于杜尚的思想,杜尚认为一件艺术品从根本上说,艺术家的观念最为重要,其物质形式是次要的。由此可见,观念艺术以概念取代媒介,以思想僭越物质(object),是一种去物质化(dematerialized)的、裸露思想的艺术。科氏《作为观念的观念艺术》由六幅独特的“油画”组成,黑色画布上写着白色文字,无多余的色彩和图像,画作上的文字呈现为红、蓝、绿、黄、橙、紫六种颜色。当然此处并没有呈现视觉经验上的色彩斑斓,而只是词典上对于这六种颜色的解释。瑟尔认为,科苏斯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把“观念”与作为艺术实现过程的“呈现形式”区分开来,不像传统艺术作品那样,思想与其显现的特定形式绑在一起。观念可以有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的任意显现(感性状态)。《作为观念的观念艺术》由许多黑板构成,黑板上的黑底白字是高度放大的字典词条的复制,其感性显现于三个向度:(1)词条来自哥特体的英德词典,里面有发音、解释和用法说明,构成一种“文本的音响”。这段文本处处提醒艺术和艺术品的处境,观者可以思考该艺术独特的出世与入世,或者设问:此处的这个对象是所谓的抽象还是具象的展品。(2)通过文本的高度放大,单个字母的特点得到明显改变,同样的字母看上去不再一样,此即印刷的不规则性(这在字典词条阅读时是忽略不见的),使得字符获得了一种“绘画性质”,看上去好像“手工制作”,像一笔一笔涂画上去的。因此,它们丧失了标准化符号的特点,获得了一种图像式的独特性。字母脱离它们所构成的文本,连成了图形的舞蹈,在黑色的背景上进行着明亮的表演。(3)观者在看到这幅“图画”时,展开了声音与意义、文本与装饰、连续阅读与同时看见之间的相互交叉重叠的戏剧——诸显象的游戏。文本变成潜能的图像,“在语言和视觉之间架起了桥梁”[18]。由此可知,为了呈现一种“作为观念的观念”,需要发音与书写,需要声音、线条和其他感性对象构成的全部审美储备——这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曾长期经营的东西。换言之,对传统绘画手段的否定性运用,在科苏斯的观念艺术中却被证明得到了强调的运用,所以,观念艺术中的诸显象以一种更为复杂多变的状态重新回到审美经验之中。
另外,不可见的装置艺术可否实现“审美显现”?瑟尔以瓦尔特·玛利亚(Walter De Maria)的《地下1公里》(1977)这个作品为例,阐述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装置艺术在审美经验中是如何显现的,显然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地下1公里》这个作品在一块砂岩板中间放置一个黄铜盖,盖子下面有一根很长的管子插入地下,这个黄铜盖掩盖了内部的一切。这个作品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是一件“看不见”的作品,它拒绝感性和经验性,只依赖创作者和知情者所赋予它的观念而存在。观看这个装置的人,无法再获得它第一次展览(建造)时的那种直观的东西,只能通过画册或有关文章来获取相应的知识。这个作品的感性“显现”是否可能?瑟尔却认为它仍然是可以显现的:“它通过对雕塑姿态的拒绝,雕塑姿态赖以展开的空间关系变得显眼。即使不可见也能变成显现事件。在此意义上,《地下1公里》正好满足了艺术的传统要求:赋予其对象以几乎不可能的显现。”[16]127瑟尔认为,这个艺术作品实际上是一个颠倒的纪念碑,需要借助审美想象去填充。当我们站在盖板上,就如同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雕像尖顶,它是通过其不可见维度来完成的地点的中央。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维度,才能够在这个地点获得对地下空间的感性——察觉意识,因为它多倍地超过任何雕塑、建筑和风景空间。站在几乎无物可见的地方,我们在地基上搜寻,因为考察对象的缺失而同时面临失去该地基的危险,通过对雕塑姿态的拒绝,雕塑姿态赖以展开的空间关系变得醒目。因而,即使不可见的也能以此变成“显现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作品正好满足了艺术的传统审美要求——赋予其对象几乎不可能的显现,如同中国艺术所谓的“象外之象”“境生于象外”一样。在瑟尔看来,对现成品和装置艺术的审美直观是离不开解释的,《地下1公里》这件作品是需要建立在解释之上的对象,它只对那些掌握特定历史与艺术史知识的人才有效。感知者所应当具备的所有的艺术史知识、反思、解释和想象,都具有意义,可以用来复活作品的艺术显现。[16]96-97因此,这件深埋地下的装置作品并不能构成显现美学的反例。
概言之,瑟尔的显现美学以“显现”(Erscheinen)这一概念为中心,建构了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几乎所有审美对象所共有的一种“现实性”。审美就是通过对一切感性事物进行直接感知,把握其深不可测的特殊性,获得当下(在场)的直观[16]11-13,这一“当下显现”的理论与观念化的当代艺术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悖论:当代艺术似乎反复地从至自身中去除了“显现”,无论是杜尚的现成品还是玛利亚的装置艺术,按照一般艺术批评家的观点,我在此所面对的对象超越了“感性显现”,而“显象游戏”和“显现事件”的重新阐释,一定意义上证伪了当代艺术反审美的观念。现成品、装置艺术和波普艺术等通过将在外观上完全无异于日常对象的事物带入艺术语境,强调艺术与审美无关,但瑟尔认为,审美从来就不依赖于固定事物,只是依赖一种此时此地的“显现”,一种审美感知与审美对象相遭遇的特殊方式。现成品和波普艺术在讥讽传统艺术趣味的同时,所借助的也是独特的感性状态,它们通过语境重置和命名,以重新出场的方式(“显象”)而被感知。
四、气氛的迷狂:当代艺术的通感经验
与瑟尔的显现美学几乎同时出场的,还有当代德国美学家格诺特·伯梅(Gernot Boöhme,又译为格诺特·波默)的气氛美学。伯梅在早期生态—自然美学的基础上重构了一种直面当代艺术与审美问题的气氛话语,使得“气氛”(atmosphere)一词从物理—气象学跃出,成为新的美学概念。在气氛美学中,气氛既非客体、亦非主体,它是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一种现象,“居间”状态是气氛的本质属性。伯梅认为,气氛“不是被构设为某种客观的东西,即物所具有的属性,但气氛仍是某种似物的东西(etwas Dinghaftes),是属于物的东西,就物是通过其属性——作为迷狂——来表达它在场的领域而言。气氛也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比如某种心理状态的诸规定性。但气氛是似主体的(subjekthaft)东西,属于主体,就气氛在其身体性的在场中是通过人来察觉的而言,就这个察觉同时也是主体在空间中的身体性的处境感受而言”[19]22。从在场性而言,气氛有“似客体”的一面,但它不是物本身;从身体在场和心理感知的角度看,气氛有“似主体”的一面,但气氛又不是纯粹的主观感受。进一步而言,“间性”思想是理解气氛审美的关键,因为“气氛概念促成了客观的环境条件与人们在这个环境身上所经验到的处境感受之间的中介”,气氛是“知觉和被知觉者共有的现实性”[19]4,气氛的中介性和居间性正是“美”的属性。
气氛美学极为重视营造和感受“真实的气氛”,在情境化的气氛萦绕中,无物(包括一切艺术品)不显示出美的光晕。在气氛美学看来,当代艺术是注重营造气氛的艺术,如现成品、装置艺术、工艺美术、爵士乐等都是可以显现气氛的对象。通过气氛的观照,一切“物”皆能彰显出感性的形式。伯梅认为,传统美学将自身局限在艺术理论上,并且具有严格的区隔功能,它将艺术与日常生活、严肃艺术品与低劣艺术品、手工艺品与商品等区分开来,形成明显的审美等级体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前卫艺术要求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弥合严肃艺术与应用艺术的鸿沟。气氛美学悬置传统美学的趣味专制和品质评判,要求对所有审美实践产品予以平等的承认。气氛美学要对不断发展的“现实审美化”进行详细辨析,不仅要指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合法性,还要对当代艺术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传统美学已经不能胜任当代艺术的阐释和评价工作,“日常美学、商品美学和政治美学带着同样的权利登台亮相于艺术品美学身旁。一般美学的任务在于,让这个宽广的审美现实性领域变得透明和可言说”[19]35。
气氛美学关注当代社会的诸多审美现象、主题和领域,气氛理论可以对艺术、自然生态,以及影响我们日常体验的声光环境等作出解释。气氛美学是一种分析当代感官世界的手段,艺术、社会、政治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可根据气氛审美来加以合理解释。当代社会的审美化趋势日益加速,虚拟世界已支配了实在世界,图像(显像)的自我增殖主宰了世界的审美逻辑,“审美领域排斥着实在事物”[19]1,物的展示意义超越了实存意义,场景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注重气氛营造的当代艺术(如舞台艺术、装置艺术等),正是当代社会生活戏剧舞台化的一种表征。在这种普遍“奇观化”的审美态势之下,自然环境、城市景观、艺术作品等都成为一种空间性和气氛性的对象,当我们身处气氛之中,才能感知或识别某个对象。当代艺术的很多类型都是场景化的,语言、光、声响、气味、空间场所等,在当代艺术的气氛营造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使艺术品在特定空间中散发着“迷狂”。美国当代艺术理论家罗伯森和迈克丹尼尔将场所视为当代艺术的七大主题之一,认为场所和空间在当代艺术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场所的空间也可和录像、幻灯和光投射相互融合,各种声音和气味也能渗入并弥漫于整个空间。”[20]空间与实体相互转化,达到虚实契合的效果,气氛就被营造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譬如雕塑、装置艺术、地景艺术等)就是场景化的艺术,也是气氛艺术。
从气氛美学看,审美知觉是身体在场性的,是身体处于环境之中的感知方式;同时,审美知觉的第一对象是气氛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先于所有个体事物而被最先感知到的东西就是“迎面袭来的流体(Fluidum)”[19]83——气氛,在气氛感知的背景下,人们对更为具体的个体事物(如形式、颜色、气味等)进行区分。按照伯梅的观点,气氛是一种情感化的空间,气氛美学将艺术作品的空间性推到了关切的中心。如果想在艺术作品中获得审美经验,那首先艺术品和欣赏者必须同时在场,这种共同的在场性创造出了独特的气氛。为了进一步阐发艺术品包括当代艺术的感性特征,伯梅引入了“物的迷狂”(Extase)概念来解释,就“物通过其属性或其形式作为气氛的营造者散射到空间中”[19]5并营造出特定的气氛而言,“迷狂”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作品在一定的展示空间(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内以其属性或形式营造出特定的气氛,这个艺术品就具有了感性的“迷狂”。譬如杜尚的《泉》或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它们脱离了商品、日用品或仿造物的语境,被艺术家代表的艺术体制重新命名,被赋予艺术身份,成为一个新的“能指”,从而冠冕堂皇地进入艺术展示的空间中,它们以其旧形式、新身份(属性)与新语境的结合,创造出特定的气氛,如此,它们走出了物自身而登台亮相,从而获得了“迷狂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审美经验中的观照对象。伯梅还指出,先锋艺术家们并未如本雅明所预言的那样,将艺术带到生活中而消除了艺术的“灵晕”(aura),相反,“杜尚正是通过将一个现成物阐释为艺术品,从而赋予了该物以灵气”[19]14。这里,伯梅认为本雅明的灵晕就是指一种特殊的气氛,一种关于艺术品的“空洞而无特性的在场性之外壳”。在气氛美学对艺术的感性观照中,艺术品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物,而是被气氛渲染的空间,它存在于当下直接的具身感知经验中。在气氛笼罩之中,艺术品就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极端的意义上成了美学的对象”[19]2。
人们对气氛的感知通过视、听或个别感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通感”(synesthesia),也就是所有感官的聚集,是身体的统一性体验。按照梅洛-庞蒂的理解,通感是一种物我之间感觉共通的身体图式,它体现了感官和对象的统一性,“我的身体是所有物体的共通结构,至少对被感知的世界而言,我的身体是我的‘理解力’的一般工具”[21]。气氛的通感经验可以用来解释当代艺术的审美感性问题。气氛的中介性、“似物非物”性,可以在超越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对当代艺术做出新的审美评价,艺术家不是要赋予某物(媒介)以一定的属性,而是要让物走出自身而与场景交融,让物的在场性成为可感知的对象。气氛的首要特征就是居间性(betweenness),居间性恰好可以解释当代艺术的审美属性问题,当代艺术的审美感性不是来自作品本身,而是欣赏者、作品与场所空间过程构成的一种交互性体验的结果,这种体验的结果就是是非主观、非客观的当下之气氛。
自波德莱尔式的审美现代性以来,现代艺术的发展与审美理论的演进之间有一种持续竞赛,尤其是先锋艺术的激进性一再颠覆既有的艺术美观念;勋伯格和杜尚之后,现代艺术的进展已经确证了美学阐释的无能。而作为新美学的气氛美学,一方面力图恢复德国的审美感性学传统,也就是说,气氛美学希望建构成关于知觉理论的美学;另一方面,气氛美学注重一系列个案研究,在分析当代艺术品时,也是将其置于气氛的转换之中,与丰富的日常经验联结起来加以审视,在气氛的感知中重新发现当代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性特质。伯梅不仅将自然现象在审美经验中的呈现称为“气氛之物”[19]68,还认为其在诗歌(譬如松尾芭蕉的俳句)和其他艺术作品中也有鲜明体现。因此,“气氛”是普遍性的审美对象,“通感”是关于一般气氛、自然和艺术所共有的主客交互感性。当代审美领域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气氛的迷狂”去感知自然、环境和艺术,这就是多元审美实践、媒介技术变革以及先锋派艺术的演进所共同促成的当代审美领域的“气氛转向”(atmosphere turn)。
五、当代艺术的审美回归及其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生活化和观念化向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英美分析美学一直认为当代艺术作品消除了审美属性,“当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或其他艺术作品相像的时候,区别一定在于其隐藏的方面或关系,而不在于审美论所说的那种审美属性”[22]。因此,分析美学家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艺术定义和艺术的涵义等非审美属性的分析上,并提出“审美态度的神话”“理论(在美学中)的角色”“艺术的终结”等一系列颇受争议的命题。丹托曾指出,艺术最终的命运就是被哲学所取代[23];按照丹托的精神导师黑格尔的看法,绝对精神(理念)在自我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最终要扬弃艺术的感性和宗教的表象而回到自身,绝对精神才算走完了一个封闭的圆圈,也就是说,哲学取代艺术,艺术(史)被终结是它无法避免的宿命。在丹托看来,哲学褫夺了艺术的固有地位,人类艺术进化的历史已经终结,当我们以知性取代感性,以概念僭越形式的时候,当代艺术就已进入“后历史”阶段,按此逻辑推理,抽象艺术和观念艺术将是艺术的最后形态。总之,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和审美危机是以艺术品的“去物质化”和“感性丧失”的诸多症候而显示出来。
面对当代艺术的观念化实践,分析美学的艺术终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我们需要探索和建构新的美学途径和方法来应对;另一方面,激变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也需要扩展人类审美感知系统,重构人类的审美经验。在这一复杂背景下,德国新美学批评从学科层面和理论层面对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作出了回应,试图通过建立显象、气氛诸概念,并将当代艺术置于审美感知新机制中来把握,从而重新发现当代艺术的感性特征及其出场方式,通过重建感性来彰显当代艺术中的审美要素,重新唤醒被漠视的身体感知系统。从显现美学和气氛美学的融通性来看,审美对象的感性状态(显象)与审美感知方式(通感)的融合,就是“事态”或“气氛”,据此可以回到感性的基点来重新看待当代艺术。这就从丹托的反审美的艺术批评路径重新返回到鲍姆嘉通和康德的那种重视感性与鉴赏判断的审美批评路径,如此才能化解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实现当代艺术的审美救赎;同时,这一聚焦感性的阐释路径也为美学学科重新赢得尊严和话语权。
当代艺术的表征危机与美学的阐释危机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阿多诺曾指出,传统美学与现代艺术是极不相容的,既有的美学范式已深陷困境,因为它不能从理论上弄清艺术目前的情境有何意义,“唯有通过批评性的自我反思这一途径,美学才能再次理解艺术”[6]340,并获得自我救赎。马尔库塞曾指出,审美的根源在于感受力,当代艺术是用新的感觉方式修正、强化甚至摧毁了旧的感觉结构,当代艺术的发展既改造了经验的对象,也改变了经验本身。基于此,当代社会需要进行一场“感觉革命”,培养一种新的感官系统,才能有真正实现审美解放的可能[24]。当代艺术双重改造的激进和猛烈,给美学理论提出了重大课题。因此,当代美学需要以重构感性经验为核心,直面当代艺术的审美危机,拯救美感,实现当代艺术批评的感性学回归。
20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暂时胜利,对美(beauty)的驱逐和对审美经验的消解,导致了“美的观念在艺术意识中的消失本身就是一种危机”[11]14,当代美学界要想重建一种通变古今的总体美学,就必须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地对当代审美实践和当代艺术做出合理阐释。当代新美学重新发扬鲍姆嘉通的审美感性学传统,以“显现”“气氛”“突然”“超越”等为核心,在拯救当代艺术的审美危机中为我们贡献了颇具创见的话语体系。同时,这些欧陆新美学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一是要坚持审美—感性学传统,注重对审美经验进行扩容和重构;二是坚持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注重吸收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的现象学、分析哲学及实用主义等不同哲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重建当代问题域中的美学话语;三是能直面当代艺术现象和问题,将理论建构与艺术批评相结合,既能用新的美学理论来有效阐释当代艺术现象,也能用当代艺术诸经验来验证新美学的合理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当代中国美学百花齐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