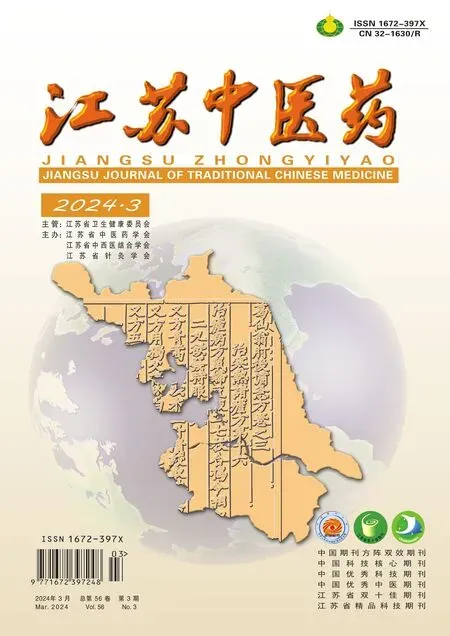黄文东“轻、灵、流、通”临床思维特色探析
李颖飞 李超男 龚雨萍
(1.河北燕达医院,河北廊坊 065201;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上海 200052;3.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200032)
黄文东(1902—1981),生于江苏吴江,为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医学家、教育家、临床医学家,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建院“八老”之一,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是海派中医的代表性人物。黄老博采众家之所长,擅长归纳与总结,尤其擅长治疗脾胃疾病,其治疗内伤杂病也总以脾胃为中心。笔者通过挖掘、整理黄老治疗脾胃病的论述、医案及经验等,发现其临床思维特色可归纳为“轻、灵、流、通”,“立论以和缓平正为宗,治法以清润平稳为主”[1]331。
黄老“轻、灵、流、通”的临床思维特色根源于李东垣、叶天士的学术精髓,逐渐成熟于其临床诊疗实践中,尤其贯穿于脾胃病的治疗。李东垣《脾胃论》强调“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2]的治疗法则,叶天士认为:“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3]352、“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3]149,皆注重恢复气机的流通,讲究用药灵动、柔和,且纵观李东垣、叶天士医案,用药精练,处方平淡,颇有轻清、和缓之意,临证不拘泥于一方一法,灵活施治。黄老继承并发扬前人之经验,以“轻、灵、流、通”立论,并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层次理法分明。本文特做归纳总结,从轻、灵、流、通四个方面分别作以阐释、分析,以期为中医临床思维、处方用药实践提供参考。
1 轻
1.1 轻于剂量药味精练 黄老指出,慢性疾病患者多病程日久,如予大处方、大剂量反碍胃气,伤其正,故不能以重药妄图速效,也不能轻易改弦更方。黄老认为,处方的剂量当效东垣之法,宜轻不宜重,一般植物药为9~12 g,矿物药为30 g,甚少峻剂[4]。如黄老擅用小剂量风药,他深刻领悟东垣运用风药的思想,并指出风药有升散发越之性,对湿浊不散、清阳不升都有独特作用,如柴胡、升麻、防风、羌活、葛根等,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故黄老讲究风药量轻,6~9 g为宜[5]。纵览黄老的医案、论著,每张处方用药大多不过十几味,很少有大方杂药堆砌,同类药仅用2~3味,最多不过5味,求于经方简洁,时方轻灵,用药精练,主张君臣佐使层次分明,主次分清,以达“轻可去实”的目的[4]。
1.2 轻于处方用药平淡 黄老处方用药不尚矜奇炫异,常以经典方加减化裁,以平淡之剂起于沉疴,慎用峻猛之剂,以甘淡中庸之品缓图其功。如针对脾虚湿盛导致的泄泻,黄老学习东垣之法,常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化裁,以恢复中焦运化,达健脾化湿之效;针对脾虚肝旺导致的泄泻,黄老又常以痛泻要方加减,以疏肝健脾,理气化湿,黄老调和肝脾还常用《伤寒杂病论》中的芍药甘草汤以酸甘化阴、抑肝扶脾;对于脾气亏虚,日久气虚及阳,导致中焦阳气不足而成泄泻者,黄老又以理中汤类方为首选[5];对于气血亏耗、脏阴不足导致的精神失常、悲忧欲哭、失眠焦虑等症,黄老常选甘麦大枣汤论治[6]。以上均为古代名医所传,众所熟知,黄老承之化为己用并加以发扬,用平淡之剂加减化裁,在剂量配伍之间运筹帷幄,每建奇功。
1.3 轻于久病丸药轻投 轻有和缓之意,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云:“用药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则寒热温凉行散补泻,未免过当,功未获奏,害已随之。药无次序,如兵无纪律,虽有勇将,适以勇偾事。又如理丝,缓则可清其绪,急则愈坚其结矣。”[7]东垣治疗内伤杂病,反对惯用猛药,以防伤及脾胃,主张循序渐进,缓以图功。“汤者,荡也”,汤剂来势凶猛,见效快捷;“丸者,缓也”,丸药起效缓慢,持续时间较长。黄老效法东垣,采用“重药轻投”的方法应对久病不愈者[5],对于病程迁延患者汤药不能取效时,或已经初步治疗病情逐步向好者,黄老常考虑以丸药缓调,取复方图治之法,如以十倍上下有效方药剂量,制成药丸,分次服用,缓缓调治,久而用之便取得较好疗效,实为“磨刀不误砍柴工”矣[8][9]31。
1.4 轻于用药平和兼顾 所谓平和兼顾,黄老认为“胃为市”,水液、食物出入其中,治脾胃病用药首要平和兼顾[1]331。用药过于寒凉则易损伤脾阳而见腹中冷痛,用药过于温热则阴伤内热而见灼痛烦躁,用药偏燥则津伤液耗而见口干咽痛,用药偏润则气机碍运而见胸闷胀满、纳呆,用药过于甜腻而见中满泛酸、苔厚腻。唯求用药平和,气血阴阳兼顾,药症合拍,方不伤胃气,提高疗效。如黄老理气常选用陈皮、佛手、枳壳、青皮,芳香行气但不耗气伤阴;气滞稍重者再用木香、香附、延胡索,且喜与芍药甘草汤合用,取其酸甘化阴以制理气药之香燥。又如黄老通常会慎选养阴药,除非症见嘈杂口干、纳少便艰、五心烦热、舌光红少苔者外,熟地黄、阿胶等多与理气药同用,通补兼施,或用北沙参、太子参气阴双补而不滋腻。
2 灵
2.1 灵于推崇异病同治 黄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诊病时灵活施治,从不拘泥于书本,推崇异病同治的思想。异病同治本质上是中医辨证论治思想的具体体现,形成的基础是疾病证候相同而治法亦相同。故黄老指出,临床上许多不同的疾病,由于他们的证候相同,常可以采用同一方药或同一种治疗方法。如黄老对于甘麦大枣汤颇有研究,指出其虽在《金匮要略》原文中记为妇人脏躁方,但并非专治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不仅见于妇人,也常见于男子,如把此方纳为妇科专方,未免过于狭隘。后世医家叶天士就常将其用于脏躁之外的惊、悸、烦、怯和痉厥等病。黄老秉承先贤,指出临床上众多疾病如失眠、郁证、癫证、心悸、自汗、腹泻、便秘等皆存在“气血亏耗,脏阴不足”之病机,遂开拓思维,遣以甘麦大枣汤加减,“和中缓急,养心安神”,每获良效[6]。
2.2 灵于辨证随机应变 黄老善于对疾病的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观察,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并根据不同阶段的主次矛盾变化和病机演变,进行稳妥合理的处方配伍用药,随机应变,章法可循。如治疗腹泻:(1)脾胃虚弱,运化不能,肝阳过旺,肝木克伐脾土太过者,肝旺为主要矛盾,可柔肝抑肝佐以健脾安神,但此时补脾理气不应过于温燥,宜少用黄芪、升麻之类,防辛燥助阳上扰;(2)久病肾阳虚衰,脾虚湿热未清,此时脾肾阳虚为主要矛盾,湿热未清为病之标,应以温补脾肾为主,清化湿热为辅,但清热用药不应过于寒凉,宜量小味少为好,以防耗伤脾肾阳气;(3)痛泻日久阴分耗伤,常有口干、舌淡、苔少、有裂纹的表现,此类患者脾胃虚弱、运化不足为主要矛盾,此时应以健脾助运为先,为后期补阴分之不足打下基础,脾胃方有纳运之力[10]。
2.3 灵于升降润燥有别 黄老指出:“李氏立论制方,着重在补中益气、升阳益胃方面,但用药偏于温燥,对胃气失于和降,胃阴耗伤等疾病,还有不足的一面。”[9]31故黄老颇为认同叶天士“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以及“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的理论,治疗脾胃病要顺应脾胃的生理特性。黄老从长期临床实践探索中发现,治疗脾胃疾病,要细致分析,必须根据脏与腑、脾与胃之间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升降润燥的不同治法。如阴血不足,同时出现脾胃运化功能薄弱时,应先解决脾胃运化功能,然后再以滋阴清热为主,此时健脾理气为先,但用药不应过于温燥,以免耗伤阴血;当脾运得健,治疗转入以滋阴清热为主时,选药又不宜过于滋腻,同时应配伍健脾和胃之品,有利于对滋阴药的受纳吸收;如阴虚内热较重又见脾运不健,应健运脾胃与滋阴清热兼顾为宜[8]。
2.4 灵于制定药后医嘱 黄老每于方后制定医嘱,认为疾病单靠药物治疗是难以痊愈的,药后调摄得当可加速康复。(1)调情志:气的运行是否调畅关乎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如治王某“贫血”例,叮嘱王某需避免情绪波动,防止血络损伤导致病情加重。(2)适寒温:寒温是人体生存的重要条件,若太过不及,阴阳失调而成诸病,应固护皮毛、防御外邪。如治蔡某“胃痛”例,皆多次告知患者要注意御寒,以防复发。(3)慎饮食:饮食有寒热温凉之不同,人体亦有阴阳虚实之差异,故疾病的康复需格外注意饮食宜忌,《灵枢·师传》曰:“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如治朱某“咳血”例,告诫患者勿食辛辣刺激,以防动血伤阴。(4)勤锻炼:运动可使气血流通,强筋壮骨,增强体质。如治王某“痿证”例,嘱其平时宜适当锻炼,渐渐得到恢复[11]。
2.5 灵于五脏相生为用 《难经·第十四难》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损其脾胃,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12]黄老非常认同,但指出治疗虚证补益五脏虽为根本,但更应注意脏腑相关,“五脏之气,皆相贯通”,要虚则补其母,就是通过五脏相生、补母益子,即当某脏虚弱时,除了直接补益该脏外,也可间接健养其母脏,此为子病求母。如临床常用的补火生土、培土生金、滋水涵木等治疗方法,都是五脏相生关系的良好运用,以子病补其母的治疗方法,可达到促进脏腑虚损恢复的目的。如治俞某“肺不张,肺结核”例,肺部病变虽为原发,但兼有脾不健运,肺为脾之子,脾为肺之母,黄老认为,肺病迁延,子病及母,累及脾脏,脾虚运化不能,土不生金则肺金愈虚,故采用培土生金之法,待土旺而金生[13]。
3 流
3.1 流于调畅疏泄肝气 黄老崇唐宗海之言“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14],认为肝脏疏泄调畅气机功能对于脾胃运化有着重要作用,其治疗痛泻、胃痛、腹胀、口臭、失眠等病症尤注重调畅疏泄肝气,防止肝郁克脾犯胃。如遇胃脘嘈杂隐痛、肋下胀满不舒、泛酸口苦、口气臭秽、脉弦者,常以调畅疏泄肝气为先,采用柴胡、香附、郁金、延胡索及川楝子等疏肝理气和胃,配合活血;若肝郁日久化热,以致出现烦躁面红、失眠多梦、嗳气胃痛、口鼻臭气、苔黄腻等症,则以黑山栀子清肝,亦常选用左金丸,辛开苦降,泄肝和胃[15];又如治疗痛泻肠鸣,强调脾虚肝旺互为因果,柔肝抑肝法必不可少,常取痛泻要方之意,喜重用白芍柔养肝体以抑制肝用,少则15 g,多则30 g[5]。
3.2 流于活血化瘀通络 黄老认为叶氏“久痛入络”“凡久病血治为多”的理论绝非虚语,其治疗许多慢性病擅用活血化瘀通络之品。如治疗胃病,常着眼于肝脾两脏,症见舌质青紫、久痛不愈、刺痛明显、痛有定处、按之痛甚、食后痛增,此为夹有瘀血之象,在补气、理气的基础上尤其注重活血化瘀法的使用,亦指出“在胃痛辨治过程中,但见一症即可按血瘀论治,各症不必悉具”[1]400[16]。如治孙某“胃痛”例,胃痛迁延,久治不愈,虽舌不青紫,亦遵久痛入络之旨,理气药中配伍红花以化瘀止痛[9]110。又如治符某“胃痛”例,胃痛较甚,且痛有定处,胃脘似有物顶住,多症皆有,瘀血无疑,故活血化瘀法贯穿全程,桃仁、当归、红花等先后用之,使持续四月的胃痛,一月不足,便瘥[9]107。以此类推,只要把握主旨,切中病机,皆可应手取效。
4 通
4.1 通于通降宽中导滞 黄老强调胃喜通降,胃气通降与脾气升发互相协调,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中焦升清降浊的运化过程。黄老健脾升清的同时,常与理气畅中之药配伍,以防补而生滞,如此可使中焦气机运化、气血流通、胃气得降。纵观黄老之医案,其最喜欢使用陈皮、枳壳、木香、青皮、槟榔、香附等理气之品,常用于治疗气机壅滞的胃痛、脘腹胀气疼痛、口臭等症。如遇泛恶吞酸、嗳气呃逆明显者,亦常配伍半夏、竹茹、枇杷叶、煅赭石、旋覆梗等通降胃气。此外,黄老守“轻可去实”之意,对于剑突下痞满不适者,取紫苏梗、旋覆梗、藿香梗、佩兰梗等理气宽中,疏导中焦气机[5]。对于食积不化、饮食难消导致的恶心欲吐、不思饮食、口气酸馊腐臭、胃脘胀满、舌苔厚腻诸症,常伍用焦神曲、焦山楂、谷芽、麦芽、炒鸡内金、莱菔子、枳实等消导积滞,积滞得消也可助脾之运。
4.2 通于润肠通腑淡渗 《本草通玄》[17]谓:“土旺则清气善升而精微上奉,浊气善降,而糟粕下输。”故黄老指出,大便秘结不通与气机阻滞存在密切关系。脾胃居中州而为气机运化枢纽,腑气不通,浊气上逆常致反胃、腹胀、恶心、口臭等,如大便通畅、腑气得通,则有助于胃气通降的恢复、气机升降的协调。黄老治疗便秘讲究“动静结合、润通并用”,使阴血充足,大便润泽而下,浊气顺势而解,气机调畅,脏腑的升降功能恢复。润肠方面,补其气血津液亏虚,重用生首乌,并常用生地黄、熟地黄、桃仁、当归等润肠通便。润肠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通腑,常使用青皮、厚朴、大腹皮、枳壳等行气散结。如遇大便黏腻、排便不尽者,理气的同时加用冬瓜子、薏苡仁、滑石等清热淡渗利湿之品,疗效亦彰。对于久秘不通便秘顽固者,可短期少量使用制大黄,给秽浊之气以出路,引火下行,但需同时配伍养阴补血之品,并强调中病即止[9]57[18]。
5 验案举隅
钱某某,女,34岁。1975年2月10日初诊。
主诉:恶心纳差2 月余。患者因活动性肺结核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且累及左肺大部肺叶,于1974 年3 月行左肺叶切除术,现已术后10 月余,仍长期口服异烟肼片等抗肺结核药物以防复发,术后体虚,食量渐减,日渐消瘦,停服抗结核药物后仍胃纳不佳,日久不得复。刻诊:患者恶心纳差症状明显,食后恶心频发,已2 月余,每餐进食仅一两半,伴大便溏泻,日行6~7 次,腹中时痛,少腹、肛门坠胀,神疲乏力,心悸,头胀,不寐,舌质淡红、苔薄腻,脉细。西医诊断:食欲不振,肺结核。中医诊断:纳差,肺痨;病机:气阴耗伤,肝旺脾弱,胃失和降。治法:健脾柔肝,理气和胃。方选痛泻要方加减。处方:
陈皮6 g,杭白芍9 g,炒白术9 g,炒防风3 g,炒扁豆9 g,山药9 g,白蒺藜9 g,丹参9 g,炒谷芽15 g,炒麦芽15 g。14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
1975年2月25日二诊:大便次数渐少,日行2~3次,但仍不成形,腹痛减轻,纳差,头晕头胀,心慌,五心烦热。舌质淡红、苔薄,脉细弱代数。黄老认为此时肺阴素虚,肝阳偏亢,脾胃运化不健。治法仍应以调理肺脾为主,更方为异功散加减,使补而有行,加以平肝潜阳、清热安神。处方:陈皮6 g,炒白术9 g,党参9 g,炒扁豆9 g,春砂壳4.5 g,制香附9 g,生牡蛎15 g(先煎),磁石15 g(先煎)。14 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
1975年3月10日三诊:大便已成形,日行1~2次,胃纳渐增,每餐可进食二两半余,亦再无恶心症状,体重逐渐增加,头晕头胀、心慌消失,五心烦热仍有,寐不安但趋好,说明阴虚潮热之象渐减,肝阳渐平,脾胃运化较前健旺,实为佳象。更方为沙参麦冬汤加减,滋阴清热安神,佐以调理脾胃善后。处方:北沙参9 g,麦冬9 g,青蒿9 g,白薇9 g,陈皮6 g,生扁豆9 g,丹参9 g,春砂壳4.5 g。14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
后于1975年5月随访,患者诉体重增加近4 kg,体力逐渐旺盛,胃口开,恶心纳差未再出现,肺结核病情亦无复发。
按:本案患者患肺结核病多年,病程迁延日久,再经大手术耗伤气血津液,术后体虚,久不得复。由于肝血不足导致肝阳偏旺,加之药物反应,肝旺克脾,导致脾胃运化失司,从而出现纳差、恶心症状。黄老认为,此时虽见心悸、头胀、不寐等阴虚肝旺之症,但大便溏泻日行6~7 次,恶心纳差,神疲乏力,皆为脾胃虚弱之象,为防更伤脾胃,出现虚虚之戒,故不能过早施用滋阴平肝潜阳之品。因此,黄老初诊时以痛泻要方加减治疗,方中炒白术、山药、炒扁豆、陈皮、炒谷芽、炒麦芽健脾和胃、理气消食,炒防风运脾升清以止泻,白蒺藜、杭白芍、丹参柔肝抑肝、养血安神。二诊时,患者大便次数减少,腹痛减轻,说明脾运好转,但大便仍不成形,纳仍差,需进一步健旺脾胃,故二诊续以调理脾肺气虚为主,更方为异功散加减,用健脾之党参、炒白术、炒扁豆配伍理气之陈皮、制香附、春砂壳,使补脾而能流动不滞,因患者心慌、五心烦热、头晕头胀,舌质淡红、脉细代数,辨为肝旺虚热,故加生牡蛎、磁石以平肝潜阳、清热安神。二诊14 剂药后大便已成形,胃纳增加,再无恶心,体重逐渐增加,此时脾胃运化功能已基本恢复,阴虚潮热肝阳上亢之症亦减,头晕、头胀、心慌消失,五心烦热仍有,寐不安但趋好,随变治之。故三诊更方为沙参麦冬汤加减,以滋阴清热为主,调理脾胃为辅。方中北沙参、麦冬、生扁豆滋养肺胃气阴,青蒿、白薇清虚热治标,合丹参清心除烦以安神助眠,但并未弃用陈皮、春砂壳之类的理气药,后者仍可助脾胃受纳运化,最终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患者得以康复。由此可见,肝旺脾弱,气阴两虚,“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待脾运复健,再以滋阴清热为主,辅以调理脾胃,则脾胃对滋阴药物才有受纳能力。否则,如一见阴虚潮热,随即先投滋阴之品,如此不顾脾胃虚弱,则脾胃更弱,气阴亦难恢复[1]307[19]。后于1975 年5 月随访,患者不仅体重增加近4 kg,体力逐渐旺盛,胃口开,恶心纳差未再出现,且肺结核病情亦无复发,体现培土生金、待土旺而金生的五脏相生运用。
6 结语
本文经追溯、挖掘及整理黄文东教授治疗脾胃病论述、医案及经验等,系统归纳和总结了黄老“轻、灵、流、通”的临床思维特色,可见其遣方用药、运筹帷幄间无不体现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对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黄老治疗内伤杂病总以脾胃为中心,“立论以和缓平正为宗,治法以清润平稳为主”,如用药精练、处方平淡,又如强调气机调畅、注重润燥有别,再如制定药后医嘱、推崇异病同治等,跟随病机演变、疾病发展不同阶段采用不同治法,颇具中医学理论与临床思维的代表性,值得同道进一步研究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