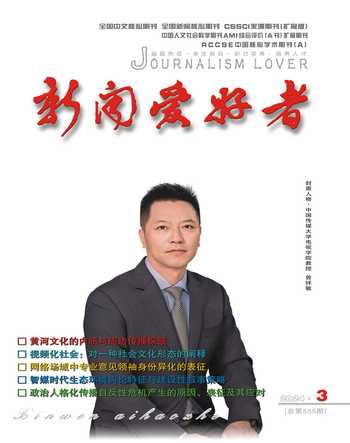视频化社会:对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阐释
孟建 符艺娜
【摘要】在媒介技术飞速的演进和作用下,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组。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被无穷无尽的视频所包裹。处在这样一个可以被称之为视频化的社会,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正在形塑。其表现为:社会空间的景观化、零碎化、滤镜化;社会交往边界的消弭与媒介交往关系的变更;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流动性以及互动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视频化社会不仅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建构了新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认知观念和心理结构。这既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急遽变迁,也带来了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思考。
【关键词】视频化;社会化;文化形态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向数字文明时代过渡的深刻转型期,其间充斥着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的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旧世界条块分明的秩序正在被打破;功能各异、壁垒森严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1]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10.44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38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8%。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454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5.2%。”[2]从数据到身边现实,无不直观地体现出当今社会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赋能,我们的生活正在不知不觉中视频化。“视频成为一种黏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3]它正在不断形塑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与文明形态。“从长视频到短视频到中视频,再到多样态的流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视频传播在中国呈现出全时空、全领域、智能化、全龄向的发展新势能。”[4]我们应该去理解和把握当前这种传播流动的不同维度,以及这种流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一、从“媒介化生存”到“视频化社会”
在过去,主流社会学采用的原初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即把社会看作一个有边界的实体,与民族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现今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很显然,这样的社会概念是不合时宜的。杜威曾经说过“社会不仅是传输(transmiss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输与传播中”[5]。“早在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之际,人们便沿着类似的思维路径,梳理那些构成‘现实的基础座架和运行元素,并尝试在媒介的维度上想象未来的生存方式。于是,‘媒介化生存‘赛博化生存‘游戏化生存‘视频化生存等一系列崭新的‘生存形式纷纷浮出水面。相比较而言,‘媒介化生存无疑是最具统摄性、延展性、包容性的一个认识概念”。[6]在《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一书中,作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使我们理解文化与社会时越来越依赖媒介及其逻辑过程。这一过程以二元性为特征,即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7]。
目前,技术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在经历着广泛的重塑。更进一步,“人类从未像今天一样,被无穷无尽的视频所包裹。随着移动终端视频拍摄技术的进步和视频平台的蓬勃发展,视频开始全面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覆盖娱乐、购物、新闻发布、知识生产等方方面面。尤其是短视频以操作简单、快速、低门槛的优势成为人们观看和了解世界、展示自我的主要媒介”[8]。毋庸置疑,我们早已进入了“视频化生存”时代。而传播领域的技术进步,导致的后现代性与全球化彻底地扩展了人们的时空观及其用途。“应付多种技术的能力、处理多重媒介化的信息情感交互的能力以及对付当地杂乱无章的非媒介化的人和事的能力,构成了当今生活所要求的复杂的传播技巧。因此,今天已经扩大了的传播环境,使文化集成与代码转换的复杂能力成为必要之物。”[9]也因此,这不单纯是视频作为一种媒介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更多地,它代表了从感觉到场景、从技术到文化的深度结构。
二、视频化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
(一)社会空间:景观化、零碎化、滤镜化
“在德波的认知中,景观虽附着于生活现实,不过与现实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10]然而,视频作为一种面向全民的影像形式,无疑是更加独特的——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如此与我们日常生活高度相似的影像形式。在数字、网络和社会化的背景下,影像能够在“泛媒介语境”中自我创造和生存,从而转化为真正源于现实世界的原生文化形态。尤其是当人们首次涉足短视频平台或视频直播时,他们往往缺乏专业的内容创作能力。他们更倾向于从日常生活开始,展示生活的某个方面。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特质,呈现出一种简单和直接的风格。而在这里就出现了两种生活:一种是现实的生活,一种是视频中所呈现的生活。“现实生活与视频中呈现的生活,两者互为映照,视频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拟态反映,也是对现实的物质世界的再现与重构,这类似于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11]视频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含义。在视频化社会中,视频媒介使现实生活在这里得到了延伸,与此同时,视频生活中所获得的关注与存在感,同样也能变现到现实社会,作为用户的视频主在其视频中所表现的各种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引领新的风潮,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部分存在,在这里视频生活又与社会生活相融。“影像生产者与传播者正大规模地与他们的生活现实齐头并进,这是生活的景观,也是景观的生活。”[12]并且,受制于视频时长的限制,视频内容自然地呈现出生活的零碎感。而无论是短视频、中视频还是长视频,“线性的、完整的、宏大的叙事被割裂成诸多碎片,完整的意义表达变成了数量更加巨大但内容趨向分散的信息片段”[13]。其碎片化的表达方式迎合了大众的阅读习惯。这种阅读习惯不仅包括内容碎片化,更表现为阅读时间的零散性、不完整性。伴随着移动设备普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里选择对视频观看、制作、评论、转发、点赞等行为,这种视频传播方式凸显了当今时代交往的便捷化倾向,通过视频的各类行为交流,用户能够更加精准地建立满足自己社交需求的社交关系。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视频来展现自我或者表现生活,作为一种主观行为,其是有选择性的,即一种“自我建构”。这一概念“最早由黑泽尔·罗斯·马库斯和北山忍于1991年提出,指的是个体在认识自我时,会将自我放在何种参照体系中进行认知的一种倾向。玛莉琳·布鲁尔等认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建构都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从自身独特性定义自我、从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中定义自我、从自己和所从属团体的关系中定义自我。他们将这三种建构倾向分别命名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也称为自我的三重建构”[14]。而基于视频的自我建构,无论其选择的是展示自己还是某处景观、他人等,处于一个开放的空间中,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公众人物”。面对着实在的以及潜在的围观者,为了展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也为了在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层面得到更积极的反馈,视频中的生活也存在“作秀”的成分。就如同拍照会选择具有美颜等功能性的拍摄软件一般,短视频是个体记录生活、表达观点的手段,也是进行自我展演、塑造个人形象的重要场所。美颜、滤镜功能已成为短视频平台和剪辑软件的必备功能,从而蒙上一层“滤镜”,因此在视频化社会中,生活内容具有滤镜化特性。
(二)社会交往:边界的消弭与关系的变更
麦克卢汉曾提出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15]视频化社会是这一事实最好的证明。作为一种媒介,视频天生就具备了这些社交功能。而“视频语言因其立体性重新激活了人类借助以视觉为主的综合感官系统进行传播的天性,但却以强大的连接力、计算力和环境的构造力,突破了人类之初视觉传播的身体边界和时空局限”[16]。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来属于私人化话语的家庭生活中,话语形式不但变得公共了而且也视觉化了”。[17]而短视频更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创新的生活模式。其不仅可以作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展现各领域的“视频”,使其成为关键的信息传播工具,为视频化社会运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虚拟现实、元宇宙等这些短视频的未来形态业已出现。虚拟现实技术使虚拟空间从对现实空间的附属、拓展演变为对现实空间的嵌套,进而消解了地域距离,也融合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用户可以实现完全的虚拟在场。而从视频内容叙事的角度出发,视频时空和现实时空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这种时空的“不在场的在场感”满足了用户的窥私欲与陪伴感。如现在日益走红的“吃播”,在拟态环境中逐渐形成沉浸式体验,虚拟的味觉快感被放大。更为关键的是,由数字技术构建的人际关系正在逐渐替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联系,社交媒体更为便捷地连接弱势关系,使得在传统社会中原本不可能建立的关系变得更为可行和简单。
另外,正如众多学者所共识的“视音频书写的基本规范之中,表达了‘一种泛众化的传播范式,为普罗大众赋能赋权,将社会话语的表达权给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18]视频依托其背后的数字传播技术,为所有人提供了进入网络世界的机会,这打破了精英主导的公共话语结构,以往的“把关人”之权由专业化生产者逐步转移为用户自身,权力和话语体系也就此发生了转变,使得持有或输出相同观点的人群能够聚集在一起,对相同的现象或事件表达类似的观点,这导致了一个情感共鸣作为连接纽带的社群的形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圈”。而视频语言的变革“既超越也重塑了时空,推动着人类社会进行着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到重新部落化,以及未来的虚实同构的新部落化的转型”。[19]我们这个“地球村”(麦克卢汉语),以其视频影像信息的快速传递和用户友好的互动为特点,实际上已经被划分为许多大小不一、界限明确的文化部落或曰圈层,个体能在其中实现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并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和自我。而这种个体发展的多样性和实践的灵活性也进一步形成了更广泛、更多的维度和更细致的社交联系。“以直播、短视频等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介正在颠覆着固有的大众传播学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社会学效应,它们在唤醒和激发社会主体传播本能的同时,或可促成福柯所言的‘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以‘全民记录的社会价值生成了一种新型的史料”[20]。
(三)社会系统:开放性、流动性以及互动性
在当前的社会系统中,一个引人关注的发展方向是,在短视频文化的催化作用下,现代视频化语言逐渐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语言”表达和交流手段。换句话说,视频影像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一种新型“语言”。凭借其视觉上的普遍认知,视频影像甚至已经突破了民族语言的边界,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语言”。通过社交媒体,运用这种新型的“语言”,并通过各种数字APP来建立与商家、客户、服务者和各种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被高度视频化的“社会系统”中,当我们使用表情包进行交流、用视频展示具身经验时,不仅有助于事件的再现,甚至还可以对其进行重新构建,并在续写中对事件进行扩充,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开放的结构,适用于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在这里,人们的生活空间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物理平面扩展到一个立体、可视的虚实混合空间,这使得人们能够以更有自由度、体验感和功效性的方式来生活。
正如上文所说,在视频化社会中,社会交往边界的消弭,使个体更有可能从集体中获得身份的认同和情感的支撑。由此,社会出现了各类以“圈层”为基础的结构。但在其加速发展的当下,没有一种“圈”是永恒存在的。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指出的:“如今的现代性是液化的,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使得共同体趋于流动,成为视频图景中的普遍常态。”凯尔纳在论述流行文化的未来叙事文本时,曾经这样归纳“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的想象图景,其表现了“新的技术社会的能量、借助新技术的乐趣与权力、界面结合的狂喜、获得新的信息与从事新的传播形式而获得的力量,以及弹指之间就可以观看世界各地的图像与产品的超然状态”。[21]这种信息流变的逻辑,实質上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指出的,‘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同样,社会关系趋于多元化与复杂化,加快了社会流动性和传播权力、社会资本的进一步下沉”。[22]由媒介变革所引发、所导致的视频化社会,其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真谛都将集中到一点,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精神交往论”,无论媒介如何变革,其实质都是人们的精神交往方式发生了革命。
三、思考:被不断形构的视频化社会
(一)理性的惰性与媒介的幻境
通过图像和视频等技术,复杂的信息场景在屏幕前得到了逼真的呈现。利用特定的算法,人们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匹配和接收,甚至实现内容的深度融合。在这种视角下,理性的逻辑逐渐被浅层的视觉呈现逻辑所取代,各种信息文本通过直观的图像和视频展现给观众,从而打破了人们的思考和体验空间。“短视频通过多变和未知的内容持续刺激大脑,使受众产生大量的愉悦感和满足感。这不仅可能引发媒介成瘾问题,还会对个体的思维模式造成不利影响。视频是连续变化的一系列图像,该形式通过对意识连绵不断的占领挤压了受众的反思空间。”[23]目前,视频已然变成了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当人们观赏短视频时,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体验。各类视频并没有为观众提供深入思考的机会和时间,他们更多的是从画面中获取感性的信息,而对于作品的深度和意义的期望也逐渐降低。在这种逻辑下,人们作为主体,在接触信息的过程中,被简化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我们被不断地塑造成一个缺乏思考的表层化主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个体的思维惰性。就像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替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同时,视频中的虚拟元素能够与现实内容进行实时互动,从而达到现实与虚拟元素的完美结合。因此,在视频化社会,人们借由网络通过视频获得信息和娱乐成为可能。但是,视频所创造出的各种幻象可能会让人沉迷于虚构的空间,从而导致对真实生活空间的忽略,这显然是一种倒置的现象。“平台时间可以视为媒介时间对人的控制,人们在刷短视频时往往会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个体的空虚,瀑布般的信息流中会有无穷无尽的内容推送,通过视频创作规律的把握牢固抓取用户的注意。”[24]在生活中,视频所形成的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叠映景象,人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媒介幻境中。“现实突然出现在景观中,使得景观成为真实。这种互相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25]我们不禁要发问:当我们逐渐被影像等视觉内容所吸引时,我们的理智是否最终会被欲望所左右?我们会不会变成一个被视频图像所束缚的人呢?
(二)算法“编程”与平台“监视”
“在马诺维奇看来,‘媒介软件由‘数据结构和‘算法组成,其中‘数据结构由媒介材质转化而来,而‘算法则由媒介技术转化而来。”[26]“在信息传播网络中,智能算法的出现,正在穷尽并重塑信息由传者生产、传播再到受者接受、理解,甚至是给予反馈的全过程,其核心在于对用户的洞察,借助逻辑规则界定用户所乐意接受并可能喜爱的信息文本类型和内容,从而实现用户需求的满足。”[27]在这种算法的逻辑框架下,筛选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内容不再仅仅依赖于发布者的理性判断,而是基于人们对特定信息的停留时长、点赞和评论转发等行为数据,其中,作为用户的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采取算法推荐为主的分发方式,受众更多的是被动接收信息。将能动性让渡给算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个体的自主性与选择权。”[28]视频社交媒体的用户界面和应用程序塑造了我们的社交方式,而其中的交互模式则决定了我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说我们在各类APP内实践着社会行为,各种APP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方位数字化的个性和生活轨迹。除了我们的主观评估,算法程序正在悄悄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感知、情感和观点,“编制”我们的生活。
再者,作为各类视频社交平台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算法所依赖的数据被该平台所独占,用户“观看”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更为精细和深入的平台“被监视”体验。视频背后的各大平台,“作为信息广场,不仅体现了联结范式的结构逻辑,也构筑了信息、数据产销的‘场域,万物在此集结,生产、发布、交流信息并形成舆论。可以说,在信息传播的联结范式中,平台既是结果,也是逻辑、过程”。[29]在此过程中,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算法逻辑精确地整合进“我的生活”,并在用户画像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推送,影像被不断地呈现在我们的視野中。而在无形中,不论是否处于有意,我们的观察量和点赞量等因素均可被平台作为“货币”来进行量化,从而进行盈利或达成其他目标,这些视觉信息本质上是在认同的过程中控制着人们的资本和权力,这可能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资本权力操作的棋子。
(三)数字技术的依赖
唐·伊德(2012)认为,“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这是一种与世界的生存关系”。技术的生活形式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如同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蕴含技术一样。数字技术对整个媒介文化的重新形塑是全方位的。当前的视频化社会凸显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垄断人类文化数千年的文字文化,正在丧失其主导性地位,作为一种整体性文化趋向于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文化认知正在从文字逐渐演变为数字技术的应用。
在这个视频化社会和数字化的当下,数字技术不仅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身份,也赋予了“物”或“机器”以身份,尤其是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物。因此,数字技术还构建了更为复杂的“人与物”“人与机”之间的互动模式,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是一个由各种物体与用户形成的网络所构成的信息系统”[30]。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人作为内容核心的需求也会逐渐下降,大部分视频将褪去大众传播年代那种仪式感和权力的光环。就媒介内容本身而言,物的广泛参与也使得内容变得更加全面和丰富。各种传感器、可穿戴设备、远程通信设备广泛渗透并参与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31]。数字技术在我们的主观判断之外,悄然改变着我们所有人的行动与感知、情感与观念,换句话说,它改变着我们的共同生活。
四、结语
从“以短视频和直播为代表的视频语言的兴盛,再到未来基于智能VR的独立性、立体化视频语言的普及,每一次语言革命的发生、每一种语言体系的独立,都推动着基于这种语言形态的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形成”[32]。目前,技术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正在经历广泛的重塑。正如彼得斯所认为的,在数字革命的推动下,媒介已经遍在自然环境。作为一种新的数字文明形态,视频化社会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官体验,再造了视觉媒介的虚拟属性,为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式,将视频从一种特定的媒介形态转变为人类生活的核心方式。如前所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和聚集模式都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升华变革。因此,社会的文化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视频化逐渐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环节。伴随着大数据、5G、区块链、人工智能、ChatGPT,尤其是势头正劲的Sora等数字技术所展示出的一种相互协作和整合的发展态势,社会制度、经济模式、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视频化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不仅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建构了新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认知观念和心理结构。这既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急遽变迁,也带来了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思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编号:18ZDA311)]
参考文献:
[1]喻国明.AGI崛起下社会生态的重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4):58-65.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3(8).
[3]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4):34-40+53.
[4]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8.
[5]Heidegger,"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79,81;"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ed.and trans.William Lovitt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12-13.
[6]劉涛.以短视频为方法,理解媒介化生存[J].新闻与写作,2022(4):1.
[7]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
[8]李佳咪.视频化生存:媒介实践与文化景观[J].新闻与写作,2022(4):4.
[9]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M].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0]刘永昶.生活的景观与景观的生活:论短视频时代的影像化生存[J].新闻与写作,2022(4):24-32.
[11]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J].中国编辑,2020(4):34-40+53.
[12]刘永昶.生活的景观与景观的生活:论短视频时代的影像化生存[J].新闻与写作,2022(4):24-32.
[13]彭兰.碎片化社会与碎片化传播断想[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09-110.
[14]刘艳.自我建构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1(3):427-439.
[1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97.
[16]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8.
[17]周宪.视觉文化语境中的电影[J].电影艺术,2001(2):33-39.
[18]吴炜华,黄珩.影像化生存的演进脉络与现实图景[J].青年记者,2023(3):9-13.
[19]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8.
[20]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8.
[21]刘永昶.生活的景观与景观的生活:论短视频时代的影像化生存[J].新闻与写作,2022(4):24-32.
[22]喻国明,苏健威.新型趣缘关系:理解未来社会组织协同的关键视点[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5):103-110.
[23]王晓培.视频化生存: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重构与反思[J].青年记者,2022(19):19-21.
[24]刘相.数字时代短视频平台广告的景观化表征及批判[J].青年记者,2023(14):107-109.
[25]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21.
[26]Lev Manovich,Software Takes Command[M].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 2013,p.199-204.
[27]王冬冬.相遇不相知:算法时代的文化景观重构[J].探索与争鸣,2021(3):5-8.
[28]王晓培.视频化生存: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重构与反思[J].青年记者,2022(19):19-21.
[29]李继东,项雨杉.数字文明时代信息传播的联结范式:生态与理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4):138-145+186-187.
[30]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M].李婉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31.
[31]顾洁,田选宁.5G时代物的回归、视频化社会构建与电视转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4):114-119+128.
[32]廖祥忠.视频天下:语言革命与国际传播秩序再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1-8.
作者简介:孟建,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符艺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上海 200433)。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