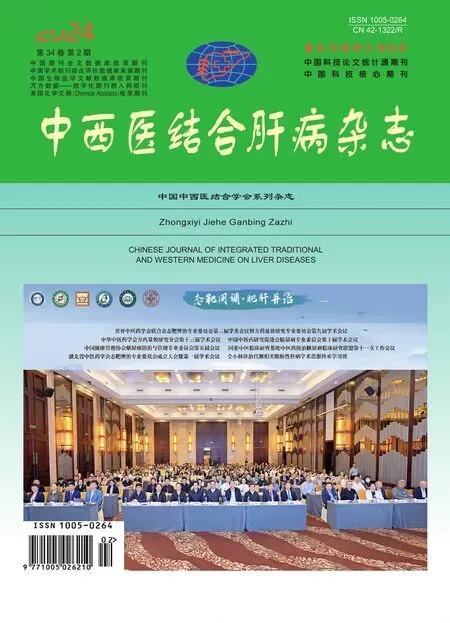尹常健教授从肝论治情志病经验选介*
李 璐 张 永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肝胆内科 (山东 济南,250011)
尹常健教授是我国著名肝病专家,长期从事肝病研究工作,经验丰富。其从肝论治情志病,学术见解独到,用药特色鲜明,临床疗效显著。现将其从肝论治情志病的经验选介如下。
1 情志病的概念
情志病为中医特有病名,首见于明代张景岳的《类经》,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情志病病因复杂,包括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受先天禀赋与情志刺激等的多重影响[1]。情志病涉及肝、心、脾、肾等多个脏腑[2,3],其概念广泛,包括一系列精神心理疾病与心身疾病,可表现为情志异常,如郁证、不寐、癫狂等,也可表现为情志受伤的躯体化症状,如眩晕、头痛、胸痹等[4]。
2 情志病的病因病机
尹常健教授认为情志病的病因为情志刺激,但能否引发疾病与脏腑功能、刺激强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病位重点在肝脏,可累及多个脏腑;根本病机在于气机郁滞,初病在气分,久则入血分;初起以实证为主,久则由实转虚,虚实夹杂。
2.1 重在肝脏,累及多脏腑 肝为风木之脏,其气升发,主疏泄,喜条达,恶抑郁。肝主疏泄的功能实则是对气机的调畅作用[5],通过对气机的调畅从而调节人的精神情志活动。肝主疏泄与精神情志间交互影响。探讨肝与情志之间关系的医家自古有之[6,7]。何梦瑶《医碥·郁》:“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王孟英医案》曰:“肝主身之气,七情之病必由肝起”。肝调畅气机使人体气机调和,血行畅利,七情畅显,助胃纳脾运,脾胃功能协调,七情的发生才有物质基础[8,9]。肝疏泄功能正常,肝气不亢不郁,则精神愉悦,血和气平。肝气失于疏泄,则可引起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异常。肝气疏泄不及,则表现为郁郁寡欢、多愁忧虑等;疏泄太过,则表现为烦躁易怒等。肝气横逆克脾,脾失健运,可出现腹胀、纳差、便溏等症。肝气犯胃,胃失和降,可出现嗳气、吞酸等症。肝气上冲于肺,木火刑金,肺气不得肃降,可有气喘、咳逆等症。肝气上冲于心,扰乱心神,可有心烦不寐、急躁易怒等症。肝主疏泄,心主神志,都与精神情志活动相关,情志病变中常见心肝二脏互为影响[10]。肝主谋虑,胆主决断,精神心理活动与胆之决断有关,胆能助肝之疏泄以调畅情志,胆之疏泄具有运转枢机、通畅三焦、升降水火,特别是流通气血之功[11]。
2.2 由气入血,化火生痰成瘀 尹教授认为情志病始于气机失调。情志刺激,气机紊乱,则可影响气血津液代谢以及脏腑功能。气有余便是火,气郁日久则可化火;气机阻滞,血行不畅,气滞血瘀;气郁不达,津液停聚,痰气郁结。情志不和,肝失调达,气机升降失枢,诸气皆逆,痰瘀形成,致诸症丛生[12]。尹教授认为肝对脏腑气血的运行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肝病最易引起本经和全身气机的逆乱[13]。肝气疏泄正常,则气机条达,血行通畅。“肝藏血”,肝病则藏血功能失职,可致血虚;肝气郁结不行则致血液瘀滞不通;肝火灼伤血络可致出血。尹教授认为情志病乃气机失调而致气血运行不畅,脏腑功能不和,肝为行气调血之重要脏腑,故而从肝论治情志病,临床常获良效。
2.3 初病多实,久则虚实夹杂 尹教授认为情志病初期病情轻浅,肝气郁结,情志不舒,焦虑抑郁,甚可出现胸胁胀满疼痛、纳差、失眠等身体症状,虽身心有恙,但仍可进行正常生活工作。此期以实证为主,治疗当以疏通气血郁滞为主。病程日久,生痰成瘀,耗伤正气,虚实夹杂,如横逆脾土,久可见脾虚;气郁化火,久则煎熬肝血,肝肾同源,可见肝肾亏虚;肝脏受损,肝血不足,亦可见心神失养。治疗在豁痰化瘀之余当注意扶助正气。
3 治疗特色
3.1 注重心理调摄 尹教授认为情志失调乃情志病的主要病因或诱因,多由情绪跌宕起伏或郁结心中难以释怀而致,易引起病情反复,若仅凭药物很难完全治愈情志病,良好的情绪调节乃是治疗成功的关键。中医情志疗法有大量的史料记载,在抑郁症中已有应用且取得一定疗效[14-16],尹教授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情志类疾病诊疗中。临床诊病十分重视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循循引之,谆谆诱之,解其心结,宽其心扉。取得患者亲属理解配合后,运用“情志相胜”之法,常用如“喜胜悲”“思胜恐”“悲胜怒”,合以药物治疗,取得良好临床疗效。并向患者推荐生活中可以采取的调畅情志的健康方式,如根据五音疗法选择合适的音乐[17]、适量运动、练习书法、观看喜剧等。反复告知患者平素应注意调节情绪,适度宣泄,抒发肝气,开阔心境,尽量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对于病情轻浅患者,甚至无需用药即可缓解病情,对于症状显著的患者,则合以中药治疗。
3.2 治身病以调心病 尹教授认为部分情志病乃躯体疾病导致情绪不畅、肝气郁结,进而出现情志症状;由情志不畅引发的情志病亦可出现胸胁胀满、心慌胸闷、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躯体症状,躯体不适与情志不畅之间交互影响,故而尹教授身心俱调,治身病以达到调心病的目的。尹常健教授临证注意询问患者起病原因或诱因,病情加重或缓解因素,根据其轻重缓急、病程久暂、偏实偏虚、在气在血等的不同,以脏腑辨证论治为原则,定性定位,审证求机,通达知变,选方遣药,合以心理疏导,临床获效显著。
3.2.1 疏肝开郁行气 病情初期,病邪轻浅,肝气郁结不舒是病机之关键,临床常以忧虑烦闷、郁郁寡欢、胸闷不舒、两胁胀痛等气机郁滞之候为特征。尹常健教授临证常用疏肝开郁行气之法贯穿情志病整个过程,通调气血,恢复脏腑功能的稳定,自拟疏肝方如下:柴胡、白芍、醋香附、郁金各15 g,炒枳实、紫苏梗、佛手、青皮、豆蔻、木香各9 g,炙甘草3 g,旋覆花12 g。尹教授采用柴胡、佛手、郁金、香橼、香附、枳壳等药物以疏肝解郁行气,此外,结合肝体阴而用阳,常并用白芍、木瓜、乌梅之品以柔肝养肝,如此刚柔并济,气血畅达,则脏腑安和。
3.2.2 疏肝健脾和胃 随病情进展,加之迁延误治,常可累及多个脏腑。往往首先影响脾胃气机的升降,出现乏力、纳差、腹胀、便溏、嗳气、呕吐等消化道症状。尹教授认为肝病传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病理过程,有时甚至贯穿疾病始终,因而疏肝健脾和胃之法在治疗情志病中的应用频率最高。李冠仙在《知医必辨·论肝气》中提到:“肝气一动,即乘脾土,作痛作胀,甚则作泻,又或上犯胃土,气逆作呕,两胁痛胀”。消化吸收功能是靠脾升胃降共同完成的,在临床上,肝郁脾虚、肝气犯胃常常不是单独存在,而是兼夹并见,脾气不升直接影响胃气和降,临床上很难截然分开。尹教授自拟健脾方如下:党参、白术、茯苓、酒黄精、炒山药、莲子、黄芪各15 g,陈皮、豆蔻各9 g,炒薏苡仁30 g,炙甘草3 g,诸药合用以达健脾益气、调理中焦之效。此外尹教授擅用半夏、干姜配伍黄芩、黄连等,采用辛开苦降之法寄开于泄,寓通于降,平衡阴阳,斡旋中焦,调理气机,以复脾胃之枢。“木生于水而长于土,土气冲和,则肝随脾升,胆随胃降,木荣而不郁”,尹教授通过治脾调肝,以条达肝气,可获良效。
3.2.3 肃肺开郁平肝 肝属木,肺属金,肝经上行,贯膈而注于肺。肝木过旺而侮肺,可致肝气壅肺及肝火灼肺两种证型,该型早期为实证,久则可见虚实夹杂。肝气上冲于肺,肺气不得下降,木击金鸣,可见气逆作咳、胁肋窜痛、咳黄痰、甚则咳血等症,亦称为木火刑金。尹教授以平肝凉肝为治疗原则,采用清金制木之法,选用加味泻白散加减,常用桑白皮、地骨皮、黄芩、柴胡、钩藤、苏梗、桔梗、杏仁、栀子等药,清肃肺气以抑制肝气上逆,肺气下降则肝气随之条达通畅。若患者病程已久,常配合培土生金法,补脾胃以养护娇脏,健脾运以助化痰,多用参苓白术散以补脾益气,肺阴虚明显者,多用沙参麦冬汤加百合、山药、石斛、知母等以健脾润肺。
3.2.4 清心补肾养肝 心属火为肝木所生,肾属水为肝木之母。肝郁久而化热,肝火上扬,扰心乱神,使神明无主,从而出现情绪甚至神志方面的改变;热盛煎熬肾阴,肾水亏竭,可见肾阴亏虚等症状,从而增加情绪负担,加重病情。此型患者多已病程日久,气郁血瘀,病情已由气分渐入血分,尹教授常以清心养肝、滋水涵木之法,采用清心凉血、补益肝肾、养血活血之品以养心肝肾之阴,润肝之燥,缓肝之急,使肝体得养,肝气自平。清心凉血多采用丹皮、郁金、川芎、丹参、黄连、生地、竹叶、灯心草等,以解郁而生热之患。补益肝肾多用地黄、女贞、山萸肉、枸杞子、牛膝、玄参、龟板等以滋养肝肾阴血,此药多甘腻,尹教授多配以柴胡、香附、陈皮、砂仁、木香等行气之品既解已郁之肝气,又防药品滋腻以碍气机,对于夹有痰饮患者慎予之。对于平素神耗过多而致心阳虚损之病患,尹教授多加用补骨脂、肉苁蓉、菟丝子、桂枝等药物以补益心肾之阳。常配伍当归、鸡血藤、桃仁、白芍之品以养血柔肝,将滋养肝体与条达肝用合理结合。此外,尹教授擅用交泰丸之黄连、肉桂,使心火与肾水上下交济,以安神宁志。
3.2.5 安神助眠获奇效 尹教授临证发现情志病患者多数伴有失眠,甚至很多病患以失眠为主诉就诊。失眠是情志病常见的共病模式之一,持续失眠是情绪障碍的危险因素和加重因素[18]。失眠与情绪障碍之间交互影响,恶性循环。尹教授在治疗情志病时常在辨证基础上加用安神助眠之品,既可缓解患者焦虑情绪,又可缓解躯体不适。根据“人卧则血归于肝”“肝主藏血”等理论,常用养心阴、补肝血的酸枣仁,清肝泻火、宣泄血中火热的夏枯草,以及解郁安神的合欢皮、首乌藤,重镇安神的龙骨、牡蛎。此外,尹教授常将柏子仁粳米粥、百合莲子炖猪心、山药茯苓红枣粥等食疗之法传授患者,深受患者喜爱与称赞。
4 临床验案
患者,女,60岁,2020年3月初诊。主诉:失眠、易怒1 年余,加重伴两胁胀痛1月。患者1年前因情绪刺激出现失眠、易怒等症状,反复就诊于当地诊所,服用黛力新、阿普唑仑等药物治疗,服药可缓解,停药即复发。1月前患者因家庭矛盾,情志再次受到刺激,失眠、易怒等症状加重,伴两胁胀痛,遂至尹教授处就诊。症见:入睡困难,梦魇烦扰,睡眠时间5 h左右,急躁易怒,悲伤欲哭,两胁胀满疼痛,善太息,太息之后自觉宽舒,口燥咽干,口苦,神疲乏力,气短懒言,纳差,大便秘结,小便正常。舌暗红,苔黄腻,舌下脉络迂曲,脉弦数。诊断:郁证、不寐、胁痛,证属:肝郁化火。治则:清肝泻火、解郁安神。嘱患者避免劳累,饮食清淡,调畅情志,耐心劝导,宽其心胸。用药如下:龙胆草6 g,焦栀子、黄连、清半夏各9 g,黄芩12 g,枳实、柴胡、香附、丹参、泽泻、桔梗、生地各15 g,当归、夏枯草各18 g,茯苓30 g,甘草3 g,共14剂,水煎服,分早晚温服。
二诊,诸证减轻,两胁胀痛已不显著,仍眠浅梦多,乏力懒言。原方去泽泻、枳壳、桔梗,加陈皮9 g,夜交藤30 g,郁金24 g,14剂继服。三诊诉服药后睡眠改善,余症减轻,要求再服半月中药以巩固疗效,遂予上方14剂继服。此后未再诊。按语:患者老年女性,素多忧思,因家庭矛盾而患抑郁症,情志不畅,肝失疏泄,气机阻滞,不通则痛,故而两胁胀满疼痛,肝气郁结,横犯脾土,脾虚不运,痰湿内生,郁久化火,痰火上扰心神,心神不安,故而出现失眠、易怒、悲伤欲哭等症。病位在肝、心、脾。方选龙胆泻肝汤合黄连温胆汤加减。方中龙胆草清利肝胆实火,为君药。黄芩、黄连、栀子、清半夏、枳实清热泻火、调气消痰共为臣药;其中黄连入心经,泻心火,黄芩清气分之热,栀子清泻三焦,半夏降逆和胃、消痞散结,枳实行气消痰,半夏配伍芩、连,寒热互用以和其阴阳,苦辛并进以调其升降,以斡旋脾胃气机。柴胡、香附舒畅肝经之气,引诸药归于肝经;泽泻渗湿泄热,导热下行;肝胆实火伤及阴血,当归、生地、丹参清热散瘀、滋阴养血、凉血安神,邪去而不伤阴血;夏枯草清肝泻火、泄血之热,茯苓健脾益气、宁心安神;桔梗配伍枳实一升一降,开宣肺气,畅利二便;共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全方合用,以疏肝泄火为主,利中有补,降中寓升,复中焦升降之枢机,祛邪不伤正,泻火不伤胃。复诊患者两胁胀痛已消失,以眠浅梦多为主要表现,原方去泽泻、枳壳、桔梗,加陈皮健脾理气化痰,夜交藤解郁安神,郁金清心解郁,患者睡眠明显改善。
情志病涉及范围广泛,临床辨证、治疗难度大。尹常健教授认为气机失调、气血不畅为情志致病的关键。肝主疏泄,调畅情志,且为调节气血的重要脏腑,尹教授从肝论治情志病,定脏腑,辨气血,分虚实,随证施治,阴阳同调,揆度奇恒,灵活用药,同时注重心理疏导,安神助眠,以提高治疗情志病的临床疗效,为我们诊治情志病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指导临床有很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