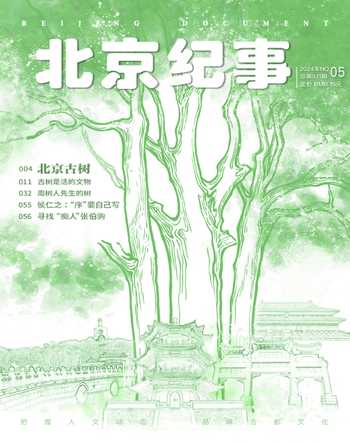寻找“痴人”张伯驹
福雨
草芦藏深山,溪水桥下过,树木越发茂盛,一派春景早已入心……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安逸却蕴藏生机。唐代的李白,则在《上阳台帖》中记录了王屋山高耸峻拔之势和源远流长之水。春光无限,大地美哉,笔墨传情,千百年前的光阴得以在千百年后的视野中相逢,这其中的功劳除了记录它的人们,势必还有如接力一般,“传递光阴印记”的收藏者,当我们酣畅于这些“神品”佳作之时,不得不提起一个名字——张伯驹。
痴心:
北京故宫《平复帖》
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1955年,当这八件足可以称得上“稀世珍宝”的书画文物被无偿捐赠给国家,人们一边慨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有实力收藏它们,一边也在疑问此人拥有怎样的慧眼与心境,在一个极讲缘分的“收藏界”与如此之多的珍品相遇。
从抗战后张伯驹所担任的相关职位不难看出,他与北京的缘分着实不浅——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并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张伯驹与文物的缘分之深,从他的一段传奇经历便可寻味,正可谓——心诚所致,对得起“朋友”,才能换的来“真心”。
在张伯驹心中,每一件文物或许是足可成为“朋友”“兄弟”的,患难见真情,可托命的那种!
1941年6月5日,当时还身在上海,担任着盐业银行总稽核兼常任董事的张伯驹突然消失了!三个手持短枪的黑衣人用贪婪的眸子监视着去银行上班的张伯驹,正当专车刚出弄堂,三人扑上前去,拦车、将司机拖出、劫持张伯驹……一切看来早已演练过数次。
疑云很快揭开,绑匪的目标便是张伯驹所收藏的、被誉为“中华第一帖”的《平复帖》。《平复帖》西晋文人陆机所作,其手迹比王羲之作品还早近百年,可想而知年代之久远,而文中墨宝不仅潇洒自如,更因不同身份的历代藏家留下的收藏印记而显得十分珍贵。
“江湖兄弟”的真情,并非一日之功,张伯驹与《平复帖》的交情也经历了考验。
1936年,张伯驹获知末代皇帝的堂兄溥儒将《照夜白图》卖给了日本藏家,于是担心国宝外流的他主动上门,希望将其手中的《平复帖》购于手中,没想溥儒要价20万,这在当时可是“天价”,对此张伯驹甚至请来张大千从中说项,可仍旧无功而返。
事情到了1937年有了转机,溥儒的母亲当时因病去世,因为急需用钱周转不开,于是张伯驹担心《平复帖》面临被出售的风险,再次找到溥儒,最终得以结缘。
正所谓“福兮祸兮”,歹徒的绑架也是奔着《平复帖》而来,张口要价300万赎金,否则以帖换人!
为了与歹徒交涉,加之以“绝食”抗争,张伯驹夫人有了一次与丈夫短暂会面的机会,张伯驹则偷偷告诉她:一定要保住《平复帖》,即使丧命也不能动文物。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歹徒的野心慢慢被消磨,张伯驹夫人也在积极通过变卖自己的首饰甚至家产筹备赎金,最终救出了丈夫。
虽然躲过这次一劫,张伯驹保住了性命,但心有余悸的他还是立刻携妻回到了北平,甚至还大病了一场。面对日益严重的日本侵华战争局面,病后的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将所有字画收藏缝入衣被,逃往了当时没有被日本占领的陕西,一路奔波,担惊受怕,好在“中华第一帖”幸免于难。
为了见证这一传奇经历,以及寄托对于《平复帖》的珍爱之心,张伯驹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如今《平复帖》已经安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了这里的“十大镇馆之宝”。
痴情:
后海南沿的《鹊桥仙》
后海南沿的小胡同守着碧波荡漾的京城水色,多少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了情思,著就了佳作,就在一座拥有着南北两排平房的小院中,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在这里度过了夕阳最美的晚年,不,在这里应该用“醉美”才对!因为这流金的岁月中,更有着伉俪情深的享受,用情至深、不顾一切的坦然,这甜蜜之情早已让人陶醉。难怪张伯驹在年近八旬时,还能为妻子写下一首让多少人为之羡慕的《鹊桥仙》:“不求蛛巧,長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
这样的爱情是足可以超越世俗礼教的。
潘素出身苏州府名门,为“清朝最年轻的状元”潘世恩的孙女,正因为潘世恩的才华外露,才得以历任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高官,也正因为他的才气才学,才让潘家的门风清朗且充满书香,就连这位孙女都是从小浸透在书香琴瑟、笔墨丹青的氛围中。7岁入私塾,十多岁善弹奏、绘画,知书达理秀外慧中。
然而,人生无常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无论你的出身与爵位。1928年,潘素的母亲病逝,父亲娶进来的后妈对她非常刻薄,加之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之前依靠清政府为官的家底,此时只剩下越吃越薄的尴尬。于是,潘素在无奈之下,只得被继母送进了上海的烟花之地,靠弹琴贴补家用。
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潘素,骨子里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气质,犹如青莲一般超凡脱俗,很快便有了“潘妃”这一雅号。不过,虽是身在青楼,但她早已声明,卖艺不卖身!一直暗暗鼓励自己,有朝一日定会脱离苦海。
作为当时被誉为“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当与潘素相遇后,便一见钟情,风度翩翩充满人文气质的“张公子”同样被这位才女所青睐。
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理念下,一位已经拥有一定地位及影响力的谦谦公子,想要将一个“青楼女子”娶进门,可想而知会有多大的压力,更何况当时张伯驹已然37岁,家中还有1妻2妾。然而,面对真挚的爱情,至诚之人的眼中一切阻力都是浮云,张伯驹立下誓言一定要为这个质清玉洁的女人,拓出新的人生之路。
张伯驹毅然休掉妻妾之后,于1935年,终于堂堂正正地迎娶潘素为正室夫人,也便开启了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段佳话。
潘素与张伯驹的结合,正所谓“灵魂伴侣”,二人均对笔墨丹青有着同样的爱好,一个懂得鉴赏,一个乐于寄情纸上。见夫人有如此爱好,一方面张伯驹邀请画坛名师为夫人点拨指导,另一方面潘素自己也在主攻花鸟题材的基础上,涉猎山水题材的文人画,细致的“小女人”视角,因为艺术展现手法的转换,更多了不少“人生智慧”的豁达,这样的结合又融入到了潘素的山水主题画作之中。
这样的转换是成功的,这样的转换也承载着夫妻二人的努力,潘素的作品在画坛逐渐声名鹊起,《漓江春情》《万松积雪》《夏山过雨》等作品,甚至作为国礼传播中国的文化语言。
这样的“心灵之交”“灵魂之交”渗透于生活的细节之中,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着这样一段故事:解放后,张伯驹虽然担任着诸多社会职位,但收入不比当年,正好当时他看上了一幅古画,所以只得向妻子要求“支援”。然而,靠工资吃饭的境况,精打细算的潘素肯定不舍得让丈夫支出额外金钱。于是也便有了这样的一段记录:“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痴迷”:
别了,弓弦胡同1号
住在后海南沿之前,张伯驹在北京着实是趁过大宅子的。
他的父亲张镇芳在弓弦胡同置下了一所宅院,这里曾经的主人据说是著名的宮内“大总管”李莲英。院子由四五个小院儿组成,游廊客厅、花木亭台一应俱全,张伯驹对这所祖上留下的宅子喜爱有加,宅院还有一个雅号——丛碧山房。
谈起“丛碧”二字的由来,还要从张伯驹30岁那年说起。当时张伯驹在琉璃厂一家古玩店门前经过,偶然发现店中高悬一幅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幅御笔与康熙帝以往稳重大气、硬朗宏阔的风格并不一样,颇有飘逸之风,拥有多年鉴赏积累的张伯驹慧眼识真,认为这一横幅定是康熙真迹,从落款、印章等处已见真伪。此外,无论风格如何变化,书写者的气韵习惯在细微之处是不会变化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彰显皇帝“真性情”的作品,才更加珍贵。
于是,“丛碧”之作有了新的主人,张伯驹的字——“丛碧”,也便由此而来。而他的号“游春主人”同样与他的收藏和这所宅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提起“收藏”,如今的人们总是会与“私藏”“资本”“升值”……一系列充满金钱味道的词汇相联系,但真正的收藏却恰恰蕴含着“品味”与“心性”、“格局”与“豁达”,张伯驹的收藏之路便充满着这样一种“侠义”味道!
《游春图》——中国绘画史上,标志着中国山水画已由“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作为人物配景的稚拙阶段,进入了成熟阶段。在世界上可与梵高的《鸢尾花》、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的画作,此画名列其中。1924年10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伴随溥仪出宫的还有不少珍贵的国宝文物,这幅《游春图》便在其中。然而,正是因为清皇室跌宕漂泊的辗转,不少稀世珍宝在这一过程中主动或是被动地流落民间。
当《游春图》再次出现在收藏圈的时候,作为当时已经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的张伯驹十分焦急,提议尽快回购《游春图》,以防这一“国宝”流失海外。可当时民国政府的资金同样羞涩,张伯驹情急之下只得决定由个人担此重任。
众所周知,痴迷收藏的大家,手中“余粮”其实并不很多,所拥有的财富均压在了藏品之上,又何况是张伯驹这样“只藏不卖”的真正藏家。在与售卖者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张伯驹只得将这座弓弦胡同1号的祖宅变卖,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知道此事后,决定以2.1万美元买下此宅。
《游春图》终于通过张伯驹的努力,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之上,张伯驹也迁居到了北京西郊的承泽园居住,为了纪念《游春图》的来之不易,张伯驹将此园命名为“展春园”。在这里,张伯驹将自己的所有收藏进行整理编目,定名《丛碧书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