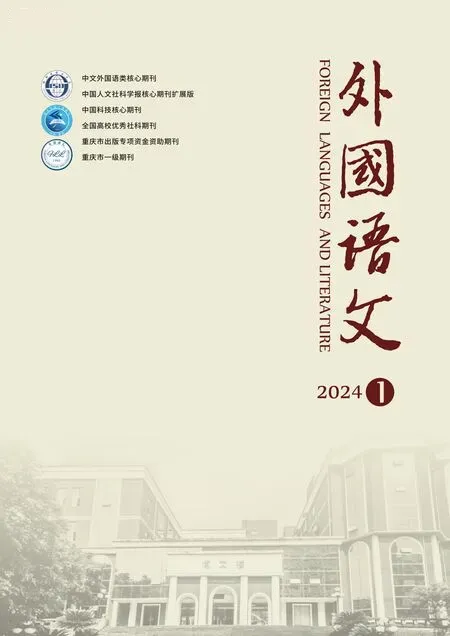论女性生命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
——芥川龙之介之女性言说
黄芳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重庆 400031)
0 引言
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作家,其最引人注目的理应是以148 篇之巨的小说扫描了近代日本的“社会世相”。芥川的文学存在,显示出通过艺术对自然主义的、小市民的现实蕴藏的矛盾、对立加以扬弃的艺术主义倾向,也因而确立了其大正文坛代表作家的地位。芥川文学以灰暗的现实为基调,描写出个性、人格等既存价值观无法支撑的人间世相,并认为这是植根于近代个人主义的艺术的一个必然归结。其作品以通过艺术实现近代自我完整的艺术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调,在广泛摄取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上实践了近代短篇小说多样化的可能性,芥川也因此在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日学术界对芥川龙之介的研究可谓经久不衰。关于芥川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分野:一是文学性研究;二是透过文学文本的近代日本的“社会世相”研究。然而,在“社会世相”研究的成果中,却鲜见有关芥川女性言说的研究,这一欠缺使得“社会世相”出现了一片不可忽视的坍塌。芥川小说中的女性言说反映了芥川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对女性认知的复杂心态,并导致其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显得杂乱。通过对芥川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加以梳理,从而将芥川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女性认知加以明晰化。
“社会世相”虽然不是地道的现代汉语的用语,但也不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新概念。用当今的话语来翻译“世相”一词的话,我认为最为恰当的表达就是“生态”。因此本文使用的“社会世相”即为“社会生态”,亦即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被人们称为鬼才作家的芥川龙之介在短短12 年创作生涯中写过148 篇小说,而如此大量的文学创作,其素材源泉正是当时包罗万象的“社会世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将纷乱繁杂的社会世相加以艺术升华,以小说的形式“反哺”予民众,给民众一个客观反照、认识自身的镜子,以文学诉说去警醒民众、教化民众,这正是芥川龙之介作为作家试图达到的目的。诚然,作家自身也是社会一员,有着诸多的局限性,社会认知仍然残留着封建时代的道德,并因此而感到困惑。
学界对芥川的研究重点往往集中在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故事性、叙事性以及中国体验等领域,而放眼芥川文学的女性言说的相关研究则少之又少。就当前仅能检索的几篇文章来说,对芥川女性观的研究,一是将芥川龙之介笔下的女性简单地分为妖妇型和淑女型,二是按照题材作出大概的归纳。此前国内学界对芥川龙之介的女性言说虽然尚停留在浅表层的现象研究的层面,但却为此后的深层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在芥川龙之介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并不多见,小说里的女性形象也不是十分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芥川龙之介在感性上将女性仅仅视为社会生态中的必然存在,而这种存在是不必特别在意、乃至于可以视而不见的。然而在理性层面上,他肯定女性作为人有着与男人同样的社会生存权利,并以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来抨击传统的男权,反映了女性生命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芥川的女性认知也在不断进步,甚至具备了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
本文试图较为全面地对芥川其人、其文学作品的女性认知进行提纲性的梳理,力求通过其女性言说之空间,去寻找芥川不同于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女性观嬗变的轨迹。
1 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芥川在初期作品里经常描写夫妻关系。“结婚对于调节性欲是有效的,却不足以调节爱情。”[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33]其笔下的男性也曾追求爱情,但却常常痴心错付。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得夫妻猜疑不断,不仅追求灵魂伴侣的愿望失败,婚姻关系破裂,甚至导致妻子弑夫的悲剧发生,使芥川对婚姻和女人充满失望,始终走不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开化的丈夫》里的三浦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文明思想洗礼的留法绅士。他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追求“拥有爱情的婚姻”[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466],绝不做任何妥协。在与友人报告婚后近况时,都能感受到三浦对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充满喜悦之情。可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后,当叙事者再见三浦,三浦却是一副忧郁深沉的模样。原来夫人水性杨花,出轨表弟,爱情至上主义者的三浦甚至想过成全妻子与表弟青梅竹马的爱情,却又发现妻子的表弟还与其他女人有染,而妻子也并非对表弟一心一意,三浦曾拦截过其他男人写给妻子的情书。这对有心理洁癖的三浦是沉重的打击,不久便离了婚。经历这段失败的婚姻,三浦憧憬的“拥有爱情的婚姻”失败了,终于明白自以为的心心相印其实是“犹如稚童般的梦想”[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475]。
《尾生之信》里塑造了一个痴情男人尾生,因等候恋人,被越涨越高的潮水淹没仍然不愿意离开,在命丧河边之后,数千年魂魄寄宿于他人体内,仍然痴等永不到来的恋人。薄暮中、桥栏下,尾生痴情苦等,用自己滋养奉献,直到自身化作虚无。关于女人的相貌、性格、年龄等,芥川只字未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仅用“女人”来称呼她。女人是否爱尾生也未提及,是一个被芥川彻底无视的存在。“女人却仍未到来。”这句话在短短的信中却出现了六次,在尾生面临危险也不离去的每一段描述后面均附上这句,不断重复的句子透露了尾生的绝望和女人的无情。芥川故事里的男人可以无怨无悔等候虚无缥缈的爱人,但对女人的描述却体现出无视和不信。
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人,是女人重要还是兄弟情重要? “虽然是兄弟,为了独占一个女人,相互之间憎恨、并产生杀意。容易丧失至亲的羁绊。”(酒井英行,2007:80)芥川的作品里对这种世俗伦理的人性拷问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偷盗》里的沙金是一个妖艳妩媚的女盗贼首领,这个生活在王朝末期最底层的女盗贼不仅委身于养父,还与多人有染,非常懂得利用姿色去支配男人。太郎与次郎同时爱上了沙金,兄弟二人在沙金的怂恿下上了贼船,从此无恶不作。太郎深感相貌清秀的弟弟抵挡不住沙金的诱惑,那么他失去的不只是沙金,还有弟弟。太郎无法接受同时失去挚爱的两个人。而次郎一方面无法抵抗“丑陋的灵魂与美丽的肉体如此结合在一起的”[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182]沙金的诱惑,一方面又觉得愧对哥哥,甚至想远离哥哥和沙金以减轻对哥哥的内疚,不想与哥哥为敌的次郎也备受情感的煎熬。改变这种局面的是沙金设计干掉太郎的一场战斗。沙金移情次郎,并怂恿次郎参与杀死哥哥的计划。激战中太郎原本驰马而去时,强烈的兄弟情感驱使他返回救出次郎。经此一役,兄弟终于同心,齐心协力杀掉沙金,沙金断气时,兄弟相拥而泣。引起太郎与次郎兄弟反目的沙金这一女人形象里隐藏着芥川的女性认知:“对我们男人来说,女人恰恰是人生本身,即万恶之源。”[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43]沙金是兄弟不和的原因,相较于沙金这个生性放荡的女人,兄弟情更为重要,男女的情感抵不过兄弟情深,最终割舍不断的兄弟情救赎了两兄弟的灵魂。这一情节设定体现了男权社会“女人如衣衫,兄弟如手足”的传统观念,折射出芥川对男权传统下的女性认知。
《竹林中》是《偷盗》系列作品之一。《竹林中》以三个人的陈述为中心展示了一个杀人事件。盗贼多襄丸首先承认自己杀人是因为真砂的教唆,而真砂通过忏悔的形式来认罪,忏悔自己杀夫之后又没有勇气自杀。丈夫的亡灵则说是妻子命令强盗杀他,他痛苦不堪才自杀的。“竹林中 ”是暴露人类本性的一个空间,也是“向制度挑战的人类情念世界的比喻”(酒井英行,2007:93)。在竹林外的丈夫气质优雅,一旦进入“竹林中”,就变成了欲望之魔鬼。妻子在外面空间时贞淑善良,在竹林中就显露出水性杨花的一面。自己被辱,丈夫不作为,反而数落妻子被强奸后竟然被强奸犯吸引的罪恶。丈夫冷漠的目光令妻子不能忍受,最终说出“你亲眼看我出丑,我就不能让你再活下去”[高慧勤 等(第②卷),2012:124]。结局是丈夫死了,妻子忏悔,盗贼被捉,没有人无辜,只有人性的丑陋被赤裸裸暴露出来。芥川的创作意图并非为了寻找真相,丈夫亡灵的供词、盗贼的口供、真砂的忏悔直接导致读者认为真砂就是真凶,而真砂的忏悔便是作者芥川对真砂的恶意。西原千博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便是“对女人的恶意”(鷲只雄,2017:97)。丈夫死了,多襄丸认罪,所有的恶意都指向了真砂。最后法官只追责杀人事件,并没有追责强奸事件,原本应该是受害者的真砂在芥川的笔下却成为害死丈夫的元凶。
在以上作品中,从男性视角观察到的女人大都不可捉摸、不值得信赖,她们对丈夫不能一心一意。《开化的丈夫》《竹林中》《影子》等一系列作品里的丈夫们对妻子充满了不信,潜意识里均认为女人是不贞的。芥川在随笔《鹭鸶与鸳鸯》里,讲述在银座偶遇两美女姐妹,称之为鹭鸶与鸳鸯。在电车里近距离看到鸳鸯的鼻毛,听到两姐妹在谈论女人月事之后,大倒口味,再无旖旎之心。由此可见,芥川认为女人只可远观不可近看,现实与梦想存在很大的差距,现实总是无情地摧毁人的幻想。他在《侏儒警语》里曾说过“纵使再心爱的女人,同其交谈一小时便觉得乏味”[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255],这是芥川对女性精神的一种轻视,他认为女性徒有其表,没有灵魂。在现实生活中,芥川曾经爱上过一个生性嫉妒和占有欲强的女人,芥川一直摆脱不了,江口涣说芥川的自杀30%是因为这个女人。被爱情辜负的人,就会变得对爱情极不信任,芥川的情感经历使芥川对女人怀有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芥川也渴望灵魂伴侣,两情相悦应该是爱情最理想的状态,但在芥川的笔下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无法实现的缺憾。
2 人性视域下姐妹连带感的丧失
中田睦美曾评价说《秋》是芥川唯一的女性小说,在此以前,芥川的作品均是从男性的视角去描写。在1919 年创作《龙》时,他感受到了文学创作思泉的枯竭,强烈的危机感驱使芥川试图改变风格。在《秋》里,将女性视角引入作品中便是芥川的新尝试,也因此使其文学创作有了转机。该作品放弃了芥川奇巧取胜的惯有风格,具有近代心理小说的特征,因此《秋》被看作是芥川向现代风格小说的转型之作。
信子和妹妹照子同时喜欢上了表哥俊吉,姐姐不动声色的暗示令周围的人都认为俊吉喜欢的是信子。在妹妹的央求下信子大度退出,另嫁他人,过着寻常夫妇的平凡生活。妹妹顺利与俊吉结婚,并写信感谢姐姐的成全。信子爱好写作,曾立志成为作家,可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令她不时回想起与俊吉之间的兴趣相投。在这样刻板的夫妻生活中,信子产生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空虚和无聊在她去新婚妹妹家里见到俊吉时便转换为一种感伤和后悔。姐妹感情产生裂痕是在两年后,姐姐回到东京去拜访妹妹,妹妹得知姐姐单独见了自己丈夫时,便心生妒意。当俊吉和信子一起走在庭院里时,信子心里在默默期待着对方的表白,但俊吉沉默片刻之后,自然地转换话题,由此可见,俊吉对信子并没有男女之情。三好行雄曾尖锐指出,“信子与俊吉的‘爱’不过是大家的传言罢了”(鷲只雄,2017:97)。信子一味陶醉在牺牲个人的婚姻和幸福来成全妹妹的美满婚姻的虚构世界里,表面是在安慰妹妹,实际上是一副恩人的倨傲嘴脸。“本是强求妹妹感谢的利己主义、却转换为在面对妹妹时的优越感,是一种自我美化。”(酒井英行,2007:203)尤其在妹妹指责她深夜毫不避嫌、单独与俊吉在后院时,信子心有不甘,也因此在心中暗下决心与妹妹从此成为路人。“最信赖、最交心的一直认为便是妹妹,而妹妹也深有同感。”(佐古纯一郎,1991:59)这样的姐妹情深在面对三角关系的爱情时,也经不起考验。所谓让爱,真正有爱又怎么让得出呢?
在故事的结尾,信子与俊吉擦肩而过是小说的高潮。不顾俊吉再三叮嘱等自己回家再走,信子乘上了篷车,意味着她的放弃。透过车窗,信子看到了俊吉,而窗外匆匆而过的俊吉并没有看到她。透过车窗看外面自然是一清二楚,而从外面便不容易看到里面,芥川巧妙利用这一点来暗示信子的视线是单向的,俊吉的视线并没有落在她的身上,由始至终都是信子单方面的情感投放,俊吉并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一场两女一男的三角恋只不过是两姐妹的幻觉罢了。俊吉走出信子视线之后,信子所有的期待落空,只剩下萧瑟的秋天映衬着心里的哀伤。现实与幻想之间的位相之差是那么明显,原来以为的牺牲自我主动让爱的故事不过是信子一个人的独角戏,青春的梦想破灭后,徒增伤感。三好行雄高度评价描写青春丧失的《秋》是“芥川文学前期作品的终结之作”(浅野洋 等,2000:242)。虽然在描写爱情,但芥川并不相信爱的存在。姐妹爱上同一个男人的故事以姐姐成为局外人而结束,信子只有回到和丈夫的平淡婚姻生活中去,再也不能和俊吉聊文学话题。秋天之后便是冬天,衬托着人生没有希望,秋天的意象象征人生的放弃,这世界上的心如死灰,大抵都如信子这般,坐在人力车上回家的信子全身心感受到了秋的寂寥。佐古纯一郎评价芥川的文学便是“秋天的文学”(佐古纯一郎,1991:63)。寂寥是其内核,支撑姐姐内心平静的便是念想之后的寂寥。
在男性占据价值体系的控制权和话语权的时代,男性执掌着女性形象的创造权,女性无法进行自我表现,于是男性习惯将一些负面价值推给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比如“嫉妒”二字均带有女字偏旁,“嫉”为歇斯底里,“妒”为“女性为了不败给竞争者而面红耳赤的亢奋状态”。这一特性从一开始便被贴上女性性的标签。同样描写嫉妒心,《偷盗》里两兄弟最后并没有因为沙金而反目,而《秋》里的两姐妹却因俊吉而从此成为陌路。兄弟同心和塑料姐妹情的对照书写演绎了兄弟血缘的不可替代及姐妹连带感的不堪一击,证明女性的嫉妒心强于男性,反映了芥川在男权思想影响下的性别偏见。
3 女性自审意识的演进
芥川在爱情短篇小说《袈裟与盛远》里颠覆传统的烈女形象,体现了女性自审意识的演进。故事由上下两段告白组成,上是意图刺杀袈裟丈夫前夜的盛远的内心独白,下为知晓盛远计划、决定替夫去死的袈裟的内心独白。独白通过主人公的内心语言活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再配以月色清冽的夜晚描述,将整个故事充满哀怨地娓娓道来。盛远在三年后与袈裟重逢,此时的袈裟已不复往日的美貌,盛远对她再也没有当初的心动。盛远的独白里自认对袈裟的爱是“欲望的美化”[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311],他用尽手段制造邂逅,最后终于得到了袈裟。对袈裟的念念不忘源自未得到的不甘和 “掺杂着相当程度的对不识的软玉温香的憧憬”[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313]。
盛远是袈裟唯一爱过的男人,袈裟背叛丈夫心甘情愿与盛远发生了关系,她的失贞是为曾经的爱情寻求一个完美的结局,可现实生活里丈夫对自己那么温柔,为了讨好袈裟,武士丈夫甚至去学习和歌。袈裟背叛丈夫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是不能被容忍的,同时,占有了袈裟之后的盛远对她显露出嫌弃之色。面对盛远浓情转淡的这一瞬间,袈裟无自杀的勇气,又不愿意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这样的矛盾与痛苦里,听到盛远提出杀死袈裟丈夫的建议时,她欣然同意,袈裟穿上丈夫的衣服,等待死在盛远的刀下。袈裟作为烈女的典型,表面是因为爱着丈夫,实际上是用死亡完成对自我的救赎。月色冷冽,烘托出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二人的心理描写细腻,微妙的陰翳、动摇的情念”(中村稔,2014:82)充分展示了芥川的才情。在芥川的文学世界里,爱情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记忆如潮水般翻涌而来,袈裟那千疮百孔的心早已不堪重负,再也没有爱的力气了。爱情如果到不了终点,不如让生命到达,对袈裟而言,因为爱情的令人绝望,死亡才那么充满诱惑。清冽的月色映照着,袈裟的心冷彻而坚定,配合着盛远完成了这场名为爱的谋杀。
在日本,自古以来袈裟这一烈女形象深入人心,但都忽略了她和盛远有过床笫之欢的事实,曾有读者写信指责芥川将为保贞洁决心赴死的烈女形象篡改。实际上在《源平盛衰记》里曾明确描述“盛远来得很早,与女人同床共枕,夜渐深沉云云”[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297]。芥川曾说“不知出于何种意图,社会上普遍无视这一史实,似乎把可怜的女主人公广泛宣传成一个超人的烈女”[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297]。芥川在小说里将袈裟与盛远持续半年之久的情人关系清晰描写出来,颠覆人们对袈裟为了保护贞操而甘心赴死的烈女印象。虽然颠覆了烈女形象,但在芥川的笔下,袈裟在因失去贞洁从而对丈夫产生内疚悔恨之心时,看到盛远露出轻侮之色,在这两者之间挣扎之后毅然选择死在盛远刀下的行为并不惹人厌恶,反而令人同情,这一颠覆令整个爱情故事充满了感伤。袈裟的独白里直接说出了自己代替丈夫死在盛远刀下并非为了丈夫,而是“因心灵受到伤害而感到愤然,身子受到玷污而为之悔恨”[高慧勤 等(第①卷),2012:316]。芥川对烈女形象的颠覆令袈裟的形象立体鲜活起来,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不再受封建道德约束的女人。
明治以前的道德是一种封建的道德。芥川认为“封建主义的道德是一种十分脱离实际或极端理想化的、实行起来很困难的道德”[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89]。“因为这道德把忠臣、孝子、烈女这类理想上的人物定位一个目标,要求人们努力向这些典型人物看齐。但是人很难完全实现这种道德标准。”[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90]芥川认为批判精神的匮乏是封建道德得以延续的条件,这种缺乏表现在没有把过去的忠臣、孝子、烈女看成是有血有肉与我们同样的人,而是看成了某种神的化身。芥川认为昨日的道德是脱离实际的,太富于理想主义色彩。芥川没有被困在世俗和偏见里,是一个接受了新道德,敢于向根深蒂固的旧道德提出质疑的作家。
4 对女性贞操观的现实批判
自古以来对女人来说,贞操是最重要的,“贞女不事二夫”是男权社会禁锢女人的一种制度。在近代日本黎明期向开化期过渡的时代,人们对贞操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女性作家们如《青踏》杂志社成员围绕“贞操论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生田花世为代表的认为“比起贞操,我们先会要求吃得饱饭”(生田花世,1914:37);另一种认为这样的想法和依附于男人的娼妓没有区别,女性的颓废与堕落在于性道德的败坏。在纸上大肆探讨女性贞操这种隐私话题的时代,芥川在《阿富的贞操》里直接将“贞操”二字置于小说的标题,塑造的阿富认为生命比贞操更为重要,对女性贞操观提出了批判。
《阿富的贞操》以新政府与反新政府开战的上野战争为时代背景,男主人公新公是新政府军的一员,时常扮作乞丐在上野一带活动。某日新公来到小杂货店避雨,遇上回来寻猫的女佣阿富。见到充满朝气活力、如水果般鲜嫩的阿富,新公产生了欲望,于是掏枪对准花猫,以此威胁阿富顺从于他。为了救主人的花猫,她宽衣解带,甘愿向新公献出自己的身体。从两人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年龄、见识明显劣于新公的阿富对新公的态度是粗暴的,而新公却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这样相处,由此可见两人之间有着信赖。正因为阿富对新公充满信赖,才心甘情愿把自己交付给他。而阿富的这一举动,让新公的心灵得以净化,并没有动阿富一根毫毛。在生命与贞操的取舍之间,阿富选择了生命,芥川的贞操观与当时的新女性作家们主张的贞操观迥异。
战乱时代,到处都会发生弱质女流被男性强暴的事情。故事的正常展开应该是持枪的乞丐新公侵犯阿富,阿富为了保护贞洁拼死反抗。可是小说里,阿富并没有反抗,而是主动躺下。对此行为,新公深感疑惑:“一个女人委身于男人。这可是终身大事呀,可是阿富姐,你却用它去换一只猫——你这不是太胡来了吗?”[高慧勤 等(第②卷),2012:247]面对危险,阿富没有抱怨,而是主动直面困难,这样一位积极直面人生的女性自带光环,是芥川发自内心欣赏的女性。
在芥川看来,传统的贞操观也好,新女性的贞操观也罢,看重的是身体本身的圣洁性,都被伦理道德所束缚。阿富在那一瞬间采取的行动是发自内心的,用女人视若生命般宝贵的贞操去换取花猫的性命,她认为值得。新公在听到阿富的理由时,感受到了阿富心灵深处的纯粹,这一发现令新公自愧不如,令他一直坚信的观念受到冲击。如果说之前吸引新公的是阿富充满青春活力的肉体之美,勾起了他男人的本能欲念,那么此刻则是被阿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深感羞愧的新公人性得以复归。
22 年后阿富与丈夫及孩子一起偶遇了新公,令阿富想起往事。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当时的行动是基于何种理由,也不明白新公为何没有侵犯她,尽管如此,她从未后悔过,在看到勋章加身的新公后,她回头对着丈夫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再次重逢时新公已经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成名人物,与第一次登场时如乞丐般的形象完全不同,而阿富也有了幸福的家庭。从阿富和新公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芥川对两个主人公的行为均持肯定态度,令两位善良的人均有了美满的结局。阿富的贞操体现在她内心的纯洁,这种纯洁具有感染他人、令他人变好的神秘力量。阿富这一女性形象不同于与以往恪守传统贞操观的女性,芥川在此探讨了贞操新定义的可能性。
“妇女占据何种社会地位,是鉴衡人类文明高低的真正尺度……富人或贵族阶层男人,大多不像妇女那样保持贞操。相反,千真万确的是,身为母亲或妻子的妇女却能纯洁地度过一生。”[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412]芥川深刻意识到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因此,他抛弃传统道德对女性身体的束缚,将贞操定义为心灵美的精神层面,应该说芥川的站位比《青踏》的“新女性们”更高,这是芥川性别意识的进步表现,体现出芥川思想先进性的一面。
5 结语
“文学在审美体验和价值评价中,透露出作家对社会、人生和美的观察和沉思。”(汪正龙,2002:217)学界大多认为芥川与自然主义作家相反,不会在作品里描写自己,这是一种误读。“我的小说或多或少正是我自身体验的告白,只是各位不知道。”[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281] 在杂文《我若生为女子》里,芥川假设自己若为女子就会“尽量做出温良贞淑的样子,尽量抓住情投意合的丈夫。尽量巧妙地操纵丈夫,尽量使自己有更大的发展”[高慧勤 等(第④卷),2012:658]。“温良贞淑”是“男权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外在强化” (罗元 等,2020:37)。讨好丈夫和操纵丈夫体现出芥川女性观的矛盾性,而使得“自己有更大的发展”则是芥川对女性精神发展的期待。他认为,女人参与工作并不会失去女人味儿。但他还是喜欢“既能生儿育女又能缝制衣服,温柔的雌性白狼” [高慧勤 等(第③卷),2012:344]。“生儿育女”这样的女性肉体记忆早就固化在稳定的男权文化心理中,体现了芥川对男权文化的不舍。
作为生活在日本近代社会的男人,处在由旧传统向新思想过渡的“思想动摇期”,芥川依然不能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尽管芥川龙之介并非顽固的传统派,但当时的“社会世相”依然反映出对男权的不舍,这就决定了芥川龙之介文学作品具有双重性:一是作家力求跟着社会的开化接纳男女平等,二是社会的现状依然留恋着男权的传统。在芥川龙之介的天平上,后者依然占据着一隅,所以在他的诸多作品上反映出男权视野下的女性认知,这体现在《竹林中》《偷盗》《开化的丈夫》《秋》等作品之中。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女性言说是在“社会世相”的折射基础上的内心言说,一方面芥川坦诚仍然残留着封建时代的道德,并因此感到困惑,但同时他肯定女性作为人有着与男人同样的社会生存权利,并以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来抨击传统的男权,反映了女性生命意识与男权文化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芥川的思想在不断进步,甚至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本文所选涉及女性的作品基本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由此可以看出芥川女性认知的演变轨迹。芥川所处的年代正是“青踏”杂志周边的女性作家们争取女性解放的时代,芥川自然也深受时代思想的影响,他对女性解放发表的言论体现其女性认知的先进性,其真知灼见甚至超过了女性解放思想家们的见识。如《袈裟与盛远》《阿富的贞操》等作品里揭露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禁锢,显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先进性,在今天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