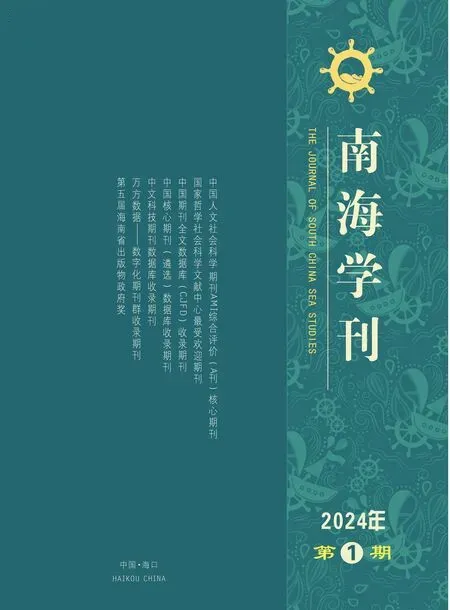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张雨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文化遗产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学界对相关议题在理论和经验层面均有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已经初具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都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新古典学派”的特点、研究成果,及其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创新与启发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进行梳理与总结,并提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文化遗产与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进路。
一、文化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
(一)为何研究文化遗产
近些年,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学术研究也大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较多的学科是民俗学等学科,与此相对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等学科则更偏向于研究物质文化遗产。但这种按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研究对象并加以研究的方式,容易仅仅只关心物质文化遗产而忽视与之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仅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忽视与之关联的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不可截然分开。更重要的是,这种分类也不利于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文化事项,因为绝大多数文化遗产都是整体的,无法拆解。把一个整体拆解成不同零部件来看待和研究,对文化遗产本身也是一种伤害[1]。因此,本文提出将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对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刻意强调,而着重以整体的文化遗产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各种文化遗产之间以及文化遗产诸要素之间的关联。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反对对于文化遗产的细化分类,而是强调应从文化遗产这个大框架来探讨诸文化要素的传承、保护与创新。
文化遗产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较高文化、历史、艺术或者科学价值,并以特定实物或者非实物的形态存在的人类创造物[2]。文化遗产的概念源于19世纪发生社会巨变的欧洲,体现为对过去的物质性存在的某种人文关怀,主要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能够展示以往辉煌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遗产概念真正得到重视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破坏,以及战后现代工业化浪潮对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引发全世界广泛关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遗产的资源作用和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人们纷纷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迫在眉睫[3]14。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路径的国际化传播。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致力于保护、宣传本国的文化遗产,以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本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中国政府正式使用国际通用的“文化遗产”概念并首次予以阐明的重要文件,是国务院于2005年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使用并阐明“文化遗产”概念,是中国的文物事业和民间文化事业向文化遗产事业跨越的标志,是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融入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里程碑[3]52-53。自2006年起,国务院决定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1)2016年9月,国务院批复,自2017年起,将“文化遗产日”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遗存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思想价值与经济价值[3]136。在当今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经验与思路,更能为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在新时代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二)文化人类学整体观视野下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开展了相关研究。经济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环境学、教育学、旅游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学科的研究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文化人类学也对文化遗产开展了大量研究。有研究指出,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应该发挥田野调查工作和民族志访谈写作这两大研究方法[4];也有研究突出强调要发挥人类学的整体论视野[5]。笔者认为,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应充分发挥人类学的方法论之一——整体论。但在目前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利用整体论这一人类学独特视野的研究还不够多,也不够深入。实际上,文化遗产研究与其他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其他研究总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文化遗产则重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3]24。这与人类学的整体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如果想做到在文化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下进行文化遗产研究,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将文化遗产放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观察与研究。当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有一种方式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非遗博物馆中陈列展出。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将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但也会将文化遗产“脱嵌”出其原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化遗产的简单陈列展出只能保留其外在形式,其与情境相关联的整体性被忽略,文化遗产也无法实现自主发展。文化遗产需要活态传承,需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理解与研究。人类学的整体论恰恰能够提醒人们,文化遗产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或外在结构,对于认识、理解、发展文化遗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以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而非具体文化事项作为分类标准进行研究。目前,学界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大多将其分类为有形的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即区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互依存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分割的。以人类学的整体论来看,如果只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只看到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全面的[6]113,因此需要将文化遗产作为整体加以看待、研究和保护。近些年,张继焦领衔的“新古典学派”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基于人类学的整体论,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类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按照文化遗产所处的场景进行分类,如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等。这种分类方式充分利用文化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进行分类,能够对文化遗产进行更加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的深入分析。依据所处整体社会情境进行分类研究的方式充分结合了中国历史与当代的具体国情,解决了西方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分类无法解决非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传承、研究、保护好中华民族的诸多优秀文化遗产(2)笔者并非反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分类,而是认为应该放在具体的情境、语境、场域中再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把握文化遗产的内外关联性。而且在进行整体性认识和保护的同时,也应该在适当时机进行细化。。
二、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能够初具规模并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是因为有张继焦的不懈努力推动,也是因为有建立在文化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上的丰富广博的田野调查。但更为重要的是,学派的产生是因为有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这一理论方法的恰当指导。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是张继焦在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并综合前人多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理论提出的直接动因就是看到了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困境。因此,在今后对文化遗产的分析与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的过去、今天与未来。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以下只对理论的一些思路与研究方法做简单介绍讨论。
(一)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与三个研究维度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面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情况,综合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功能论”[7]、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结构-功能论”[8]、费孝通“文化开发利用观”[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型发展”[11]、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竞争优势”[12]这六大理论,提出应对文化遗产自身为何变化、如何变化、何时变化进行动态研究分析,从而区别于古典“结构-功能论”的静态研究路径。
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看来,文化遗产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会被动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变化。与此同时,文化遗产自身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自主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
在实例分析中,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具有三个研究维度,分别是本体结构、外在结构与自生结构。本体结构是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文化遗产自身。外在结构是文化遗产所处的场域和结构,也就是笔者在前文所强调的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自生结构是指作为结构遗产的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自我配置资源的结构和功能[6]108-123。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时,可从本体结构、外在结构、自生结构三个研究维度入手,分析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文化遗产。
(二)中国社会“伞式”“蜂窝式”二元结构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根据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认识,在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指导下,提出“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这一对新概念[6]127。“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是两个相互之间对立统一的概念,二者共同形成了一种解释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学说,即二元社会分析法。
“伞式社会”概念主要描述的是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与当地社会组织的关系时而会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伞式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地方的资源配置时而表现出“伞式社会”特点[13]。“伞式社会”概念揭示了历史上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对文化遗产的历时性分析需要注意到政府的作用。
“蜂窝式社会”概念主要用来描述民间经济社会的结构。“蜂窝式社会”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获利的机会和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这种人人参与度较高的市场发展情况被喻为“蜂窝式社会”,即每个人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样,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构筑属于自己的蜂窝[14]。与“伞式社会”关注政府作用不同,“蜂窝式社会”更多用来分析民间经济社会行为。在文化遗产研究中,“蜂窝式”结构提醒着我们要注意到民间的经济社会行为,以及每个人都是如何利用文化遗产来开展日常生活的。
(三)三种力量分析法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强调,要重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各自起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的主导作用明显。但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进入新时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高度,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角色[6]137-152。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角色与力量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在文化遗产研究中,同样要注意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不同影响力。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各司其职,社会的参与也必不可少。三种力量分析法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应用,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逻辑,并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四)四维度分析法
新时代,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任务。对于如何实现文化“双创”,许多人会认为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下只能处于对立与融合两个极端状态。但是,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创造性地提出,传统和现代之间除了对立、趋同两种状态以外,还存在并存、联结等中间状态。对立状态主要是指传统文化遗产在面对现代社会时产生的对抗、冲突。趋同状态主要是指传统文化遗产没落,生活方式越来越与现代西方靠拢,同时伴随着对于文化同化的担忧。并存主要是指传统与现代并存而不相害,二者互不干扰,如古建筑与现代设备的同时并存,传统技艺与现代工业的同时并存等。联结则是指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完全隔离,二者可以是连续或连接的。笔者认为,联结状态在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开发过程中居于主流地位。许多景区都在进行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联结、并接,一些节日等文化遗产也呈现出结构未变而功能改变的联结状态[6]158-162。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时,应注重使用“四维度分析法”,关注到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行业在进行融合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状态,以便从整体上把握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三、“新古典学派”与文化遗产研究的五种社会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15]。近年来,在张继焦的不懈努力与推动下,一批研究者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与文化人类学学科视角,从不同的整体性情境,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分析与研究,形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学人类学“三大体系”的重要成果之一。文化遗产的“新古典学派”研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注重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理论依据,大多从整体情境入手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新古典学派”的梳理,有助于总结这些研究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
按照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进行分类,笔者认为目前可将文化遗产“新古典学派”的相关研究,分为对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社会情境下文化遗产的研究。
(一)城市复兴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复兴问题愈发得到人们关注。在城市复兴研究中,由于人们对精神世界追求的增强以及对文化遗产资源属性的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新古典学派”认为,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看似存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但实际上二者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而是互相协调促进的关系。在城市复兴过程中,文化遗产要因时因地制宜,不断生成新功能,促进二者创新融合、协调发展[16]。
许多研究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理论视角,对文化遗产在城市复兴中的作用做出了细致研究。张继焦、邵伟航以北京的烟袋斜街、南锣鼓巷、前门大街三处城市文化中代表市井文化遗产的老街为例,论证了作为“结构遗产”的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困境,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需求下通过内源型发展体现自身价值并以相伴相生的关系实现老街区市井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的共同发展[17]。张继焦、谢圣庚通过对海南省海口市城市文化遗产的考察提出,文化遗产是推动城市复兴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和载体,并从本体结构、外在结构、自生结构进行分析[18]。张继焦、邵伟航在对海南省海口市牌坊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神圣空间”还是“凡俗空间”,牌坊在产生之初都是以实现某种社会功能为特点的专门化空间。而空间专门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也在影响、制约社区成员,并构建出新的社会关系[19]。二人将牌坊放置在城市整体情境中进行研究,充分展现了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城市复兴中很重要的一种类型。在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不同地区、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文化遗产和发展路径,但这些不同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一些共性。张继焦、吴玥以广州、中山小榄、洛阳三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花卉文化为例,将文化遗产置于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分析。二人还借助人类学整体论视野提出,只有将文化遗产放置在城市复兴的脉络下,才能使作为一种结构遗产的花卉文化的“结构-功能”变迁与城市的“传统-现代”转型相协调,实现文化遗产与城市复兴的共赢[20]。邵伟航、张继焦通过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蓬莱“八仙传说”文化遗产的形成和当地文旅产业集群过程的田野调查,提出文化遗产动态变化的过程实则是产业化的过程。文化遗产所自带的能量与社会结构中官方与民间的推动力量,共同造就了历史文化名城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21]。
(二)县域发展
截至2020年,我国县的数量已达1 869个,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此背景下,文化遗产也在县域发展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学界对县域范围内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但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对县域文化遗产的研究应给予适当重视。
雷潮、张继焦以广东信宜玉器产业为例,探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成为当地县域经济振兴的内源性动力。广东信宜对作为产业内源型发展要素的玉器与玉雕工艺进行商业运作,突出其文化功能属性,重塑品牌形象,推动传统产业的结构性改革,形成新的产业发展结构。以玉雕工艺为核心的泛玉器集群产业体系使信宜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信宜的玉器产业成为驱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振兴的动力源[22]。张继焦、郝双玉的研究呈现了化隆牛肉拉面从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的跨越式发展过程,并提出政府与民间都在化隆牛肉拉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23]。
(三)特色小镇
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22%。在城镇化不断高水平发展的今天,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类型应运而生。与开发区等其他类似规模的发展模式相比,特色小镇的发展特点不仅仅是受到产业驱动的现代区域增长,更重要的是将文化的创新和再造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4]。特色小镇之所以能够“特”,正是因为其有独特的文化遗产,文化成为它的重要内核。
“新古典学派”认识到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特色小镇与文化遗产的关系进行分析。李宇军、张继焦认为,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特色小镇与众不同的内源性发展新动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小镇[25]。二人以海南地区特色小镇为例,提出在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表现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结构,更可以在特色小镇建设中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推动资源配置并促进小镇内源型发展[26]。
在以往相关研究中,位于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新古典学派”注意到这一不足,产出了多项研究成果。张继焦、宋丹以我国民族八省区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及自治区级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提出国家级特色小镇以民族或历史文化型和特色产业型为主,自治区级省级特色小镇则以特色产业型、民族或历史文化型和生态旅游型为主。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秀美的自然风光、多样的特色产业、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都是推进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资源,更能彰显出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的特点[27]。张继焦、侯达选取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云南省孟连县娜允镇、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历史文化名镇在“传统-现代”的转型中可以能动地产生新的功能与结构,促进产业融合与文旅融合的发展,并作用于古镇的发展之中。在古镇的发展中,要认清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多种关系,兼顾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28]。
(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对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不同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着各自的路径。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各地人们的关注,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对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分别关注了文化遗产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促进,乡村振兴视野下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不足,文化遗产传承中的角色定位,乡村振兴视野下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对策等。一些研究还对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实例进行分析,提出传统乡村与文化遗产双重振兴发展的实现路径[29]。
在“新古典学派”的系列研究中,杜华君、张继焦以宁夏黄渠桥镇近十年来的文化遗产开发为个案,探讨当地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二人的研究展现了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场域中,文化遗产不仅可形成新结构和新功能,还可由此衍生出竞争优势并带动资源配置和产业集群,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动力[30]。陆霓、张继焦通过对广西隆安、南丹、三江、靖西、苍梧五县的调查研究,展现了当地文化遗产是如何通过在“结构-功能”上的发展进而成功助力当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31]。以上研究展现了在乡村振兴整体情境下,文化遗产如何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文化遗产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结构功能上的变化。
(五)区域社会
区域研究在当下的文化人类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文化人类学研究已不能再将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村落,而是要注意到研究对象与更广泛世界的多重联系,并将研究视野放置在更加广阔的区域之中。许多文化遗产也并非仅仅是某一个狭小地域或者某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更可能是在某个区域内部或在众多民族之间得到共享。文化遗产的“新古典学派”注意到文化遗产在区域中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发展,并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讨。
“新古典学派”对中国许多区域的文化遗产做了丰富细致的研究。作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室,海南岛在中国的区域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新古典学派”对作为文化遗产的海南牌坊、琼剧进行研究,展现这些文化遗产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实功能。张继焦、孙梦华以海南鸡饭、客家酿豆腐、海南老爸茶、海南咖啡、千层糕等饮食文化为主线,展现了中国与东南亚在饮食文化遗产上的双向影响互动[32]。晋商文化是中国特有的区域文化。杨波、张继焦注意到晋商会馆碑刻具有重要的商业文化遗产价值,亟待研究保护[33]。黄孝东、张继焦提出,蒙晋冀长城金三角区域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明清时期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见证。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34]。除此之外,“新古典学派”目前正在对海南岛、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大运河等区域的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从整体情境与外在结构对文化遗产进行全景式、整体性的研究。
四、结 语
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都在关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文化人类学也在不同场合利用多种渠道与自身学科优势,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作出贡献。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学科特征与方法论就是整体观,这恰恰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所需要的。只有把握好文化遗产研究中的整体观,才能从整体上、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分析好、研究好各类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联。
目前,许多学科都在深度参与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研究与开发利用过程之中。但一些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观察描述,缺乏理论分析与深度反思。中国的文化遗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应该利用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基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并对许多领域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这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于分析文化遗产的有效性,对其合理有效地运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新时代保护、研究、传承、发展好中国文化遗产。
目前,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也值得进一步探索。一是尽管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入手对文化遗产进行分析讨论的研究数量众多,但涉及范围仍然较小,许多议题还有待积极探索。对于历史悠久、丰富多样的中华文明而言,“新古典学派”可以做的研究还有很多。二是目前研究大多局限于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分析,对其他地区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较少。对域外文化遗产的研究能够丰富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解释力,也能够增强“新古典学派”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三是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提供的是一个理论框架,在理论上还有很多可以补充、扩展甚至对话的空间。如何立足时代之变与中国实际,完善和发展好新古典理论,也是未来“新古典学派”可以积极探索的重要领域。简而言之,“新古典学派”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化遗产的广阔天地中,新古典理论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