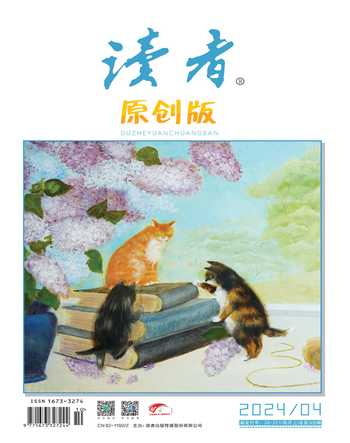女工诗人与一块有点儿野心的矿石
李晓芳

47岁的温馨是攀枝花钢铁集团矿业公司的一名焊工。闲暇时,她会写诗。2024年1月,温馨的18首写矿山的诗刊登在《诗刊》上。
她最初没想过写矿山,潜意识里觉得这个地方枯燥、无聊,迫切想离开这里。然而15年前听从诗友的建议,开始专注写自己在矿山的生活后,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更紧密地和矿山捆绑在了一起。曾经想逃离的矿山成了她身上最大的标签。
把矿山的一切写成诗
四周都是铁皮厂房,堆着氧气管、铁板、钻机零件,黏腻的工业用油洒落在地上,经年累月,角落地板的颜色呈现出一种更浓重的黑。更远一些是灰黄色的山坡,光秃秃的,像是画里模糊的背景,一层叠着一层。
没什么波澜的生活里,工人靠种点儿什么来打发时间。有人种了杧果树,有人种了4棵花椒树。一排稀稀拉拉的小树里,那棵挨着厂房的枇杷树并不引人注目。树将近两米高,枝叶算不上繁茂,周围时常随意堆放着生了锈的铁板和暂时用不到的木材。
某个午后,连着焊了好几块铁板后,温馨站起身,活动僵直的腰背,一转头看到枇杷树居然结出了果实,空气里有甜甜的植物香气。她跑过去,站在树旁一层层堆叠的铁板上,摘下一串果实。果子很小,并不饱满,“但是吃着还是有点儿甜的”。她招呼工友们都来品尝。
她后来把枇杷树写进了诗里:
“厂房里,一棵枇杷树,被一块块铁板/干干净净地掩映/……人生苦短/我应该向一棵枇杷树学习/时不时地给生活一点儿甜头。”

温馨,47岁,是攀枝花钢铁集团矿业公司的一名焊工。她剪着齐刘海,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她准时坐上从家前往采石场的通勤班车;11点从采石场回到厂房,吃午餐、休息;下午1点再根据工作安排继续去采石场维修采矿机,或是留在厂房焊铁板,直到下午5点下班。
每天,同样的工作内容循环往复,这样的日子,她过了25年。
她尽力在生活中靠写诗创造一点儿自己的乐趣。前段时间,她在收拾放氧气罐的棚子时,发现架子生锈、扭曲了,得用切割枪一点点加热,再用铁锤将钢筋一一敲直,最后刷上油漆。干完活,她写了两首诗,取名《修复氧气棚子》:
“一个废弃的棚子/锈蚀爬满了每一根钢筋/绝望的呐喊,是无声的/蔓延着一种孤独与悲凉。”
在夏天的采石场碰到一只螳螂,她也能写成诗:“夏天的矿山可晒了,人都被烫化了,它还在采石场上跳一跳。”在沟渠里制作一个踏板,焊接断裂的轴承,工友满是油污的双手,甚至是随处可见的巴茅草和灰扑扑的矿石,通通被她写进诗里。
攀枝花诗歌协会的诗人朋友、零星一两个读诗的工友对温馨都有类似的评价:只有她能把矿山上的一切写成诗。工友杨波说:“其他工人干活时只会想活没干完,得抓紧;看到周边一块挡路的石头时会一脚踢开。很多人是发现不了这种美的。我们描述不出来的,她都能用细腻又很质朴的语言写出来。”
《诗刊》编辑部副主任聂权同样被那股仿佛要破开矿石跳出来的生命力打动:“诗歌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言志,她写的就是真实的、深刻的那种生活体验。”聂权还记得当时一位诗人向他推荐温馨描写采石场的诗,他看完后迅速做出判断:“肯定能放在《诗刊》上发表。”
他将这些诗转给主编,第二天就收到反馈,要将温馨的一组诗共18首放在《诗刊》醒目的位置上。诗人余秀华、外卖员诗人王计兵,乃至圈子里大大小小数得上名号的诗人,都曾在这个位置被推荐过。
那组诗的开头宣告了一位矿山女工的入场: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正好可以丈量—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唯一的女焊工
这天上午,温馨走进了工人休息室,换下旗袍样式的裙子、高跟短筒靴,穿好宽大、板正、带一点儿粗糙质感的工作服,坐上被油污和粉尘盖得看不出原样的小巴车,一路颠簸到达采石场。
焊枪喷溅着火花,太阳一点点挪到正中,但阳光始终透不下来,粉尘在空中飞扬,笼罩着整座矿山,像是给眼睛套了一层灰蒙蒙的滤镜。二月初的气温已然很高,恍惚有了夏天的感觉。“矿山的夏天让人很难受,(体感)温度有五六十摄氏度。”温馨形容着,汗水流得像一条小溪。但矿上规定工作服和安全帽是绝对不能脱下的,她就往背后塞了一条毛巾,被汗水浸湿后抽出来再换一条。
温馨所在的矿区原来有十几位女工,但近些年工人数量少了将近一半,四个班合并成了两个,女工如今也只剩5位了。她们的工种也不相同,有钳工,也有叉车工,她则是唯一的焊工。
采石场上的工人其实很难分出性别。女工藏在工作服里,藏在安全帽里,藏在诗人的笔下:
“他们抢我的书,手指绕我长发/他们个个趾高气扬,学我语气。
“换上工装,戴好安全帽/纵身一跃,上了值班车,到了山里/我就是矿山的一朵焊花了。”
有一天夜班,她去采石场干活,矿山深处吹过来的风阴沉沉的,还有机器轰隆作响。她捡了两块石头,一边走一边敲,发出声音给自己壮胆。回到家已经凌晨2点了,她开始写作:
“前面是矿石,后面是矿石/漆黑的采场,一只脚陷下去,另一只脚跟着陷下去。”
休息时,温馨会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并匆匆记下脑中的想法,“切割时画的一个圈”“厂房里的橡胶”。笔记本上,她积累了180多个或长或短的灵感,中间偶尔夹杂一些生活琐事的提醒,比如补种睫毛的日期。
中午的休息时间,她在休息室琢磨刚记录下的灵感。休息室很简陋,两排储物柜,两张长椅,唯一的一张小木桌横放着,上面堆满了安全帽、水杯、手套。其他人在刷手机、打瞌睡,温馨则弓着背在这张桌上读诗、写诗。窗外还是连绵的山坡,时不时传来采矿运输车驶过的轰隆声。
“生活是个漏洞”
温馨起初没想过写矿山。
没工作前,她和姐姐上过采石场一次,去探望父亲。当时的记忆不算美好,“我看到父亲的工作服上全是油,有的凝结成块,能直接掉到地上。这边天气不好,粉尘也大,夏天很热”。
她说自己就喜欢做两件事:买好看衣服,买好书。上学时,她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读《简·爱》,幻想自己也能写一个故事。她还没想好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反正得先上大学。然而,人生突然在某一天拐了弯。爸爸告诉她,供哥哥姐姐上大学已经让这个家负债累累,实在无力供第三个孩子上学了。
温馨哭了又哭,但没有别的办法,她还是听从父亲的建议,进了攀钢,从一名焊工学徒做起。当了3年学徒,手上被烫过数不清的水泡,眼睛10天里有9天肿着……她终于出师了。
可是如深潭般寂静的生活依旧需要找点儿寄托,“我必须做点儿什么”。2008年,她开始写随笔。之后,她把自己写的随笔发在网上,收获了不少鼓励和赞扬。攀枝花当地的诗友鼓励她尝试诗歌创作,并邀请她参加线下的聚会。因此她认识了越来越多写诗的同好,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该写什么内容?”
诗友建议她就写采石场,那是她体验最深也最难被其他人代替的部分。“其他诗人不会比她更了解一线工人的生活。”一位攀枝花的诗友说。
温馨觉得这是个好建议。在采石场上干活,或者碰到一点儿新奇的事物,比如厂房的向日葵开了,她都会第一时间思考能不能将其写进诗里。她所在的矿区从铁矿产量来说是一座贫矿,但在过去的15年间,这座贫矿为一位诗人提供了最丰富的创作养料。
温馨记录下工人戴着安全帽,大汗淋漓地吃午饭的场景:
“盒饭里/滴下的机油是作料,落下的粉尘是作料,流下的汗水/也是作料。”
也写下一幅幅矿山工人的“素描”:
“如果需要画像,只能用素描,用尽所有矿石的色彩/脸膛要黑,眼睛要亮,眉心要皱……手上提着的扳手要多,背上扛着的大锤要重……”
诗是她最可靠的伙伴。她说:“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一些话和心情,我都写进诗里。”
“一块不合格的石头”
温馨在诗里把自己比作一块矿石,一块不合格的石头,因为“风一吹,小野心就动一下”。
起初写诗时,有工友打趣道:“瞎折腾什么,老老实实上班就行了。”她笑着说:“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写诗也确实给她带来了一些改变。2018年,她的作品入選四川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之后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2024年1月,采石场组诗在《诗刊》刊登后,陆续有媒体前来采访她;《诗刊》编辑部为她组织了一场直播活动,她很紧张,连着几天都在念叨没怎么参加过公开活动,担心说错话,更怕观众听不懂自己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诗人朋友叮嘱她:“你要保持一种清澈的产业工人状态,更重要的还是要立足一线,将攀枝花、攀钢还有工人的真实生活都宣传出去。”
温馨连连点头:“要得嘛,我取得的成绩离不开采石场。”她如今是攀枝花文学圈里的红人,也是攀钢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前几年,她在诗里写自己的变化:
“刨开表面上的粗粝/矿石内部,柔软,仿佛我的心/被命运不断改写,而变得淡然、温顺。”

如今,她积极融入矿山,她并不排斥“矿场诗人”“女工诗人”一类的称号。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现在身上最大的标签。
聂权对她有更高的期待,并不希望她被困在标签里。聂权注意到许多被关注的草根诗人会落入一个循环怪圈。“因为引起关注的是写自己劳动生活的诗,他们就会不断重复地写劳动生活。”聂权语气恳切地说,“那次直播我就提醒她,别拘泥于自己采石场女工的身份,我希望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采石场只是她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温馨还没想过更遥远的事。儿子今年要高考了,下班后,她还得去打印店取厚厚一沓习题、试卷。她希望儿子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梦想就去实现,去努力”。
她依旧认为自己是一块普通的矿石,只不过是偶然得了一些机会,能敲出一点儿声音,让更多人知道整个矿山。
那条通往采场的路
温馨
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
路,分明是活的
一个胸中有路的人,才能阔步向前
才能在转身之间,瞥见命运的正反面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
工友说我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
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正好可以丈量
—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极昼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