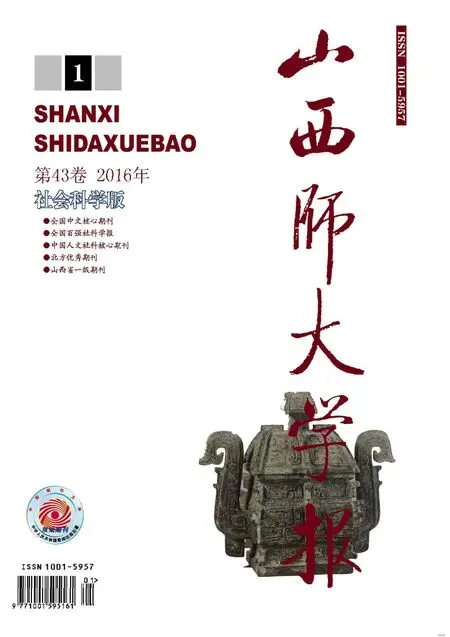民族文化“扎染式”认同的内涵及实践路径
田 夏 彪
(大理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民族文化既要积极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经济、科技上不断追赶主流文化之步伐,又能保持自我之个性,实现其“开放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发展。因此,民族文化有必要践行“扎染式”认同之道,以主流文化或他文化为“染缸”,通过与之“交往浸染”形成以主流文化为背景且“民族文化个性”凸显其上的“民族文化艺术品”,从而促进民族文化多元和谐、与时俱进地发展。
一、当前民族文化“扎染式”认同构建的必要性
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与他文化的交往比较,在不断“放大自我与缩小自我”的“拉锯”之后,以确立起自我在多元世界中的位置。可现实中民族文化发展却缺乏真正的“认同”,并未坚守“自我的同一性”,以致变为一种满足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使民族文化之价值远离了人们的心灵。
(一)民族文化认同思维的“谄媚与谩骂”
民族文化认同思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它在价值意识上厘清民族文化发展的“去留”和“走向”问题,包括两大层面:其一是明了所要“认同”之民族文化和他文化“是什么”,并对其进行事实性描述与比较,进而判断双方之“殊异差别”;其二是权衡民族文化的“内忧外患”和“自立自强”问题,通过交往、借鉴、吸收、改进而发展自我,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防“外患”之“侵蚀”,消“内忧”之“不足”,实现相互之间“取长补短”的“共谐”局面。总之,民族文化认同只有确立起辩证统一的思维,方能促进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的和谐发展,而不是在“不知道自己是谁”和“知道自己不是谁”的“忧郁与幻灭”中走向两极,或表现出对“现代化、主流文化”的无尽“崇拜”,不假思索地使自我“脱胎换骨”而被淹没于无形;或表现出“受害之状”而“力鸣不平”以“博得怜爱”。毋庸讳言,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思维处于非自觉状态,人们常常呈现出“谄媚与谩骂”的思维心理,“谄媚者”往往视主流文化为“天堂”,为进入“天堂”可以“不顾一切”地“改造、牺牲”自我,以“扭曲或伪化”本民族文化“生命”为代价去换取“现代化生活”,这似乎成了当下人“不容置疑”的真理,为实现这一“宗旨”可以将“文化”当成手段去换取“物质财富”,“经济、名利”被人们视为主宰一切的“上帝”,出现了民族文化发展“本末倒置”的状况。“谩骂者”则内卷于自我民族文化内部,对“他文化”持有一种“嘲笑、讽刺、拒斥”的心理,常常以一种“自大”的心态和“盲目”的举动来“美化”自我和“丑化”他人,往往通过“应付”或“窃笑”的方式与“他文化”展开交往,或以己为中心让“他文化”为我服务,于己有利则对之“笑逐颜开”,反之则“冷眼视之”。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思维存在着两个极端:其一是对“现代化、权力、名利”充满了“信任和向往”,以致到了“偏执”的程度,得者喜之,失者忧之;其二是对“他文化”缺乏信任与尊重,充满了“戾气”去审视“他文化”,却无“认识反省自我”之思维自觉。
(二)民族文化认同实践的“盲从与逐利”
民族文化认同思维是内隐的,它作用于外显的民族文化认同实践。与民族文化认同思维的“谄媚与谩骂”相对应,当下民族文化认同实践则存在着“盲从与逐利”的倾向,二者之间“遥相呼应”,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思维的“谄媚与谩骂”和人们对经济利益追逐的功利目的不无关系。只要能实现物质经济收入的增多,民族文化如何发展对社会成员而言“无所谓”,即使民族文化“个性”消失殆尽也在所不惜,甚至只要有“利益甜头”就算践踏“法律和道德”底线也无不可。可以说,当前民族文化已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无名小子”,相反它们或争先恐后地去寻找“商机”,尽可能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演出成功,以博得“名利双收”的效果;或被动地跟随着他人进行“文化建设或改革”,这也成为当下的一种世风,似乎各地民族文化都朝着“高大上、绝无仅有”的模式去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只有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或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才能借助于“旅游消费”来更多地获得经济回报,实现“旅游创收”的目的。总之,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是“有意识而无自觉”地展演,所谓的“有意识”是人们都认定一个普遍性的目标即“金钱获取”,想尽办法将自身民族文化“商品化”,不断通过对民族文化加以“精细化包装修剪”而博得人们“眼球”的认可;所谓“精细化”则意味着要把自我“最独特”的东西呈现给别人,问题在于民族文化之“最独特”常常是“包装之下的最独特”,或者为了“最独特而最独特”,结果使得不少民族文化内容“伪化”了。[1]不可否认,民族文化认同实践的“盲从与逐利”虽然使得民族文化“活动起来”被人们所关注,但民族社会成员在“争先恐后、你争我抢”式地让民族文化“现代化”起来的同时,也使得民族文化发展不断“迷失”了方向而难以“知返”,诸如人们在经济增长的角逐中导致“乡情”的荒漠化,人和人之间缺乏了互信、文化与文化之间减少了相互的“尊重”,民族社会成员生活中存有或增多的是房屋建设的“豪宅化”,礼俗活动的“奢靡化”,日常用品的“品牌化”。民族文化看似“热闹非凡、活动多多”,可都是些“集体娱乐狂欢”,并非扎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且渗透着价值思维的文化肌体。
(三)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漠视与虚化”
民族文化认同思维与实践之间是“内隐与外显”的关系,一个是价值心理,一个是行为动作,二者之间在目的上保持一致性,也即现实中人们将民族文化当作一种手段来实现经济获利的目的,为此目的可以放弃民族文化自身的“身份或个性”。无疑,当前民族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远离了人们的价值世界,这是当下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危机。往昔与人们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化已经不再支撑着社会成员的心理世界,其精神、信仰处于空虚和空洞状态,而于此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却“无所作为”,并未有效承担起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着当前民族文化认同的异化,并通过“有意无意”的教育实践强化了这种结果。所谓的“有意”是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教育系统走的是“应试之路”,围绕着升学考试课程进行各种“训练”,而与升学考试无关的“民族文化”则不断被“排挤在外”。一方面“民族文化”在学校课程设置、教学实践中处于次要地位或是其就没有成为“教育设计”的组成部分,即使有也会随时被“考试课程及教学”所占用;另一方面是“民族文化”虽然进入了学校教育教学视野,但更多是被当成“点缀”或“娱乐”而存在,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减缓“高度紧张的应试”的调节剂而已。所谓的“无意”是校外民族文化教育的“空缺”,它被“权力驱使”下的“文化工程”所取代,由“民间组织、艺人、风俗”文化结构所组成的“活”的教育生态系统所破坏。在纵向上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出现传承人的“断代”,这不仅仅反映的是一个“民族文化内容”的“消亡”,而是作为未来社会主人的年轻一代逐渐对“民族文化”的抛弃和不认同;在横向上民族传统文化事项处于“保护中的颓废和消逝”的处境,随着所谓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繁琐、沉重”的各种传统文化内容被“缩减”或“删除”,民族文化似乎只剩下能供人们“娱乐狂欢”的部分,虽激起的是人们的“狂热”,浇灭的却是人们的“精神”。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漠视与虚化”的,这不在于以“民族文化”为名的教育活动之多寡,而是人们对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重要性和意义的信仰缺失,这才是最大的危机所在。
二、民族文化“扎染式”认同的内涵
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为了促使其融入时代且能保持自我特色,有必要从思维、实践及教育层面确立起“扎染式”民族文化认同之道,确保民族文化个性在“浸染”了全球化、现代化“染缸”之后能“跃然于上或脱颖而出”,以确立自己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一)融入时代发展潮流,加快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不可否认,当前不少民族地区依然面临着贫困问题,而且社会贫富差距呈拉大趋势,这无疑给民族文化认同提出了一个难题。一方面要加快物质经济发展水平,让民族地区社会成员逐渐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化发展更重要的是人们要具备现代化的文明素质,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是摆在民族文化认同面前的重要任务。无需赘言,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因子不断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都不会也不可能封闭起来,社会成员至少在思想意识上都是“向外开放”的。因此,当前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现代化发展”是必要和必须的,只有解决了民族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资生活需求,才能不断提升其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加强其现代化文明素质,让他们拥有开放的眼光和责任意识。所谓的“开放眼光”是指民族文化无法回避“与时俱进”的趋势,不可能拒绝现代化发展而“自我封闭”,所以当下一些人对现代化进程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的破坏之指责并非完全“中肯”,毕竟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社会成员有着和他人一样的“共同人性”。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现代化存在着使“人性”中物欲膨胀的可能性,但这并非现代化自身的错误,如同有了汽车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但可能存在着交通事故隐患是一个道理。尤其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而言,通过增加经济收入改善居住环境、医疗健康、交通设施、生产方式是必要的,因而对民族社会成员而言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吸收现代科学文明来提高生活水平,在满足了低层次需要之后去追逐“归属、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而所谓的“责任意识”是在面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及社会成员不仅仅是“自利”的,还需要考虑“人生意义”的问题,对本民族文化及其濡染于人们心灵中的“精神信仰”进行存养,而这种存养离不开民族社会成员的“内省自觉”,借助于对现代化优秀文明成果的吸取和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真正实现民族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
(二) 注重核心价值观培育,积极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素养。民族社会成员的生活只有现代化起来,让其过上“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生活,才有心思去考虑“价值意义”问题,但必须看到现代化发展所带给人们的负面冲击,由“资本、金钱、名利”等所构成的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吞噬了民族社会成员的生命世界,人们不加反思地去追逐“过剩”的物质。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民族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价值信念,确立起良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让人们认识到作为手段或工具的物资财富是服务于生命生活的,而不是以“一身为代价”来将物质财富当成目的去追逐。并且,民族文化认同是在交往中发展的,民族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了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交往双方才能对所存在的“分歧”有所“保留”,这样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步伐才有方向和尺度,而不至于丧失自我“个性”。总之,民族文化认同不是“同化”,也不是“特殊”,而是一种“发展”,一种让人能够“找到自我”的发展,其前提是民族社会成员能够具备现代公民素质,成为一个自立自决的主体。基于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有必要着重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让“进取、合作、责任、多元、个性”等现代化精神品质在民族文化中孕育生长,让民族社会成员真正成为有着“全球意识、地方性行动”的社会公民。
(三)夯实制度法治建设根基,不断推动社会道德文明生长。民族文化“扎染式”认同是一种理念和应然理想,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众所周知,人性是善恶交织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人人都是恶的,但是只要有人为恶,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惩处,如此才能保证人们交往的秩序化。同理,民族文化认同也应在文化交往中有着基本的原则,而且这种原则更多应该是对人性“贪婪、欺诈”等行为的限制。如果说食品、建筑行业的“假冒伪劣”会危及人的身体健康,那么民族文化产品的“虚假”则危害着人们的心灵健康,而且这种危害往往是在“欢快赚钱”的感觉中完成的,往往会麻痹人们的神经。因此,为避免民族文化发展遭遇商品经济冲刷的“异化”,有必要采取“双管齐下”的治理办法,一方面通过夯实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法治建设,使其能够利用公平、透明、诚信的“市场环境”来发展自我,杜绝当前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中“伪文化产品盛行”的现状,让民族文化认同回归“正途”;另一方面将“理解、关爱、尊重”等品质内化在自我的行为实践中。换言之,民族文化认同不仅仅在于“认同什么”,更为重要的是认同中的反省。无论这种反省是针对自我民族文化还是他文化,其共同的特点是使人性中“善”的品性得以充盈。总之,民族文化认同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人之外的实体或对象,而是融入在人们具体生命生活中的,它需要在法治秩序和内心自觉的日常化中来展开。只有如此才能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真正使得“扎染式”文化认同生根。
三、民族文化“扎染式”认同的实践路径
(一)着眼于主体,构建以人为本的教育结构体系。文化认同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文化之“认同”,而非仅指向于所认同的“文化”,也即文化认同是主体之精神、价值、态度之映射,显现为社会成员具体的文化实践。换言之,有着怎样的文化认同实践表现,其背后则会存在着怎样的思维心理。因此,民族文化认同要得以良性发展,其关键在于民族文化认同之主体须确立起合理的“文化认同观”,在意识和行动上取得统一。民族文化认同需要积极加以培育,最重要的是要让民族文化认同主体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在思想意识上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开放性与民族性。众所周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他所要培养的是一个身心健全的生命主体,是一个具有反思和行动能力的个体,能够恰切处理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真正在多元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作为民族文化发展主位因素的民族文化认同,其主体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研究者、政府机构、文化旅游机构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而是所有人的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风气环境,而这种风气环境离不开教育“化民成俗”的作用。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着眼于全体社会成员,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形成一种自觉意识,能够辩证地处理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构建起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体系,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社会成员都能受到教育的引导,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取向和行为实践。
(二)着重于品质,构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时空。随着人们物质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却呈单调或低迷之态。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很多社会成员的业余文化生活集中于广场舞或打麻将活动上,我们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但似乎不足以成为支撑人的生命意义提升的文化内容,尤其渗透于城市和乡间的“黄赌毒”日益侵蚀人们的心灵,加之贪腐、物欲、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得真正叩问人的“灵魂”、激发人的“德性”的文化生活不被人们所“信从”。因此,为了改变民族文化认同实践的“颓废”之态,树立起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平等、公正、诚信、友善、敬业”等核心价值[2],有必要创设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时空,一方面加大投入建设公共文化活动机构或场所,包括图书馆、健身中心、文艺排练演出场所空间,让人们有选择地从事学习或接受教育,改变当前众多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公共生活空间不断缩小、文化活动单调的状况;另一方面,对体现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内容加以保护、传承、创新,对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化内容进行组织设计,让民族社会成员能够在文化生活中提升人的品质。总之,只有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构建起丰富多元健康的文化生活时空,才能逐渐使人们在参与各种文体活动中陶冶、培育“真善美”之品质。
(三)着手于当下,构筑“上下结合”的改革合力。为了不再让民族文化发展恶化下去,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直接承载者之间应形成互促关系。其一是民族文化生态离不开民族社会成员的有意识传承,不宜让各种民族文化内容或事项在现代化浪潮中日益消逝,甚至是人为的一种放弃。当前城镇化进程席卷着中国大地,农村地区或民族地区日益加快了经济发展步伐,不少社会成员纷纷外出打工以增加经济收入,但不容忽视的是随之出现了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断代现象。这一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外流的同时,既使得传统文化活动缺少了组织者,也不断引致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漠视。所以,民族文化在追随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同时,有必要让民族社会成员能够自觉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具有的精神意义,主动将传统文化生活保留下来,在建筑、人生礼俗、公共空间等方面要凸显传统文化特色,而非完全的“现代化”。其二是政府部门、民族文化研究者理应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筹谋划策,本着服务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旨来制定政策理论和凝聚共识,真正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将重心转移到民族文化建设上来,通过构筑起“上下结合”的合力作用,让所有社会成员和多方社会力量共同促进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
[1] 田夏彪.“事物化”与“特质化”:民族文化认同思维误区[J].贵州民族研究,2014,(11).
[2] 段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实践[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