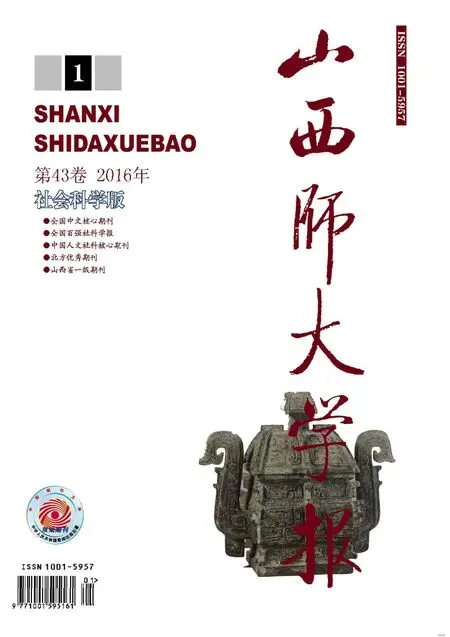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无字说”、“极微说”探究
韦 强
(四川大学 文新学院,成都 610065)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评点大家,金圣叹对于小说、戏曲的评点突破了明代以往碎片式、感悟式的批注式评论,从而具有了宏观的理论概括高度。金圣叹往往在作品的每个段落之前设置总评,全面、完整的论述自己的文论。在其评点中,往往融入其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极富理论性和哲学性。这种理论性和哲学性,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极大的丰富和提升,但是也为后人的理解和阐释带来了难度。因此,在金圣叹的文论思想中,虽然有的文论思想影响极大,但却不能使后人真正理解。金圣叹评点《西厢记》提出的“无字说”和“极微说”,就属于这样的文论思想。二者拥有密切关联,互为观照。这两种思想都源自于金圣叹对佛教的吸收,但又并非是谈论佛法。它们虽然源于佛教,但已被金圣叹融入到自己对于文章的理解和指导之中。正如谭帆先生所说,金圣叹的评点“是他的内在情感和人生理想在艺术批评中的延伸”[1]16。所以对于这两个文论思想的理解,脱离佛教不行,而单纯的以佛教观念理解亦不行。
一、“无字说”之探究
“无字说”是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读法中提出的。金批《西厢记》的读法,是金圣叹对于《西厢记》的总体评论和宏观解读,所以其评点并不像传统评点那样紧紧附在文本上,而是可以独立成文,具有序言的性质。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读法,共八十一条,“无字说”是其中的第二十七条至四十三条以及四十六条,其精华摘录于下:
横直波点聚谓之字,字相连谓之句,句相杂谓之章。儿子五六岁了,必须叫其识字。识得字了,必须教其连字为句。连得五六七字为句了,必须教其布句为章。布句为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为一章,次教其布十来多句为一章;布得十来多句为一章时,又反教其只布四句为一章,三句为一章二句乃至一句为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为一章时,然后与他《西厢记》读。
子弟读《西厢记》后,忽解得三个字亦能为一章,二个字亦能为一章,一个字亦能为一章,无字亦能为一章。
《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赵州和尚,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是此一“无”字。
圣叹举赵州“无”字说《西厢记》,此真是《西厢记》之真才实学,不是禅语,不是有无之“无”字。须知赵州和尚“无”字,先不是禅语,先不是有无之“无”字,这是赵州和尚之真才实学。[2]860—862
这一段金圣叹引用佛教著名公案“赵州和尚论狗子佛性是无”的论述,历来令研究者难解。赵州和尚是唐末著名禅僧,此段公案出于《五灯会元》。净慧法师说:“千百年来,所有参禅的人,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无’字来寻找自己生命的源头。”[3]325足见其在佛学领域的影响。但是此公案的“无”字历来玄妙难解,而金圣叹引此公案阐读《西厢记》,对“无”的论述同样非常玄妙。很多学者试图用纯粹的佛教公案的方法来解读,这其实忽略了金圣叹自己所说他并不是说“禅语”。诚然,金圣叹本人深受佛教影响,也写过大量关于佛学的论著,所以其在评点之中融入佛学思想,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此处,他却明白地说明,他引用公案并非“禅语”,而是为了阐述《西厢记》的“真才实学”。所以,我们就应该跳出公案和佛学的圈子进行解读,探讨金圣叹所言的“真才实学”。那么,《西厢记》的“真才实学”又是什么呢?
中国有一句俗语:“读书先越读越厚,然后越读越薄。”意指读书初期生疏难懂,需要仔细和积累,等到熟读之后,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即可把握书中精华。金圣叹此处论文之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金圣叹特别提到,习文初期,需要一字、一句、一章的积累,这是一个由浅到深、由生到熟的必然过程。此时,由于文法生疏,需要利用很多的字句才能表达词意,故而圣叹说:“布句为章者,先教其布五六七句为一章,次教其布十来多句为一章。”然而等到文法越发熟练之时,即可用越来越少的字句表达词意,金圣叹认为此时既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水准,所以可以读《西厢记》了,“布得十来多句为一章时,又反教其只布四句为一章,三句为一章二句乃至一句为一章。直到解得布一句为一章时,然后与他《西厢记》读”。
之后金圣叹所提到的各种“无”,就是指随着文法的愈发提升,所需要的字句越来越少,最终达到“无”——即一个字都不需要了。现实创作之中,当然不可能一字不写,金圣叹此处只是强调一种最高的境界,就和中国武术强调的最高境界“以无招胜有招”一样。正如朱熹所言:“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斗糜也;欲其融会贯通,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4]273所以,无论是“《西厢记》只是一章、一字”或者干脆是“无”字,其表达的意义,都与字数多少、章句长短和其赋予的内涵并不是正比关系的。高手为之,既可以用非常简短的字句表达最充分的内涵,也可以在简短的字句中包含丰富的意义,达到“说到至约之地”的境界。所以,很多需要一章表现的内容,高手可以以一句、一字表现,这就是“一章即一句”或“一句即一字”。所以圣叹的“无字说”,归根结底就是以最少最精炼的字数,表达最充分、最丰富的内涵和内容。在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具体评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金批《西厢记》的“赖婚”一出,金圣叹评莺莺“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一句:“‘识人多’措辞妙绝。便以吾张解元为宰相不愧耳。看他只三字,岂复三百字、三千字、三万字所得换哉。”[2]967正是因为“识人多”三个字,完美地表现了张生在普救寺解围中的功劳和莺莺对张生的爱慕,所以虽然只有三个字,却表现了三百字、三千字都未必能表现的内容和含义,因此获得圣叹盛赞。
“赖简”中,评张生“是槐影风摇暮鸦,是玉人帽侧乌纱”云:“槐影乌纱,写张生来,却作两句;只写两句,却有三事。何谓三事?红娘吃惊,一也;张生胆怯,二也;月色迷离,三也。妙绝妙绝!”[2]1021张生此唱词只有两句话,但是圣叹认为它却包含了红娘吃惊、张生胆怯、月色迷离三个内涵,故而圣叹惊叹妙绝。
同样是在这一出,张生久等双文时胡思乱想,唱道:“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圣叹评:“搔爬不着,横躺在床,胡思乱想,急写不尽。看其轻轻只写一句云‘我欲改过’,却不觉无数胡思乱想,早已不写都尽也。”[2]1045“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九个字,把张生各种焦急难耐、胡思乱想统统表现了出来。而且它所包含的内涵,不仅仅是张生久等之后的焦急,而且还隐藏了张生早已苦等多时的内涵。而庸者可能用九十字、九百字都不能写出张生的久等焦虑之情,更不可能表现出张生早已久等的状态和内涵。
“拷艳”中,以红娘“相思事,一笔勾,早则展放从前眉儿皱,密爱幽欢恰动头。谁能够!”的唱词来诉说双文张生恋情的合法性,对于这一句,圣叹评:“只三个字,便抵一大篇《感士不遇赋》。”“只三个字作一篇,却动人无限感慨。”《感士不遇赋》乃是陶渊明所作,充满了激愤不平的感慨。金圣叹此处意指红娘“谁能够”三个字所带给读者的心灵和情感的触动,就如同读了《感士不遇赋》一样。虽然二者具体针对的情感体验并不相同,但二者所能引起的情感震动则是相同的。所以圣叹认为,“不能够”三个字所达到的情感震撼的效果,和《感士不遇赋》一样。而能够用很少的字数表达更为丰富和充分的内涵,无疑意味着其文章水平很高。
可见,金圣叹的“无字说”不是无字,而是可以用最合理、简短、精辟的文字表达最充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可以把作者希望表达的情感、内涵用简约之笔表达充分、完整、彻底,还可以用简短的词句表达多层含义以丰富内涵,同时还能够给予读者深刻的审美体验、情感震动和回想空间,这可以说是作文的最高境界之一。所以,“无字说”看似玄妙,但是如果能够理解金圣叹对文字精炼的追求,那么对于“无字说”的理解就可以在纯粹的文论之中进行,而不必单纯的落入宗教、哲学的漩涡。
二、“极微说”之考释
除了“无字说”,金批《西厢记》中另一影响极大而又难解的文论理念是“极微说”。“极微说”与“无字说”虽然是两个理论,但其实相成于一个体系之中。它们都反映了金圣叹大小辩证转化的哲学思想。
金圣叹是在“酬韵”的总评中提出“极微说”的,“极微说”也是金圣叹从佛学中得到的启发,他说:“曼殊室利菩萨好论极微,昔者圣叹闻之而甚乐焉。夫娑婆世界,大至无量由延,而其故乃起于极微。以至娑婆世界中间之一切所有,其故无不一一起于极微。”[2]917极微的梵语为Paramanu,意指物质可分解的最小单位。《楞严经》有云:“汝观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至邻虚尘,析彼极微。”[5]69“极微说”是金批《西厢记》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人谓圣叹的评点‘字字有情思’,即从此极微来”[6]204。对于“极微说”,历来解读极多,异彩纷呈。如徐懋庸就认为“极微说”的启示是写作应“从细微处多加留意”[7]188。那么,金圣叹所指“极微”到底何意呢?我们以为,极微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它意在表明,即便外在看来宏大的物象,从其内部看来,却都有自己最为微小的部分;而最微小的事物,如果从内部看,也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大。所以,无论事物大小,都可以无限细分,寻找事物最细小的元素;也可以无限扩大,对事物不断进行丰富。这并非是唯心主义,而是观察的角度有内外之异。金圣叹以云、花等物举例:
秋云之鳞鳞,其细若縠者,縠以有无相间成文。……人自下望之,去云不知几十百里,则见其鳞鳞者,其间不必曾至于寸。……今自下望之而其妙至是,此其一鳞之与一鳞,其间则有无限层折,如相委焉,如相属焉。所谓极微,于是乎存,不可以不察也。
草木之花,于跗萼中展而成瓣,人曰凡若干瓣,斯一花矣。……人自视之,一瓣之大,如指顶耳;自花计焉,乌知其道里,不且有越陌度阡之远也。人自视之,初开至今,如眴眼耳,自花计焉,乌知其 寿命,不且有累生积劫之久也。此一极微,不可以不察也。[2]917—919
金圣叹认为,人从地上望云,云朵之间的波纹、褶皱很大,但是如果从云的内部看,其波纹则会无限细分下去;人从外部看花,是由花瓣构成的花朵,但是从花的内部看,一样可以从花瓣、跗萼、花的根部无限细分下去。所以万事万物,无论大小,其内部都有最为细小、细密的部分和元素。金圣叹因此认为,文章也有最小的部分:
人诚推此心也以往,则操笔而书乡党馈壶浆之一辞,必有文也;书人妇姑勃溪之一声,必有文也;书途之人一揖遂别,必有文也。何也?其间皆有极微。[2]9919
可见在圣叹看来,即便送饭、吵架、道别这样的寻常普通之事,也必然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因为从外部看,这些事情并无稀奇之处,但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每件事情都可以从最细微的部分出发,进行不断详细、全面、扩大的写作。而对于《西厢记》,金圣叹认为“酬韵”一出就是“极微”之法的运用:
上文《借厢》一章,凡张生所欲说者,皆已说尽。下文《闹斋》章,凡张生所未说者,至此后方才得说。今忽将于如是中间写隔墙酬韵,亦必欲洋洋自为一章。斯其笔拳墨渴,真乃虽有巧媳,不可以无米煮粥者也。忽然想到张、莺联诗,是夜则为何二人悉在月中露下,因凭空造出每夜烧香一段事,而于看烧香上,生情布景,别出异样花样。[2]919
圣叹认为,按照情节的正常发展,张生在借完房间之后,可以直接在道场之时和莺莺相遇,在一般人看来,其间并没有必要的情节连接。然而《西厢记》却在中间插入“酬韵”一出,就是从极微之中作文章。
按照普通模式,才子首先瞥见佳人,一见钟情,然后借了一间临近佳人的房间,准备接近。下一步,就是才子佳人见面了,中间并没有需要额外书写的情节。然而《西厢记》并没有安排才子佳人立即见面,而是又安插了二人赋诗联对的情节。正是在看似无可书写的情节里,根据情节发展的合理逻辑,又横空造出一篇精彩的文章,因此圣叹认为这是“极微”之法的巧妙运用。
而在“请宴”的总评中,圣叹以游玩之论譬喻作文之论,认为无论是游玩还是作文,不仅要关注宏大的景象和内容,还要关注细微的景象和内容。如世间游玩之人,往往赶往于各种海山方岳、洞天福地之间,以为只有这些才是游玩的妙处,然而在圣叹看来,这都是不懂游玩之法。圣叹认为真正懂得游玩的人是: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忽然结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骇目惊心之事,不必有道也。然吾每每谛视天地之间随分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则初未有不费彼造化者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而得成者也。[2]954,955
圣叹认为,无论是宏大、壮观的洞天福地,还是微小、精致的花鸟树木,都是造化而成,因此都有其自身的美妙之处,所以“世间之所谓骇目惊心之事,固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有此,亦为信然也”。“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未到于后之中间三二十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耶。一略彴小桥,一槎枒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圣叹所谓“当其无”,语出《道德经》,老子认为车轮、器皿、房室的有用之处不仅在于木条、陶土、门窗,更在于“无”,即它们所构成的“空”的部分。空的部分看似没用,却恰恰是最大的用处所在。金圣叹把洞天福地比作木条、陶土等,而把洞天福地之间的各种微小景物比作“无”,认为它们虽然不如洞天福地壮大、显眼,但绝不得忽视。
根据此法,圣叹又套用到作文之法,他以“请宴”一出为例,云:
前文一大篇,破贼也;后文一大篇,赖婚也。……今此,则于破贼之后,赖婚之前矣,此际其安得又有一大篇也乎?
千不得已,万不得已,算出赖婚必设宴,设宴必登请,而因于两大篇中间,忽然闲闲写出一红娘请宴。亦不于张生口中,亦不于莺莺口中,只闲闲于闲人口中,恰将彼一双两好之无限浮浮热热、脉脉荡荡、不觉两边都尽。[2]957
圣叹认为,破贼解围和夫人赖婚都属于“洞天福地”级别的宏大情节,是构成《西厢记》故事发展的高潮情节。但是为了赖婚,夫人必须请张生赴宴,因此必须有请宴的情节,而且这个情节不能一抹而过,因为为了充分表现张生和莺莺在赖婚后的痛苦,必须先把二人的相思相爱之情表现充分。所以,在破贼之后,请宴之前,需要插入张生对莺莺的进一步相思,以及莺莺对张生的爱慕。这个情节较之破贼和赖婚,较为平淡,属于“草木鱼虫”,但是金圣叹认为它不仅不能忽视,而且亦有非常值得品味的妙处。因为只有把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爱慕表现得越充分,才能反衬出二人在赖婚之后的痛苦。所以,一般人看来,在破贼和赖婚之中,本无情节可过多渲染,然而圣叹却从中发现重要情节可以挖掘。
金圣叹的观念里,“极微”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前候”总评中他还提到“至微”,亦是“极微”之意:“文章之事关乎至微,其必有人骤闻之而极大不然,殆于久之而多察于笔墨之间,而又不觉其冥遇而失笑也。”而在“前候”总评里,金圣叹还提出“那辗”说,亦属于其“极微”观念的延伸。“那辗”最初是金圣叹的朋友陈豫叔在讨论一种叫做“双陆”的博弈游戏时谈到的:
今夫天下一切小技,不独双陆为然,凡属高手,无不用此法已,曰“那辗”。“那”之为言“搓那”,“辗”之为言“辗开”也。……所贵于那辗者,那辗则气平,气平则心细,心细则眼到。[2]988,989
陈豫叔所谓的“那辗”,就是用细微、细致、细腻的眼光分析解剖事物。这个观点和圣叹的“极微说”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表明,任何微小的事物,如果以“至微”的眼光看,都可以进而进行无限细分,从而把握事物最微小的部分。圣叹将此理论引入论文:
凡作文必有题,题也者,文之所由以出也。……吾由今以思,而后深信那辗之为功是惟不小。何则?夫题有以一字为之,有以三五六七乃至数十百字为之。今都不论其字少之与字多,而总之题则有其前,则有其后,则有其中间。抑不宁惟是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后之后。且有其前之后,而尚非中间,而犹为中间之前;且有其后之前,而既非中间,而已为中间之后: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2]989,990
圣叹认为题目和所有事物一样,有宏大的,也有微小的。有的题目字数多,有的题目字数少。但是圣叹认为,无论字数多或少,如果能够根据题目,把与题目相关的元素和材料充分挖掘,那么无论题目长短,都可以作出优秀的文字。有的人面对微小的题目便言尽而词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充分挖掘和利用题目的能力。而优秀的作者则可以针对不同的题目,发现题目相关的素材,挖掘题目的深度,进行各种细分和扩展。他进而以《西厢记》“前候”为例:
此篇如【点绛唇】、【混江龙】详叙前事,此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不叙前事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详叙前事也。;【油葫芦】双写两人一样相思,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不双写相思也,而今已如更不可不双写相思也。【村里迓鼓】不便敲门,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即便敲门也。【上马娇】不肯传去,此又一那辗法也,甚可以便与传去也。【胜葫芦】怒其金帛为酬,此又一那辗法也。【后庭花】惊其不用起草,此又一那辗法也。乃至【寄生草】忽作庄语相规,此又一那辗法也。[2]990
金圣叹认为,这一出的主要内容是张生央求红娘传书给莺莺,重心在所传之书,只要张生把书笺交给红娘即可。按照普通布局,这一出所费笔墨不过几十字即可。然而作者却洋洋洒洒六七百言,正是因为其深悟“那辗”之法,善于挖掘题目细微、深入的内容,所以不断扩充,最终写得丰富多彩,内容饱满。一般的作者为之,可能情节模式就是张生交给红娘信笺,红娘答应后离开,然而在《西厢记》中,红娘最初并不肯传书,使得文章横添波折。正是因为红娘不肯,张生又准备用金帛收买红娘,然后又造成了红娘对张生更加的不满,表现了红娘刚烈仗义的性格,也使得文章进一步出现波折。除了这两处较大的波折,“不便敲门”、“惊于张生不用起草”属于小的插曲,都是作者慧眼发现并妙笔写出。所以,圣叹所谓“那辗”,其核心就在于“辗开”,在某一个特定的题目里,充分地挖掘各种可能性的情节和细节,“前候”就是在“张生请红娘传书”这个题目里,“辗开”了“两人相思”、“不便敲门”、“红娘拒绝”、“不用起草”等细节。它首先将题目细分,然后再针对每个细分后的元素进行发挥,这正是由“搓那”到“辗开”的过程。所以“那辗”属于金圣叹“极微说”在具体文法上的运用。
总之,“无字说”和“极微说”在表述上极为玄妙,宗教和哲学色彩浓厚,但是如果结合金圣叹的具体例证,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作为文论文法的内涵。它们虽然来源于佛学,但是金圣叹并非谈佛,而是借鉴佛学理论来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 “无字说”引用赵州和尚的公案,用排比的“是此‘无’字”句式论述,看似玄之又玄,但结合圣叹具体评点中的例子,就可知道其实就是圣叹关于文法精炼的讨论。而圣叹的“极微说”更是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极微说”主张辩证地看待事物,宏大的事物亦有最微小的元素,最微小的事物亦可进行不断的扩大。而具体到论文,金圣叹的核心理念就是发现、挖掘主题和题目的细节及深度,把平淡无味的文章变得波澜丛生、丰富多彩。所以,“无字说”、“极微说”虽然玄妙,但是其主旨思想实为一致,都是在追求一种文章的“大小转化”,力求以最简洁的文字、最微小的细节来构建出内容精彩、内涵丰富的作品。
[1] 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 金圣叹全集:第2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3] 净慧法师.禅宗入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弘学注.楞严简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2.
[6] 丁利荣.金圣叹美学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版,2009.
[7] 徐懋庸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