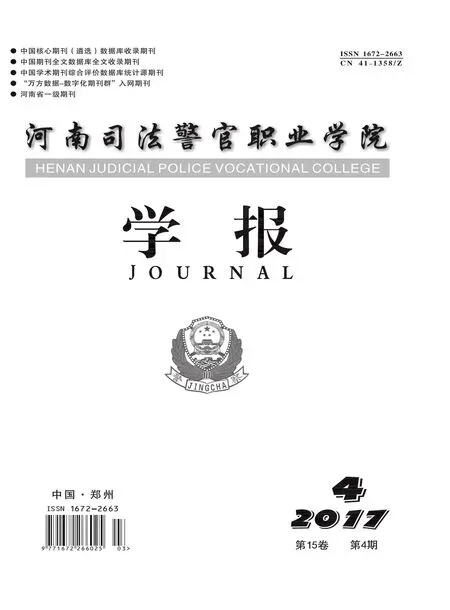普通法视角下表见代理性质的重新审视
尚彦卿
普通法视角下表见代理性质的重新审视
尚彦卿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401120)
大陆法系通常认为代理性质上是一种资格或地位,表见代理为广义无权代理之一种,但这一界定忽视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是建立在意定代理的范畴内。普通法中代理权的性质为权力,不容否认代理可因概括授权、容忍代理等表面权限而成为有权代理。表见代理与不容否认代理趣旨相同,应当赋予表见代理独立代理形态的法律地位。
表见代理;不容否认代理;普通法
所谓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从我国大陆《民法总则》第172条、《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来看,无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抑或代理权终止后”,立法均是认定表见代理人没有获得被代理人的授权,也就是说,立法对表见代理的定性采取的是(广义)无权代理的立场。民法理论界多数学者认为,无权代理有广义、狭义之分,表见代理为广义无权代理之一种。〔1〕有学者从代理权的性质为“权力”出发,认为表见代理为有权代理。〔2〕也有人认为,表见代理是独立于无权代理和有权代理之外的第三种代理形态。〔3〕可见,理论界对表见代理性质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拟在普通法的视角下,从代理权的性质、来源、表见代理与有权代理及无权代理的联系、具体表现类型等几个方面出发,比较分析大陆法系表见代理与普通法不容否认代理制度,以图更清晰地认识表见代理的性质及地位。
一、代理权性质论
关于代理权的性质,在大陆法系有以下几种学说:其一,民事权利说。〔4〕即代理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在性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并无差异。其二,资格或者地位说。〔5〕此说认为,代理权是代理人以本人名义为法律行为的资格或地位。“代理权谓得因代理行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之地位。”〔6〕它之所以不是权利,是因为代理权的赋予并不是为了代理人,而是为了被代理人,而代理人只起着辅助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行为人可以以他人名义独立为意思表示,并使其法律效果归属于他人的一种法律地位。其三,权力说。〔7〕此说为梁慧星、杨立新等学者所主张。梁慧星教授认为,代理权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首先表现为对本人的拘束力,本人必须承担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所实施的法律行为的后果。这一拘束力是不可抗拒的。尤其在表见代理的场合,本人并无授权行为,他必须承担法律后果。这种法律效力还表现在,凭借代理权,代理人可以改变本人与其他人的法律关系”〔8〕。
我国大陆民法理论通说认为,代理权为一种法律资格和地位。〔9〕这种资格和地位具体表现在:第一,代理人取得代理权后,实际就取得了一种能够从事代理行为的资格,换言之,享有代理权就是取得了代理人的资格;第二,此种资格是基于授权行为而产生的。〔10〕按照此种理论,代理人代理权之产生与否,依赖于被代理人是否授权。显然,法律资格或者地位说产生的理论基础是意定代理,“意定代理之发生,系基于本人之授权行为”〔11〕。换言之,基于代理权的法律资格或地位之性质,大陆民法理论在划分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时并没有考虑法定代理。因为“代理权以法律规定而发生者,称为法定代理”〔12〕。在不考虑法定代理及其代理权性质的情况下,称表见代理为无权代理之一种,勉强说得过去。①事实上,即使在此意义下,称表见代理为无权代理之一种,也存有瑕疵,因为因授权不明而导致的表见代理并不能保证表见代理为无权代理。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第一个问题。但这种分类是在对代理类型涵盖不周延并进而定性代理权的基础上得出的,其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为何不基于“法律为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之需要而赋予表见代理以有权代理之法律效果”〔13〕的客观事实,而将其纳入法定代理之范畴并进而认定其为法定代理之一种?法律之赋予代理权算不算有代理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的理论和法律依据何在?
而反观普通法,代理权在普通法中性质上并不是什么资格或者地位,“权力—责任关系是本人与代理人关系的本质(essence)”,“代理人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其被赋予了改变本人与第三人法律关系的法律权力(power)”〔14〕,“这种权力是代理关系的本质,它使得代理人区别于其他能够影响他人法律关系的人”〔15〕。可见,普通法代理制度中的代理权性质上为权力(power)。而这种定性也符合《布莱克法律词典》对权力的第三种解释:“权力是做或者不做的法律权利或者授权;是一个人或者组织通过行为改变他人权利、义务、责任或者其他法律关系的能力。”〔16〕在普通法的语境之下看大陆法系的表见代理,因表见代理的代理人能够使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归由被代理人承担,故表见代理人应是有代理权之代理人,大陆法系将表见代理称为无权代理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或许,也正是基于此,梁慧星教授才有“表见代理为代理之一种,谓之无授权之代理可矣,谓之为无权之代理则不可”〔17〕的经典论述。
二、代理权来源论
代理权的来源也就是代理权发生的原因。在台湾,学者一般根据该地区民法的规定,认为代理权发生的原因因法定代理和意定代理(任意代理)之不同而相异〔18〕,认为法定代理权之发生一般基于“法定事实之发生和制定或者选定监护人、选定遗产管理人之地位而发生”,“任意代理因本人代理权授予行为而发生”〔19〕。在我国大陆,也有学者以法定代理和意定代理的区分作为划分代理权发生原因不同的根据。〔20〕有学者则认为代理权的产生主要基于本人授权行为(意定代理)、依法律规定(法定代理)、依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指定(指定代理)和外表授权(表见代理)。〔21〕前已述及,主张表见代理为无权代理之一种仅是在将表见代理纳入意定代理范畴前提下的一种断定,而这种断定显然忽略了法定代理的存在。并且,表见代理制度的旨趣在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维护动态交易安全。为达此目的,法律赋予表见代理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力。既然如此,理论上又为何仅仅将表见代理束囿于意定代理的范畴之内而定性为无权代理呢?最后一种观点承认外表授权是产生代理权的原因之一,该种主张跳出了意定代理的范畴。但让人不解的是,在已经承认外表授权为表见代理产生原因的情况下,持该观点的学者却得出“表见代理也是一种被视为有权代理的无权代理,表见代理人也有代理权”〔22〕的自相矛盾的结论。
在普通法系,代理人的权力(power)和权限(authority)是有区分的。“权力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意味着一个人通过一些行为改变法律关系。在法律上,代理人的权力正是这种能力。权限是一个事实问题,它意味着一个人指令或者允许另外一个人代其行为。代理人的法律特质——他的权力——可由其获得本人授权的事实而产生,但是它也可以由于其他事实比如案件的需要而产生。”〔23〕“权力,是一种凭借一个法律规则而存在的法律关系。代理人的权力并不是由本人授予,而是由法律赋予。本人和代理人为一定行为,使这个法律规则开始运作,代理人从而获得权力。”〔24〕由此,在普通法中,代理权的取得可以基于代理人的(明示或默示)实际权限(actual authority)②基于实际授权,产生的是协议代理,类似于大陆法系的意定代理。不同之处在于普通法认为本人与代理人的协议即产生代理权限,而大陆法系则需要单独的授权行为。See:Freeman and Lockyer v.Buckhurst Park Properties(Mangal)Ltd[1964]2 QB 480 at 502.、表面权限(apparent authority)③基于表面授权产生不容否认代理(agency by estoppel)。对此,在Rama Corpn Ltd v.Proved Tin and General Investments Ltd([1952]2 QB 147)一案中,斯莱德(Slade)法官曾作过经典陈词:“表面权力只不过是不容否认的一种形式,诚然,有人将它称作不容否认代理。”、通常权限(usual authority)④Goode认为通常代理权限是一个与代理人一样占据或在同一职位的人所应当享有的权限。(See:Roy Goode,“Goode on Commercial Law”,Edited and Fully Revised By Ewan Mckendrick,Penguin Books,Fourth Edition,2010,P184)、推定权限(presumed authority)①基于推定权限产生紧急代理(emergency agency)。该种紧急代理为法律自动构成的代理之一种,法律自动构成的代理还包括妻子对丈夫的代理。(China Pacific SA v.Food Corpn of India(The Winson)[1982]AC 939.参见:何美欢.香港代理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3.但该书著者认为妻子的该种代理权力在当今社会已愈来愈不重要)、追认(ratification)。换言之,在普通法中,代理权力本身包含了不同类型的代理权限:首先是(明示或默示)实有权限,其次是表面权限,还包括禁反言(estoppel)、固有代理权限(inherent agency power)和紧急代理权限(emergency authority)。〔25〕而其中因表面权限而产生的代理为不容否认代理(agency by estoppel)。〔26〕由此可见,在普通法中,不容否认代理为有权(力)代理。而在大陆法系中,与不容否认代理类似②台湾学者陈远雄直接把“agency by estopple”称为“表见代理”。(参见徐海燕.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41)的为表见代理③“大陆法系中与不容否认代理相对的概念是表见代理。”(参见徐海燕.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38)。“英美法系的不容否认代理与大陆法系的表见代理制度在制度功能、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乃至适用情形方面,都大致相当。”〔27〕由此推之,在普通法语境下,表见代理应为有权(力)代理,即基于表面权限之有权代理。
三、表见代理联系论
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表见代理与无权代理及有权代理均存在一定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一方面表见代理的实质内涵确与无权代理有相通之处,即,一般而言,代理人均未就其代理行为获得被代理人之授权;并且,于特殊情况下,表见代理人须如同无权代理人一样直接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倘相对人对表见代理之本人(被代理人)事实上不能请求履行时(例如:本人移民国外、或不知去处),则为保护交易安全,行为人仍应负责。”〔28〕另一方面,表见代理之表象特征及法律后果又与有权代理有共同之点。表见代理之客观表象使相对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已获授权,也正是基于此,法律强使名义上的被代理人承担类似有权代理之责任。质言之,表见代理兼具了无权代理与有权代理的某些基本特征,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简单把表见代理归入二者中任一代理形态,尽管冠以广义、狭义之分,于理论上仍有不妥——有难为自圆其说之嫌,即:为何单单基于表见代理实质内涵与无权代理有相通之处(况且特殊情况下,有权代理亦可形成表见代理〔29〕),而将其归入无权代理(冠以广义),而不是基于法律效果与有权代理有共同之点,将其纳入有权代理呢(不妨也冠以广义)?
在普通法中,代理关系可以基于四种方式建立:其一,基于本人与代理人之间明示或者默示的协议(协议代理);其二,基于表面权限规则(不容否认代理);其三,基于法律的操作(operation)(法律自动构成的代理);其四,本人对代理人行为的追认(ratification)(追认代理)。〔30〕以上四种代理类型中,代理人均享有代理权力(power),是否享有代理权限则有所不同。“在表见代理和法律自动构成的代理(含紧急代理)的情形下,代理人其实并无实有代理权限,只不过具有约束被代理人的代理权力而已。”〔31〕在此语境下,表见代理人并非无权(力)代理,而是“无实有权限”代理。可见,在普通法中,不容否认代理是一种独立的代理形态,其并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代理类型。由此,在“权力”与“权限”相区别的框架之内,我们很容易理解表见代理的性质及地位。而我国在对代理权性质仍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对代理类型简单作非此即彼(非有权代理,即无权代理④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从逻辑上分析,代理人或有权代理,或无权代理,二者必居其一。”(参见葛云松.委托代理授权不明问题研究〔J〕.法学,2001(12):47)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此。但客观上确实存在无法查清本人是否授权的情形。简单从理论上理想地认为非此即彼,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操作困难。)的划分,虽然冠以广狭义之分,但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客观上也不符合现实。
四、表象类型论
我国大陆民法界关于何种表象能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并不统一,但一般认为,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为代理行为而不作反对表示和授权不明为表见代理典型表象则是无疑。〔32〕以下就该两表象作具体分析:
(一)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为代理行为而不作反对表示,有学者将该种表象称为“容忍授权”〔33〕或者“容忍代理权”〔34〕。一般来说,被代理人授权行为有三种方式⑤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07-708)也有学者认为仅有两种授权行为方式即内部授权和外部授权。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60;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39-640)台湾学者施启扬认为,“以公告方式表示向某特定人为授权者,也可认为具有授权效力”。(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M〕.台北:自行出版,2009:337)笔者认为,三种授权方式更为全面,但第三种授权方式确实可理解为外部授权之一种。:一种是内部授权,即由被代理人通过向被授权人发出意思表示授予其代理权;另一种是外部授权,即由被代理人向代理人行为的当事人即第三人发出意思表示而授予代理权;第三种是向外部告知的内部代理权,即授权人授予了内部代理权后,将这一授权事实公之于外部。就该三种授权行为方式的内部关系而言,可能产生两种情形:其一,已向代理人授权;其二,未向代理人授权。如果被代理人于此情形最终亦未授权,则形成表见代理。而就外部授权而言,被代理人可以明示的意思表示(如以书面形式通知第三人)作出,也可以推断之行为(如雇佣店员出售商品)作出。“授权可以通过明示的意思表示做出,也可以通过可推断之行为做出。通过可推断之行为授予代理权,甚至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35〕笔者认为,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为代理行为而不作反对表示乃是被代理人以可推断之行为所作的外部授权。尽管就内部关系而言,被代理人并未授权,但外部授权已使代理人获得代理权,并进而产生有权代理之效果。正如德国有学者所说,“容忍行为的表示内涵,不可能是‘(正在)授予代理权’,而是‘已经授予了代理权,因此代理权是存在的’,这一点,与将内部代理权对外作公开的情形是相同的”〔36〕。
(二)授权不明。授权不明,“除委托人的签名或盖章应当绝对明确之外,代理人姓名或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均有可能产生不明确的情况;其中代理事项或权限因其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所以显得特别突出”〔37〕。本文仅就代理权限不明作以分析。权限不明一般是指被代理人授予代理人之代理权权限不具体,据其文义,可作或大或小的解释。代理权权限不明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概括授权,即被代理人授权时,未指明代理权限;另一种是被代理人的授权具有确定的授权范围,但因被代理人的疏忽,而未在代理证书上载明,或未在向相对人发出的授他人以代理权的通知中说明。权就第一种情况作具体分析。首先,就代理人主观方面看,可能出现的情形有二:第一,代理人出于善意并以合理方式行使代理权,此时即使代理人对代理权限产生错误理解,也可构成有权代理。第二,当代理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构成表见代理。〔38〕而就被代理人一方观察,则会出现:第一,被代理人本来意愿是授予代理人从事某行为的代理权,但当该行为致自身利益不利时,否认自己授权(此种情况下,代理人为民事行为时于事实上就该行为已获被代理人授权),此时,依前述代理人主观状态,若其善意为主,则形成有权代理,否则形成表见代理;第二,被代理人无论是否就代理人所为行为有授权之意愿,但于该行为对自己不利时,仍承认代理人已获授权,此时,只能形成有权代理。通过上述分析,可清晰地看出,表见代理中代理人为民事行为时,是可于事实上就其所为民事行为享有代理权的。
在普通法中,“产生表面权限的表示有许多种方式,其中最为普遍的是通过行为作此表示,也就是通过允许代理人在本人与他人的交易中为某种行为。由此,本人向任何知道代理人为此行为的人作出表示:代理人有权(为此行为的代理人通常有实有权限)代表本人与其他人订立合同”〔39〕。并且,这种表示可以通过声明、行为或者允许代理人担任某一职务等而产生,还可以产生于本人消极地不向外界透露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已被撤销〔40〕,或者说,“被代理人的声明既可以是积极行为,也可以是消极行为。消极行为包括缄默和不作为两种”〔41〕。可见,在普通法中,也有类似于外部授权的表象产生方式。同时,“表面权限(ostensible authority)几乎总是出现于实有权限(actual authority)被概括授予的案件中”〔42〕,当然,“也可以想象一些情形,这些情形可以产生表面具体授权(作特定交易)的案件,但这些案件必将是非常少且不同寻常的”〔43〕。在概括授权盛行、容忍代理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普通法视角下的表见代理同样有着在大陆法系视野下的尴尬:概括授权使得表见代理人取得本人实际授权成为可能;外部授权使得表见代理人客观上享有代理权成为现实。
五、结论
因英美代理法区分代理人的“权力(power)”和“权限(authority)”,且代理权限乃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协议而产生,并非来源于被代理人单独的授权行为,故在普通法中对不容否认代理的定位相当清晰:一种独立的有代理权力的代理类型。而大陆法系强调基础法律关系与独立授权行为的区分,且对代理权定性为资格或者地位而非“权力”,在囿于意定代理的范围内对表见代理作出“广义无权代理”的定论。这一定论忽略了法定代理及指定代理的存在,也未顾及表见代理本身可能为有权代理的客观事实,从而造成表见代理本身定性的逻辑混乱和语义矛盾。在两大法系法律制度尤其是商事法律制度日趋融合的趋势下,跳出意定代理的束囿,赋予表见代理以独立代理形态的法律地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1〕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62-663;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27.
〔2〕〔2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34-236;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78,223-225.
〔3〕谭玲.论表见代理的定性及表象形态〔J〕.当代法学,2001(1):22;张振芝,任秀敏.对表见代理性质与构成要件的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277-278.
〔4〕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29;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73.
〔5〕施启扬.民法总则〔M〕.台北:自行出版,2009:336;林诚二.民法总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43;吴光明.民法总则〔M〕.台北:三民书局,2008:315;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49;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29.
〔6〕〔19〕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29,530.
〔7〕〔22〕杨立新.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23,225.
〔8〕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34.
〔9〕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206;苏号朋.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43-244.
〔10〕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30.
〔11〕郑玉波.民法总则〔M〕.黄宗乐,修订.台北:三民书局,2008:333.
〔12〕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58.
〔13〕〔27〕尹田.民法总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12-313,318.
〔14〕〔23〕〔24〕LSSealy and RJA Hooley,“Commercial Law:Text,Cases and Materals”,Four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96,97.
〔15〕GHL Fridman,“The Law of Agency”,Seventh Edition,Butterworths,1996,P22.
〔16〕Black’s Law Dictionary,Ninth Edition,West,P1288.
〔17〕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88.
〔18〕黄立.民法总则〔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1999:378.
〔20〕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330-331;徐海燕.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82-283.
〔25〕William A.Gregory,“The Law of Agency and Partnership”,Third Edition,West Group,2001,P35-36.
〔26〕〔31〕〔41〕徐海燕.民商法总论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34,308,335.
〔2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
〔29〕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四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8.
〔30〕LSSealy and RJA Hooley,“Commercial Law:Text,Cases and Materials”,Four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11;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张文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45.
〔32〕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218-219;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79;江帆.代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57.
〔33〕吴光明.民法总则〔M〕.台北:三民书局,2008:331.
〔34〕〔35〕〔3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09,708,733,734,709-710.
〔37〕梁展欣.论代理制度中因委托授权不明而引起的民事归责问题——评《民法通则》民商法论丛(第14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2.
〔38〕章戈.表见代理及其适用〔J〕.法学研究,1987(6):12.
〔39〕Freeman&Lockery v.Buckhurst Park Properties(Mangal)Ltd[1964]2 QB 480.
〔40〕F.M.B Reynolds,“The Law of Agency”,2011,P7.转引自Reynolds教授在香港大学商法课的讲义.
〔42〕〔43〕Roy Goode,“Goode on Commercial Law”,Edited and Fully Revised by Ewan Mckendrick,Penguin Books,Fourth Edition,2010,P186.
Review of the Nature of Apparent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on Law
SHANG Yan-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 qing 401120)
The nature of agency is usually a qualification or a status in Civil Law.Apparent representation is one of unauthorized agency in a broad sense.However,this definition which is limited in voluntary agency ignores the statutory agency and the demonstrativeagency.The nature of agency is power in Common Law.Agency by estoppel is one of authorized agency because of ostensible authority such as general authorization and tolerate agency.Apparent representation enjoying the same value and objective as agency by estoppel should be granted an independent agency form in legal status.
apparent representation;agency by estoppel;common law
(责任编辑 郭 文)
DF51
A
1672-2663(2017)04-0051-05
2017-09-23
尚彦卿(1977—),男,河南中牟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普通法硕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主要从事民商法、强制执行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