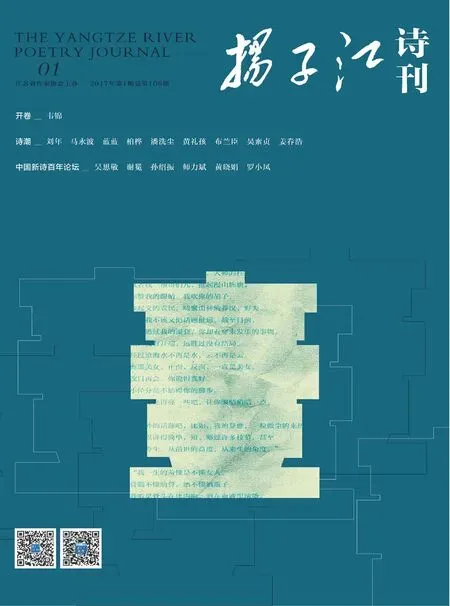江南诗歌“南腔北调”的绚烂呈现:“江南七子”诗歌简评
沈 健
江南诗歌“南腔北调”的绚烂呈现:“江南七子”诗歌简评
沈 健
语调,是说话者的话语腔调,包括说话口气、重音、停顿,语速驰缓,节奏把握,口音的方言夹杂等。说话者个人风格与面貌通过语调而呈现,听到某人语调,大脑丘壑间就会浮雕出某人活生生的模样、性情及神采。诗人,如若拥有独特的语调,也就拥有了个性与风格。研究诗人语调之独特,还须深勘其内在的思维、精神、情感、理念、识见与个性,及其透过特殊地域族群所呈现出的历史深广度与人性丰富性。
江浙地区(包括上海)的主体方言是吴方言,总称江南话,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吴侬软语”语音腔调,其精致迷幻的丰富性、刚健绵柔的融汇性、苍润秀丽的繁杂性,在古今汉语中都可谓特立独行,因风姿绰约而仪态万方。江南自古人文荟萃,以南朝“吴声歌曲”为代表的诗歌写作,以及沈约等人的声律学研究,为唐诗诞生奠定了美学格调,打开了诗歌本体自觉的时代大门,形成古典诗歌经典传统。百年新诗发展到今天,江南也因贡献了众多个性卓越的诗人,成为现代汉诗最重要的原创发声地。第二届当代中国诗歌论坛提出“江南七子”,就是一次集中展示江南汉诗当下写作的“发声”行为,傅元峰教授称之“绘图活动”——即在江南区域内标注并勘察优秀江南诗人,深究其语调与风采的“诗学地图”活动。
在“江南七子”中,胡弦的语调最为鲜明,我将之定位为一个“说书人”,业余的,而不是专业的,当下的,而不是从前的。面对一帮酒后茶余南腔北调的“粉丝”,胡弦随心所欲地胡“吹”乱“侃”,“吹”肉身的遭遇,“侃”内心的挫折,以诗的段子聊他对历史、人生和社会具体而微的种种感悟。他的口音里明显夹杂着淮扬方言特征,有吴越水乡的智慧灵性,但更多燕赵齐鲁的深厚旷达,属于一种典型的江淮文化语调。说他有江南人的智慧,是基于他的南禅悟性玄思,以及老庄的豁达灵视,但其主要的质地与底色是儒教的客观透视与主体承担。叙说中,胡弦文白夹杂,长短句穿插自如,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较多,甚至一字句、破折号感叹号也频频出场,随着诗意传达的需要自由错置,顿挫抑扬有如宋词,而俚语偈句的植入,又酷似元曲与明清说书,下里巴人的细节呈现中,总体攀向一种阳春白雪的品界,饱含家国之痛、生命苍凉、存在虚妄。胡弦的《仙居观竹》短短十一句:
“雨滴已无踪迹。一滩乱石镇住咳声。/晨雾中,有人能看见满山人影,我看见的/是大大小小的竹子在晃动。/据说此地宜仙人居,但劈竹时听见的/分明是人的惨叫声。/竹根里的脸,没有刀子你取不出;/竹凳吱嘎作响,有人体内出现了新的裂缝。/——唯此竹筏,把空心扎成一排,/产生的浮力有顺从之美。/闹市间,算命的瞎子摇动签筒,一根根/竹条攒动,是天下人的命在发出回声”。
起始句“镇住咳声”,仿佛说书人一声醒木“震”出一片寂静。接下从“劈竹、竹根、竹凳、竹筏、竹签”到“竹条攒动”,句句不离南方柔弱翠竹,却处处皆指竹外人生,在险象环生的推进中,诗意指向了存在之痛与生命之美。内在的河洛气象与表层的江南灵动浑然一体,听得读者低首沉思复又赞叹不已,我甚至能感觉到胡弦唾沫星子的激动飞迸。胡弦,已成为江南诗人中挥洒自如的一个说书人。
如果说胡弦是一个说书人,那么陈先发则是一个语言魔术师。他才华横溢,面对诗歌学院的专业学子,以专业知识分子的腔调与姿态诉说他的华彩诗思。陈先发的语速极快,意象腾挪多姿,语韵起承转合。其智性写作与思辨文本,近乎哲学与玄学演绎,他视野开阔,灵视八极,轮回阴阳,对话万物,仿佛体内住着一个西方现象哲学大师群体,一个东方禅宗的通灵哲人群体,所以他的讲述充满灵气、仙气,甚至巫气。他以举世罕匹的“学霸”诗才,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修辞词藻大师。他既不完全欧化,也不纯粹汉化,把汉语悠远古意与欧式思维糅合一体,表演着现代汉语璀璨斑斓的诗学魔术。陈先发也许已经意识到密度太高的顿悟与禅学慢本质有所牴牾,语速太快会影响心灵接纳与内在流播,因此,他的近作语速已被刻意放慢,才华受到自觉节制,过多的夸饰与修辞被果断扬弃,他的“说书”趋于隐忍内敛,迹接于一种老教授的调子,令人满蓄期待。
诗人潘维像一个没落王孙,从一开始就面向太湖、水、乡村和少女,诉说着他孤独的忧伤,以及试图抓住消逝的徒劳努力,他那优雅的南方感觉散发着黏稠、馥郁、交缠的汉语阴柔之光。他出生在陈后主的老家湖州长兴,诗思方式与前辈有一种隐约勾连,我视之为陈后主的转世灵童,他的诗充满了亡国之君的全部要素:伤感、孤独、哀怨,纵欲的短暂快乐。不过潘维丧失的不是现实的朝廷,而是一个美与爱的国度。二十多年前,他从“太湖我的棺材”,来到“西湖我的婚床”,写作了一批远离“鼎甲桥乡”的作品,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接通了汉语的源头,进入语言自觉的写作,在语调上显示了接近李义山和温飞卿的取向。当然,亡国之君对于美总有一种欲壑难填的冲动,眼下潘维又显露出向大城市迈进的企图,在《和平饭店的下午茶》一诗中,他写道:
“从车水马龙进入黄铜旋转门//瞬间,浮雕玻璃隔开了外界喧嚣//一条长廊,凉爽地致意//尽头,八角亭中央/一大捧鲜花:玫瑰、百合、蝴蝶兰……/充满仪式”
这是不是一种转型的宣告尚待观察,但它表明诗人要将优雅的南方感觉伸展到高度繁华的物质世界内部,并从中建构一个诗意的江南小帝国梦想——哪怕像扬州个园那样的小小境像——他要为现代人寻找一块在资本帝国中安妥心灵的诗意园林。这种挖掘大都市积极经验的诗学努力,也许将颠覆波特莱尔以来城市负面诗写的西方传统,能否成功颇值疑问,但雄心可嘉,勇气可佩,值得击鼓点赞!潘维,这个被权力和美的春药所激发着的“玻璃孩子”,他体内的隋炀帝腔调如何统一到陈后主的声带上,也许将成为“江南七子”中最值关注的热点。
庞培是一个低声说小话的抒情诗人。几十年来,他漫游天下,自言自语。从做过搬运工、白铁匠、焊工等底层经历来看,庞培一开始就以“弃儿”和“盲流”角色行走在人间边缘。同样也未受过正规教育,他与潘维不一样,潘维成长的梯子是其父亲的书架,“爬上去,呵,是我谦逊的南方”;而庞培则在底层经历中自我焊制成长之梯,递送他那颗纯朴的心一步一步接近诗神的星空。当生活给了他足够细腻多变的感受力,却没有同时赋予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说话的平台,因而庞培只能转向“厨房、卧室、桌子”,面对“江边落日”“平原炊烟”“母亲的遗像”,一往情深地喃喃自语。庞培的诗很少大词,没有警句,甚至罕见修辞,更无奇峭突耸的意象,却由于整体构思的机巧运行,精心挑捡的生活细节有机支撑,往往整首诗胀满了温暖人心的力量,仿佛被风吹得挺拔饱满的江上古帆。庞培有一种一流的细节提纯能力,这得益于他的小说与散文的叙事历练,他的叙说宽厚而湿润,遒劲而明丽,迸溅着一种内在的峥嵘气象。他的语速极慢,声调低沉,宜于慢慢读,细细品,静静接纳。
叶辉是另一个端口的庞培,他是一个生命神秘和恍惚的叙述者。据我所知,叶辉衣食无忧,又无欲无求,像个前朝小地主,隐居在离南京不远的某个湖边。每当夜晚降临,叶辉总是坐在湖水的拍岸声中,迷惑地眺望着飞机尾灯和萤火虫的闪烁,他分不清萤火虫、尾灯、星星和湖面闪闪波光,内心充满了疑惧与惘然:谁是叶辉?叶辉在哪?叶辉要去哪?叶辉,一个沉浸于超验冥想的现代古人,穿梭在古与今、生与死、冥与阳、鬼与神、物与我之间,不断地造出种种镜像来确认自身,用幻觉来摸一摸冷暖肉身的存在,以玄思来旋一旋时间消逝的螺帽,让想象来挡一挡虚无履带的碾压。表面上看,叶辉在向家人、朋友和身边万物疑心忡忡地诉说,实际上叶辉正对着自我,在坚信不疑地诉说。就是说,叶辉是一个清醒怀疑论者,自觉的不可知论者。叶辉有好多诗写到“郊外”:“郊外的房子”“郊外的无名小镇”“郊外的寺庙”“百里外一个男人的梦境”,逃亡的县令“吊死在郊外”……这一“郊外”,实乃叶辉“彼在”映像,也即叶辉的精神寄居地,作为远去或者未来的叶辉的镜子,它所投影的是本真的叶辉所在。正是从这一视角看,我们说叶辉是庞培的另一个端口呈现,庞培只对现实亲人亲情说话,而叶辉却对幻境自我超验说话,叶辉也喃喃自语,但他含混的唇齿音中更多的是生命的神秘经验。
杨键是在汉语佛经中独步沉思的诗歌修行者。在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中,杨键无疑是一个消极的厌世主义者,但他并不弃世,在佛的恩慈中找到了温暖的文字,杨键立地成佛,化作了一座行走的佛塔,一堵移动的寺门,成长为一个经书传播人。他语调坚定无移,有一种超验的自信与镇定,在近三十年来的长吟或者短唱、低语或者悲歌中,杨键一以贯之地以悲悯者的形象行走在汉语普渡众生的创写之中,这,已成为汉语诗坛有目共睹的一道景观。我感兴趣的是,杨键叙说中对材料的慈悲处理与佛心挑拣。比如他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一诗中,以“煤灰”和“残迹零墨”来形容母亲受尽蹂躏而不失高洁品质,我以为真正抵达了善心独运境界;在《长江》一诗中,他写道:
“一朵云压在了一条小船上,舱内的知了壳,依旧忠实于地底。”
这是一个奇峭的比喻,回归泥土是知了生命转换的本性,这一点众所周知,但诗人将之放置在命运的流水之上,搁在世事的船舱之底,匠心独运地指陈其对泥土的忠诚。这只知了壳,与“土地”之间经历了“流水”“船舱”多重转换,极其艺术地蜕变成了轮回不变的佛性象征。诗思何其超妙,几人能够写出?与庞培不一样,杨键有时很夸张,“在被毁得一无所有中重见泥土”,这个诗题极尽夸饰,诗人却以接下来的八个平实句子实施了一场诗学拗救,让题目与文本形成新的平衡,因此读起来极其自然、妥帖、有力;杨键也写大词,比如“我的祖国将从药罐里流出”,却毫无矫情造作。究其原由,我以为深蕴于杨键语调深处的内驱力,已经不是一种技巧,一种艺术,一种小智小慧,而是一种佛心境界,一种慈悲情怀。
如果说杨键是居士修行在人间,那么张维则是英雄修行在低处。张维是“江南七子”中最具南人北相者,他雄阔的额头、高耸的鼻梁和异域的眉棱,仿佛明清绣像小说中的英雄豪杰在当代悄然复活,他的“说书”天然地有一种豪杰语调。“我经历的深渊成了自己的高度”,这一警句只有身体、生命和灵魂历经磨难者才能写出。《五十述怀》是张维的巨作,仿佛虞山耸立在长江入海口,视之为平原孤峰并无不当。“世界薄得只剩下一张纸”,岁月不再,烟云俱逝,英雄暮年,回归常态,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曾经的辉煌“只剩下一张纸”,张维感慨万千,充满了对过往的省思、忏悔与哀伤:
“五十二年过去了/落日站在西边的树林/把每一个人默默地含在眼里。”
表面上看,这是另一个杨键,语调、音高、语速、情感都在同一个谱系中。但是张维的诉说中依然纠结着对世事纷争的不舍反思与进取祷告,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入世情结隐约可见。在我看来,张维就像一个被时间废黜的帝王,在暮光沉沉的生命低处叙说着他鹰扬环宙的回忆。“已经到了考虑天空和星辰的年龄了”,张维语调沉雄,情感饱满,有一种刻意的语速平缓,有时甚至有些阻滞,以至于要求助于歌吟,因而他的诗内蕴着一种歌咏的属性。张维的诉说朴素、老实,小智小慧吞没于大智若愚,长吁短叹包孕着如泣如诉,俗雅不拘,跌宕自如,张维为我们捧出的是一个汉语赤子的悲怆与怜悯、气度和心胸:
“一个人此刻才能深夜看海/一个深夜看海的人/是一个大海一样辽阔有光辉的人”
让人恍如隔世,仿佛登临碣石夜观沧海的英雄再度出生。盛大人间,众生沉沦,看海的男人以修行的语调引领我们在语言中回望自身。
沈健,
浙江长兴人,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1980年代开始写诗,在《诗刊》《星星》《哲学研究》《诗探索》等报刊发表诗歌及评论。著有诗集《纸上的飞翔》、评论集《浙江先锋诗人14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