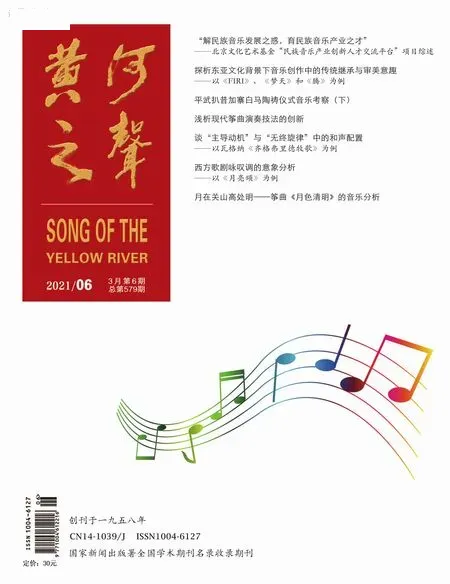敦煌壁画民俗舞蹈“十二愿”
程依铭/程一冉
一、“十二愿”乐舞图
“十二愿”即十二种美好的愿望,源于佛教经变药师经。相传药师如来在学习佛法之初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引导众生获得解脱、后依次愿而成佛,住琉璃世界。在敦煌莫高窟12窟晚唐北壁上出现了东方药师变“十二愿”乐舞,它再现了敦煌世俗生活中的巫术活动,是壁画上唯一一种以琵琶为道具的巫舞。图中女巫身着裙糯大袖礼服,头梳高髻,怀抱琵琶边弹奏边舞动边祈求,由图一可见,女巫身材匀称,倾头右腆腮,左手握住琵琶颈右手弹拨琵琶,同时单腿站立右腿微微后吸,出左胯同时身躯向右斜前倾倒,造型独特,独具风韵。
在唐代,女巫的歌舞祈福、歌舞赛神或治病等风俗,很常见。莫高窟360窟晚唐中的东方药师变“十二愿”中的乐舞图与12窟中的“十二愿”乐舞图较为相似,舞者身着裙糯大袖礼服,头梳高髻,怀抱琵琶正在舞动。与12窟中“十二愿”乐舞图不同之处在于手中握的琵琶为四弦的直项琵琶,整个身体向前倾斜的舞姿幅度相对较小。据考证,“十二愿”经常会和“九横死”一起出现,皆出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若众生信仰药师佛,静心供养礼拜药师佛,念诵《药师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造四十九尺五色彩幡,斋僧,放生,可免“九横死”。
二、“十二愿”的宗教精神与历史根基
(一)溯源——佛教药师经
“十二愿”出自《药师经》,相传药师如来学佛之初,曾发十二大愿。任何一位凡夫众生都是因地上的菩萨、因地上的佛,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佛。“令诸有情,所求皆得”,药师如来所发十二愿是他成佛的动机,是他从凡夫众生发心修行时所结的“因”。药师经不同于其他经典,在婆娑世界里,尤其是东方世界,药师经的愿望非常实际。他希望自己成佛的时候,被饥渴所烦恼,为求饮食而造一切恶业的众生,念药师如来名号,可以摆脱恶业,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然,这里并不是迷信的意思,像今天,很多人还是会有所求地去拜佛去求财或者求子,仿佛所有人只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就将佛教牵扯进来,其实更多时候佛教文化作为一种智慧的修行而存在。佛法一直围绕着一个真理即——心得解脱,药师佛告诉我们“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脱一切忧苦。”即是依仗他力(药师如来)的力量,心里没有忧悲苦恼而得到解脱。
药师如来的原理境界是满足世界众生的物质欲望,佛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又说“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故因为这种偏向于物质的思想偏差认识,在西晋时期《药师经》被翻译以后,得到了广泛流传。尤其是连年不断的战乱、社会的动荡不安的敦煌地区,为药师信仰发展提供了繁殖的温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是这种“有所求”的大众心理使得《药师经》得到社会的承认而广泛流行开来,受持诵读,手写笔绘《药师经》,蔚然成风。特别是隋唐时期,这种有所求的心理附合了人们“以生抗死”期望,同时还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推崇,使得药师经快速得到传播并深入普及到千家万户之中,颇有“此经深义人人共解,彼佛名号处处遍闻”之势。敦煌壁画中药师十二愿以及九横死画面的出现,它表达了在城破家亡之际,人们的祈求神灵保护“以生抗死”的心理,身体可以更为物质化地表达言语所无法表达出来的体验,敦煌壁画上的“十二愿”乐舞作为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进行了对生命的对抗,巫官吸收了佛教药师经里的“十二愿”文化依靠身体的他者性感觉来努力创作一种新的“语言”。
(二)接合——交感巫术
在原始社会,巫术活动已经存在,并掺杂着一定的歌舞形式。巫术的原理主要分为“相似律”(即“同类相生”)和“接触率”(或“触染律”),这两大原理皆是通过“联想”得出的结果,壁画上的“十二愿”乐舞图则是巫术“相似律”的印证,将相似或者有共性的事物看成同一事物,因为相似而建立起的“顺势巫术”。“十二愿”舞伎吸收了佛教药师经的“十二愿”中的思想:愿为众生解除疾苦,引导众生获得解脱,来达到其医治疾病的巫术目的。自秦汉以后,佛教文化的兴起,使得作为原始宗教的巫教受到了严重影响,巫教因政治上没有显赫的代表人物,理论上缺乏系统的教义宗旨,遂日渐式微。一些巫师为了能持续发展其职业,并使其不受影响,就将道教、佛教以及儒学融入巫教。这种世俗化的转换从表象上来看是巫师们的生存所需,更深一步地去认识则是巫术“相似律”原理的深刻体现。壁画上的世俗乐舞更多地是反映某一阶段的生活现状,图中女巫身着裙糯大袖礼服,头梳高髻,怀抱琵琶而舞,舞姿造型清晰,是巫术们为了保住职业将佛教文化融于巫教的“融合型”艺术载体生成。
如果说宗教是用一种幻想的方式依靠对彼岸世界的信仰来拯救苦难的人类哲学用一种逻辑的方式,借助于理性的力量来把握悲剧,那么艺术就是用一种想象的方式通过形象和情感来抚慰人类的创伤。敦煌艺术作为一种濡染了佛学精华的艺术,可以说就是一种依靠对佛的信仰用幻想的方式通过艺术形象和情感来抚慰人类的悲痛与创伤的艺术,这种精神依靠与巫术的降神祈福相吻合。
(三)杂融——中原宫廷文化
追溯12窟“十二愿”乐舞图的时代背景在晚唐时期,巫女身着宽袖曳地长袍、纤腰长巾,头梳高髻,从发髻到服饰均不同于“反弹琵琶”,相反,梳高髻,体态娇小、端庄内敛、舞姿造型温柔婉约。隋唐时期,是古代舞蹈发展的高峰期,同时,敦煌地区与中原地区联系日趋密切,从乐舞机构的设立到舞蹈种类的多样化分,无一不显示着其舞蹈的发展水平。唐代舞蹈分类有“软舞”“健舞”之分,根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与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唐代有软舞曲《绿腰》《鸟夜啼》《春莺》等;健舞曲《剑器》《胡旋》《胡腾》等。在服饰上“软舞”者大多身着曳地长裙、长袖袅袅,随着舞蹈的起伏。在歌舞情调上“软舞”讲究抒情委婉,擅长表现“琵琶一曲肠堪断”一类的动人情感。“十二愿”乐舞图中的舞伎怀抱琵琶以及服饰特征与唐代软舞的意境追求及舞伎的服饰特点出现了极度相似,舞姿动作内敛含蓄,不同于经变画中的舞伎形象,一改往日的“开胯”、“外开”等舞姿,两腿保持内扣收紧,只是膝盖以下的右小腿后翘,上身的体态也并非夸大式地横移。
据考证,巫舞在审美形态上延伸来源于古代宫廷,最早可以追溯到楚舞,壁画上的人物静态服饰装束造型与楚舞造型的基本特征“小腰秀颈”“长袂拂面”不谋而合。这种装束更表象地来讲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儒”文化,那些粗犷、野蛮的原生态舞姿在儒家教化下渐渐地用厚重的缨珞覆体,默默地穿上了衣服;其动作也变为含蓄内敛。
三、“十二愿”乐舞的视觉语汇与敦煌舞姿
(一)“S”形舞姿
身体是一种社会的和语言的概念,是某些特定的话语实践。从壁画上活脱脱走下来的敦煌舞蹈作为一种活的、流动性身体造型艺术,更成为了揭示时代背景的文化产物。大多部分舞姿是通过壁画上的形象加工提炼而来,“十二愿”乐舞图中的形象直观地反映出了其舞蹈独特的特征即“S”型舞姿所呈现出来的“三道弯”曲线美,图1中舞者右腿吸起将重力完全放到左腿上,由此同时顶左胯从而由脚到胯两个支点之间形成一条斜线,再次,舞者上身肋骨大幅度像右偏移,从脖颈到鼻尖额头整个脸部侧面于上身保持一个方向的倒式,由此,胯部与头部两个支点之间形成了第二条斜线。

图1 (莫高窟12窟 晚唐 北壁“十二愿”)
在敦煌舞中“S”形曲线是一个泛称,归纳总结大概分为6种:“S”柔和小曲线、“S”形大曲线、直角三体位“Z”形曲线、四道弯曲线、五道弯曲线、多曲线。
显然,图1中的舞姿形象属于“S”形大曲线,即通过屈膝、出胯、冲肋而形成的“S”形三道弯大曲线,舞姿在松胯基础上形成的富有阴柔之美的曲线美,图中舞者舞姿圆润柔和、婉若游龙,并没有直角三体位“Z”形曲线的棱角分明,更没有“S”型小曲线那样动作幅度温和;再次,观察可以发现舞者的右腿膝盖与左腿靠拢,没有外开,而是顺贴在左腿上形成一条斜线,因此不会是在“S”形三道弯基础上通过提胯冲肋低头侧抬腿形成的;五道弯曲线,头部没有出现强烈的歪头趋势即排除了四道弯舞姿形态。
“S”形三道弯作为敦煌舞蹈最为显著的舞姿特征,在“十二愿”乐舞中再次显现。除了肢体的曲线,舞者的手臂也呈现出了一种曲线形,舞者身抱琵琶,左手抓琵琶柄右手弹奏,双臂不约而同地弯曲到一个弧度(当然,手臂的弯曲也与琵琶的弹奏方式密切相关),手臂的这种曲线感既与肢体的“S”形曲线相迎合,营造出一种和谐的美感,又符合敦煌舞手臂多棱多弯的外部特征。
(二)“十二愿”与“反弹琵琶”
《反弹琵琶》是敦煌舞蹈中最为典型的伎乐天舞姿形象,它表现的是经变“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场面。以图2莫高窟112窟伎乐图为例进行分析,舞伎将琵琶反弹同时舞动身体,高超的弹奏技艺与美妙的舞蹈巧妙结合起来,反映了佛教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况,同时彰显了大唐盛世。“反弹琵琶”是极具俗乐特点的天乐,“十二愿”是极具天乐思想的俗乐,都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同一时期背景下,俗乐中的佛教吟唱与天乐中的世俗歌舞并非偶然,而是文化融合与冲击下的不同产物。

图2 (莫高窟112窟 中唐“反弹琵琶”)
反弹琵琶中伎乐天形象,赤裸上身,下身穿肥大的“灯笼裤”,全身缠绕着飞舞的长绸,头饰及身上的配饰华丽、明艳,舞伎单腿站立,右腿吸起的同时旁胯打开,勾脚趾、赤足,出左胯,身躯向右斜前倾倒,右腆腮,伎乐天人物形象带有一定的西域色彩,整幅图画表现了空灵欢乐的精神境界和雍容华贵的民族风格。
“十二愿”中的舞女形象,身体的主要衣饰裙糯大袖礼服,身姿俊美,头梳高髻,怀抱曲项琵琶,单腿站立,右腿后吸,出左胯,身躯向右斜前倾倒,右腆腮,似乎正在祈求神灵,女巫的祈福、歌舞赛神或治病等为唐代风俗,很常见。
舞蹈“十二愿”与“反弹琵琶”对比列表见下表。
结 语
敦煌壁画历经千年之久,又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壁画上的各种乐舞形象丰富、奇幻,同时如史书般带有历史记录性意义。“十二愿”乐舞图它体现出了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巫术的结合及在民间流传的状况。通过分析与研究的过程,又充分例证了敦煌壁画乐舞在凸显民族特色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杂糅性。■

形象 头饰 服饰 琵琶弹奏方式 舞姿 面容表情 功能 风格特征“十二愿” 头梳高髻 裙儒大袖衣服,不露脚四弦直项琵琶;放于身体胸肋部,左手持柄、右手弹拨单腿站立,右腿后吸,出左胯右腆腮,似祈求神灵 “娱神兼娱人”中原服饰,更为突出巫术文化“反弹琵琶”头戴珠光宝冠上身裸露,下身着红色带巾边筒裤,裸露小腿至脚踝,赤足,身披彩绸琵琶反弹放置肩颈部,左手反搂琴柄、右手反弹单腿站立,右腿旁吸腿,出左胯右倾头眼睛低垂,似看人间“娱佛”西域色彩,更为突出佛教文化
———史敦宇艺术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