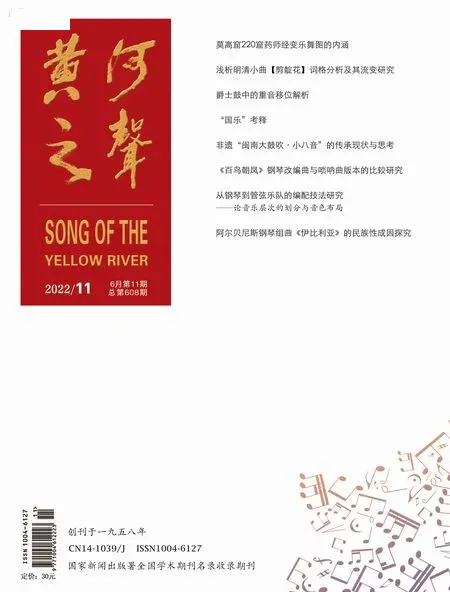“国乐”考释
曹 静
关于“国乐”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其争论之处在于对“国”的界定:是多民族国家?是政治层面上的“国”?还是一脉相承的“国”?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国乐”便成为:是中华各民族音乐大融合下的产物?是20世纪以来西乐东渐的产物?还是在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基础上传承下的民族音乐?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中收录了“国乐”这一词条,其释义为:1、中国古代宫廷音乐。2、中国传统音乐。3、民族音乐。[1]很显然,该“国乐”可以定义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音乐基础上传承下的民族音乐。此外,中国古代宫廷音乐中除中原本土音乐外还包含“四夷之乐”,故可以判断此“国乐”兼具中外音乐交流属性。郑觐文曾提出:“国乐是国家音乐的性质,不是普通丝竹就可以拿来做代表的。”由此得知,在他看来“国乐”不是民间音乐的整合,而是国家基础上的构建,本质上具备了提炼意义。近人萧梅进一步提出:“‘国乐’的内涵是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创制,实质上已经超越‘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除此之外,20世纪上半叶所掀起的“国乐改革”浪潮又曾如何定义“国乐”呢?笔者认为,虽不完全属于上述,却又各有涉及。刘天华提出了“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精神”,萧友梅也曾说“力主参照俄罗斯经验,在西乐与国乐的融合中创造国民乐派”。很显然这类“国乐观”具有鲜明的交汇性,目的在于强调东西融合后的创新。由此看来,历史环境、社会角色的不同极大影响着看待问题的视角,进而导致结论的推断各有所异。这个在20世纪热议的问题,于今依旧饱受争议,将这一难题纳入社会语境中便可以豁然些许。
一、宏观语境的整体把握
艺术的运动是充满矛盾的,更新是它的本性,“和而不同”是它的存在方式,事物的相互作用则是发展的动力。[2]国乐作为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社会变化而不断更新,如果盖棺论定国乐为某种音乐内容,那便是否定了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因此把握了国乐的动态就抓住了国乐的本质。这便是将“国乐”进行宏观划分的必要所在,“国乐”的宏观性代表了音乐对多元性、运动性的肯定。
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可将“国乐”定义于本土音乐及中国化的外来音乐,这就需要兼具纵横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纵向来讲,历朝历代的国土分合裂变,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并不会随着领土的变化而消亡,秦朝汇聚前朝文化实现大一统局面,其音乐既包括庄严肃穆的礼乐,又包括后起之秀的新声,俱可称为秦国之乐。横向来讲,隋代七部乐服务于宫廷宴饮,其中除了《清乐》是汉本土音乐,《西凉乐》是中原旧乐杂以羌胡之声且称之为“国伎”,其他乐部均属自他国伎乐,而隋朝七部乐被赋予了宣扬国威等政治手段的新意义,不可称得上是隋代国乐吗?近观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大都以中体西用的技法创作,其词为中体、曲为西用的创作手法创作出的新音乐也具有“国乐”的属性。放眼人类史,曾称为异国狄戎的西域诸国,在阿拉伯东征后经历着人种、民族的巨大改变,本非同一血脉的人种长期扎根生活于此,随着民族大融合而逐渐被汉化,代代相传于今,难道这些人当下称不上“国人”吗?若一味僵守寻宗祖而定国别,这未免过于忽视时代的纵向发展。音乐文化亦是如此,如果只承认“旧乐”否定“新声”、只承认“本土”否定“外来”,未免过于教条。既然被汉化的外域人种可称为“国人”,被收复的地域可称之为“国土”,那么中国化的外来音乐方可称之为“国乐”。据此,亘古通今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化的外来音乐皆可称为“国乐”,此乃社会语境下具有宏观意义的“国乐”概念。
二、中观语境的民族关照
黄祥鹏先生曾说:“传统是一条河流”,字里行间象征着文化的传承意义。在音乐上,“中国传统音乐”这一概念并不是自古已有之,而是在鸦片战争后为了区分“新音乐”而产生的。王耀华和杜亚雄先生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指的是中国人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3]在二位先生的见解中,音乐的“形制”似乎决定着它的属性。虽然“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提出较晚,但这并不代表1840年前中国没有传统音乐。恰恰相反,我国古代的传统音乐有着光辉的历程。就王、杜先生的话,中国传统音乐以立足于中国本民族。秦汉以后,汉民族正式建立,具有独立意义的民族正统观念和建立在汉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观念初步形成。随着朝代的更迭,历代君王秉承秦汉“天下观”不断丰盈国家内质,形成今天14余亿人口所生活的中华民族。在此期间,酿造了无数具有本民族特质的音乐文化,俱可称之为中国传统音乐。
如若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必要立足于其独特性,亦或者说是其固有的、特质的、传承的。什么样的音乐文化符合此特征呢?笔者将其归结为: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祭祀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这些音乐现象又是由独有的音乐理论、音乐思想、音乐媒介等不同要素构成,它们在其限定的场域中完成着文化使命,因此每一种音乐现象都有其不可替代性。本质上,这种不可替代性由文化性格及使命所决定。譬如宗教音乐,目的在于宣扬教义、普度众生;祭祀音乐,目的在于沟通神灵、寄托精神;文人音乐,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人格;民间音乐,目的在于叙述生活、娱乐身心;宫廷音乐,目的在于宣扬国威、服务政治。这些形态各异的传统音乐以其特有的性格和使命决定其走向及发生场域,且每种音乐现象的背后蕴含着各类音乐构成,它们的共通之处均为本民族独特性。
传统是一条河流,文化亦是一条河流,流脉在于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上文所述各类音乐文化在步入近代以后并未曾消亡,有的“原汁原味”,有的则“改头换面”。例如,民间音乐中的一些山歌、号子,依旧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音乐要素和音乐使命也未曾变化。但宫廷音乐的形式随着皇权政治的消亡也不复存在,它更多的是随着乐人的流动逐渐下移融入到民间音乐当中。所以,即便一些音乐现象趋于某些原因不再留存,但它更多的是消融在其他音乐中进行传承,这便是民族音乐独特性对其流脉传承性的决定作用。
立足于民族的“独特”与“传承”,能够发现中国民族音乐这一股清流的生生不息。这可以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国乐”,是立足文化本体论的参照下的“国乐”,是饱含民族性格的“国乐”。正如王耀华和杜亚雄先生所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人们便用“国乐”来指认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在近代又有所发展的音乐。[4]从横向来讲,传统音乐并没有宏观上“一切中国化的音乐”海纳百川,也没有立足于“国家”层面音乐内容的具象;从纵向来讲,传统音乐从发端、流传到再发展,其实质立足于民族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国乐”定义,需有传统音乐的一方净土。
三、微观语境的国家依托
有国,有乐,谓之“国乐”。因此,若想理解“国乐”,必要参照“国”、“乐”的定义。国可以称为国家,乐可以称其为音乐。“国家”: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因此,在中国古代有国、有家、有人便称为“国家”,这是“家国一体”的国家观。《后汉书.西域传》载:“王莽篡位,贬义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负役属匈奴。”[6]此处的“中国”是立足地域之别,应该指汉域地区。近代以来,国家的概念具有阶级性。从这一层面来看,国家释义为:阶级统治的机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组织,也指一个国家的领土。[7]显然,“国家”的意义在古代和近代全然不同,古代意之为“体”,背后蕴含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强调在限定空间下由不同有机体所构成的整体意义。近代以来意之为“治”,更加倾向于在统筹规划中为达到社会规范性而代表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及组织。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古今对比。那么从乐的角度来讲,古代的“国乐”意为:国家制定的音乐,用于庆典、宴会、祭祀、兵戎之间。[8]近代以来,在国家体制基础上的“国歌”则代表“国家的歌曲或乐曲。在举行国家大典、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时演唱或演奏。……国歌大都反映国家的性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状况,宣扬爱国的思想。”[9]由此来看,古之“国乐”基本等同于今之“国歌”,这是在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象征意义的国乐观。古今的国家观虽不同,但是国乐观却相近,都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专门设定的音乐,其政治性高于艺术性,是民族心理在音乐上的集中表达。
近些年来,有不少文章都提到了“新国乐”的构建,认为旧的“国乐”的内涵已经无法满足于现在的需求。“国乐”的内涵是不断充实、不断革新的,在当代多元化世界格局下的主流音乐更新速度渐快。如果根据一个国家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来重新定义音乐,这无疑是对于量变的夸大。当下对于“国乐”的内涵应该在社会体制下进行定义,这个内涵的核心即为“音乐为谁服务”。所以,明晰了音乐为谁服务的问题,新国乐的内涵也就豁然了。
那么,为何要构建“新国乐”呢?回归文章的起始,乐以国为基,古今国乐观虽然相近,但国家的概念存在变化,所以国家制度也有相应的差别。国家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其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历史上已经产生的国家制度主要有奴隶制国家制度、封建制国家制度、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国乐”的四个阶段分别为:奴隶社会体制下的礼乐文化、封建社会体制下雅乐文化、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下的中体西用音乐文化和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特色音乐文化。第一个阶段的服务对象是“奴隶主阶级”,第二个阶段的服务对象是“君主阶级”,第三个阶段的服务对象是“平民”,当代的这一阶段的服务对象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归类的话,古代的国乐强调的是自上而下,近现代的国乐强调的是自下而上,这种指向性在现阶段表现为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特色音乐文化。
对于微观层面“国乐”的界定需要立足于“国家”这一名词的概念,放在大的社会语境下来看。国乐的本质所属的功能性一直存在,不能够只从文化的流动性和传承性的角度来看待。从此层面来看,“国乐”的概念以国家体制为依托,在某种体制下通过最高的国家机构所设置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音乐即可以称为狭义层面的“国乐”。郑觐文所提出“国乐”的意义有三:一名雅乐,即国教的音乐;二名大乐,即功业的音乐;三名国乐,专司对外的音乐。显而易见,其意义大概如此层面所述,这种音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向性、服务意识、政治依托和规范效应。正如他所说:“国乐是国家音乐的性质,不是普通丝竹就可拿来做代表的。”①基于该层面,考量到国家用乐的普适性、代表性,“国乐”之意涵应置位于国家体系中考量。
结 语
将“国乐”置身于大的社会背景下,从不同的视角环视所呈现的体态各有所差。这是物质世界运动性之决定论,故要用兼具发展的眼光看待其存在。从多元动态史来看,“国乐”内涵之广,广于一切内化于中的音乐;从流变的纵向史来看,“国乐”流脉之久,久于渊源在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从阶级的政治史来看,“国乐”形象之精,精于专指向服务性的国家音乐。由此三方视角审视“国乐”之定义,方可知其全貌。■
注释:
① 萧梅.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J].中国音乐学,20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