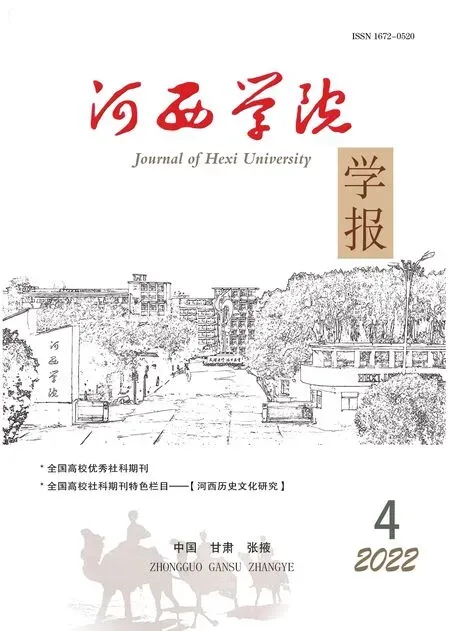历史图景与国家命运的内质透视
——浅论李学辉长篇小说《国家坐骑》的主题内涵
许 瓛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引言
李学辉出生于凉州,成长于凉州,生活于凉州,他对凉州文化有着不懈的探寻和刻骨的怀想,是一个具有浓烈人文情怀的作家。他将情感扎根在深厚的传统里,始终以凉州为写作背景,不断从悠久而独特的凉州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发掘其根植于传统民俗之中的文化隐秘,书历史于撞击,写传统于反思,化终结为起点,塑品格为精神。
李学辉作为甘肃小说八骏之一,向来以中短篇小说著称于文坛,创作了《1973 年的三升谷子》《麦婚》《麦女》《汉奸河》《绝看》《邱小姐》等为代表的诸多中短篇精品力作。虽少有长篇小说呈现于读者,但这几部长篇小说却极具题材的独特性,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感染力,尤其具有文化传统与时代变迁交织的地域民俗特点。其中2010 年出版的《末代紧皮手》,是一部土地命运的恋曲长调,被称为“农耕时代的最后一曲挽歌”[1],凝结的是一种厚重的反思。经过8 年的酝酿创作,2018 年李学辉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这部小说使深匿于视野之外的民俗文化元素以文学艺术形象展示于世,通过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声音与心灵的肖像,精微解读国家与民众的命运关系并将历史性的悲剧紧扣于现实性的生命信仰。作者将民众微弱的声音、灵魂的挣扎和改变命运、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融为一体,在看似怪诞神异的铺陈中对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给予深沉而纯粹的文学式刻画,让一个负载着盛世文化符号的义马在乱世中复活,且通过马户的末世坚守,义马的具化形象,以超乎想象的情节,塑造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艺术形象,挖掘历史与现实中民众自强不息的思想内质,将其凝结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钩沉出蕴藏在民众内心固有而永恒的民族心理。
二、在传统承接中追寻国家意识的本源根脉
《国家坐骑》由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来。面对国家民族的衰落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作者将经验世界的民俗材料与特定的时空形式统一起来,让炼狱般承载民族希望和国家兴盛的文化内涵重新复活,以决绝严苛的形象使根存于民众内心的道统和秩序还魂于乱世,在传统承接中追寻国家意识的本源根脉。从表面看,义马半人半马的形象是在讲述义马的命运,实则渗透的是国家的命运,注重的是文化的坚守。简而言之,义马所反映的是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以及文化的命运。民族羸弱,军阀乱政,政府欺民的现象与义马的奋力抗争,形成命运的对撞,一面展现出义马高贵的国家品格,一面又将人的命运、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和文化命运的重重危机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在看到培育国家之马的永恒信念时,不自觉地引发深思,使得国家之马所体现的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演化为普遍认同的审美理想。进一步地说,从历史的存在到社会的动荡;从命运的抗争到文化的坚守;再从人性的践踏到现实的毁灭;从生命的祭献到精神的延续,义马作为一种承载,不仅仅昭示了其存在到消亡的悲剧过程,更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国家之马的消散与重建,这是民族国家意识之中存在的一种文化积淀、人文品格和精神高地,承担着聚拢民族精神的重大使命。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呈现。
(一)小说故事的展开直接从本源根脉中走来
“光绪十九年的凉州咳嗽了一声,便把除夕唾到了城门边上。”[2]1这是《国家坐骑》的开篇第一句,以奇异梦幻的语言,点明时间、地点、背景,将读者目光牢牢钉在凉州,钉在咳嗽了一声的凉州城,钉在最能体现凉州文化习俗特点的除夕大年。故事的第一幕便自然地进入到凉州自古而有的除夕祭祀,拜马神,贴马对,同时又以惊现于凉州的龙驹飞影、绕城而奔来点题启幕,从而引出“国家积贫,人丁羸弱,马亦疲态,挡不住坚船利炮”[2]4的社会现实,一下子将凉州毫无悬念地贴到时代命运柱上,使读者走进一个没落而动荡不安的风雨岁月。继而,马政司官员“龙驹一出,天下大兴。国有兵才稳,兵有马才胜,家无马不兴”[2]4的长声慨叹,将小说视线向深处无限拉长延伸,重重地落在凉州马文化时代所固有国力支撑的本源根脉上,既点出培育国家之马这一国家意识的小说主旨,也奠定了整部小说为国而生,为国抗争,为国而死的主题基调。
(二)民族精神的集体意识性体现
《国家坐骑》以特殊的思想载体,特质的文化土壤及特定的历史事件与特别的艺术形象之间的高度契合,将本是正常环境营造与故事抒写的地理风貌和历史事件与精神原点的本源根脉相伴相生,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说,马文化作为民族的深刻记忆被积淀下来,深深烙印在中国人心里并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文化原型概念。一旦触及根植于血脉的文化原型,马意象的集体无意识便会被激活,蕴含的精神内质便被唤醒,从而复活关于马的记忆,寻找时代所需。由此,小说关于凉州金东街、银北街,破铜烂铁西、南街,半人半兽马户街,七寺、八庙、九台,以及巴子营,八旗满城营,巍巍祁连山、茫茫大牧场的描写就不仅仅是地理风貌的渲染,更是马文化时代里凉州辉煌的追寻。这些景象地铺陈让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宏大气象与丰厚底蕴得以重现,为龙驹出世、义马成长与国家之马培育渲染出历史和文化的立足点,其中蕴藏的是凉州以马为思想载体的国家意识之本源根脉。随着故事的演进,光绪驾崩、宣统继位、清廷内变、民国建立、军阀横行、凉州大地震、日寇入侵、张少帅兵退、新思想宣传、红军西征等历史事件被作者一一反映于义马的生命过程,刻进义马的身体骨血,以义马的视角呈现出传统承接与历史现状的巨大反差,把多灾的历史和多舛的国家命运与存在于民众内心的至高信念贴合在一起,形成为国育马的行动自觉与动荡不安苦难重重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对冲,在传统承接中追寻国家意识的本源根脉。
(三)本源根脉的赓续和力量聚合
小说对于国家意识的本源根脉不但从传统承接走来,而且在现实中予以呈现,表现为信仰的一脉相承与新旧交替的力量延续,即以马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固守与以义马祭献为代表的前景希望都是国家意识本原思想的一致性承载。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马政司作为马时代国家特殊的官署机构,马户作为马时代为国家培育良马的专门人群,在国家日益衰微之时,以圉人、相马师为代表的马政司衍生人员,以韩骧夫妇为代表的马户人群,依然坚信良马的作用。这既是一种传统承接,是本源根脉的追寻,更是一种现实努力,是本源根脉的延续。也就是说,面对国家衰落的现状,将振兴国家的根脉与希望寄托于龙驹出世和国家之马的培育。这既是民众心中曾经国家强盛的原因要素,也是国家未来所向,以国家之马的培育为衰落的国家注入新的力量,救民于水火,挽狂澜于即倒,可谓从传统中走来,从承接中前行。
(四)承接与前行继续向未来发展走去
在《国家坐骑》中,本源根脉是始终一贯的,具体表现为小说不但从历史的传统走向现实努力,而且体现在以新思想宣传为代表的新生力量与新的精神基点之上。对此,小说给予了特别的情节安排。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声呐喊,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现在凉州,摆放于凉州从未有过的新知书店里,义马喜欢鲁迅的书,直直地盯着,想过读书,对着《呐喊》封面上的鲁迅头像又是嘶叫又是咧嘴笑。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新青年》,以及法捷耶夫进行人的巨大改造的小说《毁灭》一并出现在凉州新知书店的书架上,这不只是义马逛街时的一次误闯妄想,而是义马对新生事物的一种兴趣。新思想的传播让历史出现一道曙光,预示着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并以此凝聚为不竭的思想动力。义马的种种感知,彰显的是一种新纪元的开始,是一种历史必然发展的追寻,从而义马的形象在不自觉间得以提升,为义马所蕴含的全部思想内涵找到了落脚点。这是义马形象所包含精神内涵的再次承接与延续,亦是本原信仰根脉的永远所向。这表明义马形象所呈现的国家意识精神不但涵括在传统里,而且也具有现实的根脉,同样是民族与国家未来发展的根脉,是一种精神的溯源性继承。要而言之,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发展,国家要兴盛,民族要振兴,人民要幸福,就不能没有义马所蕴含的国家精神,亦即国家意识的本源根脉不能丢。以此探究,义马的头之所以被夹扁,表面是人头变成马头,讲究形似,以便人作马养,死后能够转世为国家之马,完成人为马生的使命,实质是为了禁锢义马的思想欲念,让他只为马生,不为人活,定格于传统的固化心理。然而面对时事变迁,新生事物的出现与新思想的传播仍然使义马的扁头里不自觉地闪现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并表现出一种人性的渴望与时代交替变迁的心理冲动,这就将表面的不合理转变为实质上的合理,将实质上的合理转化为永恒主题。
(五)牺牲精神是民族本源根脉的理想密码
义马形象所负载的牺牲精神,是承接传统国家意识及其本源根脉与继续前行的重要内核构成。不论是韩骧夫妇对义马的呵护与万般无奈,还是圉人对义马酷刑般的赋型锻造与自焚殉道,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羸弱的国家培育国家之马,以求民族振兴、国家强盛。这不仅是故事展开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信仰涅槃的必然前奏,更是孤独的精神追求不可逾越的文化认知。以韩骧夫妇为代表的马户为培育国家之马、践行存在于内心的国家意识,既牺牲自己又牺牲后代的命运归宿,其中所映现的就是为国而生、为民族而立的自杀式牺牲精神,以此在人性最深处透视出民众的本真和动能,使其凝固为一种永远的文化力量,进而折射出传统和现代的理想密码,显示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牺牲精神。正是这种以我为用、功成有我的力量聚合,使国家大兴所依存的国家意识在本源根脉追寻与继续前行印证中具有更高的价值意义。它是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不论任何信念意识的实现,都需要这种至高至深的牺牲精神做支撑。
三、在精神坚守中赓续生命价值的实现路径
鲁迅先生评价陶元庆的绘画,“他以新的形象,尤其是新的色彩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3]这句话用来解读李学辉和他的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及其义马形象也是贴切的。李学辉和他的小说世界,同样具有向来的魂灵:借历史文化民俗的抒写,以他新的形象,新的色彩寄志于民族精神内涵的挖掘。在冷兵器时代,民族的属相是马,它和英雄与生俱来,与国家命运血肉相连,浑然天成。因而以马所蕴含的血性精魂来彰显国家力量,寄托民族精神,并以此振兴衰退的民族与动荡的国家就成为现实的信仰需要与力量支撑。《国家坐骑》中的义马,就是马文化时代里民族精神的魂灵,也是以新的形象、新的色彩塑造的全新艺术形象。它并非以怪诞吸引眼球,而是具有文化记忆里民族与国家魂灵的原型意义:生命价值的最大体现是将存在于民众骨血里民族精神与国家精神内质为基础的国家意识转化为实现国家兴盛、民族振兴的有效路径。作者提出的正是这种魂灵的深厚底蕴,永恒精神以及如何在精神坚守里实现生命价值的命题。具体而言,《国家坐骑》在三个方面揭示了这个途径。
(一)龙驹的传统内涵
小说自始至终强调龙驹的传统内涵,即承接马文化时代所体现的国家意识。小说写道:随着相马师“真正的龙驹”的一声吼,“四野很静,马户们呼啦啦跪成一片。”[2]31一吼,一跪,开启了义马时代,燃起了天下大兴的希望。将这惊天喜人的一幕铺展开来,从韩骧妻子怀孕、相马师翘首以待、圉人固执坚守到龙驹出世、敲骨听音、相面观体,再从衣不裹体、睡圉床、头夹板、割卵净身,测马观相到走熊窝、行狼道、过火关及祁连逐鹰的兽养苦修,造就了义马飞身入湖,幻化成马,四蹄踩风,掠过湖面,一声嘶鸣如天上炸雷,无数匹马从天际涌聚,马群绕湖与化作龙形的意念动感表达。这其中时时贯穿着龙驹转世成为国家之马,能够为国效力的期盼。同时也艺术地再现了以圉人、义马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固化于内心的图腾式精神凝练出一份梦想,让没落衰退的民族国家支撑起一份美好的憧憬。而最终义马殒命及圉人自焚,使他们完成了祭献于国家的使命与发心,将精神坚守定格为一种永远的生命价值,为苦难的民族与国家实现强盛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二)义马的现实抗争
小说对于义马生命价值所包含的国家意识及其路径实现,不仅仅体现在传统承接的梦想与憧憬里,在信念里为国为民,更是放在现实社会的抗争里。其形式就是将义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拯救苦难的人来对待,使义马精神多出一个层面,形象更具立体感。诸如,凉州被屠城前,义马奔驰报信;屠城时,冒死救人;大地震时,同样拼死救人,凉州城中幸存的人大多受过他的救助。义马心中的信念不仅是成为国家之马,还是传统的责任与愿力,老百姓的当世悲苦。在现实中救民于水火,以至于在他转生成国家之马的仪式上,家家户户都为他接雨,人人感念他的恩德。这些情景将虚幻的路径转化为现实的努力,从而使渗透在骨子里的精神追求有了现实主义冲击力,并赋于义马一种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可谓义马生命价值所反映的国家意识之又一实现路径。
(三)龙驹义马精神的赓续转化
小说将国家意识的实现路径由一种精神信念接入现实的努力,并将这种现实路径向前推进,最终完成在精神坚守中赓续国家意识实现路径转化的目的。为此,小说将故事抒写伸向代表民族与国家未来前景的发展进步青年以及对新思想的宣传和对新信仰的追求上。特别是来到凉州的李德铭不但不为圉人、义马的表现惊奇,反而认为圉人身上有一种精神,义马就是精神的载体。他看到了圉人的自尊与高贵,看到了民族罹难、国家衰落后所需要的一种具有国家意识的信仰,一种具有国家意识的精神,且肯定圉人和义马也是在追求信仰。这体现在李德铭在圉人与马军长辩论时争辩义马是一种精神,精神要留给国家,中国缺的就是这种体现高贵国家性格的不屈不挠之精神,赓续的就是义马所包含的接连不断的民族精神,就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为国而生,为国而死之牺牲精神的永远坚守。义马与进步青年,圉人与李德铭的转化,强调的就是由国家之马到国家之民精神载体的转变,这是一种精神坚守中生命价值实现的新式路径,即使这种新的路径同样遇到挫折:常有“穿风衣”的人紧紧盯着,凡是见红的东西都被收了,书店的门帘只剩半幅,“知”字也只有了一个“口”字,书店被砸得稀烂,李德铭更是被“穿风衣”的人送进了监狱。但义马精神却被新精神的代表李德铭隐隐地留在心里,暗暗地揣进监狱,这就使义马形象具有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特别意义,成为实现国家兴盛、民族振兴的新型路径。
对此,小说在新知书店店员和老板李德铭的对话中给予了鲜活地表达:
“我李德铭在追求信仰,人家也在追求信仰。你不听那位老先生说国家之马时的口气,自尊而高贵。义马的事,我听人说起过,并没在意。听了老先生的言谈,看了老先生的举止,我对这个国家还是充满了希望。那位老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他让义马作了这种精神的载体,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2]228
再有《呐喊》的鲁迅木刻头像,《毁灭》封面的红五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小册子,既承上又启下,使传统固有的精神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思想内核,续接着一种从历史到当世到未来的路径变化。这种向往式的路径追求,完成了以义马为精神载体的传统路径与以新思想为精神载体的未来路径的复合式交接。特别是小说通过人们熟知的鲁迅形象以及鲁迅的深刻和尖锐,将其“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和民族忧患意识”,“彷徨中发出的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4],以义马眼中的鲁迅植入读者心中,将读者的思绪导向小说之外,引申出《呐喊》与《国家坐骑》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思考空间。《呐喊》是以国民劣根性入笔,披荆斩棘,革旧图新,砸碎旧观念,鼓吹新文化,批判的是愚昧和麻木,关注的是民族国家的命运。《国家坐骑》则是以传统信仰入笔,踏雪寻梅,执着坚守,执手本源正统,面向新的道路,解析困惑迷茫,寻求新式道路,同样紧盯的是民族国家的命运。二者看似相悖,实则包含的都是强烈的国家意识,是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刻骨思考和探索,自然地表现为由国家之马转化为国家之民的国家意识实现路径的赓续。
四、在苦难对撞中聚合命运转化的信念力量
李学辉的小说始终关注的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是对传统与现实的深刻思考。《国家坐骑》不但是传统与现实矛盾的书写与思考,而且透过镜头式的图景展现,对现实的苦难有更多的撞面式表达。这种思考凝聚为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直白式解读,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性,且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实的承接更具中断风险,人物命运形成断崖式转化。作者透过对撞性的苦难与断崖式的命运转化,直面民族衰落、国家不兴、社会混乱对人民的欺凌与侮辱及造成的悲惨生活,批判反思,透视人性,从另一面反映国家意识在本源根脉、实现路径的力量聚合,可谓小说主题内涵的又一层次。具体而言,通过四个方面的意境,呈现出小说主题内涵的这一层次:
(一)编年体的历史图景展现
小说如编年体历史一样展现混乱的社会与苦难的现实,“但是,这部作品却绝不是历史小说”[5]45,历史只是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只是人物环境登台入镜的舞台幕布。小说从光绪十九年,一转眼,便是“光绪三十四年的冬天,天空像光绪活着一样忧郁”[2]105,马街的马蹄铁敲出“宣统——宣统”的声音,光绪驾崩、宣统继位,而宣统一登基,朝廷更不像朝廷,县衙更不像县衙了,大清就像“老母兔大冬天怀兔子,生不逢时”[2]149,势在必然,又是一转眼,清廷内变、民国建立,而民国更像没足月就出世的小兔子,被袁世凯夺位复辟,接着的是新军阀现世,国民军横世,更有日寇入侵,镜头一一推于凉州。凉州就像变戏法一样,风风雨雨、变幻莫测,凉州人就像盲人行路一样,跌跌撞撞、不知所向。
(二)人民苦难的淋漓刻画
混乱无序的社会,相应的就是人民苦难。总体而言,曾经的精神寄养所马神庙被毁,马政司更像头上的一根头发,多了没人在意,少了也没人注意,现实的精神寄托义马也一次次处在刀口之下。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大清灭亡,皇帝成为记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政府无状,军阀乱世,府县频换。不论是清八旗,还是军阀的镇守军,马家的国民军,都是民众的灾难,一面是以军乱政,摧残杀戮,一面是政不系民,孤苦无依。不论什么信仰、什么精神,都抵不过军长的一句话。一个县长不如一支鞭子,凉州在马督军的鞭子下惊颤,也如王县长陀螺般晕头转向,以至于到了连衙门告示都没用,只有铁链才有用的境地。国家暗弱,凉州飘摇,民不聊生,扑面而来的是动荡中的冷漠与荒寒。小说中最为典型的描写有二:一是梅知县这个百姓的父母官只顾着加税增捐,祸害百姓,“放炮要炮捐,买肉要肉捐,买菜卖柴都要捐,换身新衣服也要捐,迎先人也要捐,拜神也要捐……”[2]115各色苛捐杂税琳琅满目,全然置百姓生死于不顾。就连旗人也是卖衣卖桌卖画,卖掉炕皮卖炕灰,卖光了祖先留下的东西,卖儿卖女。二是在天倾南北、地陷东西的大地震时,民众依然无依无靠,手握兵权的镇守使马廷勷言道:“只要兵在,一个凉州城毁了又算什么!”[2]178吩咐副官抢富户,掘地三尺,也要把金银财宝全拿来,不给,则杀。刀是用血喂饱的,兵是用银元和女人撑起来的。马家军过处,留马不留人,留驴不留头,稍有不慎,砍头就像切西瓜。刘志远的脸只有见到金子时,才灿烂起来,钱一到手,便抛下凉州城独遭灭顶之灾,西宁军见不到金银,就把女人们摁倒在炕上,完事便点了被子,在烤人肉不好吃的感叹里,看着女人们在火中翻滚。屠城、掠夺、烧杀、奸淫充斥整个凉州城,除过野蛮与屠刀,一切都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像是一切的混乱、劫难、灾祸、厄运、不幸都压在了凉州。“由此,可以说,《国家坐骑》展现了1893年以后西部凉州人民的灾难史。”[5]45
(三)人物命运的历史转变
在苦难的社会里,在灾难和野蛮,屠杀和掠夺,麻木与冷漠的重重挤压下,信念和挣扎,希望和失落,荣耀和痛苦的矛盾既显得顺理成章,又使人物命运形成大反转,凸现出一个鲜明的前我与一个后我,只是这个前我与后我不仅是故事发展使然,更是小说自始至终所蕴含的信念精神反思的结果。小说对于历史故事的铺陈层层涟漪,波纹相连,痕迹清晰,没有任何的断裂感。点点成线,线线成面,将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化以及人物的大波动、大恐慌在几乎静默中展露无遗。作者或通过人物对话,或通过人物所见所看,或通过物象征兆,将种种场景一笔带过,蜻蜓点水似的,在轻描淡写中点出即可,从不作宏大场景的叙述性过渡,并将历史演变与人物命运贯穿其中,使得历史叙事、现实刻画和人物塑造融为一体的主线完整地呈现出人物命运所坚守的为国为民的信念精神主旨。要而论之,《国家坐骑》这部小说,不论其浓重的根脉意识还是其精神坚守与生命价值的实现路径,最终都反映在国家层面的深刻反思上。作者是以信念为依托展开故事,并非以故事见长,而是以精神为寄托找到思想落脚点与新起点,是一部呈现信念力量,保存信念力量,凝聚信念力量,提升信念力量,发展信念力量的作品。
以此形成的前我与后我的人物命运,便具有了信念的对抗与反思的痛点。具体表现有五:一是义马命运。前我因是出世龙驹,国家之马,虽是人为马生,人作马养,却有高贵的身份,万般的呵护。就连宣传新思想的李德铭也将义马看作国家精神的载体,认为其接续着国家民族的本源根脉,命运光鲜而奋发。后我却被马户杀人,地震毁人,新军阀横行,国民军弄权所累,以人身之体与神骏“盖西北”比力,命悬一线,化成一堆灰,涅槃消亡。虽完成全部的使命,却落得个凄惨下场,使国家之马成为一种国家命运和人物命运的伤痛。二是韩骧夫妇因生龙驹而改变命运,由马户变成人户,得到无上的荣耀,命运达到峰顶,却因培育义马而导致人性遭受无情地摧残。面对义马兽养苦修,倍受煎熬,甚至痛彻心扉,又为维护国家之马的义马不受伤害,惨遭屠杀,在义马祭献国家之前,悲情而死,命运跌入冰点。他们既没有得到真正的尊严,也没能看到国家之马的光环,信仰与尊严在屠刀的血线里显得着实可怜。三是相马师为马而生,为龙驹而喜,为义马又时有恻隐之心,最终又口诵马经栽倒在过火关的火堆前,手攥《铜马相法》死于无声无息。圉人育马成痴、冷酷无情而又为义马转生为国家之马而自焚,成为悲情绝唱,如一缕轻风在视野中消失。其中命运的矛盾交织,风雨飘摇的不安,信念的苦难,坚守的痛苦,无不展示于读者眼前。四是马户群体,本是一心为国家喂马养马的底层人群,执着、善良,本份,可是一旦他们揭不开锅,便不接先祖,不拜马王神,即使韩骧一家将积存的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勒紧裤腰带挨饿,也不参加义马的烙印。游街时,没有一个马户出门,连他们都不爱义马,被饥饿和捐税封闭了心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为养育龙驹而沦为扁头的马户,一方面在坚守信仰,极具悲情色彩,另一方面在马鞭和马刀的驱使下组成了“扁头营”,成为杀人工具。
小说对马户的杀人场景作了惨绝人寰的描写:
“大街小巷乱窜的扁头们杀人杀得手软。看着满大街横躺斜倒的人,他们直怨马家军下手太快,没把这些人全留给他们。他们便在街上寻巡还没断气的人,看到一个,一个上去砍一刀,另一个扑上去再戳一刀。”[2]194
五是人们可以为了感恩义马而家家户户接雨,可是一旦对自己没有了利益好处,便也“连自己都顾不住了,还管什么神啊鬼啊的!”[2]279只有风陪伴着义马和圉人的尸骨,连义马转生的舞马人也将马舞服扔进灰堆消失了踪影,无人再去关心为了国家百姓而献祭的圉人与义马。人性在这里显得有些赤裸,所谓世态炎凉,文化断裂,生命价值不存,大概便是如此。在小说凛冽的文字中,常会感到彻骨寒冷。对死亡的恐惧,让马户无法善良,这与接雨的本心形成巨大的反差,人像动物一样,本能地要急于逃避责任。于是,他们的世界里,太多寒光闪闪,太多明晃晃的丑陋与不堪。他们维护不了自己的信仰,也无法保持自己的善良。在信仰追求里,从来没有哪个理由,如此让人心碎,小说构建的信念故事一下子塌了天,成为虚空,如马神庙一样坍塌,构建的生命价值一下子陷了地,成为荒诞,似马户举刀杀人一样怪异。
(四)国家命运和人物命运的对接升华
义马的宿命是国家之马,他为国家的兴盛而受供养,通过祭献国家而转生为国家之马,为国家服务。马户的宿命是为国家养马,这是一种制度体系的存在,为国家的强盛而献身。相马师、圉人的宿命是为龙驹而生,为义马而活,为国家之马而守,但是他们的结局却都以命运急转、生命终结收场。就连认同义马精神、宣传新思想实现新路径的李德铭也被县长留给了举着屠刀的马军长,只能被迫在监狱里守护神一样地揣着自己的所有信仰和精神。马户的前后反差更是强烈,不但成为了杀人工具,而且比军阀还残忍百倍,他们颠覆了自己的宿命,走向了本心反面。人物命运在历史的风风雨雨、飘飘摇摇,社会的动动荡荡、跌跌撞撞里,如几条平行线,或明或暗、或隐或显,也如交叉成网,各自前行,又始终脱离不了这条线和这张网,只剩下凉州城在风中摇摇晃晃。
然而,正是这种人物命运的断崖式转变,让苦难对撞与命运转化得以贯串,让传统与现实得以对接,让现实与前景得以赓续,让信念信仰与人性本真得以融会,使读者完成评判态度的自觉转变,使觉悟与由国家之马到国家之民的契合具有了文化沉淀的根本意义,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分解式视角定格在最稳定的精神结构里,以新思想的传播反省国家命运和人物命运的转化,使旧传统与新生力量达到两存的目的,并将其聚合为精神信念与生命价值的全部力量。
五、结语
《国家坐骑》以奇异的题材,独特的视角,把传统与现实、国家与个体、文化与地域、信仰与归宿融为一体。通过国家社会层面的动荡与普通民众层面的信仰交织、撕裂、对抗和挣扎,将信念在飘摇中坚守,悲情在灾难中丧失,命运在绝唱中涅槃,路径在新思想中升华的各类表达展露无遗,揭示特定人群的命运归宿。小说在传统里追寻信念,在批判里推演历史,在呐喊里解析精神,在坚守里聚集力量,深刻地体现了国家意识的主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