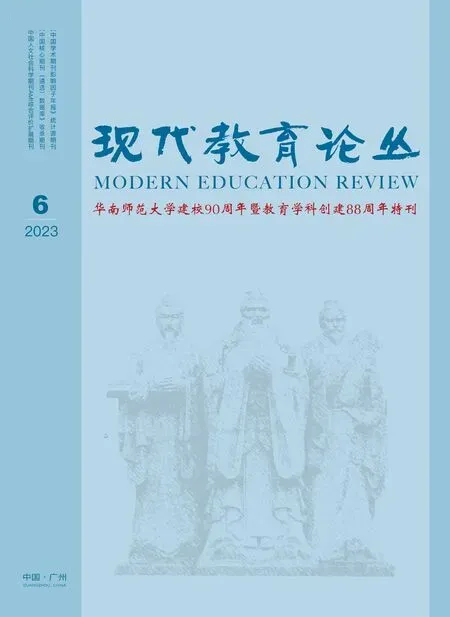林砺儒教育思想的逻辑演进
李盛兵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林砺儒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活动家。作为教育理论家,他东渡日本高等师范学堂学习教育学专业,回国后在北南两大师范高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课程,研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发表100 多篇教育学术论文,出版《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教育危言》《伦理学要领》等专著。作为教育活动家,他生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终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而奋斗。他批判儒家教育和国民党反动专制教育,提出进步教育要为进步政治服务,要对旧教育实行革命。他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附中校长、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广东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厦门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及副部长等职,不畏反动势力的迫害,坚持追求救国真理,大力主张教育的大众化、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化,鼎力开展进步教育,力求实现教育的根本变革。由于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卓越的教育研究和进步的教育革命工作,他受邀以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员身份(正式代表15 人)参加新中国首届政治协高会议,并作为唯一一位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在大会发言。林砺儒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扬光大。
今年华南师范大学适逢建校90 周年,其前身是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而林砺儒先生是华南师范大学前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的创始人,首任院长。在学校大庆之际,研究和传播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既是一种对先辈的纪念,也是献给校庆的礼物。林砺儒教育思想内涵丰富,论题广泛,包括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民主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教育目的、考试等。本文主要遵循其进步的社会才有进步的教育,教育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进步的教育是人格教育,培养进步的人——进步人的培养需要进步教师及师范教育这一逻辑进阶来展开研究和分析,以期反映林先生的进步人生和进步教育思想。
一、追求进步的一生
林砺儒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追求进步的一生。他意志坚定,志向明确,为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而奋斗。他终生从事教育事业,“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他不断追求进步,是一位勇于探索和坚持真理的教育家”[1]。他的一生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一)广东-日本求学时期(1889—1918 年)
林砺儒1889 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广东信宜人。他幼年丧父,母患癫痫,靠祖母、叔伯父养育成人。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1911 年在高州高郡中学堂毕业后受聘于信宜县中义学堂任教。期间,他动员并资助已婚堂侄女上学,为之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中增设女子部作出了早期实验。他说:“妇女读了书,才能够解放,没有知识,没有本领,只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2]这一段教学时间虽短,但体现了他男女平等教育的进步思想和实践。
1911 年,他获取公费留学名额,前往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筑波大学)主攻师范教育专业,并立志献身教育事业。这与当时其他留日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大不相同。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除了学习日本教育理论和考察教育实践外,还广泛学习和了解欧美教育思想和教育发展实践,尤其重视裴斯泰洛齐教育理念和各国师范教育发展。他的思想还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反封建反殖民的进步观念,为回国后开展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教育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8 年3 月林砺儒学成回国。
(二)北师大任教时期(1919—1931 年)
这是林砺儒的第一个“北京时期”,工作单位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以及后面更名的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这一时期,他初步形成了师范教育思想和中等教育思想,参与反对反动军阀统治活动。
1919年4月,林砺儒受邀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讲授“教育概论”“伦理学”“近代教育思想”“西洋教育史”等课程,传播国外教育新思想和新实践,调查和思考中国教育现状与发展路向,教导学生要独立思考,立志笃行。此外,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支持学生开展平民教育,反对北洋政府逮捕和屠杀游行请愿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在报纸上撰文抵制日货和倡议组织“使用国货同志会”,参与进步教授组织的索薪运动。[3]1471928 年,国民党统治北平,北平九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成立第一师范学院(次年独立设置为北平国立师范大学),林砺儒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艰难办学。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面临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生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国民党政府委任新校长加强学校控制,他被解聘,回归养育他的广东,开始了他的第三段人生历程。
这一时期,林砺儒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校长。从1922 至1931 年,他以一位卓越教育理论家的思维大胆思考和推进变革,把附中办成国内知名中学,培养出钱学森等一大批优秀人才。据说,梁启超还为年家子上附中找过关系,为此,林砺儒专门撰《子弟入学之请托运动》一文,公开答复和批评这种腐败行为。林砺儒在附中任校长10 年,比较突出的工作和业绩有两大方面。
一是在教育理论方面,他阐发了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的关系以及中学教育的本质。他特别重视设立附中对师范教育研究和师范生培养的重要作用。1930 年,他公开发表《附属学校之使命及其与师范本部之联络》一文,通过回顾欧美师范教育与设立附属学校的关系,提出“附属学校系师范教育之母”的观点。关于师范学校和附属学校的关系,他形象比喻“有点像骨和肉。若师范没有附属学校,就等于没有筋肉的枯骨。而附属学校若离开师范,就等于无骨的一块肉,已失掉其作用”[4]19。关于中等教育的本质,他借用教育即生活,提出教育即人格的成长。他说:“我认定理想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决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若有人问我中学毕业生做什么,我就说也不为士,也不为农,也不为工,也不为商,是为人;也可为士,也可为农,也可为工,也可为商;而且为士而士,为农而农,为工而工,为商而商,若不认定全人格的陶冶,而老早赶紧把未熟的少年铸入于一定职业之型,以充社会之工具,作吃饭的机器,是误认社会为目的,人格为手段,且误会人生目的就是吃饭。这种短视的教育主张,我老实不赞成。”[5]他反对将中等教育作为高等专门教育之准备(现今是追求高考升学率),提出要对中学生施以适合少年时期的趣味教育、活力教育以及人格生长教育。
二是教育实践方面,他做了三项改革,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坚决贯彻推行当时教育部推进的中学三三学制,为全国中学学制的现代化积累了经验。第二,在推进新学制的过程中,组织教师编写初一至高三各学科一整套教材。这套教材被教育部推广到全国各中学并一直沿用到1949 年。第三,提倡男女同校,1922 年在附中设立女子部,招收一个女生班。在当时,国内招收女生的学校仅有湖南长沙的岳云中学、广州的执信中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3]151-153
(三)主政南方师范教育时期(1931—1941 年)
1931 年秋,林砺儒接受进步教育家许崇清校长的邀请到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开启了第二次“广东时期”。1931—1941 年11 年间,在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之下,林砺儒开启了艰难的办学历程,主政南方师范教育,为广东师范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山大学,他讲授“师范教育”“教学法”等课程。据他的学生阮镜清回忆说,他“在理论上阐明师范教育对振兴教育,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激发国魂,培养建设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民族富强的重大作用”[6]。次年他兼任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校长,并参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筹备工作。1933 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成立,设立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学院。其师范学院由市立师范学校转变而成,设立文史系、数理系、博物地理系,培养中学教师,并开设附属中学。林砺儒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教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师范学院(简称勷师院,下同)的成立,意义重大,被高觉敷称为“与北高师南北对峙,可称‘双绝’”[7]。因为当时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沈阳五所高等师范学校都根据教育法令改为普通大学,仅存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此后,勷师院又历经八更其名(勷勤大学教育学院(1935)、广东省立教育学院(1938)、广东省立文理学院(1939)、广东省文理学院(1950)、华南师范学院(1951)、广东师范学院(1970)、华南师范学院(1977)、华南师范大学(1982)),遂发展成为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
林砺儒在勷师院前三次更名后都任院长。不管校名如何变化,他都坚持举办师范教育,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中学教师为己任。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抵抗日本侵略行径,招聘进步教师,开展进步教育。1933—1941 年8 年间,由于日本的侵略,林砺儒带领学校五迁校址(广西梧州、藤县、融县、广东乳源、连县),保护师生和办学设备,顽强办学,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为社会进步培养进步师资。因此,学院所在地连县东坡被人们称为“小延安”。[8]42由于他进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第二次被国民党当局解聘。
在这一时期,林砺儒主政广东高等师范教育,虽陷战乱之中,却坚持真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显现出突出的进步性和战斗性[8]36[9],知行合一。他身处革命与反动、战斗与投降、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时代,他充满激情和坚定地选择了革命、战斗和进步,追求和奉行三民主义和民族解放。在艰苦的办学过程中,林砺儒笔耕不辍,发表了《日本师范教育的特点》《关于指导师范生进行教学实习的意见》《从批评中学新法令说到未来改造》《中国师范教育之检讨》《对于中学课程中军事训练的一个建议》《中国教育与国难》《民族建国与国民教育》《对于读经的意见》《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等作品,批评教育当局用繁重的课业负担和读经限制学生的进步思想和运动。他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中写道:“民族抗战的烈火,炼出了我们这支青年军。走遍了险阻,历尽了艰辛,却淬砺了奋斗精神。我们要探索真理之光,我们要广播文化食粮,哪怕魔高十丈,恶战千场。同学们,挺起胸膛,放大眼光,这是我们的校风,这是我们的大勇。”这展现了他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教育精神。在师范教育研究上,他指出中国师范教育成功很少,提出师范教育既要重视学艺(所教专业),又不能偏废教育专业训练,在教师人格训练上不能仅要求教师具有圣贤品格,而是要提供使其安心向上的条件,别无后顾之忧。[10]至此,他形成了完整的师范教育观。
(四)桂林-厦门著书立说时期(1941—1948)
1941 年10 月,林砺儒赴桂林,开启了他第四个人生阶段。他先在广西教育研究所任导师,次年任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继续未尽的师范教育事业。他依然聘任知名的进步教授,接收被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勒令退学学生,在桂林师范学院形成了严谨、求实、民主、自由的学风。[11]在桂林师范学院,除了担任行政工作外,他亲自教学,讲授“教育概论”“中等教育”“伦理学”“教育哲学”“西洋教育史”。他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教育危言》《教育哲学》,发表了《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成年人凭什么而指导青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八·二七路线——纪念三十二年教师节》《五四运动的评价》《筹措国民学校基金问题》《儿童保育与人性改造》《养士》《漫谈课外活动的指导》《世界师范教育运动史之战斗性》等影响甚大的文章,振聋发聩。他不仅自己做研究,还鼓励老师们开展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广西民盟政治活动,与其他进步人士一道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中。他多次收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称李公朴、闻一多就是他的下场。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身体状况不佳,他离开桂林,回到广州。
1947 年,他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授,以马列主义观点讲授“国民教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并积极支持进步爱国学生运动,成为该校最受爱戴的教授之一。[12]这一时期,他仍然积极写作,发表了《对于传统思想的几种态度》《从教育救国说到“救救教育”》《教育能否防止战争及剥削》《如此中国,如此中国教育》等文章。他指出:自京师同文馆(1862 年)开始所采用的西式现代教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教育机关越来越黑暗,师道越来越陵夷,作风越来越阴险”[13],直呼“救救教育”,批判旧教育,提出教育为进步政治服务。
(五)参与新中国教育管理时期(1949—1977 年)
1949 年4 月,林砺儒北上北京,开启他第五段为进步社会服务的精彩人生。他作为教育界代表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委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政协委员,任新中国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1950—1952 年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 年升任教育部副部长,参与新中国教育管理工作。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坚持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等教育研究”两门课程,体现出他“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的一贯品格。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林砺儒主持起草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为建立新中国现代中学体制和师范教育体制做出了贡献。他尤其关心师范教育的发展。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校长期间,毛泽东主席约他谈话,要求扩大办学规模,培养更多中小学教师;到广东视察时也建议广东省政府重视发展师范教育,争取把华南师范学院办成重点院校。
林砺儒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仍然勤于思考和研究,发表了《在社会转型期中教育的任务是甚么?》《从教育的角度看白皮书——在北京师大教育学院白皮书座谈会发言》《中等教育的两个问题》《说“新师大”,讼旧教育》《了解少年儿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给教师们贺教师节——尊师观念的改造》《怎样对待学校考试》《师范教育问题随笔》等文章,指出新中国的教育任务是开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培养他们参政的觉悟、知识和能力,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教育要大众化和现代化。这一时期,他的教育研究主要聚焦社会转型期如何扬弃封建的、殖民的、资本主义的旧教育,实施为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他的教育思想是革命的、进步的、人民的。
二、进步社会与进步教育
林砺儒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从社会出发的,认为社会的进步性决定了教育的进步性。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教育对社会的发展作用是间接的,是为一定的社会服务的。这反映了他教育思想的辩证唯物史观。
在论述社会与教育的关系时,他形象地指出:“自从教育成了国家的公共事业以来,某一国某一时期的教育,必然反映着那个国家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国民教育,对于政治,真是如影随形,响之随声。”[14]143在讨论社会对教育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他总结到:“进步的政治必产出进步的教育;颓废的政治必不能完成进步的教育。进步的教育可以助成进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颓废,更不能为颓废的政治做掩饰。”[14]153封建政治下的教育必然是封建教育,资本主义政治下的教育必然是资产阶级教育,三民主义政治下的教育必然是三民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政治下的教育必然是社会主义教育。反动政治下的教育必然是反动的教育,而不是人民的教育。他在这里既阐述了政治对教育的决定性作用,又分析了教育对政治的作用是协助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此,他对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改良主义思想,是有害的。在社会决定论思想下,他进而提出普及国民教育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即经济的条件、民众生活的条件和政治的条件。只有生产力发达了,民众文化生活需求增加了,民权政治发展了,普及国民教育才能够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工业没有现代化。因此,他提出:推翻反动的政治,建立进步的政治和发展的经济,才能发展进步的教育。他在1949 年11 月撰文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教育的政治的条件是存在了,可是还不够力量。广大的群众虽然需要文化,可是还不能掌握着教育文化......今天中国的教育工作要把专为广大群众而设的文化教育列为第一位。”[15]208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还要进一步建设已经存在的进步政治,发展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唯有如此,中国的进步教育才有可能。
此外,他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指出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间接作用。首先他认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历史的社会的必然事实,倘若不能自觉地为进步政治服务,便必不免不自觉地为反动的政治服务,这里断没有中立的余地。尤其是师范教育,这种教育的自身就是一种政治,办师范教育而又想避免政治关系,是千古笑话。”[15]229-230他在《中国教育与国难》一文中专门论述了“教育救国的间接性”。他指出:“教育的对象,从个人说,便是人格。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可以肆力生产,可以效命疆场,可以从事职业,可以研究学术。总括地说,要人人都可以在社会文化生活当中尽一份职责,社会才能生长不息。于人格陶冶之外,教育别无直接救国的捷径。教育的对象是文化生长。教育若能陶冶人格而推动社会生长,便算尽了能事,此外实在别无捷径。”[16]虽然他反对“教育救国论”,但是他提出教育通过培养追求民主、自由、真理,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大丈夫”,为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民众生活条件的进步服务,为人民服务。
三、进步教育与培养进步的人
发展进步教育是林砺儒的主要教育思想。在他看来,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是进步的教育。一是要配合进步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去办教育,通过进步人才培养加强政治和经济建设。二是在反动、腐败的政治环境和不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要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培养铁骨铮铮的“大丈夫”去开拓,培养刚直不阿的勇士去改造,从而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为他指出办好教育的先决条件是要改造教育背景,“只有‘认真着手改造社会’这个假定执行,才可谈教育。”[17]所以,要培养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进步青年。20 世纪初,他在北京高师任教时就对学生说:“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
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林砺儒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论述,这问题也是他一如既往关注的核心问题。罗佐才对林砺儒教育目的观做了历时性梳理,认为其观点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即从培养“健全的人格”到“大丈夫”再到“有身手而又有革命头脑的劳动者”。20 世纪30 年代,林砺儒认为教育的效能在于教人生长,养成人格,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他指出,“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学生学习的是他们的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18]“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19]抗战期间,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发展了他的教育目的观,指出“现在抗战建国,教育当然要培植大丈夫,而不要奴才。”[20]那什么是大丈夫呢?他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之大丈夫,也是孔门的德育目标。他们有志气,有理想,有主张,个性坚强得很。由此,他提出培养“大丈夫”的方法要发生改变:对走上军阀、权贵门路,甘做爪牙的青年学生要开除;对参与学术讨论、辩难、求真理、明是非的学生要鼓励;老师的学说、讲义要任由学生怀疑批判,绝不忌讳。这样的大丈夫,才能够参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旧社会,有勇气建立新的进步社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他提出要配合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培养能够运用政权的群众和手脑结合的劳动者。为了培养“健全的人格”、“大丈夫”和“有身手而又有革命头脑的劳动者”,他提出必须要用多方面的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作为教学内容,来武装年青一代。总之,他主张进步社会需要进步教育,进步教育必须着眼于培养进步的人才。
四、进步教师与进步师范教育
从逻辑上说,进步的人才需要进步的教师去培养,进步的教师则需要进步的师范教育去培育。林砺儒教育思想不仅包含这个逻辑,而且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专业是师范教育,回国后从事师范教育管理和研究40 余年,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师范教育思想。
首先,他把教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教员与军官的地位相提并论,认为教师承担为国家培养各种保卫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光荣任务。由此,他提出国家要保障教师的政治地位,专门出台教师待遇法,保护教师的俸给、向上修养的机会以及教育子女之可能,这样既能避免影响国家前途的威胁发生,又能更好地发挥教师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作用。
其次,他重视发展进步师范教育。要培养进步教师就要发展进步师范教育。早在1930 年代初,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沈阳五所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普通大学而仅存北平高师之际,他主张举办独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并出任校长。在培养目标上,他强调培养“有守有为”的教师。为了培养进步师范生,他积极聘请进步教授如张栗原、郭大力、尚仲弄、蒋径三、李平心、高觉敷、陈守实等来学校授课。在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之际,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今天新师大无疑是要努力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培养人民所需要的中等学校新师资。”[21]这就要求改变服务对象,从特权教育转到人民路线中来,培养人民教师。
最后,他在研究国内外各个时代师范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出师范教育的三个特征。(1)政治性特别强。他说各级各类教育无疑是为政治服务的,但不是只凭做出的事或物服务政治,而是直接培养后一代新人。师范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最可靠的教育工作者。(2)知识要特别丰富,要保证毕业生饱学有识,师范学校的知识教育要比同级学校高出一头。(3)要有专业的教育训练,保证毕业生成为内行的教育工作者。为此,他特别重视师范学校与附属学校的密切关系,认为附属学校是师范教育的完成处。他指出,“要之教育断非冥想之所能成功,不论研究教育或学习教育,皆不能离开实际教育儿童。”“师范与附属学校之关系,有点像骨与肉。若师范没附属学校,就等于没有筋肉的枯骨。而附属学校若离开师范,就等于无骨的一块肉,已失掉其效用。”[4]18-19二者关系密切,彼此联络、互助、互惠。
综上可见,林砺儒一生追求进步,把“进步”二字融入他的理想、思想和事业中。他从建设进步社会这一理想目标出发,一方面积极参与反对社会反动势力的斗争,聘任思想进步的教师,办进步的师范院校,培养“健全人格”的公民、“大丈夫”和“有身手而又有革命头脑的劳动者”,为建设进步社会做贡献;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进步的社会才有进步的教育,只有进步的教育才能培养进步的学生、进步教师的培养需要进步的师范教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横跨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时代,对我们理解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些教育大命题,至今仍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