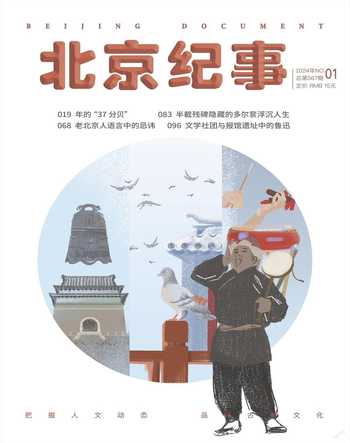声音艺术:韵与现场
后商

“音顾: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声音创作三十年回顾展”展览海报,声音艺术博物馆
2023年5月18日,声音艺术博物馆在宋庄艺术区开幕,这是最早一批“类博物馆”,次日对外开放。近年来,秦思源主持了多个声音项目,随着北京宋庄艺术发展基金会创始人洪峰的加入,一座声音博物馆就构想了出来,并成功落址于槐谷林艺术花园。
5月19日,由秦思源、王婧联合策展的“音顾: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声音创作三十年回顾展”在声艺空间A、B、C开幕。5月20日,由葛宇路策划的“天上人间”在声活中心开幕。
2005年,还在英国使馆文化处工作的秦思源策划了“都市发声”项目,他邀请四位音乐家来到北京,进行声音创作。彼得·科萨克(Peter Cusack)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征集“你最喜欢的城市声音是什么?”发展出了他对声音艺术的独特嗅觉。最终,他制作成了声音专辑《彼得库萨克最爱的北京声音》(Favorite Beijing Sounds),从天安门升旗声开始,电报大厦钟声、景山公园老歌、鸽哨、街头哭泣声、“你吃了吗?”招呼,终于天坛公园环境声。“都市发声”引发了很热烈的反响,这促使秦思源更专注于声音艺术。
1975年,四岁的秦思源第一次来北京。那之后他多次往返北京、伦敦,并于2002年彻底定居北京。什刹海体校、北京师范大学,标记着秦思源的重要人生节点。1990年代初期,秦思源和于微、于伟民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穴位乐队,这是他与声音对话的最早源头。
近年来,秦思源还策划了很多声音项目,比如“声坊”声音总站”“园音”“声击”“时言”。在秦思源的构想中,声音是人与社会、人与记忆之间的通道。在陈西滢与凌淑华旧居被改造为史家胡同博物馆时,作为后代的秦思源受邀参与,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讲声音的故事。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一个小房间里,陈列着他收集来的市声,驼铃声、吆喝声、鸽哨……很多声音都采自老北京人,其中杨德山几乎复原了所有北京吆喝。
旧时,北京大街小巷活躍着的是“五行八作”的流动商贩、手工修理者、服务业者。有的吆喝声相当具有滋味和活力,比如夏天卖西瓜的吆喝:“吃来呗,弄块尝,冰镇的西瓜脆沙瓤;三角的牙儿,船那么大的块儿,冰糖的瓤儿,月饼的馅儿,芭蕉叶轰不走那蜜蜂儿在这儿错搭了窝,沙得您的口儿那甜那,两个大嘞,吃了呗,弄块尝……”
除吆喝外,还有响器。有的行业兼有吆喝和响器,有的行业只有响器,比如典型的“八不语”,卖掸子的、修脚的、绱鞋的、劁猪的、锔锅锔碗的、行医的、剃头的、粘扇子的。老北京响器大致可分成梆、鼓、锣、铃、铁五种。例如,卖豆腐、卖香油的小贩专门用梆子声来吸引顾客,顾客通过辨认梆子的质地、敲击的节奏,分辨这家是做什么买卖的。卖冷饮、瓜果的使用的是小小的冰盏,将碟形碗夹在指间,几指配合使其发出“嘀嘀、嗒嗒”声。
震惊闺、平安梆子太平锣、绒线拨浪鼓自然是老北京声音的主调之一,但如今被津津乐道的主要还是虫罐里的虫声、鸽哨声,所谓的市井声音。这些市井文化,生存的土壤是清朝及民国的旗人悠闲、快哉的娱乐生活。很多旗人吃俸禄,培养出了很多闲心,养鸟、鸽、蛐蛐,也玩书法字画、戏鼓词章。
人们对声音的探索和人们对声音的依赖完全不成正比。 1787 年, 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克拉尼(Ernst Chladni)在撒有细沙的黄铜板上放置一架小提琴,他拉动小提琴,细沙在声波的作用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和图形。这些克拉尼图像产生的原理很简单,震动发声,声音创造了图像。后来,瑞士自然科学家汉斯·詹尼(Hans Jenny)将其命名为音流学(Cymatics)。“Cymatics”源自古希腊语“κῦμα”,意为波浪。
直到1816年,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才推导出一个声速公式,它论证了声速只取决于它所经过的介质的密度和弹性。
发明家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创造了一个简易的声音增加设备,并将其命名为麦克风(microphone),这是麦克风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麦克风的应用改变了环境中的声音,因为麦克风所发出的声音与人声总有很多不同。在音乐方面,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与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等歌手率先对着麦克风唱,麦克风的加入使他们的歌声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和升华,比如音乐中间或传来的呢喃低语,以及最彻底的呼吸。
现代剧院和舞台,收容了很多专业的声音设备,比如扩音器、音响,它们通常陈列在空间里的适当位置,以保证声音的极致呈现。今天,声音的存在主要被分配给剧院这样具体的现场,观众入席听交响乐、民谣歌曲。不妨将它们统一命名为声音的艺术,借助声带、口腔,以及姿势,成为可供欣赏的展演、表演。经历了三年线上生活,人们比以往都要渴望面对面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几寸之隔的那人所传达的声音。他举手投足间留下的声音,她眼睛眨动时的声音,他们辩论、低语、呼吸混合在一起的声音,只有这些声音真正的近在眼前,我们才能复活那些暗淡的事物。
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中,声音也不曾缺席。《海浪》是有49台电风扇同时运作的矩阵,这个矩阵占满了一个50平米的地面空间。当所有电风扇同时启动,它们的扭杆的机械声几乎成了唯一的声音,因为从风扇吹来的风声总是相互抵消为很低的声音;而在它们被抵消之前,高速旋转的扇片带来的风声成了这个环境最重要的织体。《海浪》最早一次出演是在2016年上海双年展。
某个夏日午后,殷漪被风扇声所吸引,突发奇想:“如果两个电风扇相互遇到,会是什么样子?”尝试之后,殷漪发现,风扇吹来的两股风编织成了某种不定的韵律,比如两股风汇聚在一起时会相互抵消,成为空明的声音。殷漪保持着随时随地采集声音的习惯,他称之为实地录音。殷漪发现,在大都市进行实地录音,最吸引人的是,如何借助声音的实践,聆听一座城市,甚至触及某些隐秘的部分。他较新的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也很耐人寻味。
耿建翌的《完整的世界》以四台显示屏中的声色故事,构建出一个相当完整的空间;曾是“双飞艺术中心”小组一员的林科自比“视觉信号的收集者”,制造出一个围绕观众做圆周运动的声点、动点;《我的生命飞来飞去》将各种发声的器械以跷跷板的方式连在一起,使其长久地运动下去。
通过《扩音现场:一个私人空间的交叉回声》,施勇利用设备将公寓房间里的声音放大,并在大倍率的声音中生活了一个月。冯晨的《光的背面》借用百叶窗和声音的关联,用声音的高低有无开启或关闭百叶窗,从而将观众的感知与空间的律动融为一体。
在音乐厅,细致排布的环境与音响使观众能享受到更宽阔的声音;走到室外,声音被拆散,同时也被解放,人们听到蝉鸣、树叶摇晃声、脚步声,以及难以枚举的环境声;在地铁站,所有乘客的声音都被这架机器所覆盖;而再次进入室内比如卧室,声音看似像短小的虫儿那样消散了干净,但它们却更加逼近我们的心灵、记忆。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