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魂的摄像机
刘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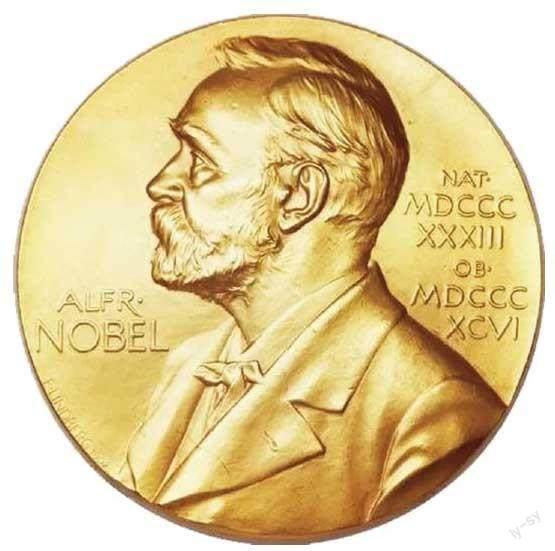

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下文称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现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毕业后做过老师、记者,这些职业经历让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风格更加纪实。
在她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这部非虚构作品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上百位在切尔诺贝利爆炸事件中的亲历者、幸存者,最终以“口述史”的方式整理成书。这本书是当代罕见的纪实文学经典,极具新闻价值。
新闻写作与非虚构文学创作有相似,更有不同。它们都属于非虚构写作范畴,都源于事实,都尽可能地用实地采访、调查的方式接近事实。不同的是,新闻写作更倾向对事实的选择和记录。而非虚构文学是—种写实性的文学体裁,在事实的基础上要用文学的方式完成艺术化的表达。相比新闻写作,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叙事方式更加多样化,它借助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经验和手法,完成调查、研究和创作。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非虚构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作家经过提炼和淬火的心灵写作,是作者灵魂与人类精神的展现。”
本文通过研究这部完成于上个世纪末的作品,追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背后的创作观念,体会她在创作时进行的各种艰难尝试,为当下的新闻写作收集浓缩的养料。
冲击的涟漪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怎样通过口述者的言语构筑起一个叫切尔诺贝利的世界的?她选择了哪些人?为什么这样选择?又是如何选择的?
作品中的近百位口述者绝大多数是平凡的普通人,这些悲剧的主角出现在媒体上的机会很少,“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在《谎言与真相》这一篇章中,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口述)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作品中借口述者的叙述为事实画像。口述者们的处境是相似的,看着身边的人不断病倒、离开,他们的疑惑、痛苦、愤懑与悲伤长久以来没有任何出口,知情者遵守保密原则,没人为他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时选择了涉事各方:有被蒙蔽的百姓,有政府选派的执行领导,有苏联政府的护卫者,有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有科学家(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等。通过他们,读者得以了解当时政府的政策是怎样形成并如何执行的。这位接受采访的科学家说,他始终无法理性地叙述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
他对接到的第一个任务的描述生动至极。他要将一笔钱分给三十五个寡妇,他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特指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后处理善后和融毁反应堆核心的人)。“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他为这个问题辗转反侧。每一个寡妇都有自己的境况,有些已经生病,有人需要抚养四个孩子……这位科学家做不出这道生活上的数学题,最终只能把钱平均分配给这三十五个寡妇。
当人面对巨大的灾难而无法了解真相,而巨大的悲恸又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当生命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时,这位科学家尝试用科学来衡量,用理性来认知,却以失败告终。生命的意义无法量化,每个牺牲的生命都无法重来。
这位科学家还接到了组建切尔诺贝利博物馆的任务,他想起了一位哭泣的寡妇。她愿意用亡夫的奖章、奖状、抚恤金换回她的丈夫。她号哭了好久,最终把奖章、奖状留给了博物馆,连同她丈夫的名字。每当科学家摆设这些奖状时,耳边似乎都回荡着她的哭声。
谈到亚罗舒克上校,这位科学家说:“只有等他死了,才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但他还活着,只能躺在床上等待那一刻的到来。他一贫如洗,做不了肾结石手术。亚罗舒克上校是一位放射化学家,他曾经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凭一双腿和辐射剂量计勘测出高辐射地点,把它们一一标注在地图上。“政府彻头彻尾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
同样被当作机器人的还有三十四万士兵,他们被派去清理反应炉屋顶,他们都是年轻人,也都是牺牲品。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核爆炸,政府在士兵中征集自愿去打开排水管活门的人,保证提供汽车、公寓、别墅和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科学家说,这些无名小卒都过世了,他们不是冲着物质保证去的,他们最不看重的就是这个。而是他们被教化成要从死亡和牺牲中换取人生的角色和意义,他们因此而去赴死。
这部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爆炸发生后的切尔诺贝利,游荡着各种人。
时间捕手
全书的序幕《孤单的人声》和最后一篇《孤寂的人声》在内容上首尾呼应。它们分别是两位有着相似经历的妻子的讲述,她们的丈夫都执行了致命任务,她们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并在超乎理性之爱的驱使下陪爱人走过强辐射后的临终一程。
在《孤单的人声》这一篇章中,口述者露德米拉的讲述自然地穿插着她和丈夫瓦西里甜蜜的新婚生活,口述在时间线上的跳跃,让读者更能体会她一生难以痊愈的伤痛。讲述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开始。在露德米拉的讲述中,所有和瓦西里有关的细节她都以小时为单位进行。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没有把她时常穿插的对往日幸福时光的回忆以及讲述瓦西里的重叠的部分按照时间顺序理性地规整排列,而是保留了这部分,这样读者更能感受到露德米拉的注意力只围绕着瓦西里和不随时间改变的爱。
“當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是这篇口述的咏叹调,重复了四次。
有灵魂的摄像机若隐若现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有一个鲜明的个性——隐去“我”。所有的表达、观点、感叹、神情都来自口述者。作者成为记录者,不只记录口述内容,还包括口述者当时的神态、表情和动作:开始哭、沉默、停了下来、再次沉默不语、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对于一般的采访者而言,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很容易被忽略,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会对每一个口述者做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她不是出于猎奇而采访,她关切这些有着独特體验人群中的每一个人,关心他们的生命和灵魂。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像一架有灵魂的摄像机,记录下另外一架有灵魂的摄像机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看到的、感受到的、铭记的。
读者在全书中看不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自己感受的描述和她个人的明确立场。就连面对口述者歇斯底里的质问时,她也只是做了一名忠实实的记录者。例如在《大叫》这一篇章中,一位农村医疗服务员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想问我们问题?我拒绝出卖他们的悲剧或谈论肤浅的哲理。不要来烦我们了,拜托。我们还得住在这里。”另外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自书中唯一一位无名氏的口述,无名氏发出一连串责问:“你在写什么?谁允许你写的?谁准许你拍照的?东西拿走。把相机拿走,不然我就把相机弄坏。”读者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场的气氛和口述者的情绪,而记录者永远不为自己说一个字。
作者摘录了一篇《历史背景》,三段文字堪称新闻写作的典范。它们分别来自白俄罗斯百科全书、白俄罗斯萨哈罗夫国际生态学院的《切尔诺贝利灾变的影响》以及核泄漏十年后《星火》杂志上的一段文字,三段文字分别立足于白俄罗斯、全世界、四号反应炉的炉心,用新闻、统计数字和资料极简而科学地表述了切尔诺贝利的地理位置、爆炸事件和事发之后给全世界带来的至今难以估量的影响。
三段说明文字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客观准确的世界,说明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影响了什么,作者的选择体现了她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认知。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把事件的时间、地点、来龙去脉、世界各地对环境的监测再说一遍,但这样的“转述”会比这三段文字更直接和具有说服力吗?作者又一次隐去了“我”,而仅仅充当了《历史背景》这一篇章的一个编辑的角色,而这些宏观的、出处明确的、客观权威的论断对于读者来说,无疑都是振聋发聩的。
“摄像机”不发声,却有灵魂。“有灵魂的摄像机”和口述者交流,引导口述者进入回忆模式并开口说话,这些过程在创作中被全部略去,对于当下媒体环境的记者而言,对“我”有意地“隐藏”是残忍的选择,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刀阔斧地删除了个人外在的表现,完美地隐身在文字里,向读者呈现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后一个个被刹那间全然改变的人。近百位口述者讲述同一事件,每个人的篇章长短不一,没有长篇大论,有些人的口述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段文字,没有重叠的内容,可想而知,阿列克谢耶维奇对这些采访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删减。
书中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无不是作者的选择和“再叙述”。但这种叙述完全忠实于口述记录,从大量叙述中萃取出他们灵魂深处的发声,表达出口述者的立场和观念。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我试图透过无数鲜活的讲述,无数深埋多年的欢笑和眼泪,无数无法回避的悲剧,无数杂乱无章的思绪,无数难以控制的激情,看见唯一真实的和不可复制的人类史。”
只有在后记中,作者才“吝啬”地表达了自己:“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将其仔细保护起来。”在追寻事实和关注基于事实的感受的过程里,作者关注事件带给人们的感受的变化,不放过口述者转瞬即逝的任何细枝末节,精微地感受他人的情感脉络。
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认知过程,如果说揭示事实是认识论,那么关注感受的变化则是人类独有的无可替代的伟大情感。
亲历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他”成为作者笔下的“我”,是叙述主体。作者从有限的、杂乱的、模糊的言语里走近他们、了解他们、成为他们,让“他”成为那个“我”,遴选出近百位口述者,“他们”如此动情地叙述。“关心他人,才是真的人道主义……当学会尊重他人,又得到了他们的回报——人好像就不再害怕孤独。”作家张承志的论断似乎可以作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动力的另一种有力的注脚,她以自己的方式——用笔关心生活在切尔诺贝利周围的人(包括儿童,甚至包括牛、猫、狗和植物)、去清理的人及其家人、政府派去的官员以及被污染后移居切尔诺贝利的人们,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的“他者”。
在新闻写作中,“感受”是不容易找到容身之处的。记者不是囿于篇幅,就是受限于时间,很难像作者这样用三四年的时间采访近百位亲历者,耐心地倾听,任凭事实与感受在心中发酵,从口述者表达的蛛丝马迹中敏锐地发现语言与思维的风暴,那背后有民族的、地域的和时代的文化对人的塑造,舆论氛围和社会风潮在新闻写作中是非常难准确表达的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