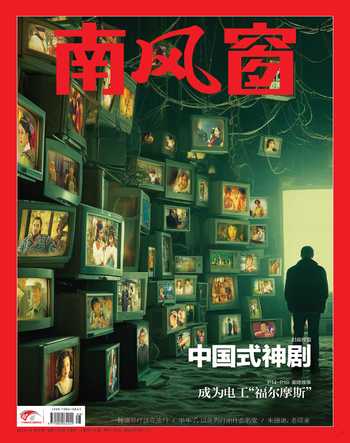面对小恶魔,法律不能再忍
肖瑶
3月中下旬,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明确指出:应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表态。过往,未满14岁少年的恶性犯罪,多数以教育与引导为主。而近日,伴随着邯郸三名初中生残忍杀害同学并埋尸一案发酵,一些“犯人”未被合理惩罚的案件被公众提起讨论。比如2019年,大连一名13岁男孩奸杀一名10岁女孩后,仅被实施收容教养。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态度,从人民群众的朴素情感和从法律的逻辑考量两方面是存在冲突的。若代入家长立场,都会为自己的孩子被害而痛彻心扉,同时为小恶魔逍遥法外不寒而栗。但再转念,如果犯罪的是自己的孩子,一切又变成不可言说。
此外,少年犯罪常常与校园霸凌挂钩,随之又牵扯出无穷尽的对家庭教育、城乡流动与留守儿童等问题讨论,变成复杂的、难以一锤定音的结构和阶段症结。
社会层面的争议也一直以来划分为诸多派别。其中一派是持“子不教父之过”的父母责任论。近期,知名犯罪学者李玫瑾, 就针对邯郸事件提出“按同罪刑期重罚父母”的建议。
从法律上,监护人自然有监护责任与义务,但从人伦与道德层面来说,将人的性格与行为完全归咎于环境,又容易落入一种超现实的虚无之中。
60多年前的胡适,就与李玫瑾持完全相反观点。
知名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的原型事件,就是发生于1961年6月15日晚的台北市牯岭街,一名16岁的男生茅武残忍杀害了一名初中女生。而该名男生的父亲茅泽霖是“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彼时,院长是胡适。
当时,不少人支持开除茅泽霖这个“少年犯的父亲”,胡适却坚持替他说话,致信给研究院负责人,大意是:“儿子犯了法,应该由法律去解决,不能要他的父亲去负责。要父亲负担儿子犯罪的责任,这是野蛮的专制行为。”
依胡适的观点,“罪人不孥”是现代文明法制的意志,教育一个孩子应当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不可全推给父母。若如此,便是将家庭视为最小治理单位而非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株连没有本质区别。
“连带罪”的大众情理有其出处。由于法理和伦理上的争议,短时间内,由于无法确定小犯人的下场,人们急于为“长歪了的孩子”寻找一个确切的出处,本质上,是对这种不可控的少年犯罪的恐慌。
恐慌源自不確定和不可控,我国司法适用的是成文法而非西方的判例法,过往案例虽然不能直接延用于后来的类似事件,但大众的情感和理智需要一个可触的落地。在法律规定无法对应情理的情况下,过往的判决便成为舆论所倚的重要参照物。
与成年人信息失序相对应的是,今天的未成年们,懂得的实在太多了。就在近日,随着河北未成年血案一事发酵,网上流传出的另一则视频里,几个模样不到十岁的孩子对着另一个孩子嬉皮笑脸地说:“我们就算杀了你也不用坐牢!”如此骇人听闻的发言,或许出现在无数看不见的隐秘角落里,在少年们心照不宣的规则世界里。他们只要上网一搜,就可以看见那条宛如保护神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当他们从小知道,“杀人偿命”“罪与罚”并非常识和公理,而是可以用年龄逃脱惩罚的漏洞,成年人又如何能指望他们对生命、对规则和法律保有敬畏呢?
正如针对此次邯郸事件发声的罗翔所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逻辑命题就值得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