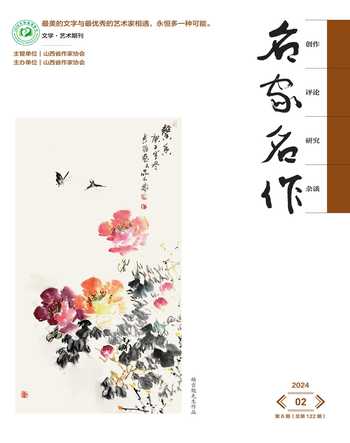“孤愤之书” 心读碎
潜问根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生活在明末清初顺治康熙时期。作者在《聊斋自志》中最后写道:……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康熙己未春日。
蒲松龄说自己的书是一部“孤愤之书”。
何谓“孤愤”?孤愤,原是先秦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所著的书篇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司马贞索隐:“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后以“孤愤”谓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愤慨之情。
如此,我们对蒲松龄的“孤愤之书”就可以理解一二了。
那么,我们不妨作一推理:略迟一点出现的《红楼梦》,从某种角度上看,不也是一部“孤愤之书”吗?
《红楼梦》无疑亦为“孤愤之书”。只不过《红楼梦》与《聊斋志异》表达“孤愤”的方式迥然不同。
《聊齋志异》主要是采用了“幻化”这种艺术手段,写鬼写妖,刺贪刺虐,但作者有时候实在忍不住,还是要大喝一声,以吐露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如卷八《司文郎》写一姓宋的少年,遇到两个读书人,一个是平阳的王平子,一个是余杭的年轻人。这两个人都要到顺天府去参加乡试。经过一番较量,余杭的那个走开了。最后,在姓宋的鼓励与帮助下,王平子有了长进,“是年,捷于乡;明年,春闱又捷。……”那么,姓宋的少年何来德才?作者借少年之口说:“……某非生人,乃漂泊之游魂也。少负才名,……甲申之年,竟罹于难,岁岁飘蓬。幸相知爱,故极力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
甲申之年,即明朝被灭亡的那年(1644年)。可见,作者心中因亡国而产生积郁的“孤愤”之情何其深也! 而“今文字之厄”则直截了当痛快之至!
再如《促织》篇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有意放在“宣德间”,即明宣宗(1426—1435)时期,说完了故事,作者却要针对皇上大发感慨: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可见这个满肚子孤愤之情的蒲松龄有时候又是何其直率、何其大胆!
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是如何表现“孤愤”的。第一回开篇点明“梦”“幻”等“却是此书本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当日闺阁中所有之女子。这亦梦亦幻给人一团迷雾,那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更是让读者莫名其妙。其实这些都是为了抒发作者心中的“孤愤”之情而特意使用的云雾障眼法。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四句题《石头记》的诗,可谓一字一句饱含“孤愤”之情,“孤愤”得淋漓尽致了!
从这些来看,《红楼梦》的表达方式显然与《聊斋志异》迥然有别。但那亦梦亦幻,那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那“你”和“我”,其中隐含着作者的“孤愤”之情,谁说得清?
让读者云中雾中扑朔迷离一番后,是一个一个人物登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钩心斗角,生离死别,字里行间虽无明明白白写着“孤愤”二字,但细细体会,似乎又处处无不有孤愤之情。
林黛玉走进大观园,虽然牢记先母的告诫,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但她的诗词,她的话语,时不时就会流露出她的“孤愤”之情。细细体会“葬花词”,其情感是否颇带“孤愤”?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与之相呼应的“秋窗风雨夕”,那结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不也一样饱含孤愤之情吗?
小说不单单是讲故事的,也可以抒情,只是不同作家,抒情方式各有千秋罢了。
作家毕飞宇说,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的慈悲会让你心软,甚至一不小心能让你心碎。
没错,《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两部著名的小说“传递”情感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但因为这两位著名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共同之处,他们的胸中都藏有一股强大的“孤愤”之情,所以,无论是读《聊斋志异》还是读《红楼梦》,我的心真的是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