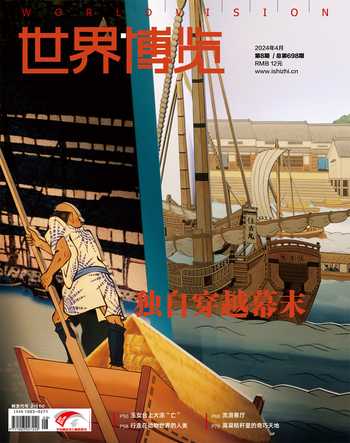粉头果鸠鸣声中的起源神话:关于“声”的人类学
彭李菁

卡鲁利部落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高地省博萨维山的热带雨林中。他们的祭祀仪式和日常活动中,声音占据着关键的地位。他们的认知方式的建立和传递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声音完成的。
我想用我和儿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开始这篇文章。
我的钢琴老师给了我一篇文章,是匈牙利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佐尔坦·柯达伊(Zoltán Kodály,1882—1967)1953年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的年终致辞。其中,他引用了俄罗斯作曲家和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的一段话,大致可以翻译为:“弹钢琴是手指的移动,钢琴演奏则是灵魂的律动。现在大部分时候,你只能听到前者了。”
我读完文章后把它忘在了钢琴上,儿子练琴之前看到,随手拿下来读,然后叫我过来,指着这个句子说:“我不明白。” 儿子在德语中学上学,德语很好,我知道他不是看不懂这个句子,于是让他翻译一下并告訴我哪里不明白。他的翻译没有问题,他不明白是因为他认为“任何手指在琴键上的移动都是有灵魂的,而不可能只有手指的移动”。说着,他打开琴盖,放上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的谱子,指着一处“forte”(强音或亮音)跟我说:“看到‘forte,你知道要让这凸显出来,但谱子上并没有标注音量和音色。弹到这里,你可以抬起手指砸下去,声音就会又高又响亮;你也可以完全不抬手指,用手臂的力量慢慢压下去,这样声音就又深又圆润;你也可以抬起整个手掌,非常快速地进入这个地方,但是进入之后马上稳定和平衡你的手,通过速度差异来凸显,这样音色非常均匀。虽然你弹的时候没有时间想,任何处理都是凭直觉,但那一刻的直觉取决于你对一首曲子的高低起伏和韵律发展的理解,同时还取决于你那一天、那一刻的心情,也会受你弹到那个地方之前的速度和音色的影响。无论如何,你的手指的移动是你的想法和情感在物理层面的实现,取决于你想要怎样的声音……” 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只有你在钢琴上创造的声音是属于你自己的,其余的是只属于作曲家的音乐。”
当然,这只是对鲁宾斯坦的观点或对钢琴演奏和西方古典音乐表演传统的一种解读,仍有很多其他解读。儿子的话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认为在钢琴上创造的声音就是他自己,而他传递的音乐则属于一个边界不明的、懂得这为何是音乐的群体。人类学家用英语讨论声音的时候用得最多的术语是“声”(sound)。儿子在讨论中对“声”和“音”进行了区分,恰恰很好例证了人类学家对“声音”(最常见的术语是voice)的解读。何为“音”,在每一种文明、文化和实践中都有各自的解释传统;何为“声”,则是个体的感受和直接的情感表达。我们听到并认为有意义的每一种声音,都是两者的结合。
从“纯粹声音”到“声音的社会性”
为什么人类学家要研究声音?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说:“声音是人类身体中最先能体现差异性的少数机制之一。”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研究驱使人类学家思考: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理解和诠释所处环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北美影响深远的符号学家查尔斯·皮尔斯在语言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上,对诠释符号机制的探讨告诉我们,每一种看似未经反思的身体直接反应都蕴含了社会和历史赋予的逻辑推断和文化象征的影响。在西欧影响较大的符号学家朱利安·格雷马斯则推动了人类学家们探索由身体感受推动的认知和共情过程。
关于声音的人类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任职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尼古拉斯·哈克尼斯(本身就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西方古典音乐声乐家),就非常深入地研究了韩国近半个世纪的声乐表演传统怎样通过声音,诠释韩国人对历史、经济发展、宗教信仰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和变化。
哲学思考总会慢慢渗入其他大部分学科的思考,经由感观建立的认知过程逐渐在人类学研究中深入人心。然而,20世纪以来,虽然人类学家们从田野调查中带回大量的访谈和视觉材料,但对声音材料的处理和对于声音的系统性记录和研究却异常缓慢。美国语言哲学家和早期的语言人类学家之一爱德华·萨丕尔建立了从“纯粹声音”(voice proper,完全通过生理机制产生的声)到“声音的社会性”(sociality of voice)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算是人类学关于声音的系统性阐述的起点。
卡鲁利部落的粉头果鸠神话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史蒂芬·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代表着比较成熟的关于声音的人类学探讨。他提出了“声音认识论”(acoustemology)的概念,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怎样通过声音理解历史、生活经验和生活环境与景观,以及如何通过模仿自然的声音进行群体价值观的展演和共情。菲尔德的田野调查在新几内亚的卡鲁利(Kaluli )部落进行,整个过程都显得诗意而忧伤。
卡鲁利部落的起源神话,是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只鸟的故事。男孩和姐姐一起去河里捕鱼,姐姐捕到了一只河虾,男孩什么都没抓到,就哀求姐姐分点吃的给他。姐姐说:“虾不能给你,要留给妈妈。”到了另一条河,姐姐又捕到一只河虾,男孩依旧两手空空,而这次姐姐说:“虾要留给爸爸。”又一次,姐姐说:“虾要留给哥哥。”悲伤的男孩哭着哭着,发现自己的鼻子变成了红色的喙,再低头一看,发现两手变成了翅膀。他渐渐飞起来,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粉头果鸠。姐姐一边哭一边追着他跑,说:“快回来,虾全部给你吃!”但果鸠还是飞走了。
菲尔德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很完好地阐释了鸟的神话是卡鲁利部落的人们理解、诠释和内化死亡的方式。他们的认知方式的建立和传递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声音完成的。所有的重要场合,包括婚庆、葬礼、重要首领主持的宗教仪式上,声音的产生和传递都是关键的环节。而且,日常活动如狩猎、洗濯、娱乐等,都有对应的歌谣和相关的声音。女人们在葬礼上的哀悼歌声,被认为是最忠实和准确的对粉头果鸠的鸣声的模仿,对卡鲁利部落的人们来说,这种声音本身象征着哀悼和悲伤,以及对他们部落往昔的理解。在宗教仪式上,专门请来的表演者必须为主持仪式的重要首领歌唱,而判断表演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表演者的声音能在多大程度上让首领悲伤地哭泣。因为部落起源神话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能够让人闻之泪下的声音,就是让部落中的人们最大程度共情的连结点。

卡鲁利部落的起源神话,是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只粉头果鸠的故事。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史蒂芬·菲尔德在卡鲁利部落进行田野调查,试图用西方古典音乐的记谱法来记录卡鲁利部落的歌谣。

史蒂芬·菲尔德的著作《声音与情感:卡鲁利人表达形式中的鸟语、哭泣、诗歌与歌曲》,是一本声音的民族志,研究了森林中鸟类的声音等如何成了当地的文化象征。
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前,菲尔德是经过严格西方古典音乐训练的音乐家。他来到卡鲁利部落之后,还尝试了一項非常艰难的工作——用西方古典音乐的记谱法来记录卡鲁利部落的歌谣。他认为,既然人类学家们会记录所研究人群的语言,并以西方语言学为基础,编撰所记录语言的字典和语法书,那么他也可以尝试记录卡鲁利部落的音乐,作为自己学术写作的原始材料。可以想象,在西方古典音乐的乐谱上不可记录的音,在当地的音乐中会有更灵活的变化,音色的深浅也是非常难以记录的。当他一边学,一边请教当地人怎样唱出那些音和歌谣的时候,所得的回答往往要经过层层的“文化翻译”才能转为音乐上的实践。比如,他的当地老师们会告诉他:“这首歌的声音是瀑布从山上倾泻而下,你要让水声落入下方的河里更深一点!”又比如,他们会说:“这首歌是瀑布水滴溅落到树叶上,你要让树叶真的湿掉!”又或者,“那只鸟虽然飞过低空,但它在下雨后不是这样叫的!” 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理解了他自己耳中听到的“声”,在卡鲁利部落的人们听来,是有内在文本的“声音”。
至今,菲尔德的作品不仅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启发了许多人类学家系统性地把关于声音的记录和诠释作为田野调查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启发了许多音乐学家们思考“声音”和“音乐”的边界,以及“何为美?”“何为音乐的意义?”等等有趣的问题。
(责编:刘婕)
——造梦城市中的精神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