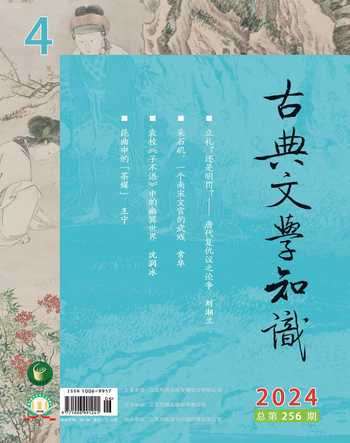文人可有风骨?
赵源
我们今天常见“文人风骨”之说,是语常被用来表彰从古至今文人之有风骨者。然而在古代,“文人”之品行往往为人鄙夷,不被看成“风骨”的承担者,“文人风骨”一词并不成立;近代以来,“文人”逐渐成了“文化人”的省称,“文人风骨”一词实际上折射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分子承担道德价值的期待。
“风骨”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是书专设《风骨》一篇,中云:“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刚开始,“风骨”多被用于文章品评,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再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二《释慧光传》云:“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不过,“风骨”一词从诗文评范畴逐渐流入人物品评领域,成为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人物品评的用语。如《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传》结尾处,初唐史臣评赫连勃勃,称其:“器识高爽,风骨魁奇。”高适《答侯少府》诗有:“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便是揄扬对方性格伟岸,坚韧不屈。在随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风骨”一词兼有诗文评与人物品评两个维度上的涵义,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主要还是从后一维度上对该词进行接受。而在这一语境中,称某人有“风骨”,便是赞扬对方具有“刚正的气概”。传统中国的人物品评中,“德”往往远远重于“才”,我们常援引司马光之论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风骨”一词是对人之德行的高度赞扬,故当之者,应是品德高尚之人。
吊诡的是,在中国古代,“文人”在士人中的地位并不高。北宋刘挚常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一判语因被顾炎武录于《日知录》而广为流传。事实上,刘挚对文人的偏见并非古代的个例,而具有相当丰厚的社会基础。盖“文人”在中国古代一般指“知书能文的人”。古人崇信“三不朽”之说,在没有机会立德、立功的情形下,士人们才从事撰述以期立言。然而文人之撰述,对应古代四部之学中之最末流者,即集部之学。从事集部诗文写作者,往往脱离了社会关怀,摛(chī)藻逞才,往往只诉说一己之幽情,故往往为正统士人所鄙薄。前引刘挚语其实化自《旧唐书·文苑传》中裴行俭的品评之语,其辞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也即在裴氏看来,虽然王勃等人文采惊人,性格却“浮躁浅露”,不堪重用,这实际上颇能代表古代士人的一般意见。如欧阳修言:“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宋人晁公遡亦言:“世未有以文章称之者,何耶?君子而稱文章,君子之不幸也。”从相当大的程度说,“文人”好比“匠人”“画人”,一如后二者是精于匠艺与画艺的手艺人,文人不过是精于文字之技艺的手艺人。而古代中国士人的普遍意见是道重于技,如《论语·述而》中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子·天地》言:“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从事于技艺的前提应当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道德涵养,因此,不修德立身而游戏文字,自然受到立德之士的鄙薄。
在此我们不必循着古代修德之士的一贯意见,继续对文人进行攻讦。相反,古人正是认识到“文人”同“匠人”“画人”一样是技艺的承担者,而非道德事业的承担者,故往往不对其承载道德价值给予期待。郭沫若在《屈原》一剧中借婵娟之口对宋玉吐出那句“名骂”曰:“你这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这一句放在古代真实情境中颇为有趣,如前所述,“文人”在古代并不是道德价值的承担者,因此“文人”并不会与“风骨”“骨气”等有正面联系。
就笔者检索所得,“文人风骨”一词,最早见于1947年朱怙生发表于《东南评论》的同名文章,不过,此后这一词汇就长期消匿无闻。此词被普遍使用始于21世纪初以来的报刊文章。为了叙述“文人风骨”之题,朱文中罗列了三人事迹,分别为罗振玉、王国维、汤寿潜,此三人以古代之标准衡量之,均非寄意于诗文创作、发一己之幽怀的“文人”。前两人自不待言,汤寿潜则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与实业家,一生为政治事业奔走不暇,人望崇隆,道德卓著。而这恰恰折射出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即,近代以来,“文人”一词的含义发生嬗变,已非古代士人所鄙薄的撰述诗文、有才未必有德的群体。近代以来大众所使用的“文人”一词大致可以视为“文化人”的省称,或云“知识分子”。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旧有秩序趋于瓦解,在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民众对知识分子有了极高的期待。
陈寅恪曾论曰:“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越是变革时代,民众所见道德败坏之事迹越多,对于道德重建的期待就越强。此时,知识分子,或曰“文化人”—大体上也即承接传统“四民”结构中的“士”阶层就成了这一期待的承担者。20世纪末,当市场经济之潮卷向学术圈时,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此时,呼吁“文化人”坚守道德底线之后,进而能承担起重建失落的道德传统的声音便愈演愈烈,“文人风骨”一词也就传扬开来。
以上,我们简单梳理了“文人风骨”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在古代,“风骨”用于人物品评时,是赞扬对方道德高尚、有耿直刚正之气,然而从事撰述的文人往往遭受有才无德之讥,并不被看成道德事业的承担者,因此“文人风骨”一词在古代的语境中无从说起。近代以来,“文人”一词逐渐嬗变为“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在道德失落的时代,民众或知识分子自身渴望有人承担起重整社会风气的责任,并将目光投射到知识分子群体,最终促成“文人风骨”一词被广泛使用。当然,当今一般民众普遍疏离于古代的真实历史情境,误以为舞文弄墨的文人成了“风骨”的承担者,并以此构建他们的历史想象,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