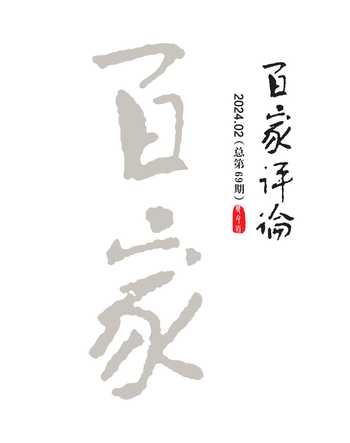乔洪涛创作艺术论
程相崧
内容提要:乔洪涛是活跃在山东乃至全国文坛的一位实力作家,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而旺盛的创作力。他擅长小说和散文创作,并且两种文体的作品都数量大,质量高。他思考深邃,笔触细腻,叙述风格借鉴西方技巧又不失传统文学的厚重大气。本文试图以乔洪涛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的部分小说、散文文本为例,梳理他20多年的创作历程,分析其在所擅长的小说和散文两种主要文体上,艺术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绩。
关键词:乔洪涛 散文 小说 叙事艺术 人物塑造 自然文学
乔洪涛自世纪之初步入文坛之后,一直保持着稳定而旺盛的创作力,以其高质量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已经成为活跃在山东乃至全国文坛的一位实力作家。他思考深邃,笔触细腻,叙述风格借鉴西方技巧又不失传统文学的厚重大气。在经过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之后,创作出了像小说《少年两匹马》《骑白马,扛梅花》《蝴蝶》《一家之主》《一个人的盛宴》,散文《湖边书》《大地笔记》《纸与字》等一大批深受读者喜爱,又在文学圈和评论界引起一定反响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有的在叙事上独具匠心,有的在人物上颇具功力,有的显示出作家对于平庸生活、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呈现出深刻而独特的思想内涵,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造诣。
乔洪涛跟很多年轻作者不同的是,自从步入文坛之初,即以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引起了不同类型读者的关注。他的创作,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文体之间自由跳跃。从早期发表在《散文》上的《镰刀的婚礼》、入选《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的《芦苇》《缓慢》等散文开始,到近期发表在《福建文学》的《纸与字》;乔洪涛的散文起点高,质量优,在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山东散文界,也因为其呈现出的自然文学、非虚构、哲思风格和文化含量而风格鲜明,十分扎眼。他的小说,从早期发表在《清明》上的《尖子生》、《中国作家》上的《老师、老师》,到近年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饮鸽记》《骑白马,扛梅花》、收入小说集《一家之主》《一个人的盛宴》中的诸多篇什,以及长篇小说《蝴蝶谷》,都显示出乔洪涛作为一个小说家,不仅高产,而且高质;并随着生活阅历、阅读积累的逐渐深入,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小说文体,创作风格逐步形成,创作状态也渐入佳境。
本文试图以乔洪涛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的一些小说散文文本为例,梳理他20多年的创作过程,分析他在所擅长的两种主要文体上艺术方面所做的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绩。著名作家张炜有一个观点:“一个糟糕的小说作者不太可能会是一个高明的散文家,反过来也一样。”所以,本文也试图对作为两届“张炜工作室高研班学员”的乔洪涛能够熟练掌握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这一当代文坛并不多见的现象,探讨两种文体趋近求同的途径和一个作家具备两种能力的必要。
一、小说论
乔洪涛作为生长在齐鲁大地上的作家,他刚刚步入文坛时的创作,多取材于儿时生活过的乡村留下的深刻记忆,写作方法也继承了这片土地上老一辈作家身上的厚重朴实。他早期获得关注的作品,例如小说《西北望蒲苇》《乡村火枪手》《红鲤》《吹猪》《赛火车》等,大多取材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文字洗练,风格朴实。他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变化,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另外,他还擅长通过对人性复杂性的挖掘,使人物形象更加全面、立体。
当然,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自从西方小说叙事学传入中国之后,小说写作在众多作家的眼里,“怎么写”的重要性一度远远超过了“写什么”,成为写作水平高低、写得高级不高级的衡量标准。在乔洪涛刚刚步入文坛的时候,虽然有批评家指出,其小说当时写得还显太过“老实”,但在叙事上,他也已经在传统的基础上,试图做出种种尝试,并形成了保持多年的艺术特点。
他那时的小说,在叙事上开始多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这不仅增强了叙述内容给人的真实感,还便于传达出小说中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能够增强小说人物与读者心灵之间的同频共振。这种叙述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三个男人》《我家的电视机》《鲸》等小說。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将读者带入的,不管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家庭环境,还是有些荒诞变形的虚拟世界,都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实质感。
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同时,乔洪涛的小说往往又喜欢采用童年视角。这一视角的使用,让读者看到一个新奇别样的世界,容易获得非同寻常的阅读体验。在《少年两匹马》和《骑白马,扛梅花》中,乔洪涛便是通过几个少年的成长经历,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两部小说中的少年形象都充满了活力和朝气,他们在大自然中奔跑、嬉戏,感受着生活的美好和纯真。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不得不逐渐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和挑战,开始思考人生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乔洪涛的小说在叙事上前后最大的变化,则是由宣泄变得更为克制,摈弃了铺张的叙述而转为极简的刻画和呈现。我们在读他前期的小说时,不论是《西北望蒲苇》中如诗如画故乡风物的描写,还是《故乡谣》《捕鲤记》中农村风俗的交待,都不吝笔墨,让读者眼前似乎缓缓展开一幅生机勃勃、草木丰茂、人欢马跳、民俗独特的乡土画卷。那个位于鲁西北黄河岸边的小小村庄留在作家脑海中的记忆,似乎不由地就要进入作家的小说世界,成为人物活动,故事生长的强大背景。这种写法给乔洪涛当时的小说带来一种浓郁强烈的生活气息,使其作品风格厚重大气,阅读体验庄重震撼。这也让他当时的一些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比如《空地》《每一个人的秘密》《鹅鹅鹅》等脱颖而出,在读者和文学圈获得了一定的反响。
但是,随着作家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写作兴趣逐渐转向短篇小说创作,面对新的写作题材,面对小说创作领域审美趋向的不断变化,这种叙事方式日渐显露出其“短板”。著名小说家刘照如在2018年前后就曾经指出:乔洪涛的一些小说在对所写题材的“控制能力”上,稍显无力和疲态。那个时期的乔洪涛,在创作上一度陷入难以逾越的苦恼“瓶颈”。但是很快,他就突破自我,完成了其在叙述风格和方式上的嬗变过程。从《湖水冰凉》《百年好合》《潜水家》和《在山上捉野鸡是一件危险的事》开始,乔洪涛的短篇小说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大变。这些小说不仅削减了作家之前为之着迷的不节制的景物描写和情绪宣泄,场景的呈现替代了曾经得心应手的叙述和交待,在情节切入时也往往单刀直入。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善于用简洁明快的句子来描绘场景,刻画人物,使得整个故事节奏紧凑、引人入胜。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为之一变——如同看一个招数日渐娴熟的武者左右突击,夺敌兵器,取敌首级,如入无人之境。
乔洪涛后来的很多小说,不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情节往往充满张力,故事发展紧凑,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得不保持着精神的紧迫感。他的长篇小说《蝴蝶谷》中的白冰初到蝴蝶谷所受到的热情款待,便让读者心生疑窦,并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又擅长利用“突转”的手法,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戏剧性和张力。这些转折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使得故事更具吸引力。例如在小说《潜水家》中,写了一个不擅长农活却擅长游泳的农民父亲热衷乡村游戏比赛最后遁入湖底消失的故事,通过突转,隐藏在人性中的微妙细节得以呈现。例如在《一个人的盛宴》中,写了一对贫穷的乡村夫妻在儿子入狱后的精神崩溃,把当今乡野极端生活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男人的精神危机和盘托出。例如《少年两匹马》中的白马自杀而死,红马失踪消失的结局,而小说《我家的电视机》的结尾出现的小红点和朝着我走来的电视机,则更是以一种真实与魔幻结合的出奇方式,峥嵘突起,意外之中,带给人的心灵一种震撼的力量。
乔洪涛曾经一度推崇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并为小说《白象似的群山》而着迷。近年来,短篇小说大师卡佛的作品,也因为其极简而被很多作家和读者追捧。其实,极简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风格特色。中国的诗和画一向讲究留白,艺术大师往往都是留白的大师,方寸之地亦显天地之宽。这种有意的“留白”,也大大拓展了乔洪涛小说的叙述空间,让他的小说变得更加耐人寻味,更有嚼头。
例如其小说《风雨二题》《被雪覆盖的男人》,作家对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有意进行了淡化和模糊化处理,甚至大量留白。这样不但丰富了小说的意蕴,还让读者不得不参与其中,获得非同寻常的阅读体验。当然,乔洪涛深谙留白的魅力,所以他的小说,有的地方描写密不透风,有的地方又疏可走马。他在小说《鲸》中对于主人公生存困境,对于他生活小区庸常琐屑生存环境的描写,又不吝笔墨,故意地铺张到了极致。
读乔洪涛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很难用传统的“深度”“广度”概括其写作追求,他似乎正在一次次挑战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的“难度”。他在很多小说中开始运用意象、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来深化主题,使得作品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其短篇小说《蝴蝶》中的“蝴蝶”、《风雨二题》中的“风雨”,《被雪覆盖的男人》中的“雪”、《鲸》中的“鲸”,还有《骑白马,扛梅花》中的“梅花”,作为一个个意象,无疑都超出了现实的层面,而具有了象征与隐喻的意味。再例如长篇小说《蝴蝶谷》中的“蝴蝶谷”,作为一种意象和隐喻,无疑暗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心灵的困境和追求自由的渴望。这一意象的选用,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将读者引入关于人性和自然的哲学思考。正如古人所说,言不尽意,语言在现实的无限丰饶面前,往往表现出其有限性。乔洪涛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就会借用一些意象,委婉含蓄,也是举重若轻地把心中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让作品在艺术上,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乔洪涛早期的小说重在写实,近年来则多写得轻灵飞动,举重若轻,并呈现出更多的当代性和实验性。他的两篇短篇新作《鲸》和《我家的电视机》,语言简练,叙述风格冷峻;以略显破碎的情节、浓得化不开的细节、蒙太奇的剪接、意象的象征与隐喻和奇崛有力的结尾处理,深刻揭示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其小说人物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精神的孤独,绝望;亲情、友情、爱情和人际关系的那种疏淡,隔膜,无不给人以震撼的力量。
小说作为一种古老但也在不断成长的文体,可以一板一眼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将八分之一的冰山露在水面以上。当然,也可以通过对有韵律与节奏的语言的把握,对环境、气氛的酿造,甚至通过对情感的看似废话连篇的宣泄,使其表现严肃的主题,揭示生活的真相,并呈现出独特的形式。正如奈保尔所言:“如果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只能将小说写作推向一条羊肠小道,甚至逼上一条绝路。”而作家乔洪涛作为永不满足的探索者,正在以自己的不断探索,将小说写作这条路越走越宽。
二、散文论
如果说乔洪涛的小说运用多种艺术手法,以其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动人心魄的矛盾冲突来反映幽微的人性、多样的生活;那么他的散文则多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乡村和山野的风物,描写四季的物候和身边的寻常事物,展现出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卷。他的散文有鲜明的“自然文学”特点,又富有场景的代入感,能够让读者暂时抛开城市生活的喧嚣,进入一种宁静的世界、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与山川草木同呼吸,共命运。作为散文家的乔洪涛,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讲述者,更是一个思想者。他通过对大自然和身边事物的深入挖掘,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人心的变化、社会的变迁等深刻主题,富有哲理性和思想性。他的散文作品相对小说,虽然数量少很多,但都能够启迪读者,引发人们对生活和社会的深度思考。
在乔洪涛早期的散文《芦苇》《听秋》《雨水与惊蛰》等篇什中,出现在作者笔端的是镰刀、芦苇等乡村司空见惯的器物、植物;还有雨水、惊蛰等季节和节气。那时候的乔洪涛,像一个双脚踏在齐鲁大地上的歌者,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眷恋和感恩。在这些散文里,他的语言优美而富有诗意,擅长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逼真地描绘记忆中的事物,富有感染力。在对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场景和农人劳动场面的细腻描写间,常常表达对乡土生活、乡村生活习惯的思考,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思考,并对昔日的乡村,由衷地流露出热爱与眷恋。
乔洪涛这一个时期的散文,虽然已经呈现出“自然文学”的特征,但毕竟还有些表面化、浮浅化。“自然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虽然来自西方学界,并因为《瓦尔登湖》等作品在中国的畅销而为人熟知,可它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唐宋之后久盛不衰的山水田园诗当然是几近成熟的“自然文学”,如果要向上追溯的话,还可以追溯到陶渊明和《诗经》中大量写到山野和乡村的诗歌。作为“自然文学”,仅仅去描写甚至复制自然是不够的,仅仅是赞美和眷恋自然也是不够的。如何与大自然相拥生活,如何從大自然中获得滋养,如何把在自然中得到的感悟转化为精神的升华,自然要成为作家们思考的一个课题。
在散文写作方面,乔洪涛自然也不甘心一直描写一些琐碎的乡村风物、山石物候,他是把自然当作一种隐喻的神性存在来看待的。所以,他的散文到了《大地笔记》和《湖边书》系列,再次发生了一次飞跃,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在《大地笔记》中,乔洪涛将笔触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大地之上。他所描写的对象,并没有超越大多数散文家,甚至也没有超越他以前散文所涉及的范畴。可是,在这两个大部头中,大地和湖泊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们既是四季轮回、生生不息的现实世界,又成为一个精神的隐喻和寄托。乔洪涛作为大地和湖泊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者,正试图透过真实逼人的现实世界,去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去表达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
在《湖边书》中,乔洪涛的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平实而不失感染力。他以湖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湖水的波光粼粼、湖岸的草木葱茏,极具画面感和视觉效果。他的描写,常常让人想起理查德·杰弗里斯笔下的英格兰乡村,或者苏珊·库珀的《乡村时光》中描绘过的场景。而跟他们两个稍有不同的是,乔洪涛的散文更加注重情感表达和哲理思考。《湖边书》中的一些片段,往往以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抒发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感悟,传递出一种深沉而真挚的情感。这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不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也可以领略到他对人生的独特见解和对社会的深刻洞察。
跟梭罗笔下的“瓦尔登湖”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样,在乔洪涛的笔下,大地、湖泊、风暴早已经超越了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一个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象征。收入《湖边书》中的一篇《荒野风暴》,就写了蒙山脚下、云蒙湖边的风景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一群“都市人”在湖边扎上帐篷,钓鱼,打鸟,生火,做饭。最后,当他们喝了从城里带来的白酒、葡萄酒之后,感到“睡在大地上,比睡在床上的踏实感来得强烈得多。”他们逃离了城市的喧嚣,逃离了工作的烦恼,甚至感觉自己的耳朵比任何时候都灵敏,甚至想象着“一只屎壳郎推着粪球走过,一只蚂蚁悄悄爬过,一条蚯蚓在身子下轻轻蠕动,一只田鼠在五米开外蹑手蹑脚,一条鱼儿跳起偷瞧过来的眼波,还有鸟雀半夜的呓语,鸣蝉振翅的微颤……”
这些远离自然又向往自然的“都市人”似乎已经融入荒野,完全成了这个旷野的一部分。可散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噼里啪啦的雨水滴落下来”之后,这群孱弱的“都市人”却收起帐篷,逃入湖边的木屋。这些人回到木屋之后,感到“一点困意也没有了,都感受到了自然的威力——”随之,他们又本性复燃,开始矫情地担心起风雨中的鸟雀、田鼠甚至蚂蚁。但是,“沉沉的困意袭来”, 这群渴望着亲近自然的人,却终于“倒在木板床和椅子上又睡去了……”
乔洪涛的散文元素是多元的,在《湖边书》中,既有写实性,又有寓言性;既有都市人孤独心灵的呓语,又有人与自然欢欣的互动。这也是乔洪涛的《荒野风暴》和常见散文不一样的地方。散文的开头,看似一段并不简洁的铺垫,但是,风景是动人的,抒情也是动人的。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风景和抒情,又不是简单的风景和抒情。散文中的人、鸟、鱼、荒野、云蒙湖,这些在作者的笔下,都具有了神秘性、符号性,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灵动的“象征”。在作者的笔下,万物是有灵的,作者的主观世界无限地接近了客观世界;他笔下的山川、溪流、鲤鱼、麻雀、甚至一只屎壳郎,都具有了人的主观意志和生命体验。这些元气淋漓的生命符号,将都市人的焦虑、无助、弱小、卑微、琐屑映照得无处遁形。
散文《荒野风暴》对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并怀着深深的忧虑。这些游走于大自然中的“都市人”,已经不是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所写的俄罗斯大地上行走于西伯利亚莽林中的那些健美、自信的农夫和猎手。他们仿佛被都市文明阉割了,也被都市生存法则完全打败了。他们对于自然的亲近,也不再是那种威猛精进,而是带着一种隔靴搔痒、顾影自怜和自欺欺人。
作者对傍晚湖边的“我”,曾有过这样的心理描写:“在城市里,我们害怕火。但也离不开火。为了驱赶寂寞,带来生命的安全感,每个人嘴上都叼着烟卷,四处走。”在散文的末尾,作者又借“我”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批判:“这就是荒野的法则。一个人对荒野的渴慕,就是对变幻无常的法则的渴慕,就是对人类过分秩序的厌倦。”
乔洪涛作为一位远离世态喧嚣的写作者,在对中国传统乡村生活长期关注的同时,又在有意识地体察都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局。在以《大地笔记》和《湖边书》为代表的一组“大散文”中,他善于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通过形象的比喻和巧妙的构思,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当然,在这类题材之外,乔洪涛也有一些以悲悯情怀反映底层人生活的散文,多是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波折,展现出人性的善良与悲凉。其人性的关怀和悲悯的情怀,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
总之,乔洪涛的大多数散文,结构严谨而不失灵活性,语言质朴而不失诗意;综合运用了象征与隐喻,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探索和深刻的人文思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认可。
结语
著名作家张炜曾经说:“就小说家而言,他所倚仗的最基本能力,还是从小时候学习的散文写作的能力。因为小说中的大多数篇幅都在叙述事情,这就需要一种生动简约的表述功夫。”在乔洪涛的创作中,小说与散文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在小说与散文创作方面,他分别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和尝试,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风格,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融之美。乔洪涛的小说中融入了散文的抒情性和哲理性,使得小说更加具有诗意和深度;他的散文中则融入了小说的情节性、叙事性和故事性,运用小说设置人物和场景的技巧,使得散文更加生动形象、更加抓人。
乔洪涛曾经一度关注“非虚构”这一文体,并极为推崇;可在他的散文中,却也有时借助甚至“虚构”一些人物的亲身经历,通过人物的“所见所闻”,来抒发情感、表达思考。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感染力,也使得散文更加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就像《荒野风暴》中的那些城里人和他们的荒野经历,因为借鉴了小说的写法,常常让人联想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中的人物。
有趣的是,乔洪涛的《湖边书》系列,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样,有着写实的油画质感;但不同的是,在云蒙湖边的木屋里喝着葡萄酒的这群城里人,已经再也不能跟屠格涅夫笔下打松鸡、打野猪的猎人那样,跟风景真正地融为一体。这些在物质生活上无忧无虑的都市人,心灵却是苍白的,生活却是单调的,他们幻想着融入自然,融入荒野,具有像大自然一样的蛮荒之力,但最终却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一个个显露原形。这大概也是乔洪涛在这个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焦虑和洞察。
总之,无论是那些以乡土为背景、以人性为主题,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与内心世界挖掘的小说,还是那些以大地和湖泊为对象、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类命运思考的散文,都无不包含着作家乔洪涛对于自然、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无不体现出他对各种艺术手法的尝试和探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朝着文学高峰不断攀登的作家乔洪涛,在将来一定會创作出具有更加丰厚文学底蕴和独特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第六批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