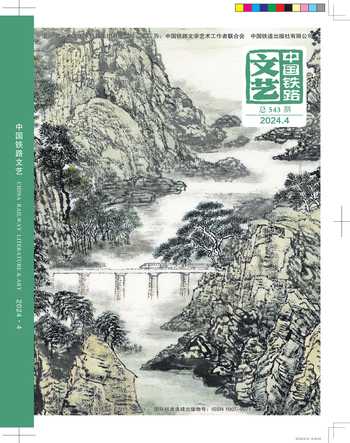孤城西北起高楼
作者简介:王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汉水文化学者。现任西南交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学术论著多部(篇),共计720万字。多篇作品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报刊刊登或转载。代表作有“汉水文化三部曲”——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金匮银楼》及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丝路大通道——中欧班列纪行》《中国力量——高铁正在改变中国》等。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俄、阿、日、罗、波等文字。
阳光绵阳,涪江江畔,矗立着一座千年古楼——越王楼。
越王楼,位于四川省绵阳市龟山之巅,是唐高宗时期,越王李贞任绵州刺史时主持修建。与其他历史名楼一样,越王楼饱受岁月沧桑,屡遭战火破坏,几度废为瓦砾,又几度重建,始终以不屈的风骨,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距今已有1350余年,如同楼下千年流淌的涪江水,绵延至今。临江吟唱,成为很多人心中的风景。它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齐名,为唐代四大文化名楼之一。
在漫长的岁月里,浪花唱歌,悲风鼓瑟,峰回路转,大江东流去。越王楼只要健在,它就是一位智者,静观世事的变迁,它不言不语,默默承受着岁月风雨,记忆着历史烟云。越王楼以其高大、坦荡的姿态,吐露着自己的真情,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每一位客人。楼阁之美,如镜中皓月,一尘不染。
登楼观光、吟诗作赋,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见的生活方式,是对历史文化名楼的一种敬畏和尊重。诗人对越王楼的爱,也不例外。自越王楼修建完工之日起,就有许多当朝大诗人纷至沓来,包括李白、杜甫、王勃、李贺、李商隐、陆游等,几乎涵盖唐代以后的诗坛泰斗。他们登越王楼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留下了无数千古传颂的经典诗篇,其中以李白的《上楼诗》、杜甫的《越王楼歌》、李商隐的《霜月》和陆游的《登越王楼》最为著名。
读越王楼诗,无论是李白的“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还是杜甫的“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无论是李商隐的“百尺楼高水接天”,还是陆游的“两脚犹堪蹋九州”,都有一个共同点:赞美越王楼的高大、壮观与气势。
客观地讲,没有诗词、歌赋、字画留存的楼阁建筑,就只是一个石木组合体。越王楼丰厚的诗文,供后人争相品颂,经代代传承,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越王楼文化。因此,越王楼被誉为“天下诗文第一楼”。
一
乍听越王楼,很多人误以为是越王勾践所修。其实,这个越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个儿子李贞。李贞虽然不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但才华出众、文武双全,很受唐太宗宠爱。他五岁受封汉王,十岁改封原王,后又改封为越王,十七岁正式出任相州刺史……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间越王作。”杜甫《越王楼歌》开篇的第一句,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越王楼由越王李贞于显庆年间任绵州刺史时所建。
公元656年,唐高宗李治深忧西南边陲之安危,为巩固大唐边境,决定选派一位忠诚可靠、才干卓越、爱国爱民的干将镇守边关。选来选去,只有自己的亲兄弟、已被封三王的李贞最为放心。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李贞只身前往绵州,就任绵州刺史。
唐史记载,在皇族诸王中,李贞“文武兼备”“富有吏干”,以“才王”闻名。
李贞到任绵州后,忠孝为本,仁义为先,兴水利,扶农商,昭示天下,融合各族民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经过一番思考,李贞向唐高宗上奏,强调奉命镇守西南边关,为壮大唐之山河,扬天威,布帝德,让绵州百姓可朝夕望阙叩拜,倍沾唐天子隆恩,需建王府,修高楼,扩建州城和军队。唐高宗准奏,拨给国库银两,由李贞督建。
李贞想到自己曾被赐封三顶王冠,建造越王楼时,他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吾建之楼应高十丈。这时,他的六叔(唐太宗李世民的六弟)滕王李元樱,已在洪州(今南昌)建造起九丈高的滕王阁。若越王楼高十丈,自然就比滕王阁高出一丈。
李貞参考了长安、洛阳诸多王府的营造规划,结合龟山的地形地貌,依山取势,历时三年,耗银五十万两,建成越王楼。这座楼阁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叠影斑斓,巍峨挺拔。其规制、风格以及琉璃瓦等建筑材料的采用,在当时的西南地区绝无仅有,充分体现了大唐的盛世气象,彰显了一代帝子的豪华与威武。最初仅作为府邸之用,后经过逐步扩建,楼阁与府邸相互连通,形成一片壮观的建筑群。
越王楼建成之后,李贞命人清理余下材料,并移到城西南涪江边,用剩余款项在此修建了一座望江楼。
登上百余级阶梯,进入红色高墙之内,便是越王府。这里是李贞处理政务的地方,实际也是当时的绵州州衙。穿过越王府,便是一座大花园,两边建有花台,中间卵石甬道,直通越王楼下。
楼高百尺,楼顶压着红色屋脊,脊上饰有龙虎及神兽雕塑,脊下为绿色彩釉屋瓦。楼阁四周的栏杆、立柱、板壁均为红色,描绘着华丽的图案,尽显皇家气派。举目望去,蜃楼微现,掩隐岸庭,烟柳隐约,虚幻止若。
据诗文记载,唐代越王楼,攀至顶层,可北望剑门,七十二峰隐约可见;向西可望岷山雪山;东南则可将绵州美景尽收眼底。滔滔涪江流经楼下,水面宽约六丈,往来船只如梭,常有大群沙鸥、白鹭翻飞,为当时绵州胜景。
二
顺着历史的藤蔓游走,大约在越王楼建成三十年后,李贞被斩首示众。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太子李显继位为唐中宗,他命李贞为太子太傅。这时,朝廷大权旁落,皇太后武则天开始操控朝政。
次年,武则天废唐中宗,立中宗之弟豫王李旦为皇帝,李贞转任豫州刺史。唐高宗驾崩五年后,武后利用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大肆为武氏家族加官晋爵,屠杀李氏皇族,大有取代李唐之势。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夏,大唐王国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忍无可忍,四处游说诸王,试图做最后的挣扎,拯救李家天下。这天,武则天下诏所有皇室成员限期“入洛阳、会明堂、行大典”,李姓宗亲都很担心,怀疑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于是,有人假造庐陵王李显的书信,串通李唐子孙起兵伐武,李贞率先响应。他联络韩王、鲁王、范阳王等,决心讨伐武则天。
然而,在李贞挥师起兵后,十分讽刺的一幕出现了——之前答应和他共同起兵的所有李家王族,无一人起兵响应。真正起兵的,只有李贞及其长子琅琊王李冲。待武则天派出十万平叛大军潮水般涌来镇压时,李贞的将士一路溃败。不到一个月,这次事件便以失败告终。史称“越王之乱”。
9月16日这天,李贞大惧之下,闭门自守,饮恨喝下毒药而死。最终,李贞、李冲父子被斩首,首级悬挂在东都皇宫门前阙楼下示众。李贞的另外三个儿子要么因为连坐被杀,要么被流放岭南,没多久都死了,无一幸免。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正式登基,成为显赫一世的一代女皇。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诸大臣请奏:李冲父子死于社稷,请复爵土。唐中宗恢复了李贞的李姓和族籍。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给越王李贞平了反,下诏追复爵土,将李贞、李冲重新改葬,谥号为敬。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山发动“安史之乱”。次年六月,安?山大军攻破潼关,唐玄宗被迫出逃西蜀,在两万御林军的护卫下,率王公大臣入蜀。一路上千辛万苦,吃不好,睡不好,伤感欲绝。此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为证:“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唐玄宗幸蜀一行,沿途艰险、劳顿、惊吓,连行宫里看见的月亮,都是伤心的颜色,夜雨中听到的铃声,宛若断肠之音,令人心碎。
令唐玄宗没想到的是,在远离长安的西南边陲绵州,竟然有一座可与长安宫殿媲美的越王宫,一切均按王制打造,舒适安全。唐玄宗感慨万千,真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不由心情大好,收住了逃难的脚步,将越王楼作为临时行宫,入住休整歇息。
历史正是这样,冥冥之中,可以有许多巧合。唐玄宗为越王平反,竟在绵州得到回报——富丽舒适的越王楼,让唐玄宗受到惊吓的心灵,得到了许多抚慰。
绵州山水美景,吸引了玄宗一行。一连数日,唐玄宗沉醉于越王楼,歌舞升平,乐不思蜀。他兴致极高,除了越王楼,足迹遍布东山富乐坛、南郊望江楼,以及开元寺、治平院、水阁院、东津督邮亭。于是,绵州有了许多关于帝王轶事的流传和留于后世的遗存古迹。
三
楼再好,也经不住战火缭绕。
中国古代楼阁都是木质结构,易燃易腐,再加上战火、天灾不断,一些名楼逃脱不了“屡建屡毁、屡毁屡建”的命运。如黄鹤楼历建历毁二十七次,滕王阁历建历毁二十九次,岳阳楼仅在清代就重建和复建十八次。
越王楼也是如此。越王楼的历史虽有1350余年,但它以楼的固化建筑物形态存立世间,断断续续不过二百多年光景。千百年来,越王楼曾数次毁损,数次重建。据史料查证,唐末时,越王楼被一场大火烧毁大半,宋初时再毁,台亦不存。元朝大规模修复后,又毁。明初,天下安定后,又对越王楼进行了修整。万历年间,越王楼再次遭受火灾,全部被焚毁,仅剩一个楼台。明末,越王楼又一次重修,但其规模和布局远不如唐代,不久又毁于兵燹。清乾隆初年,一场大火又将其彻底烧毁,仅剩越王台遗址,文物全毁,消失殆尽。乾隆中叶,蜀中才子李调元重游绵州,留下了“不见越王台,但见清江流”“惟有江边月,会照城上楼”的感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越王楼消失了,仅存越王台遗址保留迄今。
时光流淌,日月如梭。1989年9月,绵阳市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在唐越王李贞建造的龟山越王台遗址上,重建历史文化名楼——越王楼,并确立了“大唐明楼,皇家气派,山是一座楼,楼是一座山”的设计理念。2001年4月,设计师们综合专家、学者和市民的多方意见,依据唐至清历代名宦显贵和文人墨客对越王楼题咏的诗文意境,反复推敲,优化设计,形成了“主楼的高度要达到九十九米,建筑风格为仿唐出檐斗拱歇山式、全框架结构”方案。2001年10月,越王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工。2013年2月2日,越王楼重建工程竣工,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重建的越王楼,雄踞龟山之上,主楼高九十九米,共十五层,集閣、楼、亭、殿、廊、塔于一体,一层至五层是阁,十层至十三层是楼,十五层是亭,顶端宝顶似塔,二层南北两方是殿,各层有外廓。
今日之越王楼,风格繁复,蔚为壮观,其宏大气势远胜于始建于唐代的越王楼,成为绵阳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当今仿古单体建筑之最。据悉,滕王阁高57.2米,黄鹤楼高52.6米,岳阳楼高三十二米,均比不上越王楼。重建的越王楼,在高度、形态和面积上,均属全国仿古建筑之最,故有“越王楼霸气”之说。
越王楼矗立于涪江之畔,再现大唐气派。其巍峨挺立的建筑体不仅给人厚重感,其承载的内涵,更彰显了一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传承的底气。
四
绵州是诗仙李白的故乡。
若顺江而下,李白的家乡青莲镇,距涪江岸边的绵州越王楼约二十五公里。
“山秀绵州,水映涪城绵阳。”绵阳地处绵山之南,自古有“山南水北为阳”之说,故得名。
李白从小天资聪颖,智力过人,诚如后来他用诗歌填写的求职信所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也诚如他用诗歌告白的人生履历表:“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
青年时期的李白,熟练掌握了诗歌写作技巧,写得一手好诗。他还拥有一流的剑术,甚至对寻仙问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其出众才华而誉满乡里。
二十五岁出蜀前,李白就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上楼诗》就是李白在蜀中留下的诗篇。这是一首五言绝句,相传是李白十四岁登越王楼时所作。这时,越王楼落成已有五十余年。
那年中秋节前夕,李白随父亲李客来到绵州越王楼,准备参加文人相聚的中秋夜宴。当天下午,父亲就带着他游历了这座文化名楼,而且夜宿于此。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李白登上越王楼,凭栏远眺,浮想联翩。夜深人静之时,只见天空中星光闪烁,于是诗兴大发,在心中酝酿了这首记游写景的五言绝句。
在唐代,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都离不了诗,以文人酒局来说,每一场都是“斗诗会”。中秋佳节之夜,文人雅士齐聚越王楼,欢宴畅饮,行令吟诗。他们早就听闻少年李白才华横溢、思维敏捷,于是以《上楼诗》为题,即席要求他挥洒才思,展示其即兴创作的能力。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李白昂首挺胸,摇头晃脑,声情并茂,脱口而出。那流畅欢快的童声,回荡在空旷的楼宇,质朴可爱,赢得一片喝彩。
李白以少年的目光,仰视眼前的高楼,运用了极其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楼宇的高耸与壮观,表达了对名楼的惊叹与赞美之情。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想象瑰丽,夸张巧妙,活灵活现,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身临其境之感。
好的诗就是一幅画,好的画就是一首诗。李白的这首诗极具画面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摘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玩法,被这位少年诗人信手拈来,用于诗中,生动自然。手好像能摘到星星了,要小声点,不要打扰到天上的仙人,这种率直写法,分明透露着一丝可爱,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
李白采用口语入诗,语出自然,直截了当,充满动感,超越时空。只有短短四句,仅仅二十字,呈现出手摘、声语、恐惊等一连串动作,把登临高楼的愉悦、豪放、可爱与率直,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
五
时光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不知何故,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将李白的《上楼诗》更名为《夜宿山寺》。自此以后,尽管小学语文教科书历经数次修订,一直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的第二版,课本中收录的仍然是李白的《夜宿山寺》。也正是这一改名,引发了人们对这首诗猜想不断,疑惑重重。
如果仅从诗的题目来看,这应该是李白在晚上留宿山寺时写的一首诗。那么,这个山寺叫什么名字?具体位置在哪里?对此,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多年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首诗是李白中年在湖北蕲州游历期间所作。也有人认为,诗中的“楼”,是黄梅县峰顶山的江心寺,所以也名为《题峰顶寺》。
据史料记载,蕲州黄梅县峰顶山江心寺,离城百余里,在人迹罕至的乱山群峰间,并不在山顶,而且是一座砖瓦平房的小寺庙,可见黄梅县峰顶寺不是危楼或百尺楼。
有的专家考据,李白的《夜宿山寺》应该是《题峰顶寺》,是在湖北黄梅县所写。第一句应该是“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而不是“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至于后一句与《上楼诗》完全相同,可能是诗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2006年3月出版的《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1期),刊载了李德书题为《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的论文。文章认为,《夜宿山寺》和《上楼诗》是同一首诗,写作地点是四川,诗中的楼就是绵州越王楼。
李德书在论文中提供了一个证据——李白少作一直在故乡流传,有些已选入李白集和地方志,大部分失传,还有一部分保留在李白故里青莲镇的肖继周老人祖传的手抄本上,其中就有李白少作《石牛诗》《萤火虫》《上樓诗》等。《上楼诗》和今天的《夜宿山寺》完全一致。
那么,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什么要把《上楼诗》更名为《夜宿山寺》呢?也许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语言的美感上看,《上楼诗》相比于《夜宿山寺》,无论是文字还是意境都要逊色得多;二是,从全诗意境和真实背景猜测,《夜宿山寺》可能更贴切一些。
那么,李白的《上楼诗》为什么不直呼为《上越王楼诗》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避讳。李贞父子因起兵被满门抄斩,人们对李贞修建的越王楼避之不及,自然没有人会公开给越王楼唱赞歌了。李白写《上楼诗》时,尽管唐中宗已复位,但并没有给李贞彻底平反,故李白采用避实就虚的夸张手法,用“危楼”代替了越王楼。
唐代以来诸多描写越王楼的诗中,确实出现过“百尺高楼”“危楼百尺”字样,“危楼”似乎成了越王楼的代名词。古人一般用“危”字突出楼的高度。“危楼”在古代一般指三重檐以上的高楼,有时也叫百尺楼。从这些一脉相承的诗句寓意来看,李白诗中的“危楼”应该指的就是越王楼。
山川,作为宇宙的象征,我们难以真正领会它们的真实尺度。唐人尚游,得益于社会的安定富足,广袤的地域和大量的历史遗迹,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游览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繁荣的旅舍酒馆,更为诗人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在李白的漫游经历中,一些登临之作,都意在写“高”。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等诗句,这些针对“高”的夸张描写,无论是三千尺还是四万八千丈,都是对高耸与巍然的赞美,无不彰显出李白这位诗人独特的个性与气质。
六
古人争强好胜是常事,诗人也难免脱俗。
我们熟知当年李白作《登金陵凤凰台》诗,是有意要和崔颢的《黄鹤楼》一比高低。殊不知,杜甫所作的《越王楼歌》,也是一篇和王勃的《滕王阁》相较量的作品。正像《登金陵凤凰台》不让《黄鹤楼》,《越王楼歌》虽从《滕王阁》脱胎而出,但能够不落窠臼,推陈出新,直抒胸臆,艺术成就也不在《滕王阁》之下。王、杜二诗都堪称构思精巧、笔力强健的大家手笔。
记得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越王楼来了一行贵人,他们中有官人,也有诗人,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诗圣”杜甫。杜甫来时,身背一个布袋,布袋里装有一支狼毫笔,走时留下了一首诗。后来,这首诗被赞为名人歌咏越王楼的诗词中最有名气的千古绝唱。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甫从成都送好友来到绵州。好友名叫严武,曾任绵州刺史,后升为东川节度使,今又奉召回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送走严武后,作为东道主的现任绵州刺史,自然要挽留老领导的朋友。于是,杜甫住在了州府附近的治平书院。这里距越王楼不远,每日散步即可到达。
这时,李贞父子已被平反昭雪并被陪葬昭陵,武则天也死去了几十年。杜甫完全没了顾忌,可以用诗文直接、大胆地谈论李贞和他的越王楼。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对越王颇有悼念之情。加之古楼临江倚山,高入云霄,气势非凡,乃至越王楼建成百年之后,其雄姿依旧令杜甫深深震撼。正是在这份难以抑制的感慨中,杜甫创作了著名的《越王楼歌》。
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
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
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
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上下转韵,上则咏越王楼,用极其明丽的色彩描绘了越王楼的巍峨宏大、富丽堂皇,以及楼下滚滚江水之清澈,远山落日的意境;下则登楼吊古,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的杜甫,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斯人已逝,物是人非,昔日的辉煌楼阁,眼下也只能供后人游览欣赏。
在杜甫写《越王楼歌》时,《滕王阁》早已名扬四海,成为世人皆知的佳作。杜甫要写越王楼,就必须另具法眼、独辟蹊径才行。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为,杜甫借越王楼,换题不换诗,随手隐括,别成妙句。
金圣叹感叹道,杜甫此诗的成就高于王勃:“先生正是全取其诗,从头劈削,通身翻洗。试取对照读之,便见两诗脱胎换骨,转凡作圣。异样奇怪,不止是青(出于)蓝之事而已。”
金圣叹分析道,考证王诗与杜诗之不同,主要在于立意的差异。王诗的着眼点在“物换星移(希望做官)”,杜诗的着眼点在“州府磊落(建功立业)”。王诗写的是“阁中帝子今何在”,基调是感慨(忧郁)。杜诗写的是“君王旧迹今人赏(前人旧迹后人赏)”,基调是赞赏(激励)。王诗的风格在风致、姿韵,杜诗的风格在雄奇开张。王诗说:“槛外长江空自流。”杜诗说:“楼下长江百丈清。”显然,两者的情趣、格调迥然不同。
自杜甫在诗中用“磊落”来形容绵州后,绵州就有了“磊落州”的美称。清人李调元就写道:“生为磊落人,复游磊落州。”这是何等的自豪啊。
据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李德书教授介绍,当年在重建越王楼时,绵州一些市民对绿色琉璃瓦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戴了一顶“绿帽子”。李德书给市民解释道,越王楼必须再现“碧瓦朱甍”的原貌,这是根据杜甫的《越王楼歌》中的“碧瓦朱甍照城郭”设计的。
七
越王楼是天下诗文收录最丰富的名楼。
越王楼的记忆,早已积淀成为厚重的诗文。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至清末,各朝各代的文人大家题咏越王楼的诗篇多达154篇。唐诗中有关越王楼的诗词多达六十多篇,仅入选全唐诗的就有二十多篇。据绵阳县志记载,历年来,有十五位绵阳籍诗人、名宦写有讴歌越王楼的诗词。由此,越王楼享有“一座越王楼,半部文学史”的美誉。
大中七年(公元853年),于兴宗出任绵州刺史。夏末的一天,他登上越王楼,放眼楼下的涪江,眺望远处的雪山。面对诗情画意的景象,一股强烈的创作激情涌上心头。他回到书房,挥毫泼墨,写下了《夏杪登越王楼临涪江望雪山寄朝中知友》一诗。
巴西西北楼,堪望亦堪愁。
山乱江回远,川清树欲秋。
晴明中雪岭,烟霭下渔舟。
写寄朝天客,知余恨独游。
诗写成后,仍感余味未尽。于兴宗觉得,越王楼如此绝美,不能由自己独享,应该让天下人共享。怎样才能将他感受到的越王楼的美景传递给朝中的知心朋友呢?于兴宗苦思三日,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决定发起一个“远程诗会”。
中国人喜欢斗诗,先秦时已见雏形。先秦人斗诗,是通过“当筵歌诗”“投壶赋诗”等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中国最原始、也最流行的一种斗诗形式。到秦汉时,斗诗形式已有发展,表现为席间联句吟诗,名曰“即席唱和”,即“大家一起玩”的集体创作模式。直至于兴宗的“远程诗会”之前,古人的詩会,都是近距离、面对面地聚在一起,对酒吟诗。
于兴宗开了书信诗会的先河,相当于今天的信函诗会,或网络诗会。
于兴宗还将以越王楼为主的绵州山水风光创作成画卷,配上他题的诗,又附上书信,希望朋友们都以越王楼为题和诗回复。一连好多天,于兴宗废寝忘食,创作了十六幅越王楼风景画,抄录了自己登越王楼的诗十六份,并准备了十六个信封。然后通过官方驿站,寄送给朝中的十六位知心朋友。
几个月之后,于兴宗收到了十六位朋友寄来的十七首和诗。加上自己的那首,总共十八首。这场“远程诗会”取得圆满成功。史载,当朝一些有才学的官员纷纷与于兴宗和诗,如卢求、杨牢、王铎、李续、李汶儒、田章、薛蒙、李邺、于瓌、王严、卢栯等。
刘禹锡在《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并引》中云:“东阳令于兴宗,丞相燕国公之犹子。”史书中说,兴宗不仅能诗,还善于交友,他与当时诗人刘禹锡、方干、李汶儒等人均有交往酬和。
八
好景须入画。
诗韵悠悠,画幅款款。千百年来,越王楼以其独有的风姿,不断吸引着众多画家前来写生、作画。这座千古名楼,在历代画家的笔下变成一幅幅传世名作,让它得以在真身无存的岁月里,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世人眼前。
据考证,唐、宋、元、明、清历代画家留下的越王楼精美画卷中,尤为珍贵的有两幅:一幅是宋代郭忠恕的《明皇避暑宫图》,一幅是元代李容瑾的《汉苑图》。华丽的楼阁台榭建筑在高岭上,呈飞檐歇山顶,斗拱结构描绘清晰,以天空、树木、远山为衬景。画家采用鸟瞰式的构图,借助直线、横线和斜线的巧妙组合,将越王楼的殿阁亭台一一展现,绘就成一组既优美又宏伟的建筑群落画卷。
中国名楼文化历史久远,历代画家用最为直观的艺术语言——界画,表现了亭台楼阁严谨工丽、端庄雍容的艺术之美,让无数人为之倾倒。诗人们赞美其“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像一只振翅欲飞的雉鸟,充满了激情。哲人们感叹,其实现了想象与理性的和谐统一。
好的画就是诗,它巧妙地展开了历史的某个瞬间所凝固的空间,沿着这一空间,思绪可以朝着无尽的角度自由延伸。
早期的界画,专指以亭台楼阁为主要表现对象,用界尺引笔画线的表现方法。界画适于画建筑物,其他景物用工笔技法配合,通称为“工笔界画”。现存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阙楼仪仗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大型界画。宋代的著名界画有《黄鹤楼》《滕王阁图》等。
有趣的是,这些名画,见证和记忆了越王楼几度废墟、几度重建的历程,而且每一次重建都和前朝不同。越王楼没有固定版本,只能从一些古人的画作中窥得一二,领略不同时期越王楼的独特韵味。
五代时,越王楼失火,烧掉大半。到了宋朝应该进行过修复,但是在史书上找不到记载,也就不知道确切时间。研究者根据南宋画家赵伯驹创作的越王楼图轴推论,南宋时越王楼已经得到恢复。至元朝时,越王楼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有元代李容瑾的画作《汉苑图》为证。
雍正年间,果毅亲王允礼曾经来绵州游玩过,写了一首诗赞叹越王楼的景色:“唐家弟子爱楼居,碧瓦朱甍半新故……”说明此时越王楼已经恢复。而“半新故”则说明,明代最后一次毁坏并不彻底,部分建筑还有存留。清代画家张廷彦留下了越王楼图轴,印证了在清代越王楼得到了复建,并且存在了很长时间。
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
岁月流水,记忆悠长。越王楼记忆着曾经的辉煌,也记忆了诗人远去的身影。
伫立越王楼下,抬头仰望,只见朱漆廊柱,高阁层轩,参差叠置,蔚为壮观。登楼而上,遥想古人登临的情形,逐字逐句品味诗句的意境,韵味无穷。站在越王楼的最高处,凭栏远眺,天野苍茫,一揽江山,才能真正感受到越王楼的雄伟与磅礴,眼前无疑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