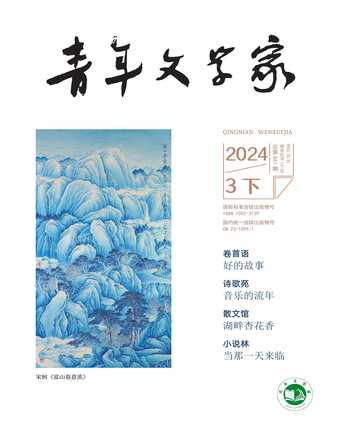从“二元对立”到“互生共融”:《幕间》的生态诗学
黄雪芹


作为现代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夫(1882—1941)的作品自出版以来,就引发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幕间》(Between the Acts)是伍尔夫的最后一部作品,发表于1941年。学者们多从女性主义、现代主义等角度解读该作品。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开始从人类学与伦理学、空间政治批评、生态批判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考量。其中,空间政治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起步较晚,属于伍尔夫研究的后起之秀。
《幕间》完成于“二战”爆发前夕。故事发生在1939年6月的某一天,描绘了英国某乡村举办露天历史剧表演的场景。小说以一天的时间为背景,展示了战争的阴影悄悄逼近时,乡村的生活和动态。通过舞台上的历史剧表演,伍尔夫巧妙地揭示了人类历史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同时反映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通性和变迁。小说凸显了伍尔夫对时间、人类关系和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在“一战”的铁蹄下,自然和人类文明已遭受不可逆转的摧毁。而伍尔夫写作《幕间》之际,西方社会正笼罩在“二战”即将来临的巨大阴影之下。在这部绝笔之作中,伍尔夫通过独特的意识流叙事技巧,深入描绘人物内心世界,同时巧妙地运用隐喻和自然意象,展现了对战争背景下人类关系和社会状况的深刻思考。
本文试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幕间》中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导致两者之间的生态失衡关系的根源是父权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伍尔夫通过揭示不对等的两者关系,解构了传统二元对立中心论,表达了作家对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互生共融的和谐社会的渴求和生态诗学。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源于法国作家奥波尼的《女性主义或死亡》。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瓦尔·普拉姆伍德在《女性主义理论百科全书》的生态女性主义词条中指出:“女性和其他屈从群体及自然,与男性精英阶层及理性,两者形成的二元论联系,是理解西方文化殖民式根本属性问题的关键。”知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格里塔·加德给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概念:“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如其名所示,是关于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或女性与自然的,还基于以下前提来讨论环境恶化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即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相互对待的方式密不可分。”国内知名学者金莉教授指出:“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生态女权主义号召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认为如果没有解放自然的斗争,任何解放女性或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生态女权主义》)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派别众多,观点各异,但在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中存在一种基本共识:人类对自然的掌控与男性对女性的利用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深入理解前者将有助于理解后者,反之亦然。换言之,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建立在一种父权制度的世界观之上,这一观念奠定了女性被支配的正当性。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将关注点拓展到对各种压迫和统治结构之间关系的考察。
二、《幕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互生共存的紧密关系。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自然逐渐成为人类奴役的对象。《幕间》的开篇即写到自然遭受的创伤:“污水沟的选址是在罗马路上。从飞机上仍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地看到英国人、罗马人和伊丽莎白庄园留下的痕迹,以及耕种留下的痕迹,因为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曾在那儿开垦山丘种小麦。”人类的斗争和对土地的开发给大地带来的伤痛尚未愈合,而“二战”的来临将不可避免地给土地和自然带来毁灭性的创伤。在父权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男性对自然的压迫和支配,而女性与自然之间则展现出更为亲近融合的关系。
(一)男性与自然
《幕间》中男性与自然的关系,多是压迫、暴力、支配。小说中父权制的代表人物奥利弗先生是英属印度行政机构的退休公职人员,尽管已经退休,他仍然“像命令一支军队一样”,喝令他的阿富汗猎犬苏赫拉布,“让其听命于他”。在他的责骂下,猎犬乖乖地“向他认错”,并“蜷缩到老人脚边”。奥利弗先生总是用一股绳索套在猎犬的项圈上,不论走到哪里,他都牵着这个套索。套索是老奥利弗实现控制和支配的工具。奥利弗先生在书房看完报纸后昏昏欲睡,在梦境中他看到自己成了“一个戴着头盔的年轻勇士”,双手紧握着枪,想射杀一头小公牛。奥利弗先生的儿子贾尔斯在演出中场休息准备去谷仓的路上时,遇到一条嘴里卡着一只蟾蜍并盘成圆环的橄榄绿色的蛇,蛇没法儿吞下蟾蜍,蟾蜍也半死不活地卡在蛇嘴里。“一阵痉挛使蟾蜍的肋骨开始收缩,鲜血渗透出来”。贾尔斯“抬起脚,踩在它们身上”,“白色帆布的网球鞋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鲜血。这是他的发泄动作”。跟父亲老奥利弗先生一样,作为父权社会的男性强者,他将对自己和生活的不满与怒火,肆意发泄到大自然中。
此外,在建造波因茨宅之时,为了躲避某些自然因素,节约马力成本,男人们让宅子面朝北建在山谷中,而不是朝向阳光充足的南面,“大自然提供了这个建房的场所,人们却把宅子建在山谷里”。躲避大自然的结果是:“冬天的冷雨敲打着窗玻璃,寒风吹落一地落叶阻塞排水沟。”在18世纪的某个冬天,宅子甚至被积雪封锁整整一个月,“树木倒塌”。年老的斯威辛太太,只能在“每年冬天来临时”,躲到黑斯廷斯居住。此外,由于不向阳导致的潮湿,书房的书本在冬天会发霉,而书房是“这栋宅子的心脏”,“书籍是‘灵魂的镜子”。
(二)女性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幕间》中,女性人物与自然呈现亲近融合的关系。《幕间》中的曼雷萨太太从伦敦回到乡下,观看露天历史剧表演。她“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就是大自然的野孩子”,她喜爱和大自然亲近,会深更半夜在花园里散步,认为乡村是“避风港湾”,是“继伦敦之后第二个能让她微笑的地方”。在这栋位于乡下的波因茨宅,这个“大自然的野孩子”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束缚,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开胸衣”,甚至想“在青草中打滾儿”。伊莎感到曼雷萨太太对于乡村的喜爱非常“真实”。斯威辛太太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座自己的房子,这样她就能“拥有自己的花园”。她居住的卧室挂着印花布的窗帘,“绿色的衬里给窗户染上了淡淡的绿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她最爱读的书是《世界史纲》,常常陷入沉思和遐想,想象史前社会的大陆,满是大自然的意象,比如禽龙、猛犸象、乳齿象。历史剧导演拉特鲁布女士选择了户外演出,将灌木丛作为更衣室,置身于大自然中。她认为这是“室外演出的最佳地点”,“草坪像剧场的地板那么平坦”,“周围的树木像柱子一样护住舞台”。大自然的元素贯穿了露天历史剧的演出。
三、《幕间》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
《幕间》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大体分为兄妹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大多充满压迫和矛盾。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和自然一样,处于他者的位置。
伊莎和丈夫贾尔斯的关系紧张。两人因为在苏格兰钓鱼而偶遇,“她的钓鱼线缠结在一起了,她便放弃了,坐在一旁看他钓鱼,看溪水从他双腿间流过……然后她便爱上了他”。三十九岁的伊莎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穿着一件褪色的孔雀图案的睡袍,一直在陪生病的儿子。她有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却因不打理而显得凌乱。她虽然关注发型,但“从没有烫过卷发或剪过短发”。伊莎是家庭主妇,依靠丈夫的工作来维持家庭开支,自己承担了家务琐事,她“讨厌家务事,讨厌占有欲,讨厌母亲的职责”,但只能默默忍受。公公跟她告状,说她儿子是个爱哭的孩子,是个胆小鬼。她虽不高兴,却不敢反驳。她爱好文学,但怕被丈夫发现,随手记下的文字和思想为了不让丈夫生疑,“特意将它装订成账簿的样式”。而伊莎的丈夫贾尔斯在露天历史剧时偶遇城里来的曼雷萨太太,便如影随形地跟着献殷勤,完全不理会伊莎的感受。在缺乏交流和压抑的氛围下,伊莎也在无意识地寻找婚姻外的精神寄托。“饱经风霜、沉默寡言、浪漫多情的乡绅农场主”—罗伯特·海恩斯,总能让她感受到神秘和热情,在她眼里“那是爱”。在历史剧演出的一整天,伊莎总是在搜寻海恩斯的身影,而她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没有感情沟通的婚姻已像无形的枷锁牢牢把她绑定。伊莎是当时社会典型的女性缩影,扮演着父权社会下完美的“房中天使”形象。马库斯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新论》中提到:“女性的价值和天赋,不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文化建构的,在男性主宰的男权社会中,都被边缘化了。”
斯威辛太太的宗教信仰被哥哥取笑,当她说“恐怕要下雨,我们只能祈祷”时,哥哥说:“并且提供雨伞。”斯威辛太太脸红了,因为哥哥“攻击了她的信仰”。当她问“碰碰木头”的起源是什么时,哥哥说是迷信。她又一次脸红了,“她连自己轻轻的吸气声都能听见,因为他又一次攻击了她的信仰”。她虽然一直想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最终还是投奔哥哥。斯威辛太太回忆起小时候她“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去钓鱼”,当哥哥让她取下鱼钩上的鱼时,她看到鱼鳃里全是血,吓得大叫,而哥哥对她低声咆哮,训斥她的胆小,而不是给予安慰。
贾尔斯对待家族女性的态度也多是消极的。在露西姑姑面前,“他出于本能,把自己的宿怨都归罪于她,如同一个人把外衣挂在钩上”。而碰到四十五岁风韵犹存的曼雷萨太太,他就像换了副面孔似的献殷勤。他一方面生气露西姑姑只会欣赏风景,但当曼雷萨太太说风景真漂亮时,他非但不生气,还“窝着手掌又给她点了一根烟”。作为男性,贾尔斯和曼雷萨太太的暧昧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不良后果,正如妻子伊莎所说:“他的不忠一点儿影响都没有—而她的不忠却会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幕间》中矛盾微妙的两性关系,体现了精神层面的生态失衡。在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始终处于强者的位置,而女性与自然一样,受到前者的压制。
四、对构建互生共融美好社会的渴望
在《幕间》中,伍尔夫不仅指出了二元对立导致的两性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还通过女导演的露天历史剧解构了传统二元对立中心论,表达了作家对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互生共融的和谐社会的渴求和生态诗学。评论家马克·赫西指出,《幕间》是伍尔夫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证明,体现了作家对构建互生共融社会的渴望。“这就是这场露天剧的好处—它把人们聚集到一起。”热爱自然、喜爱读历史书的斯威辛太太想象着“将一切融为一体:绵羊、奶牛、野草、树木、我们自己—都融合成了一体”。
《幕間》的背景设在英国乡村,伍尔夫对自然和乡村的渴望以及回归并非逃避,实际上是她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对大自然的摧毁的批判。在小说的结尾,当众人都散去,伊莎和贾尔斯“两个人第一次单独待着,他们没有说话”。然而,在争吵完后,“他们会拥抱,从那个拥抱可能会有另一个生命诞生”。融合与新生命,伍尔夫在她的谢幕之作中表明了她对互生共融社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