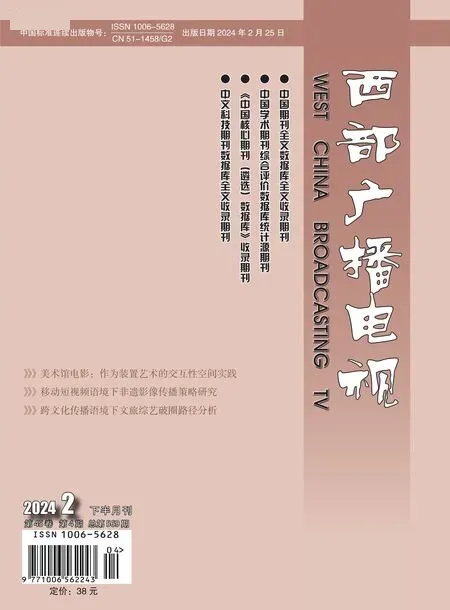浅析电影《消失的她》中的“戏中戏”
贾旖旎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2023年暑期档的影片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史诗级巨作《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国漫《长安三万里》;有老年爱情喜剧《我爱你!》;有直击体育现实的《八角笼中》;当然还有大热的悬疑类型影片《消失的她》。在这样一个神仙打架、各显神通的竞技圈中,《消失的她》突出重围,取得上映首日票房突破1亿的成绩,成功跻身2023年电影票房排行前十。《消失的她》是陈思诚继导演“唐探”系列、监制“误杀”系列后的又一大力作,延续了他所擅长的悬疑类型优势,集结了朱一龙、倪妮等实力与流量俱存的演员,堪称一部现象级悬疑电影。
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心中的谜团终于在得知一切都是由沈曼(倪妮饰)导演的一出戏时迎刃而解。这一转折为影片前三分之二发生的种种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而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导演带领观众慢慢拨开迷雾,重见天日,观众也得以撕开何非(朱一龙饰)“好男人”的面具,看到其丑恶的嘴脸,感叹人性的贪婪。在制造观影爽感与影片悬疑感方面,沈曼导演的这场戏功不可没,形成了影片“戏中戏”的叙事特色。
1 “打破第四堵墙”的“戏中戏”
随着大众对精神生活需求的逐步提高,电影作品也在持续地进行优化与创新。其中,“戏中戏”在影视创作中成为炙手可热的叙事技巧,当观众深入了解戏中人物的生活时,还能窥见人物作为演员所扮演的另外一出戏,这不仅丰富了观众的视听体验,也为影片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哲学审美意味。
“戏中戏”通常指在某一虚构的文本中存在另一个与之不同的其他文本,在电影中则表现为影片中存在另外一部影片、戏剧等。影片故事与影片中的故事形成一个套层结构,外戏为基础,内戏灵活布局,两者或相互映照、或自我解构,抑或角色间离,但它们之间都有着较为客观清晰的界限,人物的现实生活与角色生活并不完全一致[1]。然而,在影片《消失的她》中,这一常规的“戏中戏”模式有所升级,内戏的“第四堵墙”被打破,将外戏的“观众”拉入了内戏,与内戏中的角色一同为观众呈现一出好戏、一场智斗。影片中的沈曼是话剧导演,当她得知自己唯一的闺蜜李木子(黄子琪饰)在东南亚海岛上无故失踪后,她决定通过设计一场戏,逼迫最大嫌疑人何非说出真相,说出李木子所在的位置[2]。在沈曼导演的这场内戏中,陈麦(倪妮饰,是沈曼的假身份)、假李木子(文咏珊饰)、郑警官(杜江饰)等角色都由外戏中沈曼团队的演员所扮演,他们知晓角色、剧本情节,他们的戏是演给处在外戏层面的“观众”何非看的。但沈曼的这场内戏又不单单是一场围起四堵墙供何非观赏的戏,而是打破了“第四堵墙”,将何非这一特定的“观众”也邀请进来,让其成为内戏的重要角色之一,只不过“观众”何非并不知道内戏剧本的情节,甚至按照自己的剧本在表演。
“打破第四堵墙”来源于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ergeyevich Stanislavski)“演谁是谁”的观念相反,他将演员看作“中间人”,希望演员为角色与观众的互通交流搭建起桥梁[3]。演员既可以扮演角色,向观众呈现角色的生活,又能跳出角色,与观众直面交流,防止观众沉溺于角色的生活世界,从而帮助他们理性思考,起到间离的作用。当演员跳出角色与观众交流时,便是打破了与观众之间无形的“第四堵墙”[4]。然而,在影片《消失的她》中,沈曼的表演团队虽然同样打破了与“观众”何非之间无形的“第四堵墙”,与其互动交流,但他们“打破第四堵墙”的作用更接近于如今戏剧行业的“沉浸式话剧”“戏剧治疗”,他们并不想让“观众”何非理智思考,相反他们希望通过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让何非具有“观众”和“演员”的双重身份,深陷他们虚构的世界中,成为他们剧本的执行者。这种“打破第四堵墙”,模糊内戏与外戏界限、模糊现实与虚幻界限的“戏中戏”设计,不仅使内外戏连接更加紧密,还暗示了何非的命运走向,侧面隐喻了影片的主题。何非如同掉入了沈曼制造的内戏而无法辨析现实外戏与虚假内戏一般,他更是陷入了赌博发家的虚幻中,无法清晰地辨别现实与梦幻,他自认为即将实现的富有现实终究不过是戏梦一场,到头来还是要从虚幻的世界回到现实,接受惩罚。李木子为爱所困,被何非困在深海的囚笼中,何非同样如此,他被沈曼设计的“戏笼”所困住,更被世间虚无的诱惑所缠绕,正如影片主题曲《笼》中所唱“为何囚人者也像困兽”。
2 悬疑营造剂的“戏中戏”
如前文所述,观众恍然大悟的时刻,正是沈曼跳出律师陈麦的角色,以李木子唯一闺蜜的身份再次与何非相见、与观众相见的时刻。沈曼戏内戏外身份的转换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感[5]。这种身份的转换与“悬疑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经典影片《惊魂记》中的类似,当观众得知看起来天真的诺曼·贝茨与阁楼的母亲其实是同一个人时,同样大为震惊。诺曼·贝茨的两种身份是“精神分裂”所给予的,沈曼的两种身份则因“戏中戏”的设定而存在。可见,“戏中戏”的设定是一颗“定时炸弹”,在适当时刻引爆全场。同时,影片中的“戏中戏”结构还作为影片情节的大框架,为影片的悬疑色彩奠定稳固的基础。其中的内戏部分是追寻李木子的失踪真相,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给观众抛出悬念,制造悬疑感;而外戏部分则是为观众揭露真相,戳穿何非在内戏中的谎言,暴露其丑陋的内心。内戏与外戏,一寻找、一揭露,正是悬疑片的内容范式。在悬疑片中,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都让观众在迷宫中寻找出口,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真实答案。而《消失的她》则以“戏中戏”为依托,划分出了寻找与揭露两大部分。因此,影片《消失的她》中的“戏中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作为搭建悬疑类型框架的必然要素而存在。
“戏”除了作为影片框架存在,还是影片悬念制造的担当。不仅是沈曼导演的这场戏在误导观众,何非也在演一出“妻子无故失踪,丈夫着急难过”的戏码,两个剧本的情节相互交织,两方势力相互欺骗,导演借此混淆观众视听,让观众难以判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又有何种目的。影片开篇,何非来到了警察局寻求帮助,因为他的妻子失踪了,这是导演抛出的第一个悬疑点,此时的观众已经被何非痴情的表演所迷惑,并且顺着导演的引导陷入了何非的妻子到底去了哪里的疑问中。紧接着,“失踪的李木子”出现了,但何非却说她是假的,第一个疑问还没解决,第二个悬疑点便出现了,于是观众继续思索这个女人是谁?她是真正的李木子吗?如果不是,那她为什么要冒充李木子呢?这同样是何非的疑问,他希望通过手机照片、李木子腿上的疤、酒店服务员、书店监控等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面前的这个红衣女人是假的李木子,但都无果。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导演迅速又抛出了第三个悬疑点,何非的药被暴露了,观众又开始疑惑,难道这个红衣女人真的是李木子,有精神问题的是何非吗?就连郑警官都不再相信何非,甚至何非自己也陷入了对自己身份怀疑的状态。这时何非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陈麦顺势而入,取得了何非的部分信任,也获得了观众的信任。沈曼导演的内戏欺骗了何非,更欺骗了观众。导演看准时机,将另外一出戏融入何非的叙述中。就这样,观众在沈曼与何非分别导演的两场戏中迷失了自己[6]。简单来说,导演通过开篇抛出的三个悬疑点引发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无法判断危险在哪里,并适时误导观众将陈麦与何非绑定,相信陈麦与何非的所有叙述,进而让何非在内戏中“演戏”,完成“戏中戏中戏”。两场戏不断交锋,观众内心的疑问也逐渐积攒,等到陈麦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一切悬念烟消云散,观众的身心获得了释放。综上可知,“戏中戏”在影片悬疑感的营造上功不可没。
3 严丝合缝的内戏与外戏
影片将“戏中戏”作为悬疑框架,通过“戏中戏”与“戏中戏中戏”为观众构建错综复杂的迷局,模糊观众的视野,使其难以分辨现实与虚构,对于内外叙戏的设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3.1 外戏为本的内戏建构
影片中,内外戏在情节的设计上并非简单地呈现为两条平行线,而是内戏情节在外戏情节的基础上展开设计。如前文所说,制造内戏的目的是逼迫何非说出李木子失踪的真相,所以内戏的情节必须以外戏情节中李木子的失踪为核心进行构建。针对外戏中李木子的失踪,内戏围绕何非设计了“智者”陈麦、“反派”假李木子、“协助者”郑警官等角色,并“打破第四堵墙”,将外戏的“观众”何非拉入内戏。只不过内戏的剧本设定无法完全固定,毕竟何非并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场戏,他是按照自己的剧本在表演。所以,影片中沈曼的表演团队在掌握了何非与李木子的全部信息后,还需着重探求何非的心理,并计划好各种可能出现的情节状况,从而确定内戏的角色与大致方向,至于具体的细节与台词则只能靠演员即兴发挥。也就是说,影片的内戏是以外戏的何非与李木子为依托,在同为外戏“观众”身份的何非表演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两者紧密相扣,可谓是一场冒险的真人秀表演。
3.2 人物互文紧扣的内外戏
除情节外,影片还通过人物的巧妙设计黏合内戏与外戏。影片的内戏为了利用“戏中戏”诈出何非口中的真相,设计了“假李木子”的角色,其在表演前愿意为了这一角色忍痛在大腿上烫出疤痕,面对何非时毫不畏惧,威胁他,协助沈曼对付渣男。这都源于外戏中扮演“假李木子”的演员自身的亲身经历,其极其痛恨渣男。不管是在外戏还是内戏中,人物都处在与渣男群体对立的方向上。这一设计给予了人物充分的行动动机,使观众信服,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还使内外戏之间的连接有了质的飞跃。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便是沈曼,作为李木子唯一的闺蜜,她与何非势不两立,但她不得不沉住气在内戏中扮演帮助何非的律师陈麦。沈曼在内外戏中两个人物的表面立场完全相反,但她在内外戏的目的其实都是一个:找到李木子的下落。这其实也模糊了内外戏的界限,使得内外戏合二为一。
3.3 台词隐喻的内戏
影片中外戏人物一些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达的想法通过内戏角色的台词表达了出来,使台词具有了隐喻意味,内外戏的连接也更加严密。当陈麦质问何非“你有多少事瞒着我?”时,表面上是作为帮助何非的律师身份在问,实则是作为李木子唯一的闺蜜身份想从何非的嘴里套出李木子的下落。当何非拒绝告诉陈麦自己关于赌博的相关事情时,陈麦以一个正常女性的心态进行误导,“一个女人以为自己嫁给爱情,结果发现自己的丈夫是个赌徒,她就只能选择报复,她就是要制造混乱,她要折磨你,她要纠缠你,她要让你生不如死”。这段台词不仅是内戏中陈麦的剖析与误导,更是外戏中沈曼内心的真实想法,她憎恨何非,她现在就要代替自己的闺蜜李木子折磨何非,要何非的全部,让他生不如死。与沈曼一样,假李木子在被何非质疑身份时眼含泪水地说:“何非,你说过,会守护我一辈子的,这才一年。”这句话表面上是内戏中假李木子的台词,但也是扮演假李木子的女演员的内心声音,她在外戏中积攒了许久的愤怒与伤痛在这一刻爆发,这句台词和泪水不是假的,是她真真切切的内心表达。除此之外,这句台词也是假李木子在替外戏中真正的李木子鸣不平,这句话是在为角色、为自己、为更多女性发声,使得内外戏的黏合更加紧密。
3.4 跨内外戏空间的场面调度
影片不仅在文本叙事中注重内外戏的联系,也在影像叙事时将内外戏巧妙连接。影片中揭露陈麦在外戏中的真实身份时,导演并没有安排沈曼的表演团队直接全部出现在内戏的精神病院中,而是让何非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来到沈曼表演团队亮相的废弃厂房,让何非自己发现自己原来是掉入了沈曼设计的戏中。从精神病院到废弃厂房,从内戏到外戏,何非完成了时空的跨越,这样跨时空的人物行动及跨内外戏空间的场面调度使内外戏之间更加贴合,给予了观众更加强烈的震撼。
总之,电影《消失的她》以外戏情节为本构建内戏情节,通过内外戏人物的互文与紧扣、内戏台词的隐喻以及影像叙事上跨空间的场面调度,力求达到内戏与外戏的严丝合缝。
4 结语
电影《消失的她》之所以能够在类型众多、质量上乘的暑期档电影集群中脱颖而出,除了有演技与流量兼存演员的加盟,更离不开影片巧妙运用的“戏中戏”叙事技巧。影片中的“戏中戏”不拘一格,“打破了第四堵墙”,将外戏“观众”引入内戏,以外戏为核组织内戏,使内外戏中的人物相映、紧扣,借内戏台词含蓄表达,让人物跨内外戏空间调度,不仅营造了极强的悬疑感,还隐喻升华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