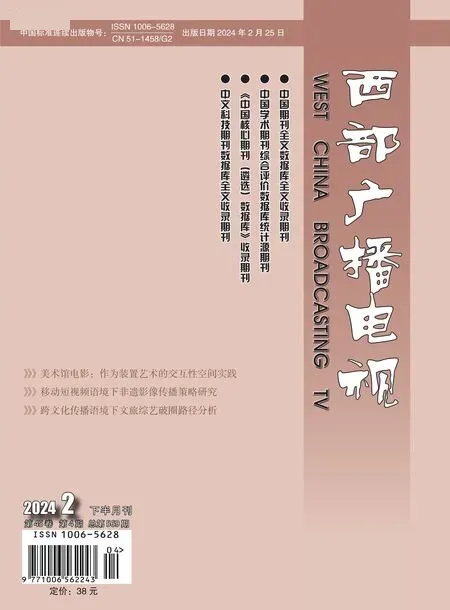历史的形象化演绎:浅析《奥本海默》的人物塑造
梁艺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
2 0 2 3 年8 月3 0 日,由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Oppenheimer)在中国上映,影片根据凯·伯德(Kai Bird)与马丁·J.舍温(Martin J. Sherwin)合著的《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一书改编[1],主要围绕奥本海默从从事物理学研究到领导美国原子弹建设以及战后受到政治审查的经历展开叙事。
电影《奥本海默》将目光聚焦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展现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精神面貌与人格特征,通过对角色的描摹与刻画,塑造出鲜活的、具有历史记忆感的人物形象。影片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片段,重演了奥本海默的人生历程,在呈现主人公人物形象传奇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其身边一众配角人物的塑造。
作为一部历史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并未止步于复现历史,而是通过饱满的人物塑造来引发观众的共情。根据角色动机和行动,结合影片“人与规则的矛盾”的主题,《奥本海默》中出现的角色可以被划作三组,彼此间互为对照。这些人物不仅具有完整的角色性格、明确的历史定位,还呼应了诺兰所欲彰显的精神内核:人类应当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防止它沦为纯粹的政治奴隶乃至不同意识形态相互对峙的强大工具。也正是如此,《奥本海默》呈现出了独特的叙事魅力和艺术效果。
1 沉默的泪水:奥本海默与凯蒂
作为全片当之无愧的主角,奥本海默是影片刻画得最深入、最细致的一个角色,电影利用技术、画面和声音的一体化效果,将其内心活动充分外化。在氢弹制造问题的质询环节,面对检察官的步步紧逼,罗伯特·奥本海默表现得极度不安,背景音乐也愈加杂乱,在剪辑中穿插了象征奥本海默往日梦魇的片段,甚至到最后,日常室内光线下的会议室中竟然出现了原子弹爆炸时的剧烈白光。不难看出,诺兰大胆运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将奥本海默面对科学伦理问题时的挣扎与迷惘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也在此时明了:身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无法预测未来,更难以背负名为“人类命运”的重担。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就人物塑造提出了“照明理论”,认为“如果你的人物占据了生活圈的中心,并且所有其他与之有互动的人物都围绕着他,那么,每当有人与主要人物发生互动时,其他人物就会揭示或阐释主要人物的不同侧面”[2]56。影片中,在公开发表过多次对当时美国政府不利的言论之后,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遭到质疑,他本人的信誉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针对奥本海默的“秘密听证会”背后,路易斯·施特劳斯是最大的幕后黑手,爱德华·泰勒则因为与罗伯特长期以来的分歧,没有为他作出正面的担保。面对他们昭然若揭的政治迫害,奥本海默本人安之若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其妻子凯蒂的义愤填膺。面对同样的“互动人物”时,夫妻二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物反应,对应的则是他们不同的侧面形象。
影片中,导演设置了多处情节点,以展现相同情境下凯蒂的愤怒与奥本海默的平静。凯蒂多次情绪激动地指责奥本海默对于不利处境的不作为,导演在她的台词设计中加入了大量脏话,并随时间线的推进和情节的展开而出现了摔打东西等更为激烈的肢体表达,显然,言语上的谩骂不足以泄愤。在愈发艰难的现实面前,奥本海默仍然面色平静、沉默寡言。影片结尾处,老年的奥本海默握住了爱德华·泰勒伸来的手并报以微笑,凯蒂却一脸铁青,拒不握手。如此戏剧性的动作设计,可谓鲜活灵动又直截了当,对二人的形象进行了强烈的对比。
诚然,奥本海默难以替全人类解决科学伦理问题,但无论奥本海默本人是否有意,他已被公众奉为神明。如此一来,对于政界明目张胆的污蔑,奥本海默显得更加谨慎。显然,奥本海默深知自己的言行所附带的影响力,他拥有的话语权也成为他的诅咒,于是他开始接受外部环境的框定,在规训之下成为一个符号,而他的妻子凯蒂则保留了更多身为人的喜怒哀乐,不必是完美的、符合道德的楷模。
但奥本海默沉默的泪水未必没有力量,他长久以来的道德焦虑,让那之后的人类在终极毁灭的边缘保有一丝清醒和冷静,始终与全面战争保持着良知的距离。
2 弄权者与旁观者:路易斯·施特劳斯与参议院助理
路易斯·施特劳斯在电影中作为反派人物出现,诺兰对其活动空间的设计极为有限,大多是在听证会的现场或小型会议室中,因此该人物形象主要借由台词与神情塑造,演员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为此贡献出了极具张力的表演。在诺兰这里,施特劳斯被塑造成一个较为典型的、以利益为导向的政客,通过表现其在面对科学家时的反应,进一步体现美国内部当时的意识形态博弈[3]。
为了塑造施特劳斯搬弄权力直至迷失自我的形象,导演设置了两处典型情节点,并在影片中通过施特劳斯本人讲述、旁人回忆等形式,不断强化这两处情节点的重要性。第一处是施特劳斯对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在湖边说了什么”这件事耿耿于怀。参议员提问施特劳斯,为何不在与奥本海默的初见之时就对他的政治过往提出质疑,施特劳斯直言自己当时只在担心“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说的话会让他讨厌我”,这句话在当时的听证会会场上引发了众人大笑。听证会会场中的人们以为这是施特劳斯的玩笑话,这显然也是导演希望银幕外的观众对此处情节的理解。第二处则是在影片的中间,在一次讨论是否该向挪威出口同位素的原子能委员会上,奥本海默公开嘲讽施特劳斯的观点。影片首次提到这个情节是施特劳斯自己的回忆,当时的他只是感叹着说出:“这个经历了许多的人怎会如此盲目?”在影片的前半部分,这两处情节点依次登场,但都点到为止,导演并未急于展示其对人物行为动机的巨大作用。如此润物细无声的处理,为影片后半段施特劳斯形象的揭露与情节反转做好了铺垫。
在影片的162分钟处,施特劳斯遭到科学家希尔不留情面的控诉,回到房间后的他气愤地说:“奥本海默第一次与爱因斯坦见面,就策动科学家反对我……”此时,导演才通过台词将这一人物的真实面孔展现给观众:原来他真的对如此细小的一件事耿耿于怀!
在影片中,与施特劳斯一同行动的是一名参议员的助理,这是电影中相对特殊的一个角色,他的性格特征、人物背景几乎无迹可寻。比起影片中其他有着鲜活印记的角色,他更像携带着“观众视角”进入了电影之中,与银幕外的观众一同被施特劳斯哄骗,在真相大白后恍然大悟,在施特劳斯落马后拍手称快。他也像是导演思想的化身,面对施特劳斯的质问“希尔为何来抹黑我?他有何目的?”,参议院助理以“做对的事需要理由吗”回应,在施特劳斯又一次强调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的“策动”时,参议院助理说道:“既然没人知道他们那天聊了什么,也许他们完全没聊到你?也许他们在讨论更重要的事。”这一句台词的设计直截了当地将《奥本海默》的情感主旨点出:对于全人类而言,科学本身比官场博弈重要得多。
在影片139分钟的一处细节显示,施特劳斯提前知道了《时代》杂志的新闻标题,参议院助理认为他手眼通天,并且精于算计。于是他顺势推断出,奥本海默遭受的政治迫害是施特劳斯造成的。施特劳斯自认“真正的掌权者不会现身”,而事实是他拙劣的政治把戏不仅被旁观的科学家们识破,更被一位无关的参议院助理识破。正是因为有了参议院助理的角色设置,才更加体现出了施特劳斯作为政客的盲目自大。“人物(需要)有一个强有力且清晰的戏剧性需求。”“戏剧性需求是指在剧本中人物所期望赢得、攫取、获得或达到的目标。”[2]49对于施特劳斯而言,“赢得政治地位”是他贯穿整部影片的戏剧性需求,而他也正是被这样的需求蒙蔽了双眼,因官场游戏的规训而割让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于生活琐事的判断力,被无孔不入的弄权者思维所侵蚀。
3 同行或者陌路:欧内斯特·劳伦斯与伊西多·拉比
美国电影编剧悉德·菲尔德认为:“电影即是行为;动作即是人物,人物即是动作;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表明了他是什么样的人。”[2]54影片中,欧内斯特·劳伦斯与伊西多·拉比以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好友身份出场,作为配角人物,电影对劳伦斯和拉比的刻画深度有限,但导演仍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出场的篇幅,通过他们的选择与行为,完成了这两位颇具记忆点的人物的塑造。
电影中,劳伦斯是比奥本海默更早加入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得知奥本海默参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后,作为好友的劳伦斯起初用言语暗示奥本海默不要牵扯太深,但奥本海默并未听取劳伦斯的建议,甚至在实验室里办起了工会。劳伦斯见状,怒吼着将所有人赶出实验室,把奥本海默单独留下来斥责他在政治问题上的不谨慎。在这场劳伦斯与奥本海默的对手戏中,导演使用手持镜头拍摄劳伦斯,凸显出人物此时心急如焚的心理状态,同时使用近景配合浅焦的方式,让演员脸上面红耳赤的表情更加清晰,与这个角色一贯西装革履的绅士形象形成对比。在这场戏中,劳伦斯对奥本海默吼道:“他们会因为这种事而不让你加入计划!”劳伦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加入战争,选择审时度势、见机而行,成为被战争环境规训的个体。
与劳伦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科学家的拉比拒绝参与曼哈顿计划,他向奥本海默直言:“我不希望累积了三个世纪的物理学成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告诉奥本海默:“脱掉那身可笑的军服,你是个科学家。”在战争和博弈的规则之下,拉比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基本良知和朴素的道德观。
在影片前半段,劳伦斯与拉比同为奥本海默的好友,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们与奥本海默的会面总是气氛融洽。但在影片后半段,奥本海默落难之后,拉比坚定地与奥本海默站在一边,劳伦斯却动摇了。在影片的147分钟处,观众得知,劳伦斯听信了施特劳斯的说辞,从而相信是奥本海默的不检点导致好友的去世。从劳伦斯的角度来看,他与奥本海默的信任与情谊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被旁人摧毁,但事实是,劳伦斯的确因为施特劳斯的挑拨而没有为奥本海默辩护。不论是真的听信谗言,还是仅仅明哲保身,劳伦斯都受到了身边环境的规训,而主动交付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理智让位于盲目,判断力随之失势,劳伦斯追逐的只是构想中的奥本海默。
作为奥本海默的“身边人”,劳伦斯与拉比的角色塑造对于科学伦理主题的探讨有着更深层次的作用。他们在大环境中所作出的选择,正是奥本海默这一复杂人物在思想中的两面:劳伦斯代表着奥本海默对世俗名利的追求,拉比则代表着奥本海默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劳伦斯与拉比如同两束对向的追光,点亮了身处交汇点的奥本海默身影,也贯穿了电影始终,个体与集体、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与伦理的角力,都在不言中。
4 结语
《奥本海默》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刻画了历史群像,随着影片发展,不同时空的诸多事件参与叙事,让观众逐渐沉浸式地感受到人物的社会处境与内心挣扎,在角色与观众之间营造出最为深刻的共情[4]。
通过三组人物的对比塑造,《奥本海默》呈现出了诺兰的某种价值理念:在特定体系的规训之下,有人被规则裹挟,而有人坚守自我,正是这些选择决定了角色弧光的定位。“人与规则”的矛盾不仅是奥本海默所面临的困惑,更是一个跨时代的命题。稍有不慎,科学就可能异化为政治博弈的筹码之一,走向不可预见的深渊,这正是《奥本海默》对科学伦理的深度审视。
作为一部讲述“原子弹之父”的电影,《奥本海默》并没有展现原子弹研究的全过程,而是聚焦历史人物的抉择与情感,定位于对科学伦理的审视,使得整个影片充满人文主义色彩。导演诺兰在采访中说:“奥本海默感到忧虑和痛苦的不受约束的科学对人的侵害、人的创造物对人的毁灭,这些不是专属于他那个疯狂时代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面对的AI和1950年的原子能,难道不是平行的镜像吗?”[5]显然,诺兰明白,这位杰出科学家曾经面对的困境并未翻篇,1950年“核威胁”的幽灵仍然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时代,《奥本海默》所塑造的一众人物形象,可能正是屏幕前的我们在面临不同境遇时的模样。
——《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文化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