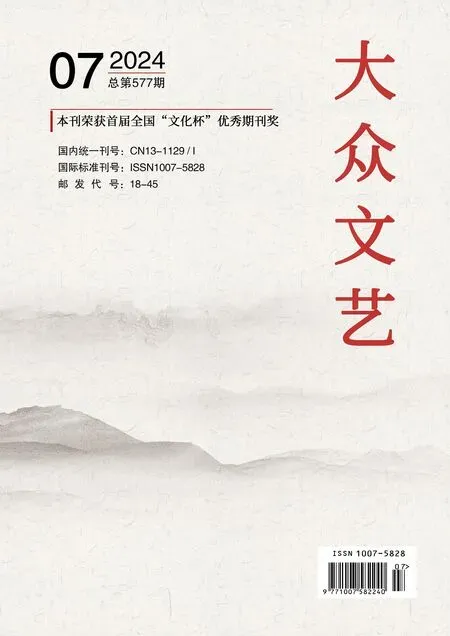真实·奇观·象征
——李沧东“文学电影”的诗性建构
胡译方 彭新宇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2.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艺术学院,山东济南 250200)
韩国电影的历史特殊性在于其立足本土文化,高度关注社会问题,从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电影文化生态与叙事风格。李沧东将现实社会的真实转化为个人表达,在作品中不断聚焦政治揭示、伦理剖析与社会批判。兼具作家与导演身份的李沧东凭借强烈的作者意识与大众性,不断收获世界性认可。
文字与视听之间的沟通差异,让李沧东更倾向于用电影与观众进行交流,而他的文学素养使其电影创作区别于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表现类型,体现为更具浓厚诗性现实主义色彩的“文学电影”。文学电影一般指文学的电影改编,包括“纯正的健康色调,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文学色彩及丰厚的艺术内涵”[1],体现为“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连续性与差异这两方面共同构成的媒介魅力”[2]。李沧东将目光聚焦普通人的浮沉一生,用诗意的台词和符合生活逻辑的镜头调度,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探赜与思考,在忠于生活的同时又超越了苦难本身,展现出最极致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真实为筹”的叙事策略
无法对文学诚实,可能意味着对我的人生不诚实,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3]。在李沧东的小说集《鹿川有许多粪》的后记中,李沧东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意图,即把真实的内心感受记录下来,与读者分享。步入影坛后,他先后执导的六部长片每一部都立足于当时的大环境,细致全面地观察了被生活左右的小人物的挣扎,展现普通人“活着”的实录。因此,生活真实在李沧东的电影中占据了永恒的主题。
《绿鱼》是李沧东电影的开山之作,也是韩国现代社会城市快速扩充,迅速取代农村这一社会图景的影像记录。影片中的“莫东”正气凛然、天真直率,然而他的“正义”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发挥的空间,反而被自己的孤勇反噬。莫东的心愿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共同经营家族店铺,而这一愿望在莫东死后才得以实现。莫东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迫卷入社会巨变的浪潮,走向绝路。心愿与现实错节的情节设计看似令人惋惜,实则真切地暴露出那个时代的暴力与残酷。
如果说《绿鱼》作为一部新黑帮电影,片中的莫东受制于黑帮势力的暴力威胁,那么《薄荷糖》中的主角“金永浩”则是一棵在时代的列车滚滚前行中被碾压的野草。《薄荷糖》采用多幕剧的形式,直接将金永浩的一生凝缩成几条时间线和与几个主要人物间的纠葛中,并用倒叙的形式,描写了像薄荷糖般纯洁的青年走向毁灭的过程,平静地叙述了“光州民主化运动”给社会带来的侵袭。
韩国电影人对大众记忆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其十分尊重,并将其再现于电影之中,这是彰明较著的[4]。现实主义样式在《薄荷糖》中就有充分体现,并应用“大与小”的矛盾对立法结构全片。
韩国现代社会中,有几个重大事件不断推动着韩国社会的转型。李沧东将影片的叙述时间锁定在1979至1999年间,用历史事件串联起金永浩的人生转折,加深了电影的历史厚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对比强度。1999年金融危机导致金永浩破产;1979年光州人民起义致使金永浩在军队中失手打死了一位女学生。影片中,社会与个人间的关系被拉近,个人的弹性在社会的不断拉扯中失效了。在《薄荷糖》的执导中,李沧东侧重社会动荡给普通人造成的伤痕,并借金永浩的自主回忆进行叙事,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可以传达给每一位经历了这一时期,以及正在感受社会发展的普通人,极具写实意义。
李沧东电影的拍摄手法同样十分注重写实,保留了半纪录片式的拍摄风格,拉近了与观影者间的心理距离。《密阳》是一部以传统母爱和现代宗教为主题的电影,聚焦“申爱”带着儿子“俊”回到死去丈夫的故乡后的日常生活。整体叙事节奏缓慢,长镜头运用较多,并多以观察者镜头结构全片。在拍摄上,采取第三者视角拍摄手法,并根据感情波动晃动镜头。此外,影片中车内视角的镜头也多次出现,如影片开头俊在车内仰望天空、申爱接儿子回家时在院长车内观察、申爱带着赎金去救儿子的第三视角及其到达儿子遇害地点仰望天空的场景等,依次营造出期待、神秘、惊慌和绝望这四种不同的氛围,通过细节构思强化了生活真实。再者,电影以同期声代替后期配乐,尽可能地还原人物所处的声音环境,增强了真实感。
在李沧东的电影建构中,心理真实同样有多重表现形式。“绿色三部曲”的收尾作《绿洲》中,李沧东就尝试把患小儿麻痹症的“恭洙”人物角色心理可视化,用超现实的想象画面填补这一过程。如恭洙与“忠都”坐公交时,镜头一转,恭洙变成了正常人与忠都打趣;恭洙卧室里挂着的绿洲画布上的大象、小孩和印度人突然出现在家中,与恭洙和忠都一起起舞。通过这种超现实的想象,把恭洙的切身疾病从人物身上抽离,强化了展示对象的陌生感,以人物深刻的心理现实来揭示其内在的真实情感——影像世界虽并不等同于生活现实,但这恰恰折射出残疾人渴求正常情感和生活却无能为力的真实生存状态。
二、“转熟为生”的镜语奇观
立足韩国复杂的本土社会,对社会现实加以分解,将熟悉的事物置于令人唏嘘的陌生环境之中,通过“转熟为生”法构建起“奇风异俗”般的人文景观,以本民族的文化逻辑去理解与诠释生命意义,是李沧东电影书写的一般策略。而其文学性的诗性建构则融合了人、事、景、物,利用镜语奇观传达出对人性与社会的态度。
聚焦边缘人,形成与观众审美的对立,是产生心理奇观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令李沧东时刻警醒,而悲悯的人文情怀又使其镜头充满诗情善意,内热外冷的作者意识愈加鲜明”[5]。李沧东电影中主人公边缘人的定位造成观众审美的不适。电影的“美德”,部分在于将观众带入角色的情感,共同体验人物的命运,进而塑造一个观众内心期待的故事结局。而李沧东电影的二元对立性却贯穿始终。在电影《绿洲》里,男女主角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形成最大的对立面,主要表现在社会地位与残疾人身份的差异上,这就促使“站在正常人一方的大多数观众不能淹没在电影所提供的幻想里,被两个人物的爱情同化,而是无意识中发现自己排他的自私的充满偏见的样子”[6]。而人物复杂性格的内部对立则进一步放大了观影者的不适。
李沧东善于建立人物关系的二元对立模式,叠加角色命运的悲情遭遇,塑造影片绝望感:金永浩毫无留恋地投向飞驰而来的火车、洪忠都最终被关进监狱。然而,他也在肯定地拥抱现实:洪忠都与韩恭洙用爱情守护了彼此“生命中的绿洲”,莫东的愿望被自己的家人所实现。李沧东正是将角色命运置于生活苦难之中,进而去塑造勃发的生命力,不断接通与观众的情感,达到精神上的共鸣。
李沧东电影的建构策略是极具想象力的,他将视点聚焦社会底层,由外而内地去想象、填充与塑造,不仅彰显出一场表现边缘人人性异化的叙事奇观,而且以苦难孕育文学,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因此,李沧东电影是叙事奇观与苦难文学的有机融合。
所谓电影的叙事奇观,表现在贴近现实的想象力构造方面。聚焦边缘人,拉开与观众间的心理距离,在陌生化的角色处理上,展现角色自身、角色间及角色与周围环境的二元对立,深化冲突。而对于角色命运所刻画的苦难记忆与忧患意识,则塑造了电影创作的文学性。苦难不仅是文学的起源,更是文学经典的主题之一。李沧东电影的文学性就是在真实社会环境下通过营造角色的苦难命运中得以彰显。
同时,李沧东专注于对电影叙事脉络的反复推敲。故事背景是真实的社会环境,而角色命运是由导演根据环境所构造的一系列假定性符号,是先验的、不确定性的主观表达。一实一虚的鲜明对比,推动叙事奇观化。
在电影造景方面,色彩起到了关键效果。影片中的基本色彩不仅发挥着再现客观事物的写实功能,而且具有独具匠心的造型与表意功能。色彩是李沧东电影诗意表达的重要元素,起到渲染环境、表现主题、塑造形象的作用。绿色是李沧东早期作品的一大标志。他将绿色看作社会底层人生活的动力,绿色正是一种希望。在《薄荷糖》里,绿色贯穿整部影片,给人以平静、舒适与安全的感觉:绿色的郊外、报停、护理服、薄荷糖、军装,这些物件细节贯穿金永浩的一生,见证他的喜与忧。同时,角色惨淡的命运又与盎然生机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人的绝望。李沧东正是运用色彩变化从而彰显出一种极致的审美宣泄。在电影《燃烧》中,惠美赤裸上身舞动着“饥饿之舞”,背光勾勒出她曼妙的身姿,与后景的夕阳相互映衬,在极具诗意与美感的气氛中,生命力随着夕阳退却而变得黯然神伤,并与钟秀四处奔跑寻找大棚的冷蓝色调遥相呼应。明亮的色调与现实阴暗残酷的强烈对比加剧了角色命运的悲恸。
文学电影对于苦难的书写具有悲剧美学精神与宗教救赎意义[7]。宗教文化以一种道具形式的“媒介物”置于李沧东多部电影的叙事中,借以回答人生经历痛苦的意义,充当孤独个体生存的现实寄托。从《绿鱼》到《燃烧》,其每一部作者电影的作者策略都涉及宗教,而导演又未在作品中真正触及上帝或宗教信仰,其不无异端立场式的“宗教伦理叙事”始终止于现实社会的边缘人物和底层人物的内心真实及那种令人唏嘘的浓郁的孤独感、痛苦感[8]。《绿鱼》里,美延每次遇到危险时会念祷告语;《绿洲》中,忠都家人会拉着牧师为其祈祷。通过宗教镜头叙事,李沧东完成了对韩国宗教现状的抓取与批判,从而揭示出现代人对精神救赎的迷恋与无助。
三、“聚焦人性”的诗性象征
诗性是一种内在品质,将思想、精神与语言相互凝聚,以语言的进入、剖解与再造书写对哲学与生命的自觉、感知与解读。因此,诗性之存在与个人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李沧东秉持讲好故事的创作原则,从文字到人物、布景,运用多重象征,加深电影作品中的诗性。
李沧东对电影题名的设定及色彩布景的安排上极具隐喻色彩。《密阳》表面指“密秘的阳光”,实则指社会中隐于阳光背后的“上帝阴影”,这一阴影笼罩于无数祈求通过信教逃避现实的人身上。申爱得知儿子被害后,曾一度无法排解内心悲痛,进而怀着尝试的心态进入教堂,开始信仰上帝,但最终信仰幻灭。因此,影片想要传达的是扭曲的信教观不仅无法实现逃避现实的目的,反而会在信念崩塌之时再次戕害心灵,造成精神幻灭。再者,色彩在表现审美宣泄的同时也蕴含象征意蕴。黄色在电影中隐喻上帝无处不在,如申爱儿子头上的一绺黄发、家里的黄色布景等。
文字、人物的符号象征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和升华。《诗》与《燃烧》是李沧东的近作,前者讲写诗,后者讲饥饿,然而诗是蜜糖裹毒药,饥饿是最难解的生活之谜。无论是新颖的主题,还是险象迭生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的诗性贯穿始终。在电影《诗》与《燃烧》中,李沧东试图用诗性来引导我们思考生活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以何种方式有意义,并以生命的终结为代价追溯人性的罪与罚,开放式的电影结局引发观众深思。
《诗》将镜头聚焦女性与现实,通过描述“杨美子”尝试写诗与其外孙及同学侵犯同校女生致其自杀两条故事线,彰显生活、道德与人性的三重困境。影片通过多组对立关系,将人性书写到极致,引发观众对贵与贱、善与恶的哲学思辨。影片最终借杨美子所写的诗——《阿涅斯之歌》,从美子楼下郁郁葱葱的树,转向事发的教室,再缓慢地转移到乡间的大巴车,最后转向女孩投河自尽的桥上,将画面定格在了滔滔不绝的江水中,叙事声音也随着场景的转换由美子变为了自杀女孩的声音。用朗读诗结尾,不仅照应了电影题目,形成完整的叙事结构,而且也借助诗歌独白中声音的替换,将救赎者美子和受害者“姬珍”身份合二为一。因此“诗”是连通美子与女孩的介质,把美子的悲悯、愧疚与女孩的绝望、悲伤汇流成全片全部的感情激流。这种情感激流冲刷着每一个对生命感到漠然、麻木的施害者,突出人性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对生命的尊重这一主题。
《燃烧》则以社会角色的符号化将诗性的象征发挥到了新高度。一方面,电影《燃烧》改编自文学小说《烧仓房》与《烧马棚》,剧情在塑造人性的基础上又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电影的文学性隐喻与象征意义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影片中角色的塑造实际也是对其进行符号化、概括并传递意义的象征性表达,是导演通过角色完成诗性转化的过程。电影《燃烧》隐喻双重主题。第一,人性的罪恶在电影中被象征性传递。“Ben”周旋于社会下层的女性之间,当他感到腻味时就会让她们消失,如同烧塑料棚一般,其罪恶极大却不自知;“钟秀”因愤怒而杀死Ban,自以为替天行道,其罪恶来源于愤怒;“惠美”没有正式工作,攀附于富人,其罪恶来源于懒惰。第二,阶级错位放大了愤怒产生的缘由,使愤怒在冲突中不断燃烧,亦象征着社会进程日益加快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
《燃烧》将“现代人群都普遍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这一内涵通过贫富差距的扩大及底层人无迹可寻的焦虑与茫然得以传达。Ben是富人中的虚无主义者,他在满足生理之需的基础上,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骄奢与享乐,而钟秀与惠美则以穷人的体态全然顾不上精神上的“饥饿之需”,归属与爱对于他们而言是另一种奢侈品。因此,影片中以Ben为代表的富人阶级和以钟秀、惠美为代表的下层阶级之间实际上存在无法兼容的利益屏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解构。李沧东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愤怒用烧大棚和互相伤害的罪恶方式具象化,把金钱与性的欲望交织在一起,隐喻城市生活分崩离析的状况,而潜藏在欲望之下、超越国别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幻灭在Ben被杀之后得到了彻底宣泄,疯狂代替理性使人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