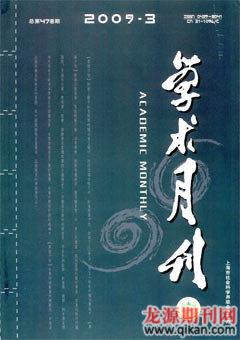佛经翻译与“格义”时代的跨越
[新加坡]顾伟康
[摘要]翻译的外在形式是语言的转换,就此而言,影响翻译水平的要素首先就是文本和译者的双语水平。在交通原始和印刷术尚未产生的古代,两者成为传播佛法的两大障碍,直接影响了初期佛经翻译的时代特色。翻译在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的转换。翻译是文化的沟通机制,同时又是文化的隔离机制。当“胡文”被翻译成“晋言”时,中国人固然可以“读”了,但却很难说“懂”了,在真正了解“胡文”背后的概念系统之前,人们往往以自己固有的思想方式去理解眼前的文字,于是便有了佛教史上的“格义”时代。我们的祖先靠以下方法走出了“格义”时代:第一,高度的宗教热忱和认真、谨慎、刻苦的态度,这是读懂西来佛法、接受其中历史信息的基础;第二,不断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事业长盛不衰的动力;第三,历代政府的支持和规划,这是中国佛经翻译精益求精的根本保证。相比之下,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风气、规模和制度,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中国佛教翻译史翻译的本质“格义”时代
[作者简介]顾伟康(1948-),男,江苏省无锡市人,新加坡佛学院教授,美国纽约“世界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佛学史和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3—0029—07
了解一外来文化、特别是哲学,首要的途径乃是翻译。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已近一个世纪。问题在于,一百年的时间,用来接纳、消化西方哲学是否够了?我们在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这里以史为镜,回顾中国佛教翻译史的点滴,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用了数百年的时间才读懂了西来的佛法、接受其中的历史信息,可能不无好处。
一
翻译的外在形式是语言的转换,就此而言,影响翻译水平的要素首先就是文本和译者的双语水平。在科技和资讯发达的今天,这两点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在交通原始和印刷术尚未产生的古代,却成为传播佛法的两大障碍。故初期佛经翻译的时代特色,就与这两个因素有直接的联系。
早期的佛经翻译,最极端的例子是没有文本,干脆靠人背诵:
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
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技尉姚爽请令出之,姚兴疑其遗谬,乃试耶舍,令诵民籍药方各四十余纸,三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
有文本者,则是由西域“胡人”零星携来;但因语种太多,带来了诸多困难,阅僧祜(445—518)《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即可见一斑:
仰寻先觉所说,有六十四书,鹿轮转眼,笔制区分,龙鬼八部,字体殊式……西方写经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
想象一下,几十种语言,还要加上不同的字体,就不难理解道安大师(314—385)的叹息:“音殊俗异,译人口传,自非三达,胡能一一得本缘故乎。”
文本如此,那么译主的语言能力呢?翻阅《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在晋安帝(396—418)时代,智严、法显、宝云等汉人译经者出现以前。更多的是这样一些人名单赫然入目:安世高(安息)、竺朔佛(天竺)、支娄迦谶(月支)、康孟详(康居)、支谦(吴地,月支后裔)、康僧会(康居、天竺)、竺法护(敦煌,月支后裔)、竺叔兰(河南,天竺后裔)、帛法祖(月支)、支敏度(不详,支姓当为月支人)、僧伽跋澄(罽宾)、僧伽提婆(罽宾)……他们中除了支谦和竺叔兰生于中国而精通汉语,其他人的汉语水平,或是来华后“突击”学习的,或者就是根本不懂华语。正因如此,当时译经的时代特征,是一帮人一起译经,他们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最典型的例子是: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179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令后普著,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于佛寺中挍定悉具足。后有写者,皆得南无佛。又言,建安三年(198年)岁在戊子八月八日于许昌寺挍定。对这段文字,汤用彤(1893—1964)解释道:
按古时译经,或由记忆诵出,或有胡本可读。善诵读者,须于义理善巧。但不必即通华言。故出经者之外,类有传译者……盖出者不但须能讽诵,且于经有深了解,译时能解释
其义。传译者仅须善方言,地位较不重要。由此人手,我们对早期佛经翻译的状况,或可有些真切的感受。
第一,对当时译经的困难,可以有所想象。像上引的《般舟三昧经》,短短十六品,二万四千余字(按:现《大正藏》中《般舟三昧经》有二本,No.417七品是十六品的No.418的摘要)。何以花了整整二(三)十年才“技定”。笔者的猜想,传译者支谶该是懂得某些“胡语”和晋言的,但那“胡本”的《般舟三昧经》,是另一种“胡文”,所以需要竺朔佛作第一轮翻译,然后支谶将其译为汉文。但支谶的汉语水平也不怎么样,所以还要孟元士和张少安二位真正的汉人将其写定。
第二,对早期译品的生硬和错误,也就能够理解。生硬者,如安世高,将“八正道”中的“正思惟”、“正精进”、“正命”翻为“直意”、“直方便”、“直法”,只是读的时候,一时感到难解。而错误者,如僧睿在《毗摩罗诘堤经义疏序》中所说的:
予始发心启曚,于此讽咏研求以为喉衿,禀玄指于先匠,亦复未识其绝往之通塞也。既蒙究摩罗法师正玄文摘幽指,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耳。至如以“不来相”为“辱来”,“不见相”为“相见”,“未缘法”为“始神”,“缘合法”为“止心”,诸如此比,无品不有,无章不尔,然后知边情险谈,难可以参契真言、厕怀玄悟矣。真是有点离谱,怪不得鸠摩罗什(344—413)有此叹息:
(罗)什每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第三,随缘而来的文本,随机而翻的译主,于是同经异译、大经节译的情况,就屡见不鲜。隋唐以前,《无量寿经》十一译,《维摩经》七译,至于《般若》经的翻译,汤用彤曾有小结:
《般若经》之翻译,汉晋最多。朔佛支谶所译为《小品》,支谦再译之,均有三十品。朱士行得梵本九十章,后译出为《放光般若经》。西晋竺法护译《光赞般若》,乃《放光大品》之异译。又译《小品经》七卷……晋惠帝世,卫士度有《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二卷……东晋释道安在长安时,昙摩蜱竺念译有《般若经抄》(一日《长安品》)。此中僧会法护之《小品》,卫士度之略出,均佚。罗什以前所译之《般若》,所知者尽于此矣。
更具时代烙印的,是僧伽提婆“今是而昨非”的故事:
初安公之出《婆须蜜经》也,提婆与僧伽跋
澄共执梵文,后令昙摩难提出二《阿(金含)》。时有慕容之难,戎世建法,仓卒未练,安公先所出《阿毗昙》、《广说》、《三法度》等诸经凡百余万言,译人造次,未善详审,义旨句味,往往愆谬。俄而安公弃世,不及改正。后山东清平,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俱适洛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岁积,转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法和叹恨未定,重请译改,乃更出《阿毗昙》及《广说》,先出众经,渐改定焉。
综上所述,这种由于文本和译主的双语水平而带来的“混乱”,可能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联想到20世纪初,我们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这种尴尬也曾刹那闪现。当年不懂外文的林琴南(1852—1924)翻译西方小说,就是请人手捧原书、口宣中文,林氏笔下流出的居然是漂亮的文言文。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先人因“工具”的原始,奋斗了几百年才走出的历史,我们可能几乎没有感觉。正因如此,我们也有理由希望,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消化,不需要化上几个世纪。
二
翻译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翻译在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的转换。就此而言,翻译是文化的沟通机制,同时又是文化的隔离机制;用于感觉、经验的对象。翻译的沟通作用是不容异议的;但若是思维、精神的产物,则翻译的隔离作用不可忽视。典型的例子,当代的《红楼梦》英译本中,潇湘馆被译为“Naiad's House”,潇湘妃子也就翻为“River Queen”。在西方文化中,“Naiad”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河泉女神,于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变成了快乐天真的“Naiad”。以今思古,当“胡文”被翻译成“晋言”时,中国人固然可以“读”了,但却很难说“懂”了,在真正了解“胡文”背后的概念系统之前,人们往往以自己固有的思想方式去理解眼前的文字。
佛法来华,正逢中原玄风盛行,以老庄成语来翻译佛家名相,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所说去理解佛法大意。最典型者,称佛为道,学佛则曰“学道”、“为道”、“行道”。《牟子理惑论》称释教曰“佛道”,《四十二章》称佛教为“释道”、“道法”,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于是乎,佛教史上的“格义”时代。必不可角的降临了。
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成附咨禀。时依门徒,井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乃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后立寺于高邑,僧众百余,训诱无懈。雅弟子昙、习,祖述先师,善于言论,为伪赵太子右宣所敬云。
到底他们是怎样“拟配外书”的,虽然时代久远,史料湮灭,但蛛丝马迹还是可以钩沉的。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出三藏记集》卷六留下了康僧会(?-280)、道安、谢敷三篇序文,他们释“安般守意”,都原封不动地用了《老子》:
(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心之溢荡,无微不浃,恍惚仿佛,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逆之无前,寻之无后。”(谢敷《安般守意经序》):“微矣哉,即之无像,寻之无朕。”(《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道安《安般经序》:“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至于般若性空之学,《老》、《庄》成说更是随手拈出:
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抄序》:“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是故夷三脱于重玄,齐万物于空同;明诸佛之有始,尽群灵之本无;登十住之妙阶,趣无生之径路。”
这样的以道家的“无”,去理解佛教的“空”,必然是方枘圆凿,风牛马不相及。道安从道理上发觉不通:
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先曰:“且当分折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
鸠摩罗什从翻译上发现错误: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姚)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
而真正的点到根本,指出问题出在两种文化精神的难以沟通,两套概念系统的不可借用,乃是隋代的彦琮。
一生致力于翻译的彦琮(557—610),对其中的甘苦知之甚深,他的《辩正论》可谓入木三分:首先,他说时间不可逆、地点无法移、师传续还断,欲得佛法三昧,谈何容易:
双林早潜,一味初损。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讹本诫。水鹄之颂,俄舛昔经。一圣才亡,法门即减。千年已远。人心转伪。既乏写水之闻,复寡悬河之说,欲求冥会,讵可得乎?
其次,他特别指出,即使是同一文明,古今的语言文字、从而思想的差距也是很难逾越的,更何况不同的文明:
且儒学古文,变犹纰缪。世人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
最令人惊讶的是,搞了一辈子翻译的彦琮,居然得出结论,要真正理解佛法,唯一的途径是不要翻译:
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并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成明,除疑网之失。于是舌根恒净,心镜弥朗。
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
或许这是彦琮的激愤之言,有点不切实际,但自觉不自觉地,他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然今地殊王舍,人异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经音若圆,雅怀应合。直餐梵响,何待译吉。本尚亏圆,译岂纯实。等非圆实,不无疏近。本固守音,译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缘情判义,诚所未敢。
这里“本尚亏圆,译岂纯实”、“本固守音,译疑变意”、“缘情判义,诚所未敢”,说的就是用一种观念系统直接的套在另一种观念系统上的做法,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的天然缺陷,即它不“纯实”、会“变意”的一面。
三
从根本上说,理解和消化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必须先精通其语言文字,舍此别无他途。但开始时,却又必须借助于翻译,犯下不少错误,经历很多曲折,这又是一历史的必然。
时至当代,我们面临着又一次文化交融,经历着同先人一样的曲折。翻“metaphysics”为“形而上学”,译“ontology”作“本体论”,于是乎,西方哲学也讲“道器”、“体用”了。用历史的尺度,说我们
现在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理解也是处于“格义”阶段,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假如这个类比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探讨,是哪些因素让我们的祖先走出了“格义”时代?
“译经是佛法之本,本立则道生。”缘此共识,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得以生生不息。
首先,是先辈们高度的宗教热忱。其典型,则有“西行求法”的先驱:朱士行为求般若精义,“誓志捐身,远求大本”。法显(334—420)慨于律藏残缺,冒死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幖帜耳”。玄奘(602—664)“轻生殉命誓往华胥”,在高昌国,“王命为弟,母命为子”,目的就是要留下他,大师乃以绝食明志……更为悲壮动人的,是那些为法献身、壮志未酬的故事:
(慧景)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法)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
(道普)道场寺慧观,志欲重求后品,以高昌沙门道普,常游外国,善能胡书,解六国语。宋元嘉中,启文帝资遣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遂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
其次,是高僧们极其认真、谨慎、刻苦的态度。认真如昙无谶(385—433):他携带着十卷《大涅槃经》前分以及《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来到姑臧(今甘肃武威),河西王沮渠蒙逊(348—433)请他将带来的经本译出——
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
谨慎如鸠摩罗什:罗什入关,姚兴命他译出经藏一
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一言三详,然后着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于时罗什出《十住经》,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耶舍既至,共相征决,辞理方定。
刻苦如玄奘:大师取经归来,可谓功成名就,但是依然战战兢兢、一丝不苟。据《慈恩传》叙大师永徽改元后的每日起居——
法师还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日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
再次,是翻译家不断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先人对翻译境界的追求,固然物化为一本本的经典,但更是升华为有关翻译的理论总结,成为历代翻译家的共同准则。道安的“五失本”,批评的是不忠于原著风貌的草率;他的“三不易”则是强调翻译时要注意时代、区域从而文化、思想的变迁。彦琮的“十例”,讲的是翻译时要注意原著的体裁;他的“八备”则是关于翻译家的“职业道德”和文化修养问题。玄奘的“五不翻”更是触及了翻译的“隔离”本质,了解到翻译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宋高僧传》的作者餐宁,在其《译经篇》的最后,写了长长的一篇《论》,历数前人之成就,进而总结出译经之“六例”,每一例都有细目,并有详解——“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佛经翻译规则统一的要求,终于成为金科玉律的自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历代政府对翻译事业的支持和管理。所谓支持,可以《金刚经》的翻译为例。现存《金刚经》的六种译本,有五本在帝王的直接护持下译出,一本则由地方郡守为护法而诞生:第一是罗什译本——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了鸠摩罗什,前秦苻坚(338—385)和后秦姚兴(366—416)两次兴兵西伐,方得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姚兴以国师之礼,为鸠摩罗什置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场,《金刚经》之鸠摩罗什译本,遂得以问世。第二是流支译本——魏永平年间,菩提流支至洛阳。北魏宣武帝敕以流支驻永宁大寺,为译经元匠。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至孝靖帝天平二年(535年),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第三是真谛译本——真谛三藏于梁太清二年秋(548年)到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佛心天子”梁武帝躬申顶礼,供奉于宝云殿,准备设立译场,传译经典。可惜时运不济,第二年即遇“侯景之乱”,梁武帝病亡,真谛开始了在中国的漂泊生活。多年后,真谛至梁安,西返无望,甚至于想自杀。这时,梁安太守王方奢特为大师造建造寺,请他安心译经。陈天嘉二年(561年),六十四岁高龄的真谛于五月初一在建造寺“依婆薮(世亲)释论”,重译《金刚经》。第四是笈多译本——达摩笈多于隋开皇十年(590年)独自一人来到中国,举目无亲之时,被隋文帝请人长安,先住长安大兴善寺,后移洛阳上林园;先是协助阇那崛多,后是与彦琮一起主持译场,十九年间,译经四十余部。第五是玄奘译本——玄奘弟子窥基记录了大师译《金刚经》的经过:
贞观二十三年,三藏随驾玉华,先帝乖和,频崇功德……于时帝问藏云:“更有何善而可修耶?”藏报云:“可执笔以缀般若。”帝既许之,藏便译出,其夜五更三点翻译即了。帝索读之,即遣所司写一万本。
第六是义净译本——义净三藏在长达二十五年的“西天取经”之后,于天后证圣元年(695年)夏回到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旋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赉梵本,并令翻译。从天后久视元年(700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的十二年间,义净先后于福先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处,译出经律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余卷。从个人友谊到任命职务,从财务支持以亲自参与,《金刚经》的六译就是一历史的缩影。
所谓管理,可以“译场”为例。“译场”的形成历史及其具体组织,《宋高僧传》中有极为详细的记录:
译场经馆,设官分职,不得闻乎?
曰: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
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西晋伪秦巴来,立此员者,即沙门道含、玄赜、姚嵩、聂承远父子;至于帝王,即姚兴、梁武、天后、中宗。或躬执干,又谓为缀文也。
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
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如居士伊舍罗,证译《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
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义净译场,则李峤、韦嗣立、卢藏用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也。
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如译《婆沙论》,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义,唐復礼累场充任焉。
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闻此位也。
次则校勘,仇对已译之文,隋前彦琮覆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
次则监护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寿为总监检校,唐则房梁公为奘师监护,相次许观、杨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员,则隋以明、穆、昙迁等十人,监掌翻译事,诠定宗旨。
其处则秦逍遥园,梁寿光殿、瞻云馆,魏汝南王宅。又隋炀帝置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唐于广福等寺,或宫园不定。又置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从“译场”我们可以看到,佛经翻译的制度化及其严密成熟,这正是中国佛经翻译常盛不衰的关键。
北宋僧人赞宁在《宋高僧传》中把宋以前的佛经翻译分为三个时期:“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本文的三个部分,正好与其相契,实是希望钩沉史料,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历史的脉络来。初、次二期,笔者都判为“历史的必然”,认为当代的中西哲学交融,也经历了相似阶段。唯“大备”的第三期,是更多的人为因素才得以造就的。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努力,好像差得很远。本文的目的,尽在此中矣。
(本文原为提交给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会议论文,应《学术月刊》之邀,在发表时又作了较大的修改。)
(责任编辑:常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