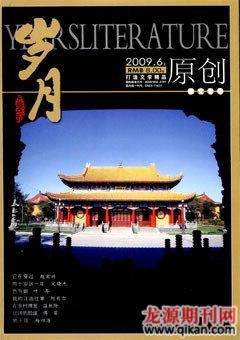火神,在房顶盘踞
吴垠康
老家的对面是座高山,在经年雨水和无数脚踏的作用下,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在烈日里白练般晃眼。这是山内西源公社进出的唯一要道,星期天的下午,父亲总会用双腿度量这条山路,他要去山内的一所小学教书。父亲出发一段时间,估计到了三里开外的山坳吧,在弄堂歇晌的再基叔开始与纳鞋底的婶娘们打赌,说华阳哥马上就要回来。华阳是父亲的名字,我狠狠地剜了再基叔一眼——对挖苦父亲谨慎有余的人,我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令人垂头丧气的是,话音未落,父亲就站在了大家面前。他掀开水缸盖看看,然后去井里挑了担水回来,再出门时,又是絮絮叨叨叮嘱母亲别粗心烧了柴搁栏,又是训责我别玩火烛。
那时,我们本族二十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屋场,屋内有五个采光集水的天井,一百多间老房子被六条交错的弄堂铆成一个几无破绽的整体,外墙都是青砖,内墙多为木柱木板,屋顶突兀着一垛一垛封火墙,据说那是火神的尊位。这种颇具徽派风格的古民居,虽有避风、防盗的优势,但拥挤、潮湿、阴暗、虫蛀等烦恼也一直是大家的心病。我家紧邻祖堂,祖堂木墙下叠放着七八只备用的棺材,小孩从这里经过,就像进了阎罗殿,难免冷出一身鸡皮疙瘩。那时的夜晚漫长而闲散,孩子们总会以捉山羊、捕流萤来打发寂寥,我进出少不了要借势火烛,父亲的忐忑大抵缘于这种居住环境。
如果你以为只有我父亲的神经才对火灾敏感,那就孤陋寡闻了,譬如庙里的和尚们。寒冬腊月的深夜,风籁如唳,正在梦乡的我被一串颇有节律的“梆梆”声惊醒,然后有人在唱: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缸中满水,一方太平。那“梆梆”声,沉重而阴森,像敲在空洞夜晚的胸口上,然后有一股寒气钻入被窝。母亲说,别怕,那是和尚在打竹梆。到了正月,和尚带着临时请来挑担的居士,挨家挨户收取大米或钱币。用打梆的形式来化缘,乡亲都能接受,毕竟三年贼偷不敌一年火烧,再怎么说也不能让辛苦了一冬的和尚空手而归吧。
日子在平淡中消磨,老谋深算的火神。似乎有意制造一个麻痹的假象,藉此证明我父亲的杞人忧天。然而,在我十岁那年,火神还是露出了按捺不住的尾巴。
那是个中午,炊烟像稻禾一样在屋顶拔节时,田间薅草的男人们,歇了打情骂俏的山歌和刺激荷尔蒙的黄段子,然后舔舔嘴唇,预支着饭菜的气息。突然间,屋顶翻滚起一团浓厚的烟幕,红红的火舌在烟幕里隐现,队长再基叔马上反应过来,舌头吓得打了卷,快!快!快回家打火啊!顿时,一个习惯了慵懒的山村,第一次尿湿了裤子。在家的女人,抢出哇哇直叫的孩子,又壮壮胆哭喊着去抢细软,手脚沾满田泥的男人,则用刘翔冲刺的速度赶到现场。再基叔是总指挥,号令三军先截火路,于是有石匠手艺的搭梯上房揭瓦,有木匠手艺的随后锯断桁挑,其他人提着桶盆在水塘间拼命奔跑。上了岁数的雪南爷爷颠簸着来到塘岸,一边没有章去地敲送葬时用的铜锣,一边撕心裂肺地呼救。接着,一批批援军从四面八方召集来了。半个小时后,明火终于扑灭,而围绕火场的三条弄堂被全部打烂,处于其间的麻子婶家,只剩下瓦砾和冒着青烟的炭头,偶尔还传来谷粒爆花的声响,瘫软在地上的救火人员都成了黑猩猩,表情麻木得像一尊煤雕。当麻子婶在河边呼天抢地的哭诉潮水般涌来时,大家似从噩梦中苏醒,才纷纷记起对肇事者的责怨。火是麻子婶煮午饭时不小心弄的,现在片甲不留的也就她一家。她在屋场上人缘极差,也许是有吵嘴的天赋吧,三天没找人赛一次骂,牙就痒痒的。几个惊魂甫定的婶娘开始说风凉话了,说蛇不乱咬,火不乱烧,灾星遭报应,活该!向来不饶人的麻子婶这回乖了,只知道哭。吃“五保”的陈大娘,蹒跚着粽子状的小脚,来到我家隔壁的祖堂,抚摩着安然无恙的棺材抹眼泪,她百年之后的最后一点尊严就指望这口棺材呢。遭了这么大的祸事,谁家都没心思继续生火,附近的亲戚当然不会坐视不管,相继送来了饭菜。再基叔端着碗扒了一口,就开始安排弄堂修补和麻子婶家房子重建等善后事宜,迷信的雪南爷爷则在大门口点上香烛,一言不发地朝封火墙叩拜,婶娘们窃窃私语,说雪南爷爷在拜火神。我望望封火墙,却什么也没看到。
父亲得知噩耗后,把学校的事安排好连夜赶回,看着家门口被打烂的弄堂,他的手在发抖。险啊,要不是有这么一个弄堂做替死鬼,我家就不能幸免于难,父亲能不后怕吗?有了这次教训,父亲每个星期天下午返校前,给我和母亲必上的防火教育课总要拖堂,而再基叔也再不与纳鞋底的婶娘们打赌了。
父亲说,不搬出去迟早还要出大事。1980年底,父亲给大队和生产队打了申请地基的报告,我家获准在半边荒山上建房子。那时学校是单休日,父亲每周只能在家呆一天,队上不允许吃国家粮的人出工挣工分,他就喊上很不情愿的我一块去开山挖地基。由于山体夹杂了沙石,连挖带运劳动量很大,加上后来来我家长住的大舅,一帮子人用了四年时间,才整好地基,扛来几大堆备用的墙脚石和砖瓦,直到1984年底,一家人背着象征“步步高”的梯子和欠债簿搬进了新房。后来,随着出门打工潮的兴起,又陆续有人家从老屋迁出,而没盖新房的堂兄银香哥,兄弟分家立户后,开口借了我家闲置的老房子,灶台也搬到我睡过的那间不足六平米的小屋。在当时看来,这是族亲间一种血浓于水的善意,但谁也没料到,这个善意竟掀开了又一次灾难的序幕。
还是夏天,还是中午,银香哥的老婆生好火后要到晒场上去看看,便让六岁的儿子续几把火,这在我们乡下太司空见惯了,但就是在这一次,火钳拖出的火星点燃了柴搁栏,等小孩哭喊着跑出来,火已上了房顶。已退休的父亲像几年前的雪南爷爷一样,跑到塘岸呼救,但由于居住分散和一些青壮劳力出门打工了,动员来施救的力量没有上次幸运,救火人员不得不让出更多地盘给火神,因为近距离切断火路无异于与虎谋皮。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神在肆无忌惮地扩疆拓土,先是从瓦缝里冒出浓烟,然后浓烟里冒出火球,颇像试验原子弹时升腾的蘑菇云。木头在瓦片下猎猎作响,烧红的瓦片似抹了一层血,轰隆,一间塌了,轰隆,又一间塌了。就这样,整个东边的房子,带着主人的疼痛和故事,破灭了修炼文物的梦想,而祖堂里叠放的棺材,无疑成了这些房子的陪葬品,其中就有我家的一只。好在孤寡的陈大娘前两年去世了,要不然她非撞死不可。事后,跳大神的旺生哥神乎其神地说,他看到了眉毛倒竖的火神坐在封火墙上煽风点火,女人们的啼哭也顿时止住了。
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屋场,曾经一定经历过或多或少的劫后余生,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葬身火海的宿命。翻开火神的记事本,哪一笔不是不可讨回的血债?即使到了人技消防能力空前强大的今天,火神仍然是盘踞在房顶的致命威胁,声音沙哑的119,一路啼哭的救火车,不忍卒读的火灾报道,都是控诉的证词。
当然,我不会相信有什么火神,先人造出一个火神来,如果不是出于对恐惧的困惑,那就是要借助神的威仪来防患于未然。从这个意义上,我还是宁可信其有,甚至希望人们多向火神敬几炷世俗的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