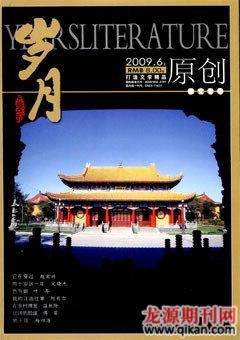散落于秋天的事物
刘川北
1
真的不知道,秋天开始于哪一场风,开始于哪一场雨,阳光从哪一刻开始,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照拂着静寂的村庄。立秋的时候,天还闷热依旧,拿着锄、铁耙,在菜园子里收拾掉豆角黄瓜,开垄整畦,种白菜点萝卜。手里摇着蒲扇,汗一个劲儿往下淌,秋天的痕迹隐藏得秘不可宣。节气到了,节气仿佛季节的指挥棒,它遥遥一指,秋天便逶迤而来。人们多多少少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一早一晚,同样打着赤膊,却有了明显的凉意。秋蝉暗地里响起,寒蝉凄切,不是夏天里聒噪的大杂唱,而是孤零零一只蝉,藏在不见人的背阴里,一声高,一声低,尖刻而深入地带来了秋天的消息。秋蝉,个头要小的多,身上披着铜锈的绿霉斑,像是夏季里淘出来的旧古董,它们吟唱着夏天的挽歌,奏响秋天的序曲。河湾边的芦苇,在日暮的时候,扬着灰拓拓的干涩的穗子,寂寥无声,指引着秋天前行的行迹与方向。
棉花白了,玉米腰间的缨子,也枯萎了,绿意统治着的夏天,一下子变得五彩斑斓。草尖上一颗露珠,轰然坠落,秋天的第一次脉膊,垂落于潮润润的大地已不知道是哪一棵树,最先张扬秋天的旗帜,树叶黄了,圣洁的明黄,暗淡的灰黄,隔着淡淡的秋雾,显得缈远幽深,或者燃着火一般的赤色,层林尽染。从田垄上走过,再不会有庄稼棵子阻碍你的脚步,收获过的秋天的田园,分娩之后的女人一般,消瘦而丰腴不再,却又不失母性的柔和。最后的庄稼也砍尽了,最后一朵棉花也开尽了,天高地远,目光所及之处,无不是秋天的声色。大地空旷,高天深邃,秋虫呢喃私语,风吹动了草的私语,吹动了树的私语,风从水面划过,带起几丝鱼鳞般的细浪……笼盖着的秋色越来越浓密,秋之声,渐渐进入高潮,秋意更加的浓厚绵细。草枯了,有村童拿着竹筢,搂柴禾,而更多的草被烧荒,火嚼着枯索的草,哔哔剥剥地响成一片,火舌漫延而去。烟气四起。树叶,终于耐不住性子,在秋风里舞蹈。秋天的雨,一点一点地缠绵着,缱绻着,它们打在苞谷秸上,打在乌青的屋檐上,打在苫着稻草的柴垛上,雨声入耳,清脆,洁净,似乎历历可数,一场秋雨一场凉,秋天的烈焰就在细雨的呼喊中一点点地熄灭。一场一场的风,一场一场的雨,深化着秋天的主题。
秋天的势力从一粒泥土,从一棵草,一片叶子开始,它的势力得到空前的扩张。从脚下一直到达天空,都镀上了秋天的色调。秋天的天空,是玻璃般的纯净精致,想必秋天的心,也应该是孩子一般的无邪。风变得越来越凌厉,秋天张扬的色彩与渲染,被一场霜,被一场雪抚平。
2
大田里的庄稼有条不紊地收走了,乡间的土道上,来来往往的架子车,牲畜拉着的大车,和提着扛着农具的庄稼人,构成了村庄繁忙的景象。乡道上的两道车辙,嵌进泥地。沿着乡道四散开来,延伸到每一块庄稼地里。金黄的玉米一车一车的拉回家,剥去外皮,堆在院落里,或者苞谷皮往外一束,在杨树,枣树。槐树的枝杈上,两两相系,轻轻一搭,玉米成了树的最漂亮的服饰。金黄的玉米,被树枝子挑着,像是一盏盏明亮的灯,映衬得院落的七零八杂犄角旮旯,也闪亮喜气了不少。空荡荡的院落一下子拥挤起来,这边垛着还没有打过的黄豆秧,那边竖着几捆高粱秆,东边放着晾晒的白棉花,西边花生秧上还有没有摘净的花生豆……村庄有点气喘吁吁,像一只胃,慢慢蠕动,慢慢消化掉扑面而来的收获。院子里的鸡们鸭们,一时间得意洋洋,吃饱喝足还不干,这屙一泡,那屙一泡,把整齐的院子弄得面目皆非。苞谷被运到房顶,那里风凉,风吹日晒,有七八分干的时候,用高粱秆编的帘子,在房顶立起围囤。流浪的苞谷终于有了着落,流浪的风,也找到了歇脚的地方。
让村庄臃肿起来的,更多的是那些一时半会消耗不掉的秸秆。苞谷秸,芝麻秸,高粱秆。花生秧……它们填充了村庄的空白,它们像是村庄的一件过时的衣物,穿在村庄的身上,帮助村庄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些秸秆或者垛成垛,或者码起来,放到角落里。苞谷秸一个一个的戳起来,戳到墙角,戳到狭窄的巷子两侧,巷子变得更加的逼仄,好在,秋天将要过去,再用不着大车出出进进拉东西,没有什么大的妨碍。有空地的场院,苞谷秸依着一棵粗壮的杨树,或者一棵古老的槐树,斜着戳,一个挨着一个,队伍不断壮大,小一点的,成了亭子,庞大的,成了一座小山。苞谷秸里,可以毫不费力掏出一个窝、一条洞,这条洞可以用来暂时的避一下雨,可以晚上藏猫猫,可以让一只耗子感到天堂般的舒适,让一只野兔子躲避偶尔遇到的麻烦……
秋天的庄稼地一下子变得清晰,空旷。南飞的大雁,在天空中做着“一”字和“人”字的造型。拾秋的人,在庄稼地里寻觅被遗忘的粮食。苞谷秸难免有遗落的几穗玉米,黄豆地总会有落地的黄豆,一脸委屈的躺在枯黄的豆叶下面。花生地被没有恒心的拾荒者,这一锹。那一锹,翻得凸凸起起,这几锨土,平整的土地就比别处高出来一些,那被挖走几锨土,便陷下去几分。会拾秋的人有自己的经验,比如花生与地瓜,在地埂子和沟垄,被主人忽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些地方,地不肥,土质坚硬,收获庄稼的人兴许有些懒,那么硬的地界,一镐下去,没有动静,就放弃了。或者收粮食的人,去喝了口水,去吃了几口饭,回来时把接茬的畦垄弄混了。一些粮食落在了地里,被村庄收获庄稼的人遗忘。有了拾秋的人,这些粮食才幸免遇难。
好在村里人不是那么独霸一方,收过的庄稼地不避嫌别人以拾秋的方式不劳而获。村里人收了大部分秋天的成果,田鼠不事稼穑,同样分享村里人的收获,麻雀、野兔,小到一只蚂蚁,它们的收获可以是一粒草籽,也可以是庄稼地里的粮食。秋天的收获不仅仅是粮食,秋天的收藏更不能简单的囿于粮食。比如,草多了,晒干,可以做冬日里牲畜的饲料。可以这样简单明了地来概括秋天的定义:秋天,是收藏的季节。即使那些粮食那些草籽,没有被村里人收藏,没有被乡间野物们收藏……至少,它们还被大地收藏了,总会有些草,总会有些粮食,在春天降临的时候,以盈盈的绿意对大地的收藏做了应有的回报。
3
农具清闲下来,三齿镐头,锄头,犁,耩麦子用的耧……有的农具一年只能派上一两次用场,比如耧,秋日播种麦子的时候用一次,其它时候,很少用到它。常用到的农具,比如铁锨,镰刀,镐头,锄,用到的时候最多,一把铁锨,可能从春日,一直到冬天,挖个沟,挡个垄,都要用得上铁锨。打扫院落,那些草屑,那些浮土,连同鸡鸭的粪便一起垫到了猪圈里去,更少不了铁锨的功劳。庄户人下地,即使只是简单地看看庄稼的长势,手里不是提着一把镰刀的话,肩上一定会扛着一把铁锨。一把铁锨,用的时间长了,木柄光滑可鉴,木头的纹络清晰,一朵一朵晕开的花瓣一样,有节疤的地方,像是睁大了的眼睛,手一遍一遍地摸抚。这花经过了汗液的浇灌,便有了不易察觉的芬芳,这眼睛经过擦拭,更加明亮。
更多的农具整整一个冬天都派不上用场,秋天的繁忙与紧张,农具的摆放便没有次序与规律。手里的活一忙起来,随手丢下了扫帚抄起来了竹筢,镐头占了铁锨的地方,铁锨不小心藏到苞谷秸里,满世界地找。这些农具,和人一样忙起来就有些晕头转向,需要找一个日子,重新打理修整,让它们好好地伸一下懒腰,舒活一下筋骨。镐呀,锄头呀,镰刀,犁,铁耙,刮耙……一一摆在了院子里,一时间,仿佛是农具的展览,农具的彩排。这些农具经过祖父的手,有泥污的地方,被小心地擦拭,不用棉布或者手巾,用的最多的是稻草,后来稻草越来越少,就用麦秸,麦秸也好,稻草也好,它们的柔韧,它们阴性的一面,抚平这些阳性的铁器的锋芒和它们身上多多少少的疾痛与暗伤。犁铧的泥结了疤,仅仅去擦拭就不太管用,碎砖烂瓦,这时候便派上了用场,瓦片刮在铁器上,声音有些紧张枯涩。灰尘一时间到处泛滥,鼻息里溢满僵涩的泥土的味道。祖父是仔细的,耐心的,我似乎从未感觉到他如此耐心细致地看管他的哪一个孩子。实际上,我的祖父爱他的儿孙,他经常把某个刚刚蹒跚学路的孩子举过头顶,他经常有意识地在口袋里放几粒落花生或者几颗通红的大枣。他蹲在那儿,逆着光,那些光长了绒毛一样,显现出一份清幽的单薄与寂寞。很长时间里,我总是在想,那些靠在房墙上的农具是多么的幸运,每一个孩子都愿意变成一把锨,或者一把简单的镐头,静静地靠在那儿,静静地等他用饱满有力的手一遍一遍地抚摩,用单纯而清澈的目光一遍一遍地照拂。
镰刀依旧插到墙缝里,铁锨,镐头,锄头们依旧放到西厢房的拐角的地方,放置到西厢房最显眼的中央位置,上面还简单地盖了些草苫子。农具入了洞房一般,换了新天地。
4
已经是深秋,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稀疏的树杈,萧条凄静。杨树叶子,槐树叶子也借着一场风,纷纷扬扬地旋落下来。最耐寒的是柳树叶子,每年的春上,它们最先警醒,秋天里柳树叶子落得最晚,对于柳树来说,做到了善始善终。灰扑扑的麻雀,在枝权间跳来跳去,它们一时的活跃,并不能改变越来越冷落的氛围。它们依旧在闹,叽叽喳喳地,像是进行一场没有头绪的辩论,或者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过冬的对策。庄稼地里阡陌纵横,展开的畦垄,像是一副摆好的棋坪,坟头,柴垛,隆起的土包,便是这棋坪上的棋子。扭结的小路上常见一二老者,笼着手,腰背驼着,走过庄稼地。便怀疑,这老人便是摆弄棋子的高人。村庄里常常有这样的老人,也只他们才有大把大把的闲散的光阴,他们不必为未知数的明天而流血流汗,时光在他们手上慢了下来,他们就这样轻悄悄地消磨掉最后的时光。地里当然不会有什么活计,年轻人忙完了收秋。去城里打工,或者忙手头的事,挣些闲钱以应付开销越来越大的日常生活。
有人喊一声家乡的梆子,声音高亢喑哑苍凉。秋天的原野一览无余,声调一出嗓门,便飞泄千里,整个平静的旷野都在回响这动人心魄的悸动。麦苗刚刚从土缝里钻出来,瘦弱纤细,它们在这声急急如风的腔调里,一下子直起了腰身。从庄稼地一直往西,是高高盘起来的河堤,河里已经干涸,没有水,一条沟在原野上蜿蜒曲折。从村子外弯进来,在南面的大洼里稍做停顿,又弯出了村庄的视线。要是有水的话,村庄秋天的味道会更地道醇厚。夏季雨水多,河里没有流水,街街巷巷汇集的雨水也会让河沟子有了水色,一时间蛙鼓齐鸣。相对夏天而言,秋天淡定了许多。村子里有孩子和管家的女人进进出出忙碌的身影,孩子的哭啕,女人大声的训斥,在这清寂如水的秋天里,都格外的清洌甘甜。一个刚刚蹒跚走路的孩子,穿着开裆裤,屁股后面早早地围上了屁帘,一走一扭,一会拾落下的树叶子,一会赶一只杂毛的土狗。
丝瓜扁豆角兀自攀在墙上,叶子经风吹雨打残破不堪。一只老丝瓜爬到了槐树枝上,拿一个葵花秆踮起脚后跟,勉强碰得到,却奈何不了它。丝瓜苍绿,在秋风里,怡然自得其乐,秋千一样悠闲地荡过来,荡过去。也许是这日常的经炊烟熏染的院落,还不像四野的庄稼地里那般清冷,院落里的秋天,比别处来的迟一些,我看到一朵丝瓜花躲藏在破败的丝瓜叶里,艰难地绽放:渺小,迷茫。总有一些花,来不及开放,秋天就来了;总有些果实,还没有成熟,秋天早已等不急了,打理起远行的行囊。这种比喻可以恰当地放到庄稼人身上,一辈子播种耕耘,忘记了日出与日落,还没有真正安排好秋天的事情,那些愿望还芽一样初露头角,秋天却了无痕迹地走完了它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