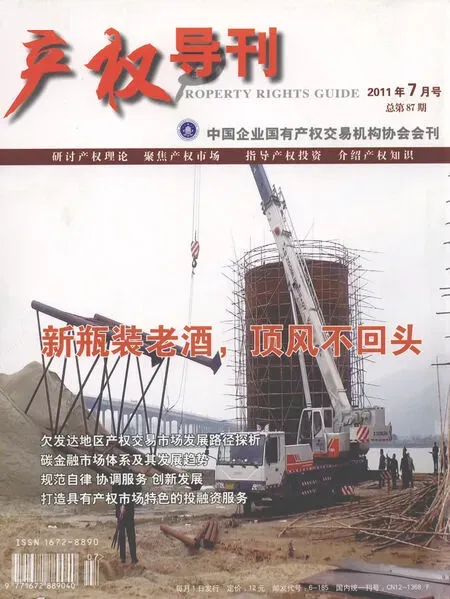新瓶装老酒 顶风不回头
■ 王 宁
(安徽电视台,安徽合肥 230022)
新瓶装老酒 顶风不回头
■ 王 宁
(安徽电视台,安徽合肥 230022)
香河征地事件,因其与京城毗邻,兼且发生在中央严肃土地纪律、严格控制房价的政策背景下,成为历年来违规征地开发的又一个缩影。事实上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高危问题。而事件中香河政府打着“建设新农村”这一政策的幌子,无非是为圈地开发的“老酒”换一个新瓶罢了。

香河违规征地,一征征出了个全国大讨论。中央调查、媒体围观、学界声讨,好不热闹。似乎早上一睁眼,大伙儿发现了违规圈地的新大陆。事情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出“圈地四千亩,商业大开发”的戏是如何开锣的。
事情的曝光源于新华社记者的一次采访:“记者就当地群众反映的土地违规流转问题前去采访。没想到这次采访过程,遭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怪事”。事情的经过简单明了,口粮田“流转”给了开发商,老百姓“自愿”的四处告状,当地政府的“社会闲散人员”加班加点的“沟通疏导”。记者的采访先是被地方宣传部门“跟踪”,随后又被社会人员“跟踪”,一路跟着的目的,不外乎是针对记者的“威逼”或者“利诱”,以及对群众的赤裸裸的威胁。观其操作手法之娴熟,当非偶然为之。由此延伸,问题发生三年之久,前去调查的媒体恐也非只新华社一家。只是或者“威逼”了,或者“利诱”了,报道尽数胎死腹中罢了。原因为何?一言以蔽之:制度使然。中央媒体乃至中央机构的超然地位,让其在能够不被利诱的道德基础上,理所当然地不被地方党委政府及其宣传部门“威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由上至下的、源于科层制的监督的有效性,与地方媒体无力作为,群众申诉无门的窘境,源于相同的体制背景和原因。
在这一事件中,媒体——而不是法院,信访——而不是法律,再次显示了“特殊国情”下的巨大作用。在缺乏NGO(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环境下,政权背景下的媒体报道以及随后造成的围观效应,为这起2008年以来持续圈地搞商业开发的事件揭开了黑幕的一角。由此想到了李刚、想到了马家爵、想到了“躲猫猫”、想到了上海大火后的新媒体表现。“媒体作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不知该说是显示出制度的强大威力,还是说明了黑幕随处可见?不知是该抚手称快,还是该扼腕叹息?
无论是4000亩,还是坊间传闻的1万亩,无论是自愿,还是他愿,无论是以租代征还是“土地流转”,违法征地既非新问题,相关法规亦非要求不严密。早在1986年,以租代征已属违反土地法的行为。可以说,香河征地事件中,不论是“以租代征”的方法,还是“有亲戚在政府、医院、学校上班的,都要回家动员拆迁,否则饭碗端不稳”的手段,都非当地政府的“创新”,更不是此处独有的“特色”。事实上,类似的描述和报道,历年来在各类媒体的记录中屡见不鲜,甚至司空见惯。香河征地事件,因其与京城毗邻,兼且发生在中央严肃土地纪律、严格控制房价的政策背景下,成为历年来违规征地开发的又一个缩影。事实上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高危问题。而事件中香河政府打着建设新农村这一政策的幌子,无非是为圈地开发的“老酒”换一个新瓶罢了。
然顶风征地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批批政府官员“前赴后继”,究竟所为何来?一边是60~80万元/亩的土地出让价格,另一边则是1150元/亩、每年每亩递增30元的农民土地流转补偿——这便是香河土地故事的基本梗概。

2007年前的10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在地方政府与开发企业的合力推动下,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以上的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在香河土地故事背后,类似的故事早已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县市乡镇中上演。
没有耕地就没有粮食,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土地的肥力不同,产量也不一样,这是种过庄稼的人都心知肚明的道理。现行的耕地保护政策允许在一地征用耕地后,异地补充使总数不变。然而实际情况是已经开垦成熟的土地多已登记备案,即便因特殊原因(如上世纪为逃避农业税,一些乡村曾主动少报耕地亩数)致使部分耕地没有备案,实际生产的粮食也早已计入流通总量之中。而新增的所谓耕地有不少一直是山地荒坡,产量极低。这就造成了账面上耕地没减少,可是实际上粮食的产能降低,最终在供求关系上对农产品价格造成影响。今年以来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上半年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逐月“高烧不退”。这固然是因为受到自然灾害、物流环节成本上涨以及我国农业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等的不利因素影响,上涨主要体现在终端市场,而非产地价格。但土地作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的减少,其对农产品供给量以及民众信心造成的巨大影响,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与此呼应的是,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达14239亿元,一些城市年土地出让收益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操作难度低,简便易行使土地出让金成了许多地区政府部门增加福利、提高收入的摇钱树。而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中,农民是丧失权利的弱势群体,而地方政府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下巨额土地溢价的既得利益者,这便是类似香河土地故事的动机。
到了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70%,实际土地出让面积42.8万公顷,同比增加105%。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出让金长期处于“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这样的暧昧地位。收入巨额且使用自由度强,让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趋之若鹜。在这背后的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商品房出售价格继续以超过百分之十的比例上涨。政府求利,必然引来企业寻租,地方政府与房产企业的利益链就此搭建——这便是众多类似香河土地故事的根源所在。
提及房地产业,地方政府常常爱做加法:拉动了多少多少上游建材产业,完成了多少多少老城区的改造,新增了多少多少就业岗位。然而对于房产业发展带来的问题,却往往选择性的忘却:征地带来的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和治安隐患;城市拆迁带来的居民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府认可度的降低;房价飞涨带来的人才流动壁垒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活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引发的仇富和冲突……对于以政绩促升迁的现行官员绩效考察制度,房产开发之利显而易见。如此说来,一边政府高调抑价,一边房价增长不休,这样一处“双簧”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没有必要把房产企业妖魔化。市场中的任何一个经济产业,都会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放弃利润而不去赚取,这与市场经济相悖。社会成员与房企的对立,因媒体的推波助澜而加剧。但究其根源,实起于政府在保障性住房领域的失位,因为权衡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功能的重要内容。
住房建设是政府职责的要求,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上,公民的住房保障责任显然应由政府担当。不论是文职机构改革诉求下的行政与政治分离,还是管理主义改革导致的“小政府,大社会”,或者以透明性和责任性为价值构建的服务型政府,基本民生的保障与追求民意支持的诉求都是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在住房体制的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后,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公平,进而保证社会稳定,促进有序繁荣,才是平抑房价、保证民生的关键。
于是,香河土地故事看似经济事件,实则政治难题。做什么样的政府,当什么样的官,这拷问着每一个官员的政治信仰。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保证事权与财权的匹配,使得民生保障得以落到实处,则考验着上层管理者的政治智慧。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差别巨大的国家,无论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土地政策中利益分配的改善,还是单纯对于耕地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监管落实,在一个房地产业构建的经济利益链背后彰显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如何落实,是社会公平的诉求,是国计民生的安全证。
尚值得欣慰的是,在事件公布于众后,主管部门迅速介入,并作出了严肃调查绝不姑息的官方表态。至于在土地利益分配体制尚待改革的当下,香河故事是否会因遭受的严肃处理,而不再于他处上演?如何割断地方政府与房产企业间的利益链条,同时合理安排地方财政,以实现保障民生的职能,这仍是待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