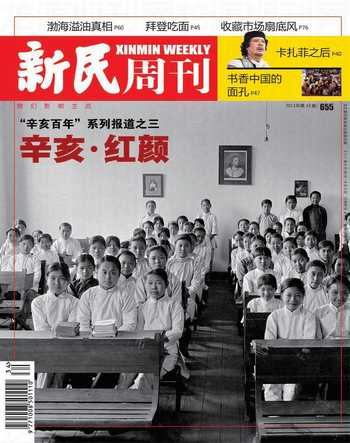公益平台为何异化?
沈洪溥
近日来,红十字会和故宫前仆后继地曝出丑闻,前者涉及种种令人瞠目的人、物、事,乱象不一而足;后者则堪称身负“十宗罪”,从门票、会所到错别字等各种“门”难以胜数。民众与媒体在讶异之余,往往将之归于监管不力,或者人员素质堪忧,但笔者以为,倘若如此泛泛定论,只怕永远不能理清来自上述机构的怪事或者乱象。
如果放宽视角观察这些涉事机构,可一目了然,它们都是身具垄断属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它们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资源平台,在制度缺失、治理混乱的环境中逐步异化,因私利驱动而变得面目全非。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在其中难以找到具备“出淤泥而不染”操守的君子群体,也无法让监管部门对这些体制内部的机构给予足够严厉的管制。
事实上,红十字会也好,故宫也罢,看似一个扶危救困,一个高贵文雅,但是都拥有令普罗大众叹服仰止的不同垄断资源。前者拥有募集善款和管理其他挂靠慈善组织的专有牌照,看似平常。可要知道,直到今年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门才敢公开表示“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此前,有社会组织如想行慈善之举,必须登记注册,找到所谓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而红十字会就是体制钦定的业务主管单位,没它挂名,你募款就是非法集资,你自主行善的想法都是妄想。至于故宫,则完全无须赘述,历代皇帝的红墙大院就是独占的资源,顶级的古代文物、建筑都归它管理,绝对威风得一塌糊涂。
垄断属性极易产生异化的结果。这种异化首先是公益性质私利化。本来,红十字会和故宫都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但却因为独占的牌照或资源成为高出民众甚多的特殊部门,这样的位置无人挑战自然滋生出以牌照或资源谋利的冲动,无论是红十字会个别工作人员购买高价物资,还是故宫私办会所搞经营,都属此类。其次是部门利益个人化。一个垄断的平台还不算,在平台说话算数的人自然也还要捎上亲朋故旧,一起加入有高度、有品质的事业,部门私利进一步被细分为家族或者个人的私利。第三是监督权威虚置化。尽管公益性质事业单位借着独占牌照与资源营利,進而内部人分食所得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在体制之内,上级部门监督往往受时空限制,同级监督又习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下级监督主体,特别是社会舆论监督,往往因信息屏蔽而“隔行如隔山”。举个例子,如果红十字会不是遭逢郭美美小朋友,如果故宫不是遭遇身手不够利落的小偷,各种问题都将继续完好地捂着盖着,绝没有如今置身风口浪尖的麻烦。
当前,垄断已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信息不公开更是完全违背时代发展的潮流。按照国务院要求,各中央部门都已经率先垂范,先后公开了部门决算,公布用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开支账本。作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红十字会也好,故宫也罢,没有丝毫理由拒绝对公众全面公开信息,没有丝毫理由抗拒媒体和公众对其进行更周详的检视和更细致的监督。
仅有媒体监督和公众治理还不够。要想彻底解决这些公益事业平台因垄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必须更加深入地解决体制与机制问题。事业单位改革必须得到根本推进。尽管当前已有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思路,但客观上没有摆脱“非官即商”的二元模式,没有处理好事业单位改革中最重要的公益事业平台定位问题,没有使之彻底服从于公共产品配置的需要,也没有将通过改革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放到首位。试问,在当前乃至改革后的框架内,如何给故宫收取的门票资金定性并监管?如何解决红十字会收取高额管理费用的问题?如何解释那些领取全额财政拨款的机构同时还在进行经营活动的现象?
笔者以为,或有三个选项可以用来部分化解上述矛盾。一是建立公益机构、公共产品配置的责权利统一体系,以公众是否满意为最重要考核标准。二是实行管办分离,针对垄断性质的公益平台,建立独立监管机构,鼓励社会监督,彻底杜绝内部人控制现象。三是引入财团法人经营原则,允许民间自主建立组织,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既避免公益名号被滥用谋利,又可以在公益事业领域形成竞争。
总而言之,不打破垄断,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难免异化,涉事机构丢掉的是公信力,主管部门丢掉的是民心,而整个社会则可能会因此丢掉对道德底线、信托原则的基本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