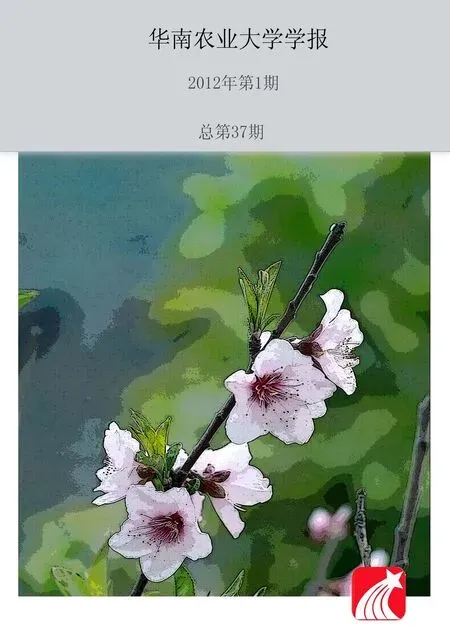史前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之变迁
李秋芳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一、华北平原原始农业的起源
华北平原农耕历史悠久,其农业的起源,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始于万年前。徐水南庄头遗址、磁山文化遗址、贾湖遗址、后李遗址、北辛遗址中出土的实物资料表明,在距今10000—9000年期间,尽管年平均气温与现在接近或偏低,但其降水量却明显增多,加速了植物生长和泥炭沉积;到距今8500—7200年间,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4℃;距今7200—6000年间,华北平原气温平均值要比今高出2.5℃—3.5℃[1]。温暖、适宜的气候环境为当时人们驯化培育农作物创造有利条件。河北阳原县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东胡林、怀柔转年等遗址中已蕴涵有一些农业萌芽的线索。于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发掘于1995—1997年,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南庄头遗址位于河北省徐水县境内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于1986和1997年,遗址中发现家猪、狗的遗骨、草本花粉以及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经测定,南庄头遗址年代距今9700—10500年[2]。北京东胡林遗址在门头沟区军饷乡东胡林村西侧,遗址中出土有石磨盘、磨棒和夹砂粗陶。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东胡林人及其文化遗存的年代在距今1万年前后,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怀柔转年遗址位于北京北部怀柔县宝山寺乡转年村,是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1992年发现并试掘,1995年秋至1996年春发掘。出土有石斧、石磨盘、磨棒和夹砂褐陶。遗址的年代,经对出土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定,约距今9200余年和距今9800余年[3]。陶器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产物,家畜的饲养需要用谷糠作饲料,尤其是猪的饲养,必须依赖于农业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北平原的原始农业已经起源并有所发展。
二、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期粮食种植结构——以粟、黍为主,兼营水稻
原始农业产生之后,自然也就有了早期粮食作物的种植,考古发掘已给我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种植情况。通过考察,笔者发现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就出土有粮食作物遗存,主要品种有粟、黍、稻。河南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有分布面积约0.8—1.5平方米的粟的碳化颗粒[4];许昌丁庄遗址中,在一方形半地穴房子中发现炭化粟粒[5]。经鉴定,丁庄遗址的炭化粟粒为春谷[6]。滕州北辛遗址的陶碗、钵及小口壶的底部发现有粟糠痕迹[7]。此外河南密县莪沟遗址[8]、巩义坞罗西坡、偃师府店东址[9]、山东济南月庄遗址[10](发现1粒炭化粟)等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遗存。对临淄后李遗址进行的孢粉分析中发现有禾本科植物的花粉,其形态酷似现在的谷子[11]。章丘西河和小荆山后李文化遗址中土壤样品的植物硅酸体也是呈现类似现在谷子的形态。
关于黍的遗存,在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20世纪70年代河北武安磁山遗址[12]中出土了大量粮食作物遗存,当时被认定是距今8000年左右的栽培粟,2009年吕厚远等学者通过重新分析,认为在距今约10300—8700年的样品中,灰化粮食的植硅体全部是黍;而在距今约8700—7500年期间,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但粟的含量一直没有超过3%,依然是以黍为主[13]。此外在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炭化作物籽粒,经农学家李璠鉴定为黍[14]11;在山东济南月庄遗址中也土有40粒炭化黍[10]247。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新石器时代早期黍在粮食作物中的确切比重,但其为这一时期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稻作遗存主要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和山东济南月庄遗址中有发现。在贾湖遗址中,出土了上千粒炭化稻谷,另外还有大量的植物硅酸体,经过浮选也发现有栽培稻谷。贾湖遗址14C测年树轮校正值为8942—7868aBP[15]。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中,经过浮选,发现了后李文化时期的炭化水稻26粒,由于现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它们就是栽培品种,所以研究者认为,这26粒水稻既有可能是野生稻,也有可能是栽培稻。无论月庄遗址稻遗存属于野生还栽培,贾湖遗址栽培稻谷的出现至少说明稻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北平原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三、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期粮食种植结构——以粟为主,趋向多元
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平原粮食作物品种逐渐增多,除了原来的粟、黍、稻外,新增了豆、麦等作物。仰韶文化时期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种植更加多元化,出土的粮食作物遗存主要有粟、稻、黍、豆、麦等。粟的遗存发现数量最多,如在河南洛阳王湾一期文化的生活用具器壁上发现有粟的痕迹[16];在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一件鼎内曾发现过粟粒[17];在枣庄建新遗址大汶口文化灰坑内获取了60粒轻度炭化粟粒的籽实[18];在胶县三里河遗址窖穴内发现了大量炭化粟粒,据推算可能有三四千斤[19]。此外在河南临汝大张遗址[20]、巩义市坞罗水库、巩义市芝田镇喂庄、巩义市天坡村[9]、淅川黄楝树、郑州大河村、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安阳后岗遗址、三门峡南交口、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新乐北郊伏羲台、邢台南瓦窑、邯郸赵城、山东莱阳于家店等遗址中均出土有粟的遗存。水稻栽培在这一时期发展速度很快,发现的遗存比早期要多。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洛阳高崖遗址、洛阳王湾遗址、淅川黄楝树、下王岗、淅川下集、郑州大河村、三门峡南交口、社旗谭岗、内乡小河[21]、巩义羽林庄、河北邯郸赵城等遗址都发现水稻印痕或稻叶、稻秆[22]。在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中发现的水稻植硅石数量,随着时间的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其含量比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含量要高,这就反映当地稻作农业在不断的发展,其种植规模在不断扩大[23]。此外,兖州王因遗址中的禾本科植物的花粉有可能属于稻(Oryza Sativa)[24]。胶东半岛北部的蓬莱市大仲家遗址、位于沭河上游的莒县盆地的集西头和段家河遗址中都有水稻植硅体[25]152。截止到目前,学界未在山东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发现栽培水稻实物的出土。
有关黍的遗存,在河南巩义市坞罗水库、巩义市芝田镇喂庄、巩义市天坡村、山东长岛北庄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中都有出土[9]。
此外,这一时期人们还种植了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在陕县庙底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麦类的印痕,距今有7000年的历史[26]18;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发现有一瓮高粱和麻籽炭化物[27];山东枣庄建新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有豆,但种属不明。
出土的实物资料使我们知道,当时人们种植的粮食作物品种主要有粟、稻、黍、麦、高粱等。不过,从出土实物数量来判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种植依然以粟为主。学者对山东莒县小朱家村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碳、氮同位素分析,发现山东沭河上游普通老百姓的食物在大汶口晚期时以粟为主,大约占65.1%的比例;栖霞市古镇都遗址的人骨测量显示当地人的食物是以粟作为主的C4类为主[28]。水稻的种植在这一时期呈现增多的态势,考古实物出土的数量比前期增加许多,有的地方甚至还以水稻作为主要的播种对象,像莒县陵阳河人的生活就是以稻米为主(占66.4%)[29]。而且,和前期相比,这一时期,一般情况下一地是以种植两种作物为多,或粟稻,或粟黍,实行多品种粮食作物种植制度,而不是种植单一的粮食作物。多品种粮食作物种植制度的意义一是可以提高农业的总体产量,二是还能减少单系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古代农业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粮食种植结构——粟稻并重,五谷形成
粟依然是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粮食作物。栖霞杨家圈遗址出土掺杂了粟皮壳和茎叶的红烧土,外墙皮中则有大量粟粒及颖壳,脉纹印痕清晰[30]198-199。在莱阳于家店遗址发现了不少粟壳痕迹,与杨家圈的粟粒相同,可以断定为粟。枣庄二疏城遗址中的一件磨光黑陶罐内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粟类遗存,此外在日照两城镇、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31]、济南大辛庄、河南新安县石寺镇寺沟、偃师马屯、巩义市坞罗南店、登封王城岗、巩义市鲁庄镇念子庄西北等遗址中都出土有粟。
从对现有考古资料统计可见,稻作农业获得快速发展,其发展程度可能超过粟。栖霞杨家圈遗址龙山文化灰坑内发现过稻谷的痕迹[32];滕州庄里西遗址发现有人工栽培的粳稻[33];临淄桐林田旺龙山文化遗址的灰坑内中发现有水稻植物硅酸体[34];日照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中用水洗法筛选出10余粒炭化水稻,可能是人工栽培的粳稻[35];日照两城镇遗址,经专家根据土壤样品中的水稻硅酸体分析,其农业主要是经营水稻生产[36];五莲丹土遗址的土样中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37]182-184;临淄桐林遗址的多个灰坑的采样中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研究者认为这里可能是贮存或加工稻谷的场所[34];在河南新密市刘寨镇发现的新砦遗址,其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是以稻作为主。此外在胶州赵家庄、茌平教场铺、河南禹州阎寨龙山文化遗址[21]、驻马店杨庄遗址、登封王城岗、汝州李楼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水稻遗存。而且在胶州赵家庄遗址、李楼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少量的野生稻。不仅如此,在赵家庄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通过对水田部位采集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确认了水田的存在。这一时期水稻遗存的大量发现,都说明当时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说明这一时期华北平原气候的温暖湿润。
黍在这一时期的不少考古遗址中有发现。在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滕州庄里西遗址、河南西平上坡遗址中都出土有炭化的黍粒,此炭化的黍粒较现代黍米粒要小,但较炭化的粟粒要大。此外在胶州赵家庄、日照两城镇、济南大辛庄、河南新安县石寺镇寺沟、偃师马屯、巩义市坞罗南店、登封王城岗、豫东三台寺遗址中都出土有黍。
麦的种植在这一时期开始增多。据报道,在莒县杭头遗址灰坑中浮选出炭化小麦1粒,但因为其形态不完整,所以难以鉴定其是野生还是栽培品种;在日照两城镇遗址浮选样品中发现了2粒炭化小麦,与现代的普通小麦相比,这两粒小麦的尺寸非常小[36];兖州西吴寺遗址还发现了一定数量小麦(近似种)孢粉的存在,就其形态看,绝大多数与小麦花粉相似,目前定为小麦相似种[38];在河南焦作博爱的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中浮选有小麦的炭化遗存[39]。此外在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济南大辛庄等遗址中出土有麦。和粟、黍相比,小麦的种植需要更高的技术,尤其是对温度和水分的要求比较高。
这一时期,华北平原也有大豆种植。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中浮选出土的炭化大豆共计168粒,占农作物总数(4357粒)的3.9%。根据研究,这些炭化大豆的测量数据恰好介于野生和栽培之间。这表明,王城岗遗址出土的炭化大豆遗存应该属于栽培品种,但仍处在栽培大豆的早期阶段[40]。以前,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栽培大豆遗存是在洛阳南郊关林镇皂角树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的[41],王城岗遗址出土炭化大豆,把中国大豆的起源时间大大往前推进。此外,在西平上坡二里头一期发现有大豆实物[42];山东茌平教场铺出土的豆科的种籽以大豆属为主,可能属于栽培种[43];新安县石寺镇寺沟出土有豆。此外野生大豆在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也不少,如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出土有野生豆,新密新砦遗址发现有野生豆,在山东滕州庄里西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野大豆遗存,在日照两城镇遗址浮选样品中也发现了野大豆[36]。这些遗址中栽培大豆和野生大豆的出土,说明大豆是这一时期华北平原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可能正处在由野生豆向栽培豆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处在栽培豆的早期阶段。
另外,在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中出土有疑似高粱的遗存,经鉴定,其颖片的形状及光泽与高粱相似,但比现代高粱的颖片要小(现代的颖片长约5毫米,宽约3.2毫米),故是否为高粱,学者们还存有疑虑[19]。
通过对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作考古实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龙山文化时期,华北平原的粮食作物种植和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粟的地位受到挑战。通过对华北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作考古实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龙山文化时期,粟的生产地位不断受到稻的挑战。目前发现有粟作遗存的遗址有12处,发现稻作遗存的遗址有13处,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新气象。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中,其稻谷的出土概率为49%,粟的出土概率为36%。植硅体的检测结果为,包含水稻植硅体的样品比例达70%[44]。对l5个人骨样品的测试结果,粟和食粟动物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最多可占到25—30%,如果鱼类不是主要食物,其比例可能更低。这就表明,在龙山时期,山东东南部居民不再以粟为主食,粟可能用于家畜饲料,如喂猪。当时人们可能更多地食用其他粮食作物,尤其是稻米[28]。由此可知,两城镇居民并非单纯种植旱作物,水稻的种植在其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中,从粮食作物种植的数量上看,水稻最多,占总数的61%,其次谷子占34%,黍占4%,麦占1%[45]。可见在赵家庄遗址,水稻的重要性已经超过谷子。山东滕州庄里西遗址灰坑中浮选出的农作物种子遗存,炭化稻米大约有280余粒,而黍的标本仅2粒。这就反映当时是以稻作为主、黍作为辅的农耕文化。
其次,小麦种植逐渐增多。就已发掘的情况看,华北平原大概有5处遗址中发现有小麦遗存,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仅发现一处遗址。这就说明麦子这种粮食作物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传播到华北平原以来,就在本地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小麦作为一种优良的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本区后,势必对原有的主体粮食作物粟和黍产生巨大的冲击,诱使当地的农耕经济体系逐步由依赖粟和黍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这在现在已经成为事实。
第三,大豆开始驯化栽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中龙山文化晚期兼有野生和栽培种特征的大豆籽粒的发现,说明当时我国大豆已经进入驯化栽培阶段,大大推进了栽培大豆起源的时间。
最后,品种增多五谷形成。虽然五种谷物都已经开始栽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遗址中同时出现这五种粮食作物,最多的也就是四种。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粟、稻、豆、黍;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粟、稻、麦、黍。不过,粟、稻、麦、黍、豆栽培品种的出现,标志我国传统“五谷”已经形成。
总而言之,史前时期华北平原的原始农业不仅开始起源、产生,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几千年的演化历史中,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简单的两、三个品种,到多个品种并存多元发展,再到形成几种主要品种。具体而言,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以粟、黍为主,发展到中期的以粟为主,多品种出现;再到晚期的粟稻并重、五谷形成。在史前时期的华北平原粮食作物种植结构中,除了粟一直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存在,并占据核心地位外,最为显著的变化有三点:
(1)稻谷较为普遍地种植。根据学界的研究,从全新世开始,华北平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水稻得到较为普遍的种植。虽然龙山文化时期华北平原稻谷种植范围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气候变暖——仰韶温暖期的影响是重要因素。
(2)小麦开始传入并逐渐发展。小麦由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未见栽种,到中期仰韶文化时期的少有种植,再到龙山文化时期逐渐发展,这既有小麦本身的自然属性因素,也与人们物种选择的努力分不开。
(3)五谷种植结构形成。由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转变为包括了稻、麦、大豆等在内的多品种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这种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形成,反映了史前时期华北平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为以后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星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J].史学月刊.2005,(4).
[2]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92,(11).
[3] 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J].文物.1996,(6).
[4] 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J].农业考古.1984,(2).
[5] 吴梓林.古粟考[J].史前研究.1983,(1).
[6] 张履鹏.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J].中国农史.1986,(1).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4,(2).
[8]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集刊.1988,(1).
[9] 李炅娥,等.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商代的植物和人类[J].南方文物.2008,(1).
[10]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济南长清区月庄遗址2003年发掘报告[M]∥东方考古第2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1] 严富华,麦学舜.淄博临淄后李庄遗址的环境考古学研究[M]∥中国第二届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论文.[出版时间不详]
[12] 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J].考古学报.1981,(3).
[13] HOUYUAN LU.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 000 years ago[J]. PNAS,2009,(18).
[14] 李 璠.中国栽培植物起源与发展简论[M]∥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5] 陈报章,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古文化生态学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16]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61,(4)。
[1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广饶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85,(9).
[18] 孔昭宸,等.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存与原始农业[J].中原文物.2003,(2).
[19] 何德亮,张 云.山东史前居民饮食生活的初步考察[J].东方博物.2006,(2).
[20] 黄其熙.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J].农业考古.1982,(2).
[21] 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J].农业考古.1994,(1).
[22]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J].考古学报,1988,(1).
[23] 姜钦华,张江凯.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史前稻作农业的植硅石证据[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1).
[24] 孔昭宸,杜乃秋.山东兖州王因遗址77sywT4016探方孢粉分析报告[M]∥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6] 金善宝.当代科技重要著作·农业领域·中国小麦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7]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9,(3).
[28] 方 辉,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先民食谱的稳定同位素分析[J].考古.2008,(8).
[29] 齐乌云等.山东沭河上游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研究[J].华夏考古.2004,(2).
[30]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M]∥胶东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31] 靳桂云,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J].科学通报,2007,(18).
[3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4,(3).
[33]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J].考古.1999,(7).
[34] 靳桂云,等.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硅酸体研究[J].考古.1999,(2).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王城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重要发现[J].中国文物报.1994,1(23).
[36] 凯利·克劳福德,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J].考古,2004,(9).
[37] 刘延常,王学良.五莲县丹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和东周时期墓葬[M]∥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38]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9]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EB/OL].2008,1(23):2.http://www.ccrnews.com.cn/100004/100007/16080.html.
[40] 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J].华夏考古.2007,(2).
[41] 叶万松,方孝廉.洛阳市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M]∥考古学年鉴(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2] 魏兴涛,等.河南西平上坡遗址植物遗存试探[J].华夏考古.2007,(3).
[43] 靳桂云,王春燕.山东地区植物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44] 靳桂云,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植硅体研究[J].考古.2004,(9).
[45] 王春燕.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稻作农业研究[D].山东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