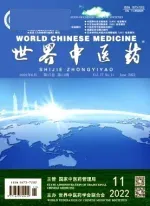旷惠桃教授论治风湿病整体观赏析
肖 燕 颜学桔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湖南省长沙市麓山路58号,410006)
风湿病是以累及骨、关节及其周围组织,如肌肉、肌腱、滑囊、筋膜、韧带、神经等部位,以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大类疾病的总称。在现代医学中,归属风湿病范畴的病种有8类近百种,临床最常见的风湿类疾病约15种,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热等[1]。风湿病在中医学属于痹症范畴,亦是属于亚种较多的疾病。按病因分有风痹、寒痹、湿痹、热痹、气痹等;按部位分有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等[2]。风湿病病因复杂,病程迁延,致残率高,令医家棘手,患者忧心。湖南省名中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旷惠桃教授,对风湿类疾病颇有心得。研读旷惠桃教授论文和医案,其过人之处,在于治学方法和临证策略都贯穿一种思维灵动的整体观,因而在辨析和治疗风湿病方面表现出不凡的见地和显著的疗效。
1 识病整体观
中医临证,望闻问切。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否借助现代医学检验,患者病态中所表现的症状是诊断的重要依据,症状的改变,则是判别疗效的直接依据。以症识病,见症治病,往往成为医、患的共同诉求。旷惠桃教授则是以更大的视野,无论对病类、病种以及治疗方药,均从理论认识的纵向沿革,到现代研究的横向综述,全面认识和整体把握,探究症状起因和传变的内在机制。如对风湿病的认识,她纵览历代中医文献,历数风湿病之渊源。“风湿病”之名,自古有之。长沙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有“风湿”记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风湿”有26处之多,《黄帝内经》除痹论篇外,以“风湿”单独出现者有17处,汉张仲景《金匮要略》首次以“风湿”作为病名[2]。旷惠桃教授认为,对痹病发病原因的研究,自《内经》以来,诸家探讨颇为深刻,涉及范围甚广。从发病学角度看,可将其概括为“正虚”“邪侵”“痰浊瘀阻”三个方面[2]。“正虚”为首因,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3]。旷惠桃教授认为,风湿的发病机制则有4种可能:邪随虚转,证分寒热;邪致痰瘀,痹阻不通;邪气交争,正虚邪实;虚瘀相搏,交结难解。风湿病的传化途径主要有3条,一为五体间传变,二为表里相传,三为脏腑间传变[2],并都引经据典,予以论证。如论及风湿病因,先引《素问·痹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医门法律》曰:“风寒湿三痹之邪,每借入胸中痰为相援。”《类证治裁·痹论》提出:“必有湿痰致血瘀滞经络。”《医林改错》有“瘀血致痹”说。继而分析认为“而导致痰浊瘀血的直接原因多为饮食所伤,湿聚化痰;情志郁结、气滞血瘀或跌仆伤致瘀血阻滞”[2]。对疾病有了如此由表及里,从古到今的全面考究,其治疗方略则能游刃有余。
2 辨病整体观
如果说病类适于提纲挈领地整体认识和把握,对具体病种,旷教授同样穷究病因、通识传变,在先贤同道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如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虽然业内通常按痹症病机论述,但疗效不尽人意。旷教授着意于澄清其类属以利切中病机,从而提升临床疗效,分别从“风湿4病”(风湿寒性关节痛、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的分类、临床表现、发病机制、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性质和病机特点、风湿性关节炎名家治验等诸多方面探索分析,通过名家临证所得,如朱良春认为“非草木之品所能宣达”,张沛虬认为“用一般祛风寒化湿药效果不显”,任继学认为“久痹不愈,绝不能用羌、防、独活之类祛风药治之”[4]。旷惠桃教授认为,从这些当代名家的认识与临床用药也不难看出,RA的病理根本,即在于瘀血痰浊为患,只是尚未见文献明确指出阳虚而瘀痰为患是RA的基本病机而已,并认为“RA不应以风、湿、寒、热来论其基本病因病机,而应从阳虚气弱、四末失温为基础,瘀血痰浊凝聚关节为基本病机来认识。与一般风湿寒痹不同,故于治疗应步步顾及到阳虚与瘀痰”[4]。旷教授借鉴名医的论述和经验,拟制虫类药经验方:30%全蝎,30%蜈蚣,30%乌梢蛇,10%地龙,共研细末,炼蜜为小蜜丸,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30例,每次5~10g,每日3次,1个月为1个疗程,观察治疗1~3个疗程。临床观察结果,总有效率为96.7%,并观察到改善关节疼痛和关节肿胀有显著作用。旷教授特别指出:“治疗期间观察,尽管全蝎、蜈蚣均为有毒之品,但未见毒副反应,可见虫药治疗RA很有前景。”[5]
旷惠桃教授多用虫药的处方经验,与中医名家路志正教授不谋而合,路老认为,对病因复杂的风湿病,“治疗当伏其所主,先其所因,灵活而施以通络活血、搜风走窜虫蚁之品”[6]。无独有偶,中医名家朱良春教授认为“一般治疗痹证中药都喜选用大队祛风燥湿、温经通络之品。但风药多燥,易于伤阴耗液,损伤正气”“虫类药既能极大提高疗效,又具有其他药物不能替代的作用”[7]。
3 病程分析整体观
旷教授虽然长于全面深刻认识疾病的本质,注意借鉴名家临床经验,每每获得较好的转归和稳定的疗效。2010年2月26日诊治1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尪痹),介绍如下。
某,女,66岁,农民。长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居住条件潮湿,四肢关节疼痛20余年,双手指近端关节肿痛变形5年余,曾于多家医院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行中西医间断治疗,效果不佳。现症:四肢大小关节疼痛,每于气候变化阴雨连绵时则疼痛难忍,遇寒冷加剧,得温稍减,双手手指关节疼痛肿胀尤甚,成梭形肿大,因畸形严重,活动受限,梳头穿衣等均需他人帮助,疼痛入夜较甚,苔白稍厚,脉沉而无力。辨证:气血亏虚,寒凝经脉。治法:养血散寒,温经通脉。选方:当归四逆汤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处方:黄芪30g,桂枝、白芍各15g,当归15g,通草5g,细辛3g,制川乌、独活、桑寄生、秦艽、牛膝、杜仲、甘草各10g。每日1剂,水煎取汁,另以全蝎、土鳖虫各10g、蜈蚣2条、乌梢蛇10g共研细末,兑入药液中内服。14剂。二诊、三诊均见明显好转,守原方。四诊:服药已56剂,关节疼痛基本消失。故去虫类搜剔之品,加温补肝肾之续断、仙茅、淫羊藿、骨碎补、巴戟天之类,再服14剂。疗效:除手足关节变形外,一切如常人。
旷教授分析此类医案:一则病程长,且多长期用西药治疗,肝肾功能多有损害,病至后期,患者多有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等,非得用“血肉有情之品”不能恢复;二则风寒湿邪外袭,日久化热,生瘀生痰,风寒湿热瘀交阻,营卫气血受阻不通,故疼痛难忍,一般驱风除湿之品均难奏效时,必须用虫类药透骨搜风,方有效验。实践证明,虫类药擅长搜剔络中风寒湿邪,驱寒蠲痹,对于痰瘀痹阻,凝滞不除,迁延日久的重症类风湿,若坚持治疗,也能每获良效。
4 遣方用药整体观
辨证是合理治疗的第一步,制方得当,是实现疗效的必要手段。旷教授无论处方立意和药物选用,也都思路开阔、博采众长,对历代名方深究用意,又凸显个人见解,在药物的功效利弊上,用配伍制衡实现扬长避短,故而疗效过人。2007年冬治愈一风湿性关节炎(寒湿痹证),介绍如下。
某,女,56岁。5年多来,周身关节疼痛反复发作,曾多次到医院进行风湿全套等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故未引起重视。近年来,疼痛逐渐加重,经常关节、肌肉酸痛,夜间辗转不能安卧。近10天,因气候寒冷,经常用冷水洗菜且劳累过度,病情突然加重。现症:周身关节、肌肉疼痛沉重,疼痛彻骨,夜间辗转难卧,关节冷痛,手足厥冷,犹如冰块,活动屈伸不利,时伴恶寒咳嗽,甚则寒战,周身无汗。自觉肚脐周围潮湿,发冷,头盖骨冷痛,呈抽掣样疼痛,遇风寒尤甚。就诊时身穿4件毛衣、2件鸭绒棉袄(1长1短),戴着大棉帽、口罩、皮手套。舌苔白,脉浮紧。辨证:寒湿痹证。治法:温阳散寒祛湿。选方:乌头汤加味。处方:黄芪30g,白芍15g,制川乌6g,麻黄、炙甘草、桂枝、杏仁、白术、附子、干姜、羌活、独活各10g。每日1剂,水煎取汁后加白蜜1勺内服。7剂。
二诊:上方服1剂后,患者周身微汗出,自觉全身轻松,疼痛稍减。7剂尽,天气依然寒冷,但外面的鸭绒大衣已去,口罩已脱下,精神好转,恶寒寒战已止,咳嗽已平,周身骨关节、肌肉和头部冷痛均明显减轻,全身已较前轻松许多。但骨关节冷痛仍存,肚脐周围仍潮湿,且自觉头晕。甘草附子汤方后有云:“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头眩),勿怪,即时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未得除故尔。”于是击鼓再进,上方加薏苡仁30g,继服7 剂。
三诊:头晕好转,关节冷痛明显减轻,手足已转温。以独活寄生汤加减,30剂,终获痊愈。
旷教授自评此案:本案用乌头汤加味治疗,全方发汗散寒,温经祛湿止痛。方中乌头大辛大热,驱寒逐湿止痛为君药;麻黄辛温,通阳行痹为臣药;芍药、甘草、白蜜酸甘养阴,缓急止痛,又能降低乌头峻猛之性(因乌头剂量不大,未按原书用白蜜煎煮乌头,而是在煎好的药汁中加兑白蜜,既制乌头毒性且能和胃)。黄芪益气固表,且防麻黄发散过度,共为佐使药。加入桂枝、杏仁、白术即麻黄加术汤发汗散寒祛湿,麻黄配白术虽发汗而不致过汗,并可行表里之湿。加附子一味方中即有桂枝附子汤、白术附子汤、甘草附子汤之意,既能温经散寒,又能助阳除湿;加干姜是因患者脐周湿冷,“脐乃神阙”,位于中焦,取肾着病“腹重如带五千钱”用甘姜苓术汤温中散寒祛湿之意;加羌活、独活意在加强祛湿力量(因患者身重甚乃湿重之故);力尚不及,药后出现头晕(如冒状)之症,故二诊时加薏苡仁取麻杏薏甘汤之意以加强除湿力量,果然头晕及关节冷痛、头部冷痛等症能较快好转。
5 治疗策略整体观
旷惠桃教授深究病因的研究力度,决定了她追求病因治疗的临床特点。尽快解除症状,是患者的直接愿望,也是旷教授实施病因治疗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她主张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她认为风湿类疾病是一类慢性疾病。无论是西药治疗,还是中药治疗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起效。对于疼痛较重的患者。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使用缓解疼痛起效较快的非甾类抗炎药(NSARDS)是必要的,也是伦理学的要求。在中医辨证治疗基础上合并使用非甾类抗炎药疗效较肯定。因为非甾类抗炎药治疗风湿类疾病主要是改善症状,但疗效不能持久,不能控制病情的进展,而且不能改善体质,对风湿类疾病引起的免疫反应不发生根本影响。而中医辨证治疗既能控制症状,又能根据体质用药,许多中药能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而且药效持久。二者合用能收到疗效互补,甚至疗效叠加的效果”[1]。
旷教授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的主要用药思路以及用药模式,如“治疗寒痹用乌头汤+非甾体抗炎药;热痹用白虎加桂枝汤+非甾体类抗炎药;湿痹用薏苡仁汤+非甾体类抗炎药:寒热错杂证用桂枝芍药知母汤 +泼尼松,虚痹用三痹汤 +免疫抑制剂等”[1]。
有专家观察到少量在国外使用生物制剂无效者,在加用补肾活血等中药后,其症状仍可获部分缓解[1]。
6 同类研究佐证旷惠桃教授辨治风湿病整体观的合理性
旷惠桃教授对风湿性疾病的理论认识和临床治疗思路及方药,无不蕴含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整体观和方法学。旷教授对风湿性疾病的整体观,来自她对中医治疗理念的解读[5],认为两种医学的着眼点是两个途径:西医着眼于病原体,中医着眼于病原体滋生的环境;西医看到的是病原体繁殖产生的疾病,中医看到的是人体内环境被干扰产生的各种改变;西药以消灭病原体见长,中医以清理病原体滋生的环境见长”[8]。旷惠桃教授所推崇的通过改善身体内环境实现病因治疗的方法,从其他同类研究可以得到合理性佐证。如:路志正教授体悟自己七十年的行医历程,总结出“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顾润燥、纳化常”调理脾胃的学术思想,在临床工作中以此为指导治疗风湿性疾病,往获良效[9]。“四旁”者,首见于《素问·玉机真脏论篇》:“脾为孤脏,中央土以灌四旁”,“四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脾属土位于中央,为气血津液的生化之源,长养四脏,故上焦之心肺与下焦之肝肾可合称为“四旁”[10]。
风湿病学科所研究的并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解剖意义的系统或器官的疾病,风湿性疾病也往往为多系统累及,临床表现复杂,同时风湿病学的临床知识又往往与基础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联系紧密,许多风湿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还不明确,各种新的知识点不断涌现,各种疾病的诊断标准的治疗的专家共识和指南更新频繁,大量的国际临床多中心实验结果不断发表[11],风湿病的多元复杂性和医学对其已有认识的局限性,无疑可以说明旷惠桃教授论治风湿病之整体观是合理的。
[1]旷惠桃.风湿类疾病中西医结合用药思路[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9(2):3-4,13.
[2]旷惠桃.风湿病的分类及病因病机研究[J].湖南中医杂志,2002,18(2):1-2.
[3]曹玉举.娄多峰教授论风湿病病因病机[J].中医研究,2011,24(10):64-66.
[4]潘远根,旷惠桃.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机的再认识[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8,5(1):11-13.
[5]旷惠桃,潘远根.虫类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1):74.
[6]姜泉,罗成贵,李纪川.路志正教授治疗风湿病用药经验举隅[J].新中医,2011,(43)9:132-133.
[7]蒋恬,顾冬梅.朱良春教授治疗风湿病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简介[J].新中医,2011,(43)6:150-151.
[8]潘远根,旷惠桃.从人体内环境治理解读中医[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1(3):6-9.
[9]张华东,黄梦媛,陈祎,等.路志正教授“持中央、怡情志"学术思想在风湿病中的应用[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1):31-33.
[10]张华东,黄梦媛,陈祎,等.路志正“运四旁,调升降”学术思想在风湿病中的应用[J].世界中医药,2011,6(2):118-119.
[11]钱龙,厉小梅,李向培.循证医学与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相结合在风湿病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J].山西医药杂志,2011,40(6):615-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