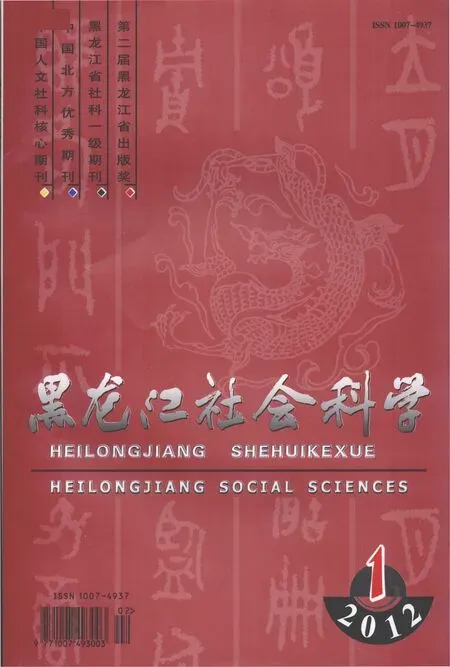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
徐 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
徐 莹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2)
“倡导”是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要宗旨和重要实践。“倡导”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始终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实践为注解,这种倡导实践则主要通过对抗性倡导和合作性倡导两种形式得以展开,并对主权国家的国际声望构成压力。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目前呈现出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特征。在准确把握其倡导现状并稳守政治底限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与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理性互动,将成为中国外交在可见的未来消解来自外部世界舆论苛责的重要手段。
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合作性倡导;对抗性倡导;中国外交战略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察和描述,以推动和维护某项特定“事业”为根本目标,试图影响主权国家政策和相关实践而进行的倡导活动,一直是大量国际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基本具象表现[1]。这些主要以倡导为己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长背景,又自称具有所谓“全球利益关切”;既是身处发达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同时又是能够超越国家边界,不断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活动的国际行为体。凭借这种特殊的背景和特有的活动空间,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倡导的矛头指向中国,在国际层面对崛起中国的国际声望构成了相当程度的舆论压力。对于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和合作性倡导,如何把握其现状特征并从战略高度加以有效应对,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略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
一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倡导,因此文中所提及的“倡导”一词皆要从西方语境的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追根溯源,英文倡导一词“advocate”是由拉丁语“advocare”衍生而来,其拉丁语原意为“召唤证人”。《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名词“advocate”的解释是“为他人提供援助、辩护或抗辩的人……在法庭上或法官面前为他人提供法律建议、帮助以及负责陈述动机”;《柯林斯英语词典》对动词“advocate”的解释为“公开支持或介绍”。而在最近30年中,当世界各国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纷纷开始以“advocacy”来定义自己的主要职能时,“advocacy”的含义则发生了演变,即“通过游说获得相关权力部门的认可与支持,从而促使一些政策、惯例、观念甚至价值观发生改变的组织性政治行为”。比如,一些人权组织就将“advocacy”看做维护“普遍人权”的手段,倡导政治意识形态能够被参照“人权标准”而设立的国际公约取代;当“advocacy”概念与一些社会运动相联系时,则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护人权,而是呼吁政府将资源均分及社会平等纳入考虑范围,同时主张自主权。此类“advocacy”在拉丁美洲尤其盛行,它通常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常以大规模支持者试图改变现有政权结构的方式出现;很多西方环保人士不断通过媒体向政客或者企业进行宣传则属于环境倡导的范畴;像绿色和平组织反对捕鲸、核试验、破坏原始雨林及转基因生物等“单一议题运动”,就是环境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的成功案例。
根据英国学者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2]对NGO倡导性质的概括性分析和判定,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主权国家政府的倡导又可以从总体上分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合作性倡导,另一种是对抗性倡导。其中,第一种形式倡导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所进行的有建设性的对话。而这类倡导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具体的发展政策、计划及发展项目,主要涉及健康医疗、农业进步、弱势群体救助以及教育等社会发展领域的问题。由于这种形式的倡导主要以合作为主而不具备任何对抗性质,因此容易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认可和接受。当然,该种倡导的有效性也有赖于国际非政府组织高水平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以及在特定发展中国家相关社会发展领域的长期实践经验。
另一种倡导形式是对抗性的,其目的是试图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进程、结构,甚至是意识形态。它表现为在国际层面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开的批评和指责。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这种对抗性倡导一般开始于同发展中国家内部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之后再同其他国家和一些特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结成纽带,最后从国际层面对所谓“违反规范”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并逐渐使某些国际规范,特别是人权和环保方面的国际规范成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制度化安排。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玛格利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学者凯瑟琳·希金克 (Kathryn Sikkink)合著的论文中,这种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中轴对发展中国家内外结合式的倡导就是“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3]。具体而言,就是国内行为体先绕过对之进行“压制”的国家,努力在国际上争取联盟,从而可以从外部对该国施加压力。而使“国际规范”在发展中国家内化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则被希金克和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称之为“螺旋模式”(Spiral Model)[4]。政治机会理论家卡格拉姆 (Sanjeev Khagram)、莱克(James V.Riker)以及希金克在《从圣地亚哥到西雅图:跨国倡导团体重构世界政治》[5]一文中,运用政治机会结构①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为社会行为体的集体行动所提供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组织资源以及相应的制度性机构。参见徐莹《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7月。的概念对此种涵盖上述两种模式的倡导形式进行了理论分析。他们指出,虽然国际政治机会不能代替国内政治机会结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可以相互作用。回飞镖和螺旋模式就是二者之间最具代表性的互动模式。这两种模式说明,由于有限的国内政治机会,如主权国家政府对相关倡导没有回应或持否定态度,国内社会运动行为体(本地非政府组织)便试图谋求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支持。也就是说,相对封闭的国内政治机会结构和呈开启状态的国际政治机会结构彼此结合,最终促成了针对发展中国家对抗性倡导的产生。
二
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所进行的“倡导”,无论是对抗性的抑或是合作性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次展开的。当下,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则呈现出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
首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对抗性倡导主要集中在人权领域。由于实施对抗性倡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经常采取“点名羞辱”(Name and Shame)的手段大肆批评主权国家,从而以高调曝光的形式令主权国家“蒙羞”,偶尔它们甚至还可能成功颠覆某个政权(如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因此,对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疑虑和拒斥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持有的态度。也正是基于中国国内不存在对它们开放的政治机会,此类实施对抗性倡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目前所有针对中国的倡导都是在国际层面展开。最典型的对抗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莫过于人权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in China)、人权第一组织(Human Rights First)等。这些组织几乎每年都要向国际多边机制,如联合国人权公约机构(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联合国人权委员会(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政府机构或部门,如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The U.S.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美国参议员司法委员会(The US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提交多份所谓“关涉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文件;此外,它们还通过大众传媒发表公开信,以及组织各种主题活动的方式,在国际层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人权观察组织为例,该组织从2003年开始共发布了九个所谓直接关涉中国人权的报告。其中,有三篇报告的主题围绕西藏,两篇关涉新疆,其他几篇分别针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戒毒康复人员、在华朝鲜妇女,以及对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所进行的评估。而中国人权组织则有着非常“系统和全面”的倡导策略,其倡导覆盖针对国际多边机构的“国际倡导”(International Advocacy),主要通过媒体向西方国家散布倡导信息(Media Work)、出版人权报告和双周刊、发表公开信等一系列手段。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最为独特的还要算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表面似乎并没有进行针对中国的公开倡导,特别是对抗性倡导,但是,该组织却每年直接向一些藏独、疆独组织以及位于中国境内或境外的倡导类NGO拨付大量款项,提供资金支持,实质上是在间接地对中国实施具有颠覆目的的对抗性倡导。

200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藏独和疆独组织资助一览表
其次,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尽管与对抗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始终保持距离,但中国对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却一直是适度开放的。于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村民自治选举、人权、司法、环境、新闻传播等领域针对中国的合作性倡导也便呈现出大幅拓展的势头。
以村民自治选举为例,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和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这两个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人员,就是受中国政府邀请对中国的村民选举过程进行基本评估的知名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国际共和协会是最早受邀观察中国村民选举的国际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观察了福建的村民选举过程(1994年和1997年),之后提出了12条改善选举的建议;1996年9月,中国民政部又邀请美国卡特中心观察村民选举所有过程,征求他们完善选举的建议。于是卡特中心派遣的观察团跋涉了中国的6个省和1个直辖市(福建、湖南、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重庆),观察了分布在这些省市的55个村庄,并针对选举程序提出了包括加强措施保证选举的秘密性和独立性、禁止或尽量减少“流动票箱”、健全委托投票的规则、提高计票的透明度多条具体的改进意见[6]。
事实上,中国在人权领域也与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着积极有为的接触。例如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RWI)这个致力于通过研究、学术教育、传播和机构发展来推动人权教育的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就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应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在中国开始了机构合作项目。1996—2000年间,该机构为来自司法部门的高层官员,包括警察、检察官、法官及监狱工作人员举办了人权培训课程。从2001年开始,RWI在北京设立了项目办公室,并开始全面实施侧重于支持中国学术界及中国监察机构的项目。目前,该研究所正在中国实施一个为期三年(2008—2010)的人权能力发展项目,致力于提升中国学术机构的人权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加强检察机关通过人权标准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和促进中国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此外,挪威人权中心(NCHR)、丹麦人权研究所(DIHR)开始与中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合作。从2001年到2007年,北欧人权机构已经为中国法学教师举办了7届国际人权法课程,200多名中国法学教师得到了北欧组织有关国际人权法的培训[7]。
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和国际司法桥梁组织(International Bridges to Justice)是在中国司法领域较为活跃的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律师协会1998年启动的亚洲法律项目与中国司法部合作,对中国法律援助实践者进行培训;它还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合作举办了多次法学伦理和刑事诉讼法的培训班;与陕西法官协会和柏林法官协会合作,由400多位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聆听模拟审讯,以比较中、美、德三国审讯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有何不同;2002年以来,亚洲法律项目在中国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与国家环保局合作实施“环境治理”项目,期间在一些中等城市召开了一系列的培训。而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司法桥梁组织,在2000年成立之后便与中国的司法部门、学术机构及社会组织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合作关系。目前国际司法桥梁组织中国项目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刑事辩护技能培训和研讨;召开刑事司法改革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国际间刑事司法的交流和访问;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项目等。此外,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也是在中国的司法领域比较活跃的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
在环境保护领域备受关注的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合作性倡导活动也相当活跃。该组织的“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从推动远离煤炭,见证气候变化,倡导能源革命和追踪气候谈判几个方面进行旨在提升中国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倡导。在推动远离煤炭方面,绿色和平经过实地考察,发布《煤炭的真实成本——2010中国粉煤灰调查报告》,呼吁政府尽快完善粉煤灰治理政策,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并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从源头控制粉煤灰污染;在倡导能源革命这一环节,绿色和平与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以及世界风能理事会合作,先后推出《风力12在中国》、《中国风力发电价格政策分析研究报告》、《中国光伏发展报告2007》以及《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0》,努力推动中国风电的迅速发展。
2004年进入中国的国际记者培训机构——英特新闻(Internews)堪称是在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最为活跃的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个从事媒体培训和支持的组织目前已成功在北京、西安、杭州、长春和昆明组织了几十场关于法治报道的专题讲座,培训了370多名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媒体与法律从业人员。2007年,该组织携手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织了国内首次“环境法制与媒体报道”研讨培训会议,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了“商业透明与媒体报道”研讨培训会议。2009年,该组织又联合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在广州举办“气候变化:媒体与NGO的对话”培训研讨会。
三
经济上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面对国内社会问题的现实压力与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在多个领域系统性超强的倡导,除了从战略高度对其全面掌握,仔细甄别,以大国心态方法得当地沉着应对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首先,面对步步紧逼的对抗性倡导:淡定从容,尝试沟通。当下针对中国的对抗性倡导,特别是集中在人权领域的对抗性倡导,由于跟中国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有一定程度的暗合,因此目前此类倡导对中国形成了步步紧逼与合围之势,对中国的国家声望和国际形象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此种形势,中国一方面要淡定从容,涵养大国心态。就人权问题而言,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权的享有和实现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权的实现都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都可能存在人权保障不充分的情况。认清当前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有的发展形势,就可以首先以大国应有的自信来面对周遭的批评和指责,而不会有英雄气短的尴尬心态;另一方面,当今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能站在理性态度、大国气度和世界眼光的更高境界上,淡定从容,敢于运用智慧,鼓励我国的相关智库与对抗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组织展开建设性的沟通,而非简单化地无视其存在;即便最初仅仅止于权宜之策,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摸索应对此类组织的基本经验,并将这种“破坏力量”加以转化,消解中国在这一领域所承受的巨大形象压力。
其次,面对全面展开的合作性倡导:纵深拓展,理性互动。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一直是以谦逊务实、积极有为的态度主动与实施合作性倡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展开广泛接触与合作。在现有基础上,目前中国与此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必将向纵深方向不断推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把握“理性互动”这一关键。即在积极回应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性倡导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实行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并非全盘按照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借鉴西方民主体制之有用成分的同时,只有依托本国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环境特质等国情,走一条真正适合本国的政治道路,才能避免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陷入的“民主—动乱—专制—再民主—再动乱—再专制”的恶性循环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严守自身政治底限,把握理性互动节奏,是当下中国应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性倡导的关键词。
最后,面对网络驱动下的渐强倡导:边做边说,公开透明。在当今这个新媒体和网络技术极尽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对抗性还是合作性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开始大量依托互联网进行特定利益诉求的倡导。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外流行的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以及中国的微博 (microblog),都因其草根性、及时性和现场性等突出特点而被针对中国进行倡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采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凭借包括微博在内的互联网技术,在扩大信息影响力的基础上,动员公众广泛参与关涉其倡导主题的相关讨论,进而利用网络凝聚起的巨大社会力量进行舆论引导,从而谋求获得相应的政府关注,并推动其所倡导的核心问题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以环保领域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性倡导为例,微博这种最新网络工具的应用,将时尚媒介与气候变化这一“时尚”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针对年轻群体的公众动员方面,确实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威力。而借重网络优势所实施的社会动员,与气候变化组织的高度道德美誉度相结合,一旦突破对政府进行“合作性倡导”的界限而转入“对抗性倡导”的范畴,就有可能对政府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这必然会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耐心,应对策略的选择和具体实施效果提出严峻挑战。面对这一考验,中国最实际可行的应对原则就是:公开透明,边做边说。事实上,中国在清洁发展和抑制气候变化方面早已扎实起步。世界权威能源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就在其2010年11月推出的《世界能源展望》中肯定了中国在低碳能源技术发展上的巨大成绩,并同时预言,中国将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和高阶煤”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上发挥全球的领军作用[8]。但是,这种扎实努力要想被世人所了解和认可,最值得提倡的办法是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借重合法性程度更高的国际组织来传递信息。因此,以自信与合作的姿态倾听气候变化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声音,同时通过与这些组织的广泛信息沟通和技术交流,最大限度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扎实举措,则不失为有效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苛责的一种可行方式。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参与世界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频密的对抗性倡导将给中国制造更为严苛的舆论压力,这将对中国的抗压能力和理性务实的回应策略提出挑战;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合作性倡导将向纵深方向大幅拓展,这同样也将考验中国对自身的准确定位能力和制度创新潜力。在可见的未来,淡定从容,尝试沟通,稳守底限,理性互动,边说边做,公开透明,将成为指导中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倡导进行战略回应的重要原则。
[1]徐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21.
[2]Michael Edwards.Does the doormat influence the boot Critical thoughts on UK NGOs and international advocacy[J].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3,1993:163 -175.
[3]Margaret E.Keck,Kathryn Sikkink.Activists Beyond Borders[M].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4]Thomas Risse,Kathryn Sikkink.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to Domestic Practices:Introduction.in Thomas Risse,Stephen C.Ropp and Kathryn Sikkink,eds.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 -39.
[5]Sanjeev Khagram,James V.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eds.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Networks,and Norms,Minneapolis[M].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6]谭青山,帕斯特.中国村民选举的意义[DB/OL].[2011-05 -04].村民自治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7748.
[7]谌彦辉,唐文竹.国际人权机构来华始末[J].凤凰周刊,2010,(35).
[8]Clifford Krauss.In Global Forecast,China Looms Large as Energy User and Maker of Green Power[N].The New York Times,2010 -11 -10(3).B3;IEA.Executive Summary[R].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Paris:OECD/IEA,2010:46 -51.
D81/D82
A
1007-4937(2012)01-0063-05
2011-12-22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08XNB018)
徐莹(1972-),女,辽宁大连人,副教授,从事国际组织、中国外交研究。
〔责任编辑:时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