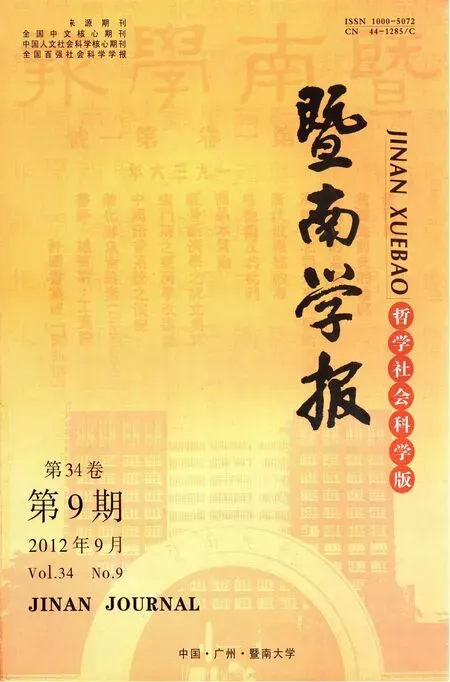《声无哀乐论》与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
陈德琥
(蚌埠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刘勰论及魏晋文学时,曾对傅嘏、王粲、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等人的作品作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总体评价(《文心雕龙·论说》)。然而,在其后论述历代作家文学才力的《文心雕龙·才略》篇中,以上作家除了点到“何晏《景福》(指《景福殿赋》——笔者注),克光于后进”外,“师心以遣论”倒成了嵇康的专擅了。由此看来,刘勰对嵇康散文的“师心”特征尤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论说》篇接下来提及嵇康著述时仅例举“叔夜之《辨声》”——《声无哀乐论》。刘勰视其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典范之作是显见的。然而,在此前的古代典籍中“声”曰“辨”者可谓凤毛麟角(《周礼·地官·鼓人》载:“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声”曰“辨”见诸其他文献则尚付阙如——笔者注)。这不能不让我们认真审视《声无哀乐论》鲜明的思辨色彩和突出的思辨特征。实际上,在“有无之辩”、“言意之辩”等成为魏晋文坛常见题域的背景下,《声无哀乐论》具有严密的思辨理路有其必然性。这既得益于魏晋时代“清谈”之风盛行、力主道家学术、突破了“独尊儒术”思想禁锢而形成的儒道互补、思想解放的哲学思潮,又与嵇康独特的思维方式、思维品质、思维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目前学界研究《声无哀乐论》思辨特征和魏晋美学思辨精神的力度明显不够,甚至存在错误释读现象。比如,言之为“一个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1]有合理的一面,但显然没能把这一“乐趣”上升到思辨精神的高度来认识;而以“诡辩”、狡辩乃至“强辩”[2]论之则是明显的错误译读,实难服众。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就《声无哀乐论》折射出的魏晋美学思辨精神来谈点体会,权作引玉之砖。
一、“清谈”与时代的思辨风尚
魏正始年间,玄学兴盛。“有无”、“本末”、“名教与自然”之辨风行文坛。自何晏、夏侯玄、王弼始,至晋王衍辈而益盛,甚至延及齐梁而不衰。三国魏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云:“幸有袁生,时步玉趾,樵苏不爨,清谈而已。”可见,“清谈”之风在当时有多么盛行。以至肇始于西周、流行于春秋以来的“赋诗”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3],此时已基本上为“清谈”所取代。一时,崇尚老庄、畅谈玄理、文主思辨蔚然成风。
然而,道家一般是不直接提倡才智、思辨的。庄子认为:“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庄子·人间世》)甚至,《老子》、《庄子》都提出了“绝圣弃智(知)”(老庄在阐发上述言论时却不乏才智包括思辨能力)。所以,历史上首倡“思辨”的不是道家而是儒家。《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思辨”语本于此。朱熹集注称:“此诚之之目也。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為仁,利而行也。”由此可见,“学问思辨”是古代儒家的修養方法。直到清代王夫之还说:“故必极学问思辨之力……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二八》)
时至魏晋,“思辨”方法得到光大,但内容却发生了一定变化。关注“思辨”的“清谈”已不像东汉的“清议”之举极力地热议经学或徒议“治天下国家”,而是侧重于老庄学术、道家智慧了[4]277。有人认为,“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5]65应当说,“人竞唇舌”与“论著之风”并举是符合魏晋历史事实的。为此,思辨能力不仅是魏晋文人宴集雅聚时“清谈”制胜的要诀,更是吟诗作文的基本功。至于“学靡宗主”,则是针对汉末繁琐的经学宗主文坛而言。实际上,魏晋时期在发挥儒家倡导的“思辨”方法的同时,也并不是将儒学一笔抹倒,摒弃蹈弊谶纬的神学和日趋冗繁的经学而力主道家学术倒是不争事实。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成了儒道哲学精神的融通。
应当看到,“清谈”之风的盛行和“思辨”方法的光大又直接影响了魏晋文人文化空间的定位。无论是正始名士“共论于庙堂”,还是“竹林七贤”寄情于山林,他们对文化空间的选择都与“清谈”之风息息相关且耐人寻味。这种文化空间的锚定一方面对士人规避“世极乱离”政治风险有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魏晋时代的思辨风尚,推进了艺术的自觉。的确,“清谈”风行文坛之后,魏晋文章便推崇仙心妙理。从诗歌角度看,“正始体”“诗杂仙心”者众;而“竹林七贤”如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又何尝不是形超神悦呢!至于散文,像嵇康的《琴赋》、《答难养生论》等与《声无哀乐论》一样,往往情感充沛、见解独到、文理慎密,气势凌厉,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思辨性,积极呼应了时代思辨风尚,因而更为集中地体现了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
二、“师心”与嵇康的思维品质
当然,“清谈”之风和思辨风尚竞逐文坛只是为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提供了外在条件,艺术作品濡染思辨色彩、彰显思辨特征却与作者内在的主观能动性如心智能力、思维品质息息相关。只有当思辨风尚深深印刻在艺术家的心灵,借助艺术家独特的思维品质、思维方式内化为创作的动因并通过艺术化手段得以外显时,才能具体呈现为充满思辨精神的艺术作品。《晋书》称:“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可见嵇康能够接通玄理与文章。实际上,这与他的思维方式方法、思维品质不无关系。即以《声无哀乐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言之,就明显看出嵇康的思维具有反思性、独创性、深刻性等品质特征。
其实,嵇康对自己的思维品质有清醒的认识。他自我描述为:“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与山巨源绝交书》),个中蕴含着明显的反思性和稳定性思维特质。他同时谈到了不能做官的九种理由即“九患”,也是较为准确的自我剖析:惯睡懒起成习、弹琴垂钓自娱、每每破衣多虱、不善也不愿往来应酬,而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甚至“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衣食、起居、心态、心智等大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做派,自己就是类似东方朔、孔子等“穷则自得而无闷”[6]92-94之人。如此自我觉解,超凡脱俗自不待言。结合“师心独见”来看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其思维的批判性品质颖然自现。
除了自我评介,嵇康思维品质的批判性、独创性等特征还引起了他人的重视。虽然目前有关嵇康思维品质方面的讨论并不是很多,但有些论述却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如《晋书》就称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既然“学不师受”,那么“该通”之学从何而来?我们的回答只能是“师心独见”使然。在此,既能见出独立思考问题、见解介然不群是嵇康惯常的思维方式,又让我们领略到他那深得古人褒奖的反思性、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特征。
另外,嵇康思维个性品质的深刻性特征也同样很鲜明。即,他能够面对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预见其发展的进程、方向。比如,嵇康在与山巨源(山涛)的关系处理上就很能看出他思维品质的深刻性。表面上看,《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给山涛的“绝交书”,而《晋书》却载有“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嵇康是否真要与山涛“绝交”?回答是否定的。嵇康临刑洛阳东市之时,能托后事于山涛,两人契若金兰当毋庸置疑[7]。值得注意的是,事情的发展恰如嵇康所料:嵇康过世后,山涛悉心照顾其子嵇绍——“为君思之久矣”[8]203,并在嵇绍二十而冠之后,极力向朝廷举荐,终使嵇绍官至秘书丞。嵇康之知人可见一斑。
除了批判性、独创性和深刻性外,嵇康思维品质还有敏锐性、系统性等其他特征。这些思维品质特征必然会程度不等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艺术创作。比如,嵇康择以“师心”为创作路向,从生命精神本源来看待文学艺术,与孔子“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所强调的音乐发自于生命精神本身如出一辙,而大不同于腐儒一味偏执于艺术的教化功能,这当然与他思维品质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深刻性等特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实际上,嵇康不仅从孔子“穷则自得而无闷”汲取精神养分,而且对夫子那种“依于仁”又“游于艺”的人生哲学也推崇备至。他如此决绝地决裂掌控权柄的司马集团而忠诚于曹魏集团,是与老庄沉浮自如的人生态度大相径庭的。其内敛锋芒、果敢坚毅而非超然尘外、顺其自然,倒更接近于儒家之“大丈夫”精神实质。如此抉择显然是他“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声无哀乐论》)即“依于仁”的必然选择。至于“师心”——立足生命精神本源对待艺术——的现实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几近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一生,可见,孔子“游于艺”被嵇康发挥得酣畅淋漓。
三、文本释读与思辨特征
在文学史上,能够体现人类睿智和哲思的“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9]。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看《声无哀乐论》,它应当是魏晋“清谈”之风、思辨风尚等外在条件与嵇康反思性、批判性、独创性、深刻性思维品质及其基础上的思想情感等内在因素有机结合的产物,从而成为呼应时代思辨思潮的“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佳作,在当时声誉广被,甚至是清谈家必读的教科书即所谓“言家口实”[10]。
(一)“师心”——思辨的立异趋向
“师心”,即以心为师,有不拘泥于成法之意。《关尹子·五鉴》云:“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奡;善心者,师心不师圣。”此处的“师心”,犹言“独出心裁”。魏晋文人思辨过程当然不可一味地承袭旧说,标新立异方能出奇制胜。《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遙》,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议于众贤之外。”成语“标新立异”的典源即出于此。嵇康思维品质本身就有很强的反思性、独创性。《声无哀乐论》的“师心”即充分体现嵇康静观“声”的全新视角。其中立足生命精神本源来看待艺术及由此而确立的无功利的审美的态度,对音乐突破礼乐教化工具的传统观念,转变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至关重要。
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於和声,情感於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嵇康认为,“声音和比”能够“导情发滞”,以至“感人之最深者也。”“和比”指协和。《周礼·春官·筮人》云:“六曰巫比。”郑玄注:“比,谓筮与民和比也。”这里“和比”即协和之意。“声音和比”告诉我们:声音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是最能感动人的。“乐”与“歌”、“舞”、“诗”一样,主要是为了人们围聚一起歌咏,一起倾听,内心被和美的声音打动,感情受到悲苦的语言的感染。显然,音乐不是政治的附庸,而应当是抒发情感的独立艺术。这显然不同于儒家视音乐为教化工具的传统观念,思辨的立异趋向非常明显。
的确,作为酷爱音乐的哲学家、思想家,嵇康对音乐的抒情功能是有充分地体认的。他在《琴赋》中直言:“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声无哀乐论》亦云:
和心足於内,和气见於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於金石,含弘光大显於音声也。
和谐之情充盈心中,安详之气显露于外,所以用唱歌、跳舞来宣泄感情……欢乐之情体现在乐器里,包容博大(的感情)表现在音乐中。可见,《声无哀乐论》视音乐展演是一种文化行为方式,而不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政治教化工具。它应当在无功利的审美态度下加以审视,立足生命精神本源进行创造,以满足人们“畅神”的审美需要。“师心”体现出《声无哀乐论》思辨过程的立异趋向,是魏晋审美自觉时代到来以及美学思辨精神的一种反映。
(二)“独见”——思辨中的独特发现
“师心”为“独见”提供了前提。借助嵇康独创性思维品质,其独特发现主要表现为蜚声文坛的“声无哀乐”说。
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於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嵇康从天地自然中探寻“声”的来源,明显受到“清谈”所推崇的道家哲学的影响。“声”如“嗅味”,人们可以判断它好与坏,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即便是遭遇巨变,其本体依然不改常态。所以,“声”并没有哀乐之情。
联系上文,嵇康明显地把声音看作了情感的载体,只有从生命精神本源进行规律性组合,它才能抒发情感,成为音乐艺术。但是,“声”本身不具有情感属性:“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按规律组合的声音之动人,正如酒能催发人的情感。不能因为喜怒之情为酒所引发,就说酒有喜怒的本性。同理,哀乐之情是被“声”引发出来的,也不能藉此认为声音有人的情感。
这明显不同于儒家音乐观。嵇康之前,“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音声观念,“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的儒家音乐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声无哀乐”无疑是对传统音乐思想的颠覆。
然而,这一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归类于道家音乐观。“声无哀乐”之论可追溯到汉代刘向《说苑·善说》、刘安《淮南子》(“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闻哭声而笑”)等音乐方面探索,更早的还有《庄子·齐物论》的陈述。嵇康尽管十分明显地受到道家音乐思想的影响,但他对音乐艺术规律的尊重等绝非老庄音乐思想所能涵盖。同时,“声无哀乐”说也不是对儒家音声观的全盘否定。比如,“声音和比”的导情作用须适度控制:“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不可绝,故自以为致。故为可奉之礼,致可导之乐。”和美的声音引发的感情有时难以控制。古人知道不可放纵它,便抑制其泛滥;同时也明白欲望不可断绝,就制订了可以奉行的礼节,创作出可以导引感情的音乐加以引导、规范。音乐移风易俗的功能便在“声音和比”的适度掌控与清明政治的潜移默化中得以凸显。至此,嵇康所论又与儒家音乐观引为同调了。嵇康已在一定程度上融通了道家、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其“颖然独见”由此可领略一二。
(三)“锋颖”——辩难的凌厉气势
对于“锋颖精密”之“锋颖”,一般解释为“立论”。这种释义未能掘其本义、深义,也与前文的“师心独见”相左。“锋颖”更多是指“犀利的才辩”和“凌厉的气势”。如,葛洪《抱朴子·知止》有“括锋颖而如讷,韬修翰于彤管”,此处“锋颖”即为“犀利的才辩”。而在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的“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和方苞《书卢象晋传后》的“未达之士,少见锋颖,即防其异日之难驯而豫遏焉”中,“锋颖”有“卓越的才干”、“凌厉的气势”之意。细究刘勰所论“锋颖精密”之“锋颖”,明显地侧重于嵇康思维品质的敏捷性和批判性,即辩难时的“才辩”特别是“气势的凌厉”。
上文述及魏晋士林“人竞唇舌”与“论著之风”并举的史实。其中争辩机锋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很大。这在《声无哀乐论》中多有体现。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隆杀。哀乐之情必形於声音,锺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变百态,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锺子之徒各审其情矣。
针对诘难,嵇康立刻锚定了反击要点:钟子期之流能听懂不固定声音的含义。他提出,如果真如其言,那么饱足、饥饿、冤屈、悲哀、愤怒、恐惧各色人等各唱歌声,各弹琴音,钟子期这样的人就一定能听出不同对象的各自情感了。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声无哀乐论》常用此“飞钳”之技,以归谬、类比等方法直逼对手,显现出辩难时对峙的气氛、机锋相向及凌厉的气势。
实际上,正始文人即便是在官场,闲聚大多“善言虚胜”、“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世说新语·文学》);而竹林贤人雅集也是“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颜氏家训·勉学》)。重要的是,“魏晋清谭之士林”中,辩难的能手同时也多为当时文坛的高手。“文章巧傅会,智术工飞箝。”(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坐中人等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能够发挥争论时的机辩,萃取辩难时的哲思,体现交锋时的气势,从而沉淀为一种特有的思辨精神。
(四)“精密”——思辨的严谨逻辑
就论说文而言,仅有审美的态度、独到的见解和凌厉的论辩气势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关键因素“精密”——推理严密。即所谓“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文心雕龙·论说》)其作用主要在于,一方面可为“师心”、“独见”、“锋颖”提供坚实的立论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强化思辨精神。
受嵇康思维品质的严密性、系统性影响,《声无哀乐论》推理的缜密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思辨逻辑原点的确立。目前对《声无哀乐论》评说出现的歧见过多甚至相互抵牾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忽视嵇康讨论问题的逻辑起点。实际上,《声无哀乐论》中“声”的概念是有严格的规定性的。“葛庐听牛”之“牛鸣”等“自然界声音”无关乎哀乐无需多言;“晨钟暮鼓”、“掌声”等无规则却有明确意义指向的音声也便于说明“声无哀乐”;而双方辩驳焦点是乐音。在嵇康看来,琴声、歌声等乐音“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它和其它声音没什么质的区别,本身只有简单和繁复、高和低、好和坏的差别,而听者只是以急躁和宁静的情绪、集中和分散的精力与它相对应。乐音为“声”而不属于“乐”。“乐之为体,以心为主”。“乐”区别于乐音的最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饱含情感体验、能够移风易俗的文化行为方式。显然,讨论“声”的逻辑起点不能在“音”、“音声”、“和声”、“乐”等概念中随便滑移。这是嵇康论文思辨缜密逻辑谨严的重要表现。
《声无哀乐论》逻辑缜密还体现在推理的环环相扣上。全文八段,第一段是总纲,其他七段为驳论。首段分析名理:声音有善恶之听,而哀乐属于人的感情,“音声之无常”决定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所以,“声”无哀乐。以下七段分别批判了“葛庐听牛”、“羊舌闻啼”、“师旷校音”、“闻啼知凶”等传统观点包括人们对“移风易俗,莫善於乐”的曲解。行文逐层推进,步步紧逼而又映扣总论。可谓“析理绵密,亦为汉所未有。”(刘师培语〕实际上,较之于后世,《声无哀乐论》也是不可多得的推理谨严之作。只要比较《贞观政要·礼乐》(比如“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闻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即可发现嵇康思辨逻辑的缜密。以“诡辩”、“强辩”等评说《声无哀乐论》问题主要出在无视“声”的规定性和推理逻辑的严密性。
四、思辨特质到思辨精神
其实,《声无哀乐论》所体现出思辨的求异性、新锐性、严密性等特质也不是“旨在追求思辨乐趣的论辩命题”能够涵盖的。宗白华先生说过:“魏晋的思想家在清谈辩难中显示出他们活泼飞跃的析理的兴趣和思辨的精神。”[13]228显见的是,“思辨乐趣”虽与“思辨精神”有关,但如果不是由“活泼飞跃的析理的兴趣”进而提升到哲学辨析层面“思辨乐趣”就难以达到“思辨精神”的高度。《声无哀乐论》即以心境的自由、思想的解放、哲思的新锐、情感的深挚和风神的高迈等凸显了魏晋美学思辨精神。
(一)心境的自由
“魏晋之际,世极乱离”,政权纷争频仍、激烈。而文人名士往往择以“善言虚胜”、游宴山水的交往方式作为一种规避策略。《世说新语·雅量》有“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刘孝标注引南朝宋王韶之《晋安帝纪》云:“〔戴逵〕性甚快暢,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遊燕,多与高门风流者遊。”这与上文述及的魏晋士林闲聚雅集很少像东汉“清议”之徒议论时政是一致的。实际上,魏晋士人在“善言虚胜”、“尤乐遊燕”的文化空间中乐此不疲,乐亦在其中,不仅承续了曹丕《与吴质书》谈及的“南皮之游”与众人欢宴赋诗的做法[11],更重要的是,为他们争取人身自由、人格独立和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保证。
《声无哀乐论》能放言古今而“师心独见”,特别是大胆挑战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与魏晋时代特定文化空间下文人心境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密不可分。实际上,空间的选择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影响很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12]190魏晋文人在他们热衷的文化空间中,创造出自由的活动场域,找到了心灵栖息地——在这种带有自由性、想象性、无限性的文化空间中,魏晋文人的思想更加开化,精神更加解放。其根源在于,文化空间的现实性是“文化视野所及与文化行为所及以及两种所及而形成的文化记忆的积淀,构成主体的生命蕴含,亦即主体文化空间观的现实体验。”[13]359无论是清谈玄理抑或寄情山水,魏晋士林共创一种几近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文化空间,而文人生活的自由度决非之前任何时代可以比拟。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空间文人雅士既入乎于内又超乎其外。入乎于内,以身体的在场性体验生命的意义;超乎其外,以想象的自由性洞识人生的价值。所以,不仅仅是竹林七贤徜徉山水了无羁绊,正始名士也在“善言虚胜”时心态超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士人在发现了山水美、身体美的同时,也充分体悟了个性美、人情美、人格美……历史进入了“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4]208。
(二)哲思的新锐
在自由而解放的时代,魏晋士人思虑精深敏捷、出语脱俗惊人成为可能;而且,受“论著之风”的影响,又将“人竞唇舌”背景下的时空观念、生命体验、文化记忆诉诸文字。《声无哀乐论》就是“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佳作。首先,声音被看作一种客观存在,无关乎哀乐,这显然是对儒家“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否定;其次,定位了“声”的情感媒介功能——“声音和比”可以导情,进而肯定了“郑声”的“至妙”和民间音乐的作用,这与过去音乐评判标准大相径庭;再次,对“声”作了精深分析特别是界说了它与“乐”的本质区别,这在此前也闻所未闻;复次,“声”无哀乐而“乐”有哀乐,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必须在“声音和比”适度掌控中完成,这绝不是对音乐的贬抑,相反,嵇康从教化的工具地位把它提升为自律性很强的艺术,等等。《声无哀乐论》的“颖然独见”是魏晋士人哲思新锐的显例。
其实,嵇康论管、蔡便也作翻案文,且语讥周公(《管蔡论》);谈到一贯受人捧奉的“六经”,更是大胆议论“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难自然好学论》)。结合“越名教而任自然”,“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看,他的思维独创性、批判性品质,思想的新颖性、犀利性特征确实非常明显。当然,这些颇具“异端”色彩的观念和行为决非嵇康独有。魏晋文人把孔子既“依于仁”又“游于艺”的人生哲学创造性地发挥,“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即“小人之儒”——笔者注)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真意义、真道德。”[14]222在张扬道家宗法自然的同时,又开掘了儒家的赤子之诚,趋向“眼往属万物,万形来入眼不”的“论天人之际”的自由的唯美的也是哲学的空气,“澄鉴博映,哲思惟文,沦心众妙,洞志灵源。”(陆云《晋故豫章內史夏府君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晋时期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信仰自由、哲思新锐、艺术创造精神勃发的特殊历史时期。
(三)情感的深挚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魏晋时代又是一个向内心发现自我深情的时代!上文论及,嵇康言“声”无哀乐,绝不否定声音的“导情发滞”功能。《声无哀乐论》甚至提出了“声音和比”有两种途径。其一“和声”:“夫哀心藏於苦心内,遇和声而後发”;其二,“应声”:“情之应声,亦止於躁静”。前者提出情感藏于内心,遇到与之协和的声音引发便宣泄出来,而后者从“应感而发”的角度言及声音对情感的引发。可见,嵇康从来就没把情感与声音对立起来看,更不可能否定音乐的抒情作用。他临刑之际,神气不变地以“广陵”绝响告别亲友、告别生命,在如此从容、勇敢甚至美丽的诀别中,饱含着至爱琴艺的真情,显示精神力量的强大!
的确,魏晋士人思考艺术、人生,同时沉思自己的情感。他们以“何可一日无此君”(王子猷种竹)欣赏自然物,以“终当为情死”(王欧)、“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来观照生命,又“一往有情深”(桓尹)地对待日常生活,从而“在刹那的限量的生活里求极限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14]221试看“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殷皓,他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和个性之美的肯定带着无比自信;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喜,那种蔼然而玄远的自然之趣、生活与艺术融通的人生境界又是多么动人……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文心雕龙·神思》)魏晋文人的情感因为建立在新锐哲思特别是对社会生活深刻理解基础上即“心与理合”,是一种的颇具深度和力度情感。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角度看,日常生活空间“是人最现实、最具体的生存实践场域”[15]191。所以,“体现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社会性,却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逐渐成熟起来。”[16]643魏晋文人以深情的目光审视当下生活,在庸常甚至“乱离”的现实中见出诗意和神奇,实现了情感的社会性和深刻性,进而发现了生活的“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
(四)风神的高迈
魏晋时代更是风神高迈的时代。魏晋文人多“志高而文伟”(《文心雕龙·书记》)。嵇康是典型之一。他“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忧愤诗》);同时希望“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食琼枝”(《述志诗》其一)不能说不“志高”,而《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文章体现出气势的凌厉、哲思的新锐、情感的深挚又不可谓不“文伟”。因此,嵇康等人高蹈出世的生活追求决不会通过手执麈尾这种“伟质软蔚,岑条疏理。体随手运,散飚清起”(许询:《墨麈尾铭》,《全晋文》卷一三五)的方式方法体现,相反,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溢于言表的高迈风神。
其实,不止是手执“麈尾”这种名流雅器之人未必是真名士,连“扪虱而谈”的做派也只是极少数人放达自任的一种表现,不可视为“魏晋风度”的标识。我们姑且不谈滥觞于汉末、上溯至孔子而为魏晋文人发挥到极致的人格美如“人物的品藻”(对时代风神之高迈的影响当然很大——笔者注)等等,仅就“人竞唇舌”背景下“论著之风”而言,英气逼人自不待言。一方面,舌战如用兵。《世说新语·言语》载:“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可见当时已有一整套诸如“坚守城垒”、“汤池铁城”等清谈策略。另一方面,作文多机锋相向。王弼与何晏曾争论“圣人无喜怒哀乐”;嵇康同向秀也争辩过“养生”;夏侯玄《辨乐论》明显与阮籍《乐论》针锋相对……所以,绵软之气难以遮掩魏晋时期文章的凌厉气势和时代的高迈风神。实际上,魏晋文人崇尚老庄、宗法自然并不是排斥和否定孔子等真儒所为,上文提到孔子“依于仁”而“游于艺”的人生哲学对嵇康等魏晋文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就是明证。仔细揣味嵇康傲兀的气质、傲岸的个性和艺术化的人生决不仅仅是道家人生态度所能涵盖,而更像封建社会儒家之“大丈夫”所为。这或许是他“远迈不群”以及魏晋时代的风神高迈的一种体现。
五、结 语
西学求真,国学向善。从东西方文化差异来看《声无哀乐论》的凌厉的辩难气势、严密的思辨理路和超迈的思辨风神及由此而凸显的魏晋美学的思辨精神,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在中国哲学、美学发展史上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这是其一。其二,魏晋美学思辨精神除了心境的自由、思想的解放、哲思的新锐、情感的深挚和风神的高迈外,还包括有脱俗的道德精神、绝俗艺术追求等等,考虑到后几个方面已多有论述,不再赘言。其三,嵇康的儒、道思想融通问题有必要再次提及。在玄学兴盛的魏晋时代,嵇康受到道家思想文化更多的浸润、滋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决不可因此漠视他思想中的儒学成分。不然,我们就难以正确释读他的“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声无哀乐论》);对他在《家诫》中告诫子女稳妥处世、守志为要等观念也不能全面认识;更不能充分理解他弹响“广陵散”慷慨赴死的伟丈夫气概。就《声无哀乐论》而言,尽管我们通常不会以儒家音乐思想予以定性——嵇康显然不是断然否定所有的儒家音乐思想如音乐的移风易俗功能等。但是,简单地言之为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似乎也是对它“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的曲解。我们认为,《声无哀乐论》包含着嵇康在音乐艺术实践上的丰富体悟,又明显受到魏晋“清谈”之风和时代思辨风尚的深刻影响,同时融合了他对儒家、道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深度反思,从而沉淀为一种儒道互补的、独特而深邃的音乐美学思想。因此,一味夸大道家文化的影响而无视《声无哀乐论》中的儒学成分明显不切合实际。结合上文分析可见,老庄沉浮自如的人生,并不为嵇康所奉行。他本来就是魏晋政权交替时决裂司马氏政治集团而忠诚于曹魏集团之“名士”群体中的典范。他兀傲不屈的人格,与其说有道家风范,毋宁更接近于儒家之“大丈夫”所为。他的死是历史长剑沥下的“路人皆知”的滴血。而遗憾的是,“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沒有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哀哉!那思想解放、哲思新锐、情感深挚和风神高迈的美学思辨精神已随着他的离去而渐次消逝消弭。呜呼,“广陵”绝而魏晋之风流散!
[1]归青.如何认识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性质[J].社会科学,2011,(3).
[2]孙杰.解析《声无哀乐论》中的强辩[J].作家,2008,(20).
[3]王妍.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M]∥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M].上海:中华书局1962.
[6]赵立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7]包秀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论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8]余嘉熙.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10]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J].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1993,(8).
[11]曹瑞锋.才情隐显与政治对话——曹丕曹植同题赋同题史论比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2]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J].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
[13]高楠.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14]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M]∥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5]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阀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6]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