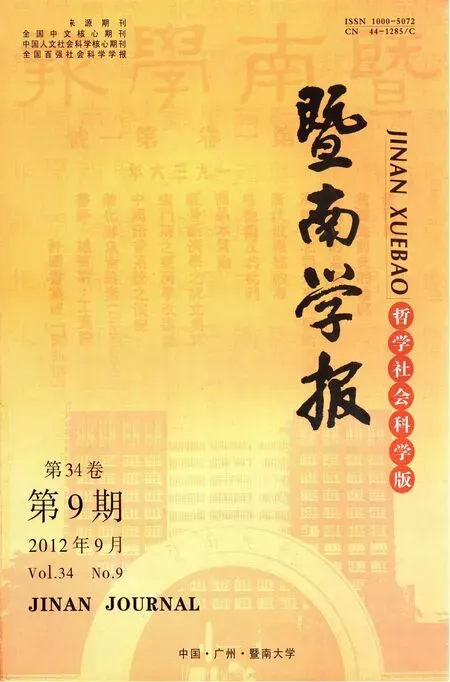宇宙与诗学:宇文所安“非虚构传统”的形上解读
沈一帆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85年出版的《传统中国的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an Omen of the World),也许是20世纪最后30年,北美汉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引起极大争议的为数不多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的话题性,不仅在于适逢其时地响应了西方人文研究的“理论转向”,标示着西方汉学考证、译注、赏析的语文学方法让位于新兴人文社科批评理论的范式更新;更重要的是,全书还尝试在几个彼此关联的命题中,建构解释中国文学模式的涵盖性诗学——“非虚构传统”。
按照宇文所安的设想,“非虚构”需要放置于一个有关中国宇宙运行模式的叙述框架中理解,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不过是这个巨大宇宙层级结构中的一环,二者则构成一种诗学与宇宙模式的对应关系。正是这一解释框架,使得“非虚构诗学”与包括“汉代宇宙论”及“汉代哲学思维”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汉学论述产生了深刻的内在关联,从而回应了自晚明传教士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中西“形上”领域的差异比较。正如刘若愚在其《中国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将宇宙论模式在文学中的显现命名为“形上理论”,那么“在‘形上’的标题下,可以包括以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示这种概念为基础的各种理论。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中,这些理论并非最有影响力或最古老的,可是我选择这些理论来开始讨论,且将给予最大的篇幅,是因为:第一,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于我所谓的艺术过程的第一阶段;第二,这些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1]20。
一
何谓非虚构传统?在《传统中国的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中宇文所安把中国诗歌显著的经验性、字面性和历史性命名为“非虚构”(nonfiction),具体来说,就是把中国诗歌视为一种历史时间内诗人真实经验的“透明”(字面意义的而非隐喻性的)显现,由此以突显其与西方“想象性”、“隐喻性”和“创造性”的“虚构”诗歌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作为现代美学与文学理论中一个牵涉“艺术真实”问题的核心范畴,“虚构”(fiction)是现代艺术自律的规定性价值之一。然而,就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而言,很少有学者采纳“虚构”这一与审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后出词汇,而倾向于从希腊传统的“模仿”观念中寻找根源。相较而言,宇文所安从“虚构”切入的比较分析,一方面全然继承了“模仿”所表征的西方二元性等级制的形而上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刻意突显拉丁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所加诸其上的思想内涵,从而构成了宇文所安以“创造”理解“虚构”的基本立场。
在《传统中国的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一书的第三章《非创造的宇宙》中,宇文所安分别以文艺复兴后期批评家锡德尼爵士《为诗一辩》中所宣扬的诗之制作(making)与中国儒家诗论之开端《诗大序》中所定义的诗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内在经验(interior history promised by shih poet)为基础,建构了他自己的中西比较框架。在西方文艺批评史上,锡德尼的《为诗一辩》一向被认为存在某种语义张力和过渡性特征:锡德尼一方面仍然坚持诗歌的模仿性,“诗,因此是一种摹仿艺术,正如亚里斯多德用‘迈米悉斯’一字所称它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形象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意识到虽然世上一切技艺的本质都在于摹仿自然,然而却只有诗歌在模仿自然时创造了另一个自然,“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而是为自己创新的气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中,如那些英雄、半神、独眼巨人、怪兽、复仇神等等,实际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所以他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局限于她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中,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中游行……(自然)她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Her world is brazen,the poets only deliver a golden)”[3]231。虽然锡德尼的时代,还无法为他所宣称的诗创造“第二自然”的特殊模仿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应概念,但其诗论中突显的“创造”观念却预示着西方美学从模仿走向虚构的历史走向。
然而,要厘清“虚构”一词的多层语义,还必须牵涉到“模仿”(mimesis)一词在“希腊语的拉丁化”过程中,衍伸出的“摹仿”(imitation)、“表现”(expression)及“创造”(creation)三个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概念范畴。
根据彭锋的研究[4],作为希腊语的“模仿(mimesis)”具有极其复杂的用法,这些用法的共同之处在于“符合或相等,即模仿的作品、行为或表演与被模仿的东西之间的符合”[4]50,正是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通过划分不同的艺术手段、所模仿活动的不同类型以及模仿的不同方式,首先把诗(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继而又根据模仿对象的不同划分出史诗、悲剧和抒情诗。随着希腊语“mimesis”拉丁化为“imitation”,模仿也被缩小为再现事物外在形象的“摹仿”(imitation),这种用法在16-18世纪的古典主义文论中尤为兴盛,表现为对文学模拟生活之内在机制的讨论。然而,人类审美领域的扩张使得“艺术如何再现人的内在经验”这一问题突显出来,希腊语mimesis一词中一度被遗忘了的“将不可见的变成可见”这层含义,经由“表现”(expression)一词获得了重生。因而,如果说“摹仿”(imitation)是对可直观把握的事物的模仿(mimesis),那么“表现”(expression)则是对不可直观把握的美感经验的模仿(mimesis)。
相比“摹仿”和“表现”与希腊传统的密切关联,西方美学中的“创造”(creation)则来自希伯来传统、根源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观。因而,艺术创造是一种历史现象,直到宗教权威开始衰落的17世纪,“创造的能力”才从严格的宗教意义中解放出来。在经过了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后,“创造”(creation)摇身一变取代了“摹仿”(imitation)成为了现代艺术的核心,而“虚构”(fiction)也代替了“模仿”(mimesis)成为艺术本质的定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及其哲学(美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①对于“创造”的另一种常见解释是在“所有权”和“标新立异”的层面上展开的。在这种观点中,“创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后果,艺术对“独创性”的渴求则是在它赖以为生的市场机制中培养出来,随后则演变为其反抗商业性的基本依据。此种观点的经典研究是美国学者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
在西方思想中,关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创造性”(creativity)的东西的真正转折点发生在18世纪。……“创造的”(creative)这个词语第一次不仅应用于上帝,而且应用于人类艺术家。……在19世纪,这种态度变得普遍起来,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这个很难相信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世界的时代,却显然不难相信人类艺术家从虚无中创造出它的作品[5]68。
随着“创造的能力”在上帝和艺术家之间完成交接,诗人(poet)也被赋予了全新的身份——天才(gift),如果把康德对这一概念的晦涩解释简单呈现,那么“天才”就是给艺术立法的才能②具体来说,康德认为艺术活动与科学认知的最大区别在于“科学活动是人替自然立法;而艺术活动则是自然为艺术立法”,因而可以说“自然通过天才的创造活动来实现合目的性”,因此,“天才”是“自然天赋”的,由此完成的艺术品完全是以人工制品为对立面的,因为艺术品是人的自然部分起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人工的结果。。这意味着艺术活动不再只是制作(making),而又是灵感赋予的创造(create)和想象(image)。
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上帝的创造即是其“无中生有”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这一特性几乎涵盖了“创造”观念的全部内涵,当把艺术活动定义为“创造”活动时,也就承认了艺术家对其作品的绝对权威以及这一创作模式的“无中生有”性。因而,以“创造”观念为基础的现代艺术“虚构”论,集中地代表了上帝创世的宇宙生成论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及对传统“模仿”理论的补益。
其实,从希腊语的拉丁化角度重新解释“模仿”的多层含义,以及“摹仿”、“表现”和“创造”的微妙差异,很有可能源自德国罗曼语文学学者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名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Latin Middle Age)。库尔提乌斯在该书中的论辩对手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把希腊作为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唯一思想本源,并把始自罗马以来的整个拉丁中世纪看作西方思想的自我偏离。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指出:“从希腊语到罗曼语的翻译进程不是偶然的和无害的,而是希腊哲学的原始本质被隔断被异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这一罗曼语的翻译后来在基督教中和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成为权威性的。近代哲学从中世纪过渡而来,近代哲学在中世纪的概念世界中运行,并从而创造了那些仍在流行的观念和概念词汇,而今天人们依然通过这些观念和概念来讲解西方哲学的开端[6]15。”对此,库尔提乌斯则认为,希腊传统与拉丁中世纪并非断裂的存在,而是欧洲文化的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只有取径罗马才能上溯希腊。在该书中,库尔提乌斯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圣经》所代表的拉丁传统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从希腊语的拉丁化过程讨论语言和观念之间的演变及继承,其中就专有一节《模仿与创造》,讨论两个寄生于不同传统的观念的演变和微妙差异。宇文所安对库尔提乌斯的观点肯定不陌生,根据刘皓明在《读书》2004年4月号和9月号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从好言到好智》以及《从夕国到旦方——纪念傅汉思教授》,宇文所安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傅汉思的学术渊源,正来自德国古典语文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塑造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基本学术方法,更产生了一批经典的文学研究著作,其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曾在耶鲁执教、名噪一时的《论模仿》的作者奥尔巴赫外,就数《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库尔提乌斯。更有研究者指出,宇文所安的中唐文学研究与日本京都学派存在重要学术渊源关系[7],而当代京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川合康三在《诗创造世界吗?——中唐诗与造物》一文中提出的中唐“创造”观念,就与宇文所安的相关论述高度一致,而川合康三所使用的“创造”,正源自库尔提乌斯的观点。
二
与大多数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现代哲学家一样,宇文所安在讨论“宇宙本体论”问题时,还试图将其转化为一个“语言认识论”问题,也即通过语言来认识和定义不同传统关于“自然”、“世界”或“宇宙”之生成及组织原则的基本假定。
对此,宇文所安认为存在两种“语言与自然的关系”。其一,“自然在语言之外”(naturebeyond-language),即认为语言是认识自然的障碍,在宇文所安看来,道家语言观是中国文化传统中“自然在语言之外”的代表,它与现代语言学实属同类,视“语言是一种讲述意识和知识的自治系统”[2]79-80,自治的语言拒绝把词与词的差异视为外在世界自然分类的对应物,正如索绪尔所言,语言不过是符号间的关系和差异构成的集合体,它并不依据外在世界的现实差异来归类。其二,“自然在语言之中”(naturein-language),即认为语言与外在自然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事实联系,在这一关系中,人们相信“自然可以通过语言而被认识,语言所制造的差别,正是那个可感的自然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差别”[2]81。这种语言观的问题在于,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和历史性,举例来说,中文和英文在色彩划分上存在的差异,如果按照索绪尔的看法,只不过是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造成的,两种语言传统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能指(读音、文字)来对应同一个所指,区别只在符号,而不牵涉到概念和现实对应物的差别。然而,如果认为语言与现实一一对应,那么,中文与英文在色彩词汇上的差异,就不仅只是语言分类的差异,而是现实分类本身的差异。因此,语词的差别就不仅是语言自身的差别,而是不同文化传统反映世界秩序的思维模式的差异,换句话说,所指的(signifier)差异可以透过与其对应的作为能指(signified)的语言符号来认识。
在此基础上,宇文所安将其比较的中西语言传统纳入上述第二种语言观——“自然在语言中”,“根据这一假定,词与物之间有一条自然的纽带,一组存在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现成对应关系”[8]105。
在西方语言中,一个符号对应的意义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一类事物的原型——“本质”或“属性”。比如,“牛”作为一个类别概念,并不指现实中个别、具体的牛,而是指抽象的“体大有两角的哺乳动物”。同时,“牛”的属性则依赖于更高一级的类属概念“动物”——“自身无法合成有机物,须以动植物或微生物为营养,以进行或维持生命活动的生物”,并通过这一属性与马、羊、猪、狗、鸡等其他概念建立联系,组成新的序列。因此,定义一物,就是将其置于一个分类系统,从而在自然的秩序中确定自己的归属。这正是西方“类”(category)的思维,可称之为“逻辑的类”,它是纵向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一种“从属”关系。
而在中国语言中,“各种概念不是相互之间进行归类,而是并列在一种模式之中。而且,事物的相互影响不是由于机械原因的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ance)”[9]304。由于在传统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中,关于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并不多见,而关注的中心往往来自基于经验推导的类比的分类。因而,一个符号的意义则是“关联性”的,“不诉诸于一个共同分有的本质或是‘自然的种类’,而是借助于独特的个别者之间所持有的功能的相似性或关系”[10]253。仍以“牛”为例,在中国的分类体系中,作为动物的“牛”却能与地、母、腹、温顺这些看似毫无逻辑联系的词整合为一个序列,是因为中国人从具体的感性经验出发,从中推导出某种共通的结构或功能的对应。这就是中国式的“类”(lei),可称为“自然的分类”(natural category)。这种“关联性”的“类”建立在“直觉”和“联想”的基础上,表现为一种横向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种“类比”、“并列”的关系。
“自然的类”与“逻辑的类”显示出中国与西方在归类和整理知识时所依据的不同秩序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因而在现代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注意。符号学家卡西尔(EnstCassirer)将其纳入“神话思维”,认为中国人通过感应和类比将颜色、季节、人体器官、心理情绪等自然及人事的诸种层面编织为“一个宏大的整体、一种根本性的、神话式的世界轮廓图”[11]99。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则将其视为一种符合神话“互渗律”的具象性“原始思维”。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更借用雅各布森对隐喻和转喻的区分,以“野性思维”的名义系统地讨论了关联性思维的生成机制和类推模式。
有趣的是,上述理论都曾受惠于西方汉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比较命题——中国的“协调的思维”(coordinative thinking)或曰“联想的思维”(associative thinking)与西方的“从属的思维”(subordinative thinking)。关于中国“关联性思维模式”的解释,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汉学界已形成以葛兰言(Marcel Granet)为起点,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为代表,包括卫德明(H.Wilhelm)、艾伯华(Eberhard)、雅布翁斯基(Jablonski)、亨德森(John B.Enderson)、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等汉学家共同争论的重要汉学命题。他们将汉代哲学的宇宙哲学视为中国人关联性思维普遍化和系统化的核心阶段,由于“汉代的思辨导致创造了纷繁复杂的对应表,它规整了人类经验之心理的、生理的、社会的、以及‘自然的’环境。这种分类包括肢体、心理-生理,以及情感状态、政风、气候、趣味、家畜、技术工具、天体等等……。阴阳两种力量被用来与这些对应项目共同组织并且表现系统内部各种成分的转化以及相互关系”[10]258,由此形成了将自然宇宙、帝国制度、伦理善恶、个体经验、器官病理、季节方位等万事万物对应和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关联性图式。由于这一图式建立在类比的分类和经验的推导之上,其所呈现出的关联性体系在习惯了逻辑分类和从属思维的西方人看来,总会引起荒诞、混乱和偶然的联想。
这一中国特殊的“类”,在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所引发的最为重要的学术事件,源自福柯《词与物》一书开头所引用的一段话:
这本书首先起因于博尔赫斯的一段话,起因于我在读这段话时发出的笑声,它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那带着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地理环境印记的思想中所有熟悉的里程碑都砸得粉碎,它不仅把我们已经习惯的、用以将杂乱无章的现存事物归置得井然有序的所有运思层面都砸碎了,而且还将长久地继续下去,使得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关于同类和他者的区分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一段话援引了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其中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于皇帝的,2.涂了油的,3.驯良的,4.未断奶的猪仔,5.人鱼,6.神话寓言中的,7.丧家狗,8.包括在现行分类之内,9.疯狂的,10.无法记数的,11.用一支很细的驼毛笔画出来的,12.等等,13.刚刚砸破了水桶的,14.远看像苍蝇似的。①Michel Foucault,The Oder of Thing:An Archaelolgy of Human Scienc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ⅩⅤ。此段为盛宁以英译本为基础的译文。见盛宁:《“认同”还是虚构?——结构、解构的中国梦再剖析》,载《中国学术》,总第7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2页。
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正是这段荒唐、怪异且可笑的中国分类法,威胁到他对人类知识分类系统的固有看法。如果在西方传统以理性力量赋予和把握的世界秩序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有序”状态,且这种“有序”,是把完全不同且互不相干的事物摆放到一起,那么西方的分类模式就可能只是一种后天的建构,这意味着在现行知识分类系统之外,完全可能存在其他的知识分类。
福柯的这段引述来自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约翰·威金斯的分析语言》(The Analytical Language of John Wilkins)。按博尔赫斯的说法,它转引自德国汉学家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所收藏的一部标题为《中国百科全书》的著作中所收录的条目。作为西方世界鼎鼎大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库恩曾于1909-1912前往中国担任翻译官,并在此后的四十年中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典作品。然而在库恩庞大的翻译作品目录中,人们无法找到博尔赫斯所说的那部中国百科全书,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该段文字源自博尔赫斯一贯的虚构和想象。不得不承认,博尔赫斯的杜撰过于荒谬,然而如果关注到库恩的汉学身份、如果考虑到他所引用的这段文字背后所牵涉到的强大的汉学话语,如果结合包括宇文所安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汉学家对中国“联想的类”的解释,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看似极其荒谬的排列可能的确反映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维模式的独特预想,就此而言,福柯的思想契机也许并未与真正的中国相关,而是来自西方汉学家所发明的那个中国。
三
具体而言,西方逻辑的“类”最集中地体现在其语言的“隐喻性”中,中国联想的“类”则通过其语言鲜明的“举喻性”(常译作借代)表现出来。中西语言所体现出的这一意义生成模式(“类”)的差别,其实已揭示出中西宇宙论、特别是宇宙生成论所指向的思维模式和运转机制的差异:
这里(中国)的“类”和西方所谓的“喻”,都是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的。然而,“喻”是虚构的,包括真正的替代者;而“类”则是联想,一种以世界之秩序为基础的绝对真实[12]222。
西方“隐喻的类”指向事物“本质”的区别,这也意味着在具体的个别事物背后,就还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原型,这一设想最早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初具完备的形态,宇文所安则把更重要的模式视为源自上帝的“创造的宇宙”,在其中,任何物种和实体都源自上帝设定的那个最初模型,并从中寻找最初的意义源头:
上帝创造了天与地、光与苍穹、鱼和兽以及每一种依照其类属(kind)而造的生物,因而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说明就属于上帝且仅仅只属于上帝(were His and His alone)。当这些活的物种繁衍后代(go forth and multiple)时,它们只能复制那最初给定的模型。大洪水可以减少人口,但只要每个物种和性别都有一个活物得以幸免,那么原初的模型就能安然无恙。天之所以是天,因为它是以此(that way)被创造的,而地的本性也蕴藏在最初的设计当中。人之为人并非在于它与走兽的区别,而是由于它来自一个神性的模型(model)[2]82。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上帝创世的神话随同宗教的意识形态一道淡出了历史的前台,“关注的中心从原初的创造者的模型转向了自然的固有模型……取代了‘已经被塑造’(have been shaped)的观念,人类发现自己‘正在被塑造’(being shaped)。……人类逐渐认识到他可以塑造自身以通向某个即刻的或最终的目标。然而,在这些巨大变化的背后还有某种更大的一致: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的定义都源自某种给定的模型,它要么是神性的,要么是进化论的,甚或仅仅只是人类自己的意志”[2]82-83。因而,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从上帝那里继承的“创造能力”,不仅使作者的身份带上了神性的光辉——“他们所拥有的是开始、打断、结束自己作品的权利,而他们所创造的‘小物种’则严格按照那种伪装在自由意志之下的教导而运转”[2]84,更重要的是,当作品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被创造的世界”时,它也同时继承了上帝所创造的那种二元性的世界结构,“那种存在于先验的和被隐藏的设定中的模型,赋予了诗人这一‘小造物主’编织虚构和隐喻的权利”[2]84。
与此相对,中国语言中“自然的类”则对应了全然不同的宇宙构想,正如宇文所安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所找到的原型,中国自然秩序的创生没有一个外在的、高高在上的本原,而是世界本身的过程、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自发地分化为相生相对的两极——阴与阳,并将这一模式类推地运用到其他具体情境和细分类别中,进而将万物纳入一个不断二分和延伸的意义网络: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濁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13]165-167。
这一中国宇宙论思想集中体现在“汉代关联宇宙论”的相关思辨中,宇文所安将之称为“非创造的宇宙”(uncreated universe),而在西方汉学界,这一模式则与“汉代哲学思维”相互印证,被视为一种连类、共感、连绵的“有机宇宙”(organism)。李约瑟认为中国有机宇宙模式的关键,就在于创造了一种循环往复(最显著的就是“四时模式”)的“感应”网络和运转“秩序”,万物不是由机械的因果关系掌控而是出于一种相互感应的“同情的共鸣”之中。
“同类相感”构成了“有机宇宙”关联模式的发生机制。所谓“同类相感”,即指同一类别(中国“自然之类”)事物间,发生的一种相互影响和回应的“感应”现象。比如同一音域的两根琴弦间会发生共鸣,就是一种自然感应现象。汉代思想家则在融合“气论”的基础上,将这种自然的感应,提升为一种“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普遍宇宙原则。而“阴阳五行、四时四方”的平衡体系,则构成了宇宙运转的“秩序”和“模式”,一种以相关和相对为基础并成对出现的图式。
因而在中国的有机宇宙模式中,宇宙的秩序、道德的秩序、社会的秩序以至文学的秩序,因内在的共通“模式”(图式),而在“感应”中彼此沟通:
由于潜在的模式通过事物固有的排列获得显现,从世界到心灵、再到文学的序列,则以一种“同情的共鸣”贯通其间[2]21。
四
如果一个非创造的宇宙可以被认为是“有机”的,那么,作为“类”的“关联机制”的“同情的共鸣”(sympathetic resonance)和“感应”(inductance)就为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同构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在宇文所安看来,有机宇宙的关联模式的确在中国文学中投下了它的影子,并至少在以下三个领域推进了中国文学“非虚构模式”的生成:
首先,产生了中国文学中极具特色的“物色”(或感物、感类、体物)理论。从汉代的“气类感应”到刘勰的“诗人感物,连类不穷”,在一个以“类”为基础而不断延伸的联想序列中,自然宇宙之秩序和运转的规律得以显现:正是基于这种自然联想的类,包括世界万物与人事代谢在内的整个宇宙被视为一个彼此关联、循环往复的运转系统,而文学的发生也因此被解释为诗人与自然之间基于“类”的相互触发。
其次,形成了中国文字的独特构型——“自然之文”。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字或文学并不是摹仿自然的一种发明,因为“文”本身就是自然或宇宙的一部分,是这个相互关联的宇宙中的一环。因此,不仅中国文字是一种“自然文字”,而且用这种文字书写的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自然宇宙的秩序和模式。因此,中国的文学是非虚构的。
最后,有机宇宙及其关联模式,还反映在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学体类——律诗——的形式结构上。宇文氏认为,不仅“对偶”的联句呈现了中国人以“阴阳”为核心的“宇宙秩序”;而且,唐诗的四联对句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三部式”结构,这一结构完美地呈现出诗人是如何与自然进入一种相互感应的状态,并最终在众多伟大诗人的实践中创造出律诗特有的“情景结构”。
五
其实,宇文所安的“非虚构传统”论述,一直是西方汉学界重要论争中的常客,并经常被纳入有关汉学诠释模式的反思性话语,它要求考察的对象从细部的新颖结论转向有关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判断和假定,并试图在那些被汉学家解释为主导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论前提和假设中,窥探和反省汉学的论述逻辑。在此框架内,宇文所安对中国诗歌“非虚构传统”的定名与表述,常被指认为西方汉学想象和诠释中国的一个典型的诗学发明,并在包括余宝琳(Pauline Yu)、浦安迪(Andrew H.Plark)、于连(Francois Jullien)、奚密(Michelle Yeh)、牟复礼(Frederick W.Mote)、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等重要汉学家的相似结论支持下,构成了当代汉学论述中有关中国文学传统最为稳固的理论预设。
按照苏源熙(Haun Saussy)在《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中的看法,对中国文学的“非虚构”界定,其实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诗学,其研究的目标是寻找和论证中西文化及文学的“根本差异性”,因而研究者“通常给出的解释仅仅是重新命名差异性,或挑出一种差异作为普遍差异的成因:例如,先验的神学(余宝林、宇文所安及浦安迪所认为的西方诗学模式),‘抽象的或精神的对象’……一种阐述哲学问题的‘一与多’的范式,动词‘to be’,俄狄浦斯情结,或者诗歌隐喻”[14]42,而这些解释则往往追溯到中西哲学范式的差异,试图在文化本体论层面获得理论支持。而宇文所安的“非虚构”论述其实建立在一种古老的中西差异论的基础上,即认为西方的文学思想,自模仿论以来就树立了二元性的本体论结构,由此创造出一个文学的二元性等级世界,而代表这种二元等级结构的隐喻模式,则被认为是文本解读的首要原则;与此相反,汉学家往往认为中国文学传统秉承一元的宇宙观,它所强调的是此在的经验,而非超验的真实,因此重视文本的字面意义和具体情境就是理解文本的首要目标。对此,苏源熙指出,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得出关于中国文学的“非虚构”解释,就变得十分自然,“它使得在别的方面观点都相异的批评家,如宇文所安、浦安迪及余宝琳对中国文学世界的结构几乎持相同的见解”[14]27。
因此,要理解宇文所安诗学建构的实际贡献,还必须在西方汉学论述的历史参照中给予解答。在苏源熙看来,这一相对主义的观察视角最终可以上溯至传教士汉学,而诸如“非虚构”一类的诗学发明,不过是这一传统中一个老问题的新版本。
[1](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Stephen Owen.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an Omen of the World[M].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3](英)锡德尼.为诗一辩[C]∥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彭峰.西方美学与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Paul O.Kristeller.“Creativity”and“Tradition”[C]∥Peter Kivy ed..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New York: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1992.
[6](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陈小亮.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与诗学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8](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M].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0](美)赫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M].施忠连,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11](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黄龙保,周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2](美)宇文所安.透明度:解读唐代抒情诗[C]∥(美)倪士豪,编.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3]何宁.淮南子集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美)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M].卞东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