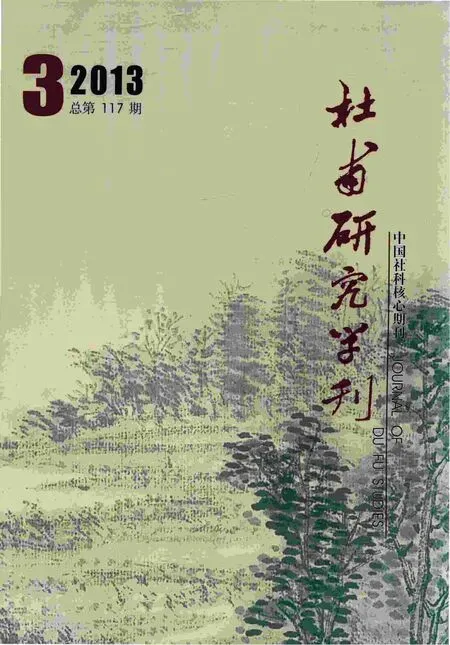浅析《诗人玉屑》中的杜律诗评
潘 玥
作者:潘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研究学刊》编辑,610072。
魏庆之(1196——1273年)的《诗人玉屑》共二十卷,全书按照诗歌技法进行分类,采用诗格的形式,通过直录、节录、合录、分录、倒录等五种方式编纂而成。关于此书的评价,魏氏友人黄昇在作于淳祐甲辰(1244年)的《原序》中谈到:“自有诗话以来,至于近世之评论,博观约取,科别其条,凡升高自下之方,繇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载”,同时“又取三百篇、骚、选而下,及宋朝诸公之诗,名胜之所品题,有补于诗道者,尽择其精而录之。”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宋人喜为诗话,搜集成编者至多,传于今者,惟阮阅《诗话总龟》、蔡正孙《诗林广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及庆之是编卷帙为富。然《总龟》芜杂,《广记》挂漏,均不及胡、魏两家之书。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这些评论说明了《诗人玉屑》无论从评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对各代诗人的归纳,以及在内容的广度、深度上都是继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之后的宋代诗话又一力作,并且为我们保留了许多两宋诸家论诗的宝贵历史资料。
一、《诗人玉屑》的编纂背景
魏庆之之前,已有《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各有特色的诗话汇编,《诗人玉屑》的编纂自然会受到启发和影响。但《诗话总龟》指归在依事存诗,《苕溪渔隐丛话》立意在诗话汇辑,而《诗人玉屑》的重心在诗法诗评。“诗的体格包括诗的体制和作诗的风格两方面内容。既可以用来指具体的诗歌体裁、格式方面的分类,也可以用来论说其风格特点。”在宋代诗话里,这是学界重点探讨的问题。正如黄昇在《原序》中谈到的;“其格律之明,可准而式;其鉴裁之公,可研而核;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说明包括《诗人玉屑》在内的许多诗话,其主要目的就是指导诗歌初学者掌握诗歌规律,学习如何写诗,以便参加科举考试。
《诗人玉屑》主要以《苕溪渔隐丛话》为底本,多数条目都是转抄自《苕溪渔隐丛话》,此类条目大约占全书数量的十之七八。另外,许多条目下方有用小字注明的出处,包括各类史传、笔记、杂录、序跋、诗格、诗话等多种文献,注明的引书达140余种。同时,《诗人玉屑》几乎全收严羽《沧浪诗话》,尽管二书作者互有交往,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魏庆之完全赞同严羽观点。魏庆之生活在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理论创作对魏氏有较大影响。有学者亦将魏氏归为江湖诗人。作为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其实魏氏在《诗人玉屑》中对江西诗法亦是推重的,书中就涉及了许多江西诗风的理论特点。这也可能主要是源于江西诗派诗歌的有法可依、便于初学的缘故。同时,魏庆之对杨万里的诗学观也较为推崇,多有引用。全书抄录和摘取了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披沙简金、去粗取精、排比成卷。可以说,《诗人玉屑》综合了多家之精华。同时,《诗人玉屑》中,魏庆之给每条诗话都加上标题,概括自己对所摘诗话的理解,给人提纲挈领、一目了然之感。这在宋代诗话中是少见的做法。可见,魏氏的辑录,并非一味抄袭,而是融入了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渗透了他对诗的体裁、韵律及发展历史的看法。正如黄昇《原序》所云:“取宝囊玉屑之饭,瀹之以冰瓯雪盌,荐之以菊英兰露,吾知其换骨而仙也必矣。”
关于杜诗,黄昇在《诗人玉屑》的《原序》引述姜夔之语“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后,指出诗法正是走近李杜圣境的阶梯:“人非李杜,安能径诣圣处!”律诗是唐代的新型诗体。杜甫以其精湛的艺术修养和才能,为律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诗人玉屑》论述甚多。下面,就将书中有关杜甫律诗的内容归纳总结,以窥宋人对杜律的接受情况。
二、《诗人玉屑》的杜律诗评
《诗人玉屑》对李杜诗歌是非常重视的。魏庆之专门用一卷分为“谪仙”、“李杜”、“草堂”来专述二人。这与《苕溪渔隐丛话》类似,后者用九卷及后集中的四卷篇幅论杜少陵。魏氏大致将诗歌分为“古诗”、“律诗”、“绝句”三大部分,对于律诗这种诗体,卷十二专门提到,另外其他的律诗讨论散见于书中,说明律诗这种诗歌体裁在宋代的发扬光大。魏庆之在卷一《沧浪诗法》中对这三种诗体给与了难易的区分:“律诗难于古诗,绝句难于八句,七言律诗难于五言律诗,五言绝句难于七言绝句。”魏氏对严羽的说法是赞同的,认为律诗因有规矩创制方面的约束,故需要诗人刻苦学习,掌握技巧,才能成功。有关律诗的总结,魏庆之吸取了其他诗话的观点,同时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杜甫律诗是宋代律诗的学习标准之一。马茂元先生曾在《思飘云外物 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中谈到:“唐代的七言律诗,到了杜甫,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对杜甫来说,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时期。盛唐诸家七律以兴趣情韵见长,但到杜甫手中,模写物象,抒发性情,‘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一变而为巨刃磨天,金鳷擘海的壮观。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三者融合无间,构成了杜甫七言律诗独特风格的基本特征。”可谓“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吕本中《夏均父集序》)。杜律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用律诗写时事,同时也重视炼字炼句,故刘熙载称其为“少陵炼神”。特别是七律,有开创之功。《诗人玉屑》卷十二《律诗》中共四条评论,第一条谈到王安石的律诗讲究声律、注重平仄,黄庭坚亦称“诗须皆可絃歌”。魏氏首先强调律诗创作要有严格的声韵要求,这也是不同于其他诗体的第一步。接下两条先引白居易《金针诗格》中对律诗各联诗意的严格要求,后引杨万里“非”《金针》之语,认为“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再引杜诗《九日蓝田崔氏庄》和《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强调意在言外,回味无穷。可视为诚斋体“活法”对《金针诗格》之议论的改进。第四条评七律,谈到杜甫七言“典雅重大”,开拓了七律的内容,可“褒颂功德”。这四条为魏氏对宋律诗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律诗一是要讲格律,二要讲意韵风格。亦可见魏氏对杜律的推崇和宋人对盛唐、晚唐诗人的不同态度。
1.杜律代表——夔州诗
杜甫夔州诗是杜甫律诗的代表,其中《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等,使七律诗体成熟并臻于至善。杜甫自己也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讲究声律的精心安排,也讲究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杜甫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特别是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是律诗较为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元祐时期是北宋诗学的兴盛期,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学,提倡“以学问为诗”,讲求自然之理与人生哲理融为一体的“理趣”。同时学习韩愈文,陶潜、杜甫诗,有意追求杜甫的浑成之境,追求“意新语工”,诗重立意,讲句法、工于炼字。魏庆之对以苏轼、黄庭坚、苏辙等元祐诗人颇为敬佩,《诗人玉屑》大量引述了他们的观点和评论。
苏、黄都提倡一种无意为文的自然脱俗之境,并溯源于老杜。魏庆之对此深为折服,他在《草堂·夔州后诗》中引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的说法:“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黄庭坚认为杜甫夔州诗既有规矩之处,又有创新的地方,外圆内方,率意成章,自然而不格乱。又如魏庆之《草堂·大雅堂》:“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正是此意。
《雪堂·南迁以后精深华妙》中有:“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夔州诗“老”,是杜甫经历宦海沉浮、人世坎坷的升华,“严”指夔州诗是杜甫一生诗歌律体创作的精髓和总结。东坡与黄庭坚比,更近夔州诗。东坡不同于山谷的用工深刻、造语好奇尚硬,杜诗的沉郁顿挫,在其贬谪诗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有一种绚烂之至归于平淡的老境美。总的来说,这反映了当时苏、黄一派力求“渐老渐熟”与“乃造平淡”。魏庆之看到了苏轼与杜甫的承袭之处,故此条归入了东坡的专题中。
《草堂·晦庵论杜诗》中提到:“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川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摹,不可学”。朱熹认为杜甫夔州诗已炉火纯青,不再遵循传统法度,不易模仿。对于朱熹论杜甫夔州诗,历代观点不一,有人认为朱熹以《文选》为准,杜甫后期如夔州诗有不按规矩之嫌。也有人认为是褒夔州诗,须有高深诗艺者方能得之。笔者认为,从魏氏的编排上看,《草堂》的收录应是对杜诗的褒扬肯定之词,朱熹在理学家中是较为肯定诗歌“性情”的,所以不妨认为这也是对杜甫夔州诗的肯定。
2.杜律诗体
《诗人玉屑》卷二《诗评·诗体上》较为完整地收录了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严羽在文艺评论中首开“诗体”之例,分为三大类,包括了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体下》中魏氏则从声韵角度对诗体进行总结,其中谈到了不少杜甫律诗。关于诗体,卷一《诗辨第一》引严羽之说就有:“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我们可以将前三者纳入诗体之列。
严羽称杜甫诗为“少陵体”。《诗体上》:“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少陵有百韵律诗,白乐天亦有之。而本朝王黄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有律诗彻首尾对者,少陵多此体。”“有借对……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闲。’言之者有是也。”“有就对者又曰当句有对。如少陵‘小院回廓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一方面,严羽指出古诗与律诗在用韵、对仗、句式方面的差别,又根据时代风气的不同和代表性诗人的创作个性把诗歌风格分为“以时而论”和“以人而论”。上述所引,总结了杜律对仗方面的特点。
《诗体下》亦涉及杜律声韵和对仗:
(1)总论“唐名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诗,用偏格者十无二三。”即杜诗五言诗第二字仄入﹑七言诗第二字平入者多。
(2)江左体“引韵便失粘,既失粘,则若不拘声律;然其对偶特精,则谓之骨含苏李体。‘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江左体不拘声韵平仄,但是对偶特精的诗。它并非齐梁体,而是后人对齐梁诗歌的模仿,是律诗中的一种拗体。是杜甫为了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有意识的打破格律的束缚,追求一种新颖的艺术效果。这种做法在宋代被江西诗派的诗人们发扬光大,模仿创作了一批类似这样的诗歌,最终形成了一种新体——江左体。
(3)偷春体“其法颔联虽不拘对偶,疑非声律;然破题已的对矣。谓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即凡起联相对,而颔联不对偶者。
(4)五句法“此格即事遣兴可作,如题物赠送之类,则不可用。‘曲江萧条秋气高,芰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烈梢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5)六句法“此法但可放言遣兴,不可寄赠。杜子美云:‘烈士恶多门,小人自同调。名利苟可取,杀身傍权要。何当官曹清,尔辈堪一笑。’……”
(6)拗句“鲁直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 ‘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苕溪渔隐曰:此体本出于老杜,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例如其中老杜的“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甘犹自青。”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由第二句的平仄可知,第一句节奏点的平仄应该是平一仄一平,因此句第六字当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因此在第四字当用仄声的地方以平声来补救。
(7)七言变体“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时用变体,如兵之出奇,变化无穷,以惊世骇目。如老杜诗云: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此七言律诗之变体也。”
(8)第三句失粘“七言律诗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侧,亦别是一体。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起头用侧声,故第三句亦用侧声。”可见第三句节奏点的平仄和第一句一样。
(9)扇对法“律诗有扇封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句对。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苏少监诗云: ‘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扇对法是旧体诗对偶格式之一,即隔句对。如第一句和第三句对,第二句和第四句对。
江西诗派创作带有“穷而后工”的性质,讲体格、论工拙、探讨诗法、醉心于诗词格律及艺术表现手法。这一点在《诗人玉屑》中有充分表现。“拗句”通常指通过句式组织上的变更而使文气反常的句子。“拗律”则是一句之中使平仄互换,造成音调的突兀。七言拗律为杜甫独创,其平仄与律体不同,以拗折之笔写拗折之情,为后世所祖。杜甫使用拗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熟谙声律,无法调和声与义的矛盾,这种情形比较多;一是熟精声律,不喜圆熟之美,所以有意为拗。宋人学杜,主要表现在有意为拗。通过拗体的大量写作,宋人把对唐人形式的探索成果转化为了一种独特的诗体风貌。正如黄庭坚有意识的多用拗句,他使拗体成为了诗作内容情感表达的必须。“山谷体”讲究语句的峭拔和诗律的兀傲,故意调换诗中的平仄,造成声调的拗折,给人以奇崛的劲峭感觉。
3.杜律句法
宋人律诗的创作一直伴随着大量自觉的理论而发展。唐诗确立了声律与属对的规则,宋人则进一步总结了诗法与诗病,并对诗作规则的进一步细化,重视字句的琢磨,使之更具有可学性和实践性。
《诗人玉屑》卷三专讲句法,分为“句法”、“唐人句法”、“宋朝警句”三部分。“唐人句法”为魏氏首创,他从朝会、宫掖、怀古、送别、写景、咏物、造理等题材的唐诗中摘取佳句,同时又从唐人近体里选出能体现典重、清新、奇伟、绮丽、自然、豪壮、工巧、精绝、闲适等风格的联句,最后总结出引带、连珠、合璧、眼用活字、眼用响字、眼用拗字、眼用实字、眼用妆句、虚字妆句、首用虚字、轻重对等字法和句法。这些体现了魏氏对唐人律绝常见造句方式的归纳,同时也有宋人提倡的“句中有眼”的诗眼说。其中,魏氏列举了不少杜甫绝律诗,可以想见杜律在这些方面对宋人的影响。如:
(1)句法错综《句法·错综句法》:“老杜云:‘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以事不错综,则不成文章。若平直叙之,则曰:‘鹦鹉啄残红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以‘红稻’于上,以‘凤凰’于下者,错综之也。”错综句法是为了适应声律、诗意要求,对句子语序作适当调整,达到新警动人的效果。杜诗中把“红稻”、“碧梧”放在句首,是起强调之意。
(2)酝藉《句法·雄伟句》:“吴江长桥诗,世称三联。子美云:‘云头滟滟闲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杨次公云: ‘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玉碧无瑕。’郑毅夫云: ‘插天螮蝀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欧永叔谓子美此句雄伟;余谓次公、毅夫两联粗豪,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酝藉也。”
(3)深远娴雅《句法·雄健句》:“老杜云:‘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耶,定留人耶?山谷尤爱其深远闲雅,盖与上七言同。”
(4)句中当无虚字《句法·句中当无虚字》:“或间余:东坡有言,诗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毕矣。老杜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后世安知无过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飞减却春’,若咏落花,则语意皆尽。所以古人既未到,决知后人更无好语……老杜谢岩武诗云:‘雨映行宫辱赠诗。’山谷云:只此‘雨映’两字,写出一时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后晓句中当无虚字。”
(5)一句多义《句法·诚斋论一句有三意》:“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对食暂餐还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两意者。陈后山云: ‘更病可无醉,犹寒已自和。’”
(6)少陵句法《句法·少陵坡谷句法》:“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 ‘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
(7)奇句《诗法第二·诚斋又法》:“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难之。”“如杜九日诗: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不徒入句便字字对属;又第一句顷刻变化,才说悲秋,忽又自宽。以‘自’对‘君’,‘自’者,我也。‘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将一事翻腾作一联;又孟嘉以落帽为风流,少陵以不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
(8)倒句《诗法第二·诚斋又法》:“苏轼‘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
(9)夺胎换骨《夺胎换骨·总说》引惠洪《冷斋夜话》:“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夺胎换骨·诚斋论夺胎换骨》:“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杜梦李白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 ‘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此皆以故为新,夺胎换骨。”
魏庆之在《句法》中的第一条引《金针诗格》概况了诗人造句的三种方式,一是“自然之句”,二是“容易之句”,三是“苦求之句”。魏氏在书中归纳的句法不出这三种。对于杜律,宋人自然需要学诗者“苦求”,以第三种句法为主。“以故为新”与“夺胎换骨”是苏、黄二人“以学问为诗”的结果。其中,“山谷体”取法老杜,以词理细密和风格瘦硬为特征,努力制造出杜律的浑成之境。“夺胎”与“换骨”是将前人之辞,一是变其意,一是不变其意。本为宋人发明,但当溯源于杜律。
4.杜律字法
宋人提倡诗以一字见工拙,旬煅月炼,工妙乃出。宋代诸家之说亦重视选字下字的功夫,推敲琢磨,成为有宋一代之共识。“功力”说盛行,使得诗人更加关注语言表现和文字技巧的用典、炼字,形成了宋诗句法新奇和炼字见筋骨的艺术特色。如黄庭坚提倡“安排一字有神”。而宋人最长于炼字、选字、下字、用字者,首推苏轼;若唐人,则当数杜甫为第一,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字斟句酌可谓尽其极。杜氏精于用字,刻划细微,以律诗的表现最为精彩,宋人趋之若鹜。杜甫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同时“无一字无来处”,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梳理《诗人玉屑》征引的文献,关于用字,大致涉及五个方面技法,一是用字精切,不可移易;二是化俗为雅,灵丹点铁;三是安排重叠字、颠倒字、连绵字;四是用活字、响字与拗字;五是用实字,虚字和妆句。《诗人玉屑》谈到许多用字方法,由此可见宋人之字法观,以及诗歌修辞美学。主要见于卷六、七、八,还有一些散见于各卷。
(1)虚实结合《下字·诚斋论用字》引《诚斋诗话》:“诗有实字,而善用之者以实为虚。杜云: ‘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老’字盖用‘赵充国请行,上老之’。有用文语为诗句者尤工。杜云;‘侍臣双宋玉,战策两穰苴。’盖用如“六五帝,四三王。”杨万里提倡“活法”,自有“诚斋体”,用字提倡“活、新、奇、趣”。七律明快、跳动。他由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对于黄庭坚的用典之说,他还是赞同的,“文语”即指老杜的用典。
(2)巧用连绵字《下连绵字不虚发》引《雪浪斋日记》:“古人下连绵字不虚发。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青’。退之云:‘月吐窗冏冏’,皆造微入妙。”
(3)炼字《煅炼·炼字》:“作诗在于炼字。如老杜‘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是炼中间一字。”
(4)一字为工《草堂·工妙至到人不可及》引《石林诗话》:“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则其远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馀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道,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也。”“有”、“虚”二字极为工切,足见宋人的重视。
(5)重韵《压韵·重押韵》:“盖子美古律诗重用韵者亦多,况于歌乎!如园人送瓜诗曰:‘沈浮乱水玉,爱惜如芝草。’又曰: ‘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后园山脚诗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强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荡析川无梁。’一篇押二 ‘梁’字也。”
(6)巧对《属对· 陵阳谓对偶不必拘绳墨》:“尝与公论对偶,如‘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以镜名对酒名,虽为亲切,至如杜子美云:‘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直以菊花对竹叶,便萧散不为绳墨所窘。”律诗注重对偶,杜诗往往推出异于常规的相比对象,扩大了对偶的范围,更能突出对偶的效果。
(7)借对《属对·借对》条: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宋人喜欢模仿唐人诗中有难度的对仗模式,并加以改造创新。
杜律文字在用韵、对仗、虚实字结合方面都推陈出新。正如魏氏所选,杜甫善于选用虚字,如“有”、“自”;“犹”、“自”之伦,不可移易,故曰工妙至道。范晞文《对床夜语》讨论虚活字、虚死字,亦征引《滕王亭子》及《上兜率寺》二诗虚字之选用。同时,又征引杜甫其他诗联,特提犹字、忽字、且字、亦字、更字、遂字诸虚词之烹炼抉择,谓“皆用力于一字”,而妙不可言。由此看来,“虚活字极难下,虚死字尤不易”。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也称:“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黄庭坚及江西诸子宗杜学杜,亦在这方面下了许多功夫。上引《石林诗话》谈到杜甫下字之道“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可见如此用字,亦可作宋人选字用词之指南。
5.杜律诗风
宋诗讲究尚意。尚意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讲求立意,追求先有意后作诗,二是意在言外,追求诗中用意的精深与多重性。以立意为先,讲求创作者之意贯穿整篇,要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到江西诗派,强调创作者主体意识。关于“意”,魏庆之在卷六专门有“命意”一题,收集了诸多宋人关于“意”的理解,而杜诗立意之高,为宋人效仿。陈师道对杜诗的总体评价,也可谓之律诗风格至概括。其书中《品藻古今人物·王苏黄杜》引《后山集》:“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可谓变化无穷。
(1)巧命意《命意·句中命意》引《诗眼》说杜诗:“句中命意,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顿挫高雅。”
(2)意在言外《命意·思而得之》引司马光语:“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皆类此,不可遍举。”意在言外是指将作者的思想通过暗示的方法表现出来,常见之法是用典。苏、黄二人是首推者,后延续至江西诗派及严羽。
(3)句外有意《命意·诚斋论句外之意》:“诗有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诗。杜云:‘遣人向市赊香秔,唤妇出房亲自馔。’上言其力贫,故曰‘赊’;下言其无使令,故曰‘亲’……”
(3)典雅重大《律诗·诚斋评七言律》:“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这可以与卷二《诗评·臞翁诗评》“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相互参看。
(4)意味深长《律诗·诚斋非金针》:“诚斋以为不然。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阳诗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夏日李尚书期不赴云:‘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野雪兴难乘。’”
综上所述,杜甫的律诗在宋代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各个方面都为宋人学习剖析,这也是宋诗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滋养之一。魏庆之《诗人玉屑》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总结归纳,涉及杜诗特别是杜律在宋代主要诗歌流派中的影响。其中既有早期江西诗派对杜律的近乎刻板的模仿,又记载了南宋时期的调整纠正,如杨万里、严羽、江湖诗人对杜诗新的看法。魏氏这种“点悟式”的诗话评论方式,虽缺少系统,但通过钩沉可以慢慢体悟。
注释:
①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诗人玉屑解题》,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④马茂元《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⑤⑭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十四。
⑥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十七。
⑦⑨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二。
⑧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三。
⑩⑬⑯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卷八。
⑪见张高评《〈诗人玉屑〉“选字下字”说述评——以意新语工为讨论核心(续)》,《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
⑫⑳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⑮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七。
⑰范晞文撰《对床夜语》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⑱李东阳《麓堂诗话》,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第一册,齐鲁书社2005年版。
⑲㉑魏庆之编,王仲闻校勘《诗人玉屑》卷十二,中华书局2007年版。